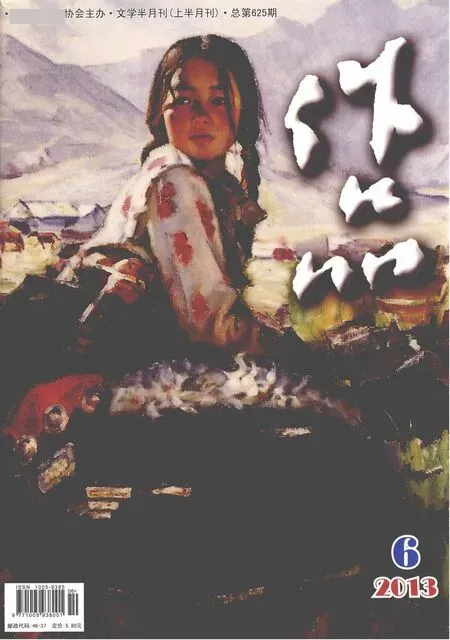猎鹿
我曾有过一段多灾多难的牙齿成长史,小时候,我就时常为咬不开一块肉发愁。我不知道我的家族为何如此热衷于肉类,我们从幼年开始就接受了吃肉类食物的训练,母亲教我们如何用侧边的牙齿使力,如何让上下颚配合无间,利用牙齿凹槽的力量把肉自然碎开。那时候我的牙齿刚刚发育,就被要求吃下一小块卤水猪里脊肉。
我把它留在了碗底,并且告诉了母亲我的努力,但这种坦陈在事实面前显得那么无济于事,到了第二次吃饭的时候,或许有一片故意切薄的红烧肉,一块牛肋排,它们最终都在我深浅牙印的作用下都变得千疮百孔。
我用一颗摇摇欲坠的乳牙表达了抗议。我站在母亲的面前张开嘴巴,她用手指摇了摇我虎牙旁边的牙齿说,要换牙了,然后试图用手指检查牙齿脱落的进度,立马惹起了我的大喊大叫。第二天,她带我去了牙医诊所,牙医用一把口钳轻而易举地摘下我的牙齿,让我含着一颗棉花就回家了。
为了庆祝我换掉了不长志气的幼齿,爸爸买了一盘长相奇怪的酱骨架,整个弥漫在基督徒分餐方式的餐桌上,更多的是异样肉味引发的食欲,当然我的嘴巴还多了带血纱棉的气味。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的左脸颊肿了,牙床被鼓起的囊包挤压得空隙全无,厕所的镜子前仿佛站了一个患了沙眼的陌生人。母亲再次带我去了牙医那里,得到的说法是牙床感染。接下去的两个星期,我处在了难得的斋戒隔离状态,每天只能吃流质的米粥。囊肿的牙龈挂着牙医用各式的药包,换药的时候,我感觉口腔就升腾起了一股中药味的蘑菇云,各式各样的蘑菇云,随着囊肿的消退变换着形态。母亲为了安慰被病痛折磨的我,带着某种歉意的暗示,她决定给我买一个小玩意。
一如既往地,她从周末的超市买来打折的肉类和日用品,一个硕大的棕色纸袋故意放在沙发的醒目之处。我拉开纸袋,一只半人高的抱熊噗地一声掉地,是一个憋成紫金色的刺松,一只粗劣的泰迪熊纺织品。我往上提起它尖尖的耳朵,这只熊正式和我打了个照面,它的眼睛是赤色新月形,肉滚滚的脸像是对我肿胀脸颊的嘲笑,嘴巴则是一条棕紫色的闭合的线。我一言不发地把它抱进房间,一边用力吸着薄荷药包来不及缓解的口腔酸麻。
母亲一厢情愿地将我的低落归咎于无法吃肉这件事上,她没有看出我对于吃肉已经有了生理性的反感,她愧疚地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我伤口愈合的长势,我抱着熊在院子里不知所措地走来走去。吃饭时间,我被安排坐在了餐桌的尾端喝稀粥,听家人咀嚼肉类的声音,特别是我那天赋异禀的妹妹,当她用小虎牙撕开一块骨头,得意发出的咯咯声简直让我抓狂,而我口腔里的囊肿也听到了这种召唤,在抗厌氧菌的镇痛作用下缩成一枚悲伤的果核。
我的口腔感染很快得到了控制,那些悬挂着的药包一一拆除,但是我的牙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有种重量感的错觉。我拒绝再吃肉,我撒谎,那些谎言在复诊中被推翻。医生给出的判断是:排除器质性损害的后遗症,建议去看看神经科,可能是得了神经性厌食症。
但是母亲并不信这一套,她买了印有粉色兔子的餐具和花朵图案的切肉器,乘机在我们的饭里放进香草味的肉酱,我却离开饭桌,表情阴郁得像手里那只嘴角下垂的熊。它紧抿着嘴,整个脸型都往下拉耸,我不知道当初妈妈是不是在我们的脸上看到了同质的表情才买下了它,现在在她看来,熊的这般神情就是合谋的证据。于是她想到了惩戒我的方式,不满也终于在一顿晚饭的进行中爆发了出来。
我抱着熊,继续坐在饭桌前一言不发,妈妈趁其不备抢过它,当着我们的面,拿起剪刀插进它柔软无防的皮肉,手腕开始蛮横地往右扯。棉絮被金属杀死,一下就被它陶罐般的身体闷声地回收了,凶器如标杆插在伤害的终点,整个阴郁的过程,在剪刀光芒飞的映衬下亮如白昼。熊不吭一声再次落地,第一次亮出自己的牙齿。我们屏气凝神,恐怖的气氛让我们忘记为这场杀害做哀悼。它正仰面慢慢死去,乖巧自如,伤口触目惊心地横贯脸上,我们都羞愧地盯着地板,它正以比岁月快十余倍的速度变得扁平敛息,变成透明色的灰尘,变成顺其自然和符合规矩的存在与消失之物。那一场家庭用餐以母亲沉痛的教训声,打翻的碗筷被重新收拾好的碰撞,和进餐间的互相告慰和哭泣结束。
时间也渐拉渐远,漂浮在每一个称之为淡忘的意识皮层之上,我记得我们是躲开了一个瘟疫病人,拒绝正视和修补它,后来让它被某个大胆的家庭成员一把提起,迅速装进一个黑色塑料袋,带到冷饭残羹集中的垃圾站。
我的第一只熊就这样宣告死亡,还有另一个假使是,我尝试过致歉和补救,我在它骇人的嘴巴上贴满了玫瑰图案密集的止血胶,或许是这种笨拙的补救显得那么错漏百出,最终我们都选择了彼此厌弃,避而不见,它自行在我的时间谱系里消失了,往后我的日子都不再需要一只熊。
我的牙齿也渐渐长得健康完好,坚固得足以咬开一个虚张声势的动物骨架,我也终于融入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各种唧唧咕咕的吃肉聚会中谈论说笑。家庭里的一些牙齿茁壮生长,一些正在衰落动摇,肉类依旧是我家食用的主角,作为能量补给的食谱也发生了某些变化。
妈妈决定在庭院里种各种有益咀嚼的食用植株,它们不约而同发出了搅得人心神不宁的气味,清晨出门的时候得捂住鼻子,衣服也会时不时地沾上那种气味。我不知道这些植物居然能与泥土发生这么不得体的效应,远远看过来,就像有一片飘忽不散的惨淡绿雾。
我家庭院成了周围最不让人待见的地方,各方植物长势迅猛得让惯常喜欢咬啮残食和根茎的老鼠都偃旗息鼓。某天早上,院子刚刚松土,旁边的花铲上沾了一些奇怪的东西,空气中有一股燥热短促的臭味。
“是牛粪,”妈妈说,“牛是怎么跑进来的?”
不知道牛是怎么跑进来的,院子南边的苦艾被踩倒了,茎叶被咬断,几个花苞泡在落叶的露水中。我们也怀疑是狗干的,但是一个研究生物学的邻居告诉我们,不可能是狗或者老鼠,从叶子损伤的切口来看,更像是野生动物所为。
我们将信将疑地把院子的围墙栅栏做高了半尺,新做的栏杆毫发无损,那些叶子却继续遇袭,我们又开始对路过的狗和牛群提高了警惕。小偷时不时地留下草籽,布条垃圾,一朵花,黑色的动物毛发,大家都在思忖需不需要拿去做举报。妈妈不厌其烦地把收集起来的垃圾证据堆在院落,向这位不速之客示威。当那些垃圾越堆越高,一个布条就出其不意地从胀破的塑料袋掉了出来,暴露在阳光下,看起来极像一根瘦弱的紫金色手臂。
记忆就是个垃圾场,那些不忍丢弃又无需再拾的美好和丑陋,堆积着,惦念着,最后成灾也乏味了。我坚信那条紫金色的布条眼皮被阳光照射产生的幻觉:决意丢掉的东西,在某年某月也会以正常消解的速度消失殆尽。
如果不是那天清晨出现了牛奶白的雾气,我就不会看到这么一张长着粗野毛茸的脸:黑如豆子的眼睛在墙外闪了几下,就熟练地攀着外面的一个独脚花岗岩石凳,笨拙而坚决地探入了院子。我压住了嗓子眼里的叫声,看那只棕色怪物以一颗秋后松果的姿态落地,随即缩小,隐身进入密不透风的叶丛。
我无法判断那是一头阿拉斯加棕熊还是东北棕熊,它离开时留下了少量粪便,蹭倒的一块木栅栏和一朵玫瑰,我走近它离开了的案发现场,发现草地上的一块灰色骨头正发出引起我强烈呕吐的气味。于是,为此自嗅觉诱发出的恶心晕眩而至:谁在那时牙齿不全,以素食为生,慢慢却接受了食肉世界饕餮腥臭的怪味和规则,借机完成了一次成长的杀戮必修课。
我回忆不起跟这股味道有过多少次的接触。我只记得小时候离我家不远的城郊,有一个很出名的农牧场,一个东北女人盘下了这块欠债抵押出去的自留地,在那里圈养起了一群野生鹿。那些鹿在成年之后,就会被运输至各类合法非法的肉类市场,据说那些载着鹿的卡车穿越到城镇另一端的时候,喜食鹿肉的人见到都会止不住垂涎三尺,他们形容那些被捆绑着装笼的毛物发出的味道,仿佛就发自于数十只鹿的集体发情。
我讨厌鹿,念幼儿园的时候,就因为频频迭不好那些五彩的手工鹿而被老师讪笑。我也憎恨所有鹿形的图案,妹妹们的衣服都有剪纸样的鹿形图案,唯有我的是房子和冷杉。在我无来由的偏执理解中,鹿就是不知廉耻的女人的自喻,我甚至怀疑爸爸买来的那盘奇怪的酱骨架,就是从那里交易得来的。野味市场的管制严打让鹿场的名声已经大不如前,在这种经营鼎盛的时期,曾经有远方食客陆续寻来,在鹿场住宿,方便在那里当场屠食生鹿肉。我听过这么一位疯狂食客的故事:他神色恍惚地在鹿群中游走了三天两夜,跟未足月的幼鹿抢喝雌鹿的奶,在第二天夕阳将尽时一口气屠杀了十七头,又在鹿场住了100天,独自吃光了那十七头猎物。
这个故事真实与否无法考证,只能说明小镇一度对于这种肉类食物的狂热,我也借此辨认并猜测出了那只怪物的藏身之处,我置信此刻必定也是云雾缭绕,笨重如拖着一只跛脚的庞然大物,在一个冷漠的废弃世界边缘自如地出没。
我去了鹿场,那股味道差点把我逼退,它们忧郁成灾般集结在鹿场灰紫色的上空,呈现某种菌类作古腐朽的形态。鹿场的后方是放养鹿群的一个平坡树林,鹿只变得像人的幻觉,混迹于树木之间,了无生机。那天的雾气湿重,它如混沌未开的肉球径直在树丛间沉沉睡去,五官模糊,呼声像远方而至的闷雷。这只凶猛的现实野兽是随地安巢,尖锐的耳目暂时沉眠于红果与松针铺成的地毯之上,这个艳丽如水彩插画的画面,无意间便软化了捕猎本性与童话故事之间的真实界限。
我吓得不敢出声,却伸手抚摸到了它的毛发和砂纸般肚皮,一种古怪的奇异感贯穿了全身,兴奋的分子迅速触发,碰撞,引燃,落入记忆与现实的分身术,在我如风的疾跑和喘息中渐成辐散的魔幻宇宙。以至于在后来见到它杀戮一幕之时,怜悯会自觉地退居在某种刺激的暴力美学的背后,一头鹿从完整到分离,统统变成冷酷的视觉分镜。
这只棕色的毛物拧住另一头毛物,对方发出恐惧撕裂的鸣叫声,挣扎地拉扯了几步之后重重倒下,惊恐的眼神渐渐失去神采。花色的脂肪皮肉之后,脉搏和血管被胡乱扒开。猎物剧烈悲惨地渗着血水颤抖,它撕纸条一样拉开右肱骨,再若有所思地扔掉,最后不小心把整个头颅拧了下来。它抱着一颗鹿头,鼓着嘴坐在草地上,像个不知所措的懵懂孩童。
那头鹿的尸体很快就被人发现了,它对鹿的残忍,恰好满足了我对这种厌恶至极的生物的想象。鹿场在陆续失去了几头鹿后提高了警觉,而熊是隐匿在狭小并且能够潜入城郊的幽灵捕手,几乎无人知晓它的存在。我去了动物园,询问他们有没有丢失过一头熊,动物饲养员说他们从来没有养过熊,我还去看了幼儿园围墙上的彩绘油画,看掉色斑马的棕色同桌是不是趁机逃了出去。
我把所有无法解释的事件归入自我理解的有限集合中,熊的出现和鹿的失踪,互为因果的表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荒诞感。鹿死亡的影像和幼儿被拐的新闻在电视上不断回放:一个小孩子的头像,草地上一头鹿的临终现场。那些被封存成禁忌的欲望也被午夜静谧的幽蓝赫兹重新点燃,那些对鹿肉念念不忘的肥胖胃口长出了无限的欲念,他们像看色情片一样对鹿的影像穷追不舍。而失传已久的盗猎行为,也卷入了鹿场的后续事件之中,盗鹿人,一度被用作解释鹿群被神秘杀死或者失踪事由的代名词:被默许的口腹之火,成队的鹿如海市蜃楼般横行于市又很快消失,倒卖野味的市场死灰复燃,食物链般组成了小镇一个个私密的幻象。
人们不知道实际上这个幻象中有两个盗猎者:一个把鹿撕成玩具碎片,另一个将整头鹿掠走,或者整齐地砍下鹿茸和躯干,或者有可能中途加入了拐卖儿童的队伍。而那些古怪的肉类似乎也再次出现在了餐桌上,嶙峋而张扬的骨架,暗示这是一个糜烂的鹿头。
我做了一个古怪的梦,熊在梦里再次来到院子里,它拍拍肚皮后腿直立,带着回访的好奇和冷峻的眼神和我对视,它指了指我手中的熊,要我跟它做交换。
“交换之后,我能得到什么呢?”
它答应教给我捕猎的方法,猎到一只鹿所需的技巧和原则。那天夜里我因牙齿旧患发作被痛醒,它也走向了晨色凝重的树林,那边有滚烫的鹿膻和磨牙霍霍的白光。
如果不是捕杀一幕的出现,人们不会相信一片小树林竟然能藏下这么一头熊。农场主把鹿圈在农舍里,在树林到鹿场的路段布下了电网和各种古老的陷阱,熊是在跨过一块岩石的时候被击毙,电线绊住了它的脚,同时给了它致命的一击。
闻讯而至的人们跑到树林围观,他们看着触电之后倒地不起的棕色熊,像观瞻一只店庆促销的陈年大型玩偶。在兴致盎然地观察了它的庞大与局促之后,他们任由它暴露在空旷之下,等待救援队来收拾现场。树林旁边有一个白色的汽油桶,有人建议把熊装进汽油桶里烧掉,以此减低城市救援队的工作难度。大风吹来,它的身体开始僵硬如石,皮毛萎缩,在阳光下变成熟悉的紫金色。
这次它所杀的一只雄鹿和一只雌鹿,它们的尸体在湖边相拥,被当地的媒体和传言评为奇特感人爱情故事一则。但是没有人知道,我的熊独自在树林的湖边哭了一遍又一遍,不知命数将尽。
最终它没有被烧掉,骨架被制作成了生物展品,一度成为了小镇猎奇观光的卖点,至今那些不愿意忘记它的来客,还能在红果树林标本展览室里找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