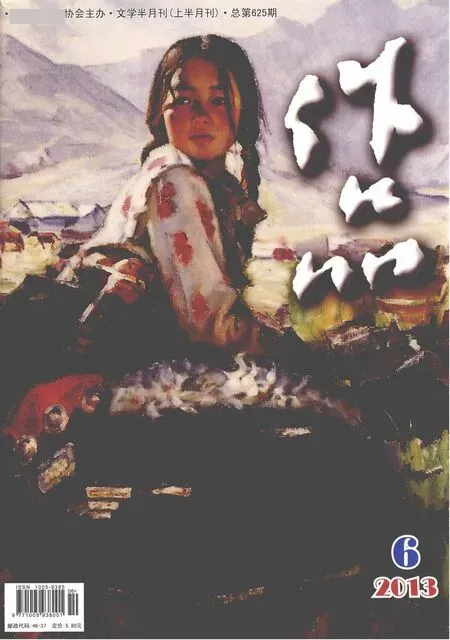医道
那个男孩又来了,陈当看见他,并注意到他。一连几天,他在医寓外走来走去,脚步放得极缓,往拿药的大方窗望。今天,陈当朝他点点头,他便往窗边走来。陈当注意到,当他点头时,男孩身体一缩,稍稍弯下腰,一只手放在肚子上,双眉往下一耸,走过来时有了呻吟声。
医生,我肚子痛。他扒着方窗窗沿,有气无力地。
陈当招呼他进门,让他坐在方凳上,伸手把脉。这种郑重其事似乎令他不安,他显得又僵硬又忸怩。陈当对他有点印象,是隔寨一个男孩,平日在路上偶尔碰见他和一群孩子打闹或背着书包边走边踢石子。
什么时候开始痛的?陈当按他的脉,边问。
好几天了。他说。
几天了?陈当想起他这几天在窗外来来去去,似乎没有疼痛的样子,也可能是自己没注意。陈当半眯起眼,细心听脉。
陈当又问他最近吃过什么,大小便情况,疼痛的部位,他含含糊糊应着,末了咬紧牙,尽力把眉头揪成一团,说,痛死了。陈当让他掀起上衣,按揉他的肚腹。他缩着身体躲闪,别按了,医生,真痛。
你叫什么?陈当问。
他似乎愣了一下,说,圆木。
圆木,你阿爸阿妈呢?
圆木的眼睛瞬间失了光彩,脖子变得弯软。阿爸阿妈进城打工,我和阿公阿嫲住。
又一个留守的。陈当想,他换了话题,笑着,我开点药,你按时吃,多喝点水,明天肚子就好了。
不要。圆木猛地抬起头,声音之干脆让陈当吃惊,也让他自己吃惊。
陈当看住他,疑惑了一会,释然笑了,我开的药不苦,一口水就吞进肚了。
圆木避开陈当的目光,说,痛死了。他弯下腰,让痛疼显得淋漓尽致,医生,我痛得夜里睡不着,好多夜没睡了,饭也吃不下。
吃了药会没事的。陈当安慰他。
没用,没用的。圆木摇头,摇得又急切又坚定,阿公阿妈全没办法的。
我有办法。陈当说,我是医生。
是,医生有办法的。圆木抬脸,睁眼,盯紧陈当,你给我阿爸阿妈打电话。
打电话?陈当莫名其妙。
你告诉我阿爸阿妈,我得了严重的病,就要死了,让他们回来看我一次。再过几天我生日,那时死掉,我才十岁,他们还不回来么……他突然住了嘴,咬着唇,似乎怪它说错了什么。
陈当看着他,不声不响,医寓里极静。
医生,求你了。阿公阿嫲给他们打电话没用的,我给他们打电话也没用的,路那么远,车费那么贵,老板那么凶,请假难,还要扣全勤。他们一直让我听话,让我再等些时候,等他们挣了钱就回来,过上好日子,天天在一起。我四岁的时候,他们就这么说,我很听话的,等到十岁,他们还是这样说,我要死掉了,看他们还回不回来。医生,寨里人说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医术很高,你打电话给阿爸阿妈,你说的话,他们一定信,会回来的,这两天回来,正好赶上几天后我……
圆木又突然住了嘴。
陈当相信,这番话,已经在这个孩子脑里翻转过无数次,但有些话又是他事先未预料过的。
陈当站起来,转过身,背对圆木,面向满柜的药,默默半天。
你是医生,你的话我阿爸阿妈会信的。陈当听见圆木带哭腔的声音。
正因为是医生,我不能随便说话。陈当说,仍背对圆木,他听见圆木的抽泣声。
我真的要死了,肚子一直痛,一直痛。圆木说。
圆木,我给你开药,吃了我的药,你身子什么事也没有。陈当转过脸,声音虚弱无力。
圆木固执地顺自己思路说下去,过几天我死掉,他们会不会来看我?阿爸阿妈说,十年前,他们两个看着我出生,他们有了儿子,世上有了圆木。现在我要死了,我想让他们看着我死,以后世上没有圆木了……孩子突然号啕大哭。
陈当变得手足无措,他绕着痛哭的孩子转圈,后来,把一只手放在那只抽泣耸动的肩膀上,轻轻两拍,说,我打电话。
哭声戛然而止,圆木扬起脖子。陈当看到一张又欣喜又湿润的脸。
只回来看一看,他们还要回城干活的。陈当说。
圆木抬袖抹着脸,用力地点头。
按圆木的指点,等午饭时间拨打电话,这个时段他阿爸阿妈方便接听电话。陈当拨了电话,听那边一个人不耐烦地说等等。他握着话筒等,圆木趴在面前,眼睛半天没眨动,像被等待凝固了。陈当感觉握在手里的话筒开始发热时,听到一个急急喘气的声音,他一下子想象出一个浑身泥水,从工地匆匆奔来的形象。那边连喂了几声,陈当一时忘了应答。圆木抢过电话,喊了声阿爸,说医生要跟你说话。把话筒塞给陈当,拼命摇晃他的手臂。
我是陈当。陈当长呼口气。
是陈医生哪。那边的口气一下子恭敬了,陈当甚至想象得出电话线另一头那张笑脸,这恭敬的口气和这张笑脸让他一下子冒出满头冷汗。
圆木的脸红得发胀,朝他抿嘴眨眼地示意。
是这样的,圆木病了。陈当觉得这句话堵住了自己的呼吸。
病了?什么病,严重么?陈医生,请你给他看看。那边的急切被电话线一波一波地送过来。
你们找个时间回来看看他。陈当咬牙说出这句话。
陈医生,圆木到底得了什么病?陈当听见一个男人抑制在喉头的哭意,感觉有锤子锤打自己的胸口。他几乎要放弃了。
圆木抓着他的手臂,指甲抠进皮肉。
你先别急。陈当一手解着脖子边的衬衣钮扣,让呼吸顺畅些,说,圆木会没事的,你们回来看看就知道。他觉得自己的话糟糕透了。
陈医生,陈医生……陈当感觉那边失了方寸。
听我说。陈当稍稍扬高声调,那边果然猛地住了声。
圆木没事……
那怎么要我们回去?那边又打断陈当的话。
好吧,我保证,圆木不会有事,只是有些治疗方法需要当面跟你们商量,圆木的阿公阿嫲是老人家,我说不清楚。
陈医生,能不能交个底,圆木得的什么病?
我已经保证了,他不会有事。这两天就回来吧。陈当说。
我和圆木说两句话吧。
圆木接过话筒,呀呀地呻吟,阿爸,我受不住了,你和阿妈快回家,医生说再不回来我就……
陈当伸手抢话筒,胳膊肘把电话摁断了。圆木对着电话的忙音愣愣地说,阿爸阿妈这次会回的吧?陈当虚脱般摊在椅子上,双手抱着头,半天不出声。
半天,圆木碰了碰他,医生,你帮了我大忙,我要死了,要是没有你,阿爸阿妈就来不及看我了。阿爸阿妈说,我出生前,世上是没我的,没我是怎么样的?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阿嫲说,她死掉后,世上就没有她,没有她是怎么样,我也想不明白。医生,我死掉后,世上就没我了,那时是怎样的,阿爸阿妈得看着,我出生和死掉都想他们看着。
陈当抚着圆木的额,你老胡想什么,别老想这些东西。
我害怕。圆木说。
陈当握住他的手,他觉得自己的手很无力,他嘴唇动了动,无声出来,他觉得所有的声音都无力。
半天,圆木问,医生不喜欢打这个电话吧?
陈当笑笑,说,打电话是我的事,跟你无关。你阿爸阿妈要回家看你了。
圆木的脸瞬间绚烂。
打工夫妻第三天早上就到家。他们满脸的忧戚吓住了寨里人,也吓住家里一对老人。老人问,怎么了,不吱一声就回来,城里怎么了?
怎么了?夫妻问,这样突然让回来,圆木怎么了?
圆木从屋里飞跃而出,伴随着高喊和欢呼,他一下子望见阿爸阿妈满脸的凄惶,这凄惶令他又一阵狂喜,他扑在阿妈面前,弯缩下腰,抱住肚子,呻吟,痛,痛死了,跳了一下,又痛了。
阿妈捧住他的脸,圆木,怎么痛,多久了?走,现在去找陈医生。
阿公阿嫲莫名其妙。
圆木脸变色,对阿妈低声附耳,阿公阿嫲不知道的,陈医生说别吓坏老人。
当阿妈的在这句话里软了双腿。
快,先找陈医生。阿爸丢下行李,要扑出门去。
阿爸的大腿被圆木抱住,死死抱住,别,先别。陈医生开了药,刚刚吃下去,现在好多了,不痛,一点也不痛。陈医生说,先吃三天药后才知道怎样,今天是第三天,明天看才准。
为了证明不痛了,圆木在厅里转圈,唱歌,他红润的脸和眉梢的喜色令人放心。他提到了生日,提到看见电视里的孩子庆祝生日,每年都记得那一天出生,说他也想过个生日,也要人记得他出生了,说这不定就是他最后一次过生日。圆木沉浸在自己的伤感里,伤感让一切在他那里成了真实的。
他阿妈扶着他阿爸的肩,极力让自己不摔倒在地。
圆木的生日过得很像样。阿妈和阿嫲用鸡蛋和面粉蒸了蛋糕,点了红蜡烛,他唱了从电视学来的生日歌,甚至让平日严肃的阿爸阿妈用手拍了节奏,还得到一个很漂亮的橡皮球。这个球圆木七岁就想要的,阿爸阿妈说城里的玩具城和超市都标着杀人的价,认为没必要买,他们用便宜的胶球代替了。这次,他们买了。圆木想,一定是因为自己要死了。死突然以美好的面目出现。
一整天,圆木没有病痛的痕迹,阿爸阿妈一提起,他不是含糊跳过话题,就是说陈医生的药有效了,加上阿爸阿妈回来看他,他的病治好了。他上了厕所,说把病拉出来了,是黑色的,硬硬的,比大便还臭。阿公阿嫲则一直处于疑惑中,完全无法理清前因后果。
第二天,也就是圆木说的吃药三天后,可以确定结果的日子,打工夫妻带着圆木冲陈当的医寓急走。圆木无法再抱住阿爸的腿,他抱着橡皮球,垂头跟在阿爸阿妈身后,重复说,我好了,病治好了。像为他的康复而忧伤惭愧。有几次,他停下脚步,对阿妈说他不去陈医生的医寓。
阿妈半弯下腰,手放在他肩膀上,说,病一定要看好,陈医生开的药吃得一时好,说不定只是止痛药,要不也不会让阿爸阿妈回。圆木不是小孩了。阿妈的手和语气前所未有的温软。不知为什么,阿妈最后一句话和她的温软让圆木惶惶不安。
打工夫妻来不及进门,半个身子伸进医寓的方窗,朝陈当伸长脖子,圆木怎么了?陈医生,他吃过三天药,说不痛了。
陈当让他们进屋,让他们坐下,招呼缩在阿爸阿妈的身后的圆木,让他伸手。陈当用心地把脉,细看了圆木伸出的舌头,按压圆木的肚腹,边按边点头微笑,夫妻的心在他的点头微笑里一层层沉静下去。抬脸对着夫妻时,陈当满脸愧色。他让圆木先出门玩球。
陈医生……
陈当扬扬手,让夫妻坐得更安心些。他说,圆木身体很好。
可你让……
陈当朝夫妻弯下腰,吓得夫妻双双立起。陈当说,真对不住,是我的错。圆木只是炸油条吃多了,上火,宿便不通,这两天吃过药已经完全好了。前几天是我误诊了,我行医不久,经验不足,看错症状,把小问题看成大病。
陈当让自己正视夫妻脸上的风云变色,他一只手抓住桌角,准备迎接任何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情形。夫妻对视的一瞬,陈当看见如释重负和狂喜在他们脸上汹涌,但愤怒很快以更汹涌的姿态淹没前者,他们把脸转向陈当。
你怎么当医生的!以丈夫的质问提头,妻子的责骂开始滔滔。他们谈到圆木对陈当说过的那些,遥远的路,金贵的车费,困难的请假,最主要是折磨。提到折磨时,陈当看到这对夫妇的眼睛变成红色,语调发着铁烧红的吱吱声,脸面上蒸腾着红色的烟,陈当半仰起脸,感觉炙热的红色灼烧着他。
陈当记得自己不住地点头道歉,顺他们的话头承认自己医术不精,还似乎提到赔偿,但自己的声音很快消失在那对夫妇愤怒的责骂和抱怨声里。
后来,陈当找到个空隙,极快地插进一句话,回来也好,看看圆木。说完,陈当往窗外看去。夫妇的目光随出去,圆木在拍球,球沾染了日光,显得发亮,在圆木的手下弹跳。尽管是侧脸,孩子的喜悦仍然很明显,和那个橡皮球一样,有着动人的曲线。
夫妇突然住了话,盯着圆木一拍一拍的手。昨天,圆木欣喜地抱住给他的球,突然问,阿爸阿妈,球不会死吧?
当时,他们哧地笑了,球怎么会死,你别糟蹋东西,不弄坏弄破,这球就一直在。
好。圆木一本正经地点着头,这就好,这是我的球,我在上面写个名字,要是我死了,看见球上的名字,就记得我,知道有圆木这个人。
阿嫲扑过来捂他的嘴,唾了两口,连嚷两声,小孩嘴无遮挡,乱说,不当真。前段时间,随我到山上摘青橄榄,见了坟,指着问这问那,回来就只管乱想乱说。
阿爸阿妈没回家,我不知道你们在不在,不知道我会不会在。当时,圆木在灯下的脸发黄,眼光不知落在什么地方,令人没着没落,觉得他确实病着,病得很重。
阿兄阿嫂,误诊是我的错,需要我怎么做?陈当在他们的安静里说。
夫妇看看陈当,垂下目光,半天,说,以后圆木有个头痛发烧的,烦陈医生多看顾。说完,他们走出门,一人一边按着圆木的肩。
圆木再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他趴在方窗边,喊,陈医生,陈医生。眉眼和语气都带着羞怯。
肚子还痛?陈当笑着问。
圆木抓着后脑摇摇头,说,我阿爸阿妈走了。
进来,给你点东西。陈当招手,端半杯水给他。圆木犹豫着不接,陈当说,放心,这是萄葡糖水,甜的,不是药。
他们坐在方窗边,望出窗外,望见老去的寨子和老去的路,夕阳又薄又亮,老去的寨子和老去的路变得轻盈温暖。
陈医生,我骗了你。圆木一口气喝干萄葡糖水,下定决心似地说。他看看陈当的侧脸,没有丝毫表情,这让他疑惑,怀疑医生没听见自己的话。
我骗了你。圆木加重语气,他看见陈当点点头。
陈医生,我肚子不痛,我就是想见阿爸阿妈,让他们给我过生日。我害怕,不是梦见阿爸阿妈不见了,就是梦见我自己不见了。我让阿公阿嫲打电话,自己打电话,他们都不回的。所以,我在你身上想办法。
陈当淡淡地笑。
陈医生,你不骂我?我害你让我阿爸阿妈骂了,还说你医术不好,别人都说你医术好的,这样会坏你名声的。
陈当扳住圆木的肩,说,这与你无关,是我自己的事。
怎么是你的事,我是装病的。对了,陈医生,你真看不出来?
陈当还是笑。
你早知道了!圆木惊叫着站起来,陈医生,你为什么还打那个电话?
我说了,这不关你的事,是我的事。
是我的事。几年前,也是这声音,让陈当立在门边,迈不出第二只脚。半天后,他把迈出门的一只脚也抽回来。
那时候,用女朋友的话说,陈当的脚只要迈出去,就迈向远大的前程,奔往他的志向,还有一种叫幸福的东西由她拉扯着,等在前方。她从遥远的城市挂来电话,让自己哭诉和对未来的描绘源源不断输送到电话这头,在陈当的胸口翻搅不住。最后,女朋友总是以这样的问题结束谈话,留在那里,你能得到什么?
得到什么?陈当不知道,他只知道,不留在这里,以后再也没法轻松地迈步。
寨里人看来,陈当属于天之骄子。两个阿兄一个阿姐供他把书一路念上去,念进名牌的医科大学。陈当是对得起这份扶持的,一直有争气的成绩。大学毕业后,进了城市医院实习,短短几个月,就被医院看中,取得留院的机会。据陈当的阿妈透露,他和他城里女友的事也安排妥了。那女孩在城里另一家医院,他们看过陈当阿妈偷偷带出来的照片,不比电视扭扭捏捏的女主角差。金童玉女,男才女貌,他们把戏文里学到的好词毫不吝啬地用在这对年轻人身上。从此,陈当变得遥远了,他的身上被无数光圈笼罩,烂灿使他失去了真实的轮廓。寨里人想象里的陈当总不像人那要走路,他不知不觉地往上升,脚底浮着云,在很高很远的地方飘着。
那年夏天,陈当又回了次家,办一些必要的手续,两个月后他将正式进入医院上班,并找适当的机会把女朋友带到阿爸阿妈面前,那时将只差个仪式了。从此,寨里人可能对他的想象也要变得遥远了。
老赤脚医生在陈当回来的第二天辞世。他无病无灾,只是老了,太老了,四乡八寨的人从小到大的头疼脑热都是由他那只手挥走的。四乡八寨的人去送老赤脚医生,他们在老医生的葬礼上悲伤又忧虑,从今往后,四乡八寨的头疼脑热将无处可医。出现在老医生葬礼上的多是留守的老弱妇幼,守着半空的村寨,像被吹离枝头的孤叶。此时,面对老医生长眠的棺木,被抛弃的感觉浓重成石,压堵住呼吸,升腾成雾,弄得日子面目模糊。
老医生的葬礼陷入一片沉默,他身后那段长长的空虚令人打寒颤。老医生有两女,都远嫁,老医生无男丁。很明显,赤脚医生后继无人。镇上的医生显得遥远又冰冷。
沉默里,不知哪张嘴提到将要回城的陈当,提到他有资格进入城市大医院的医术。
提过之后,沉默愈深。提这话做什么,城里的医院等着他,他将走进辉煌,他的医术无须提起,都心知肚明,能被大医院留住,资格很清楚。问题是,提了又怎样。没有一张嘴接这话,这是痴想,四乡八寨的人已经习惯把痴想压得很实很深。
但痴想在,那片沉默里,痴想如烟似雾,缭绕无声,触摸不着又挥之不去。这片轻薄的痴想终于还是来到陈当面前。没有哪张嘴承认说过,但这痴想成了风,拂过每个人的耳边,给每颗心留下痴想的感觉。
那几天,陈当在收拾东西。按原计划,陈当收拾过行李,阿爸阿妈在家里摆两张饭席,请亲戚好友聚一聚。接着,陈当进城去医院报到,接着会先住在医院还算不错的宿舍,会和女朋友成家,会买房,会……所有的“会”都是又清楚又明亮的。但那几天,陈当的思维拼命避开这些“会”,他收拾东西的手变得无力又颓丧。阿爸阿妈不和他对视,饭桌上,一家人垂着头,尽量小心地咀嚼,不弄出声响,像寄人篱下的落魄者。那些“会”曾让阿爸阿妈把笑声带到梦里,但他们现在也尽量避开它们。多年后,阿妈和陈当谈起这事,说,当然想让你进城,可能开那个口么?开了口,别人倒不能说什么,怕的是自己以后看不起自己。应该开口让你留下的,可我嘴唇咬破了也没有开。说完这些话,阿妈脸上的释然和轻松令陈当印象深刻。
夜间,陈当出寨,在田间小路绕行,乡下的月夜清澈得有些不真实,陈当感觉心里有些东西活跃起来,变得清晰锐利,弄得他焦躁不安,匆匆逃回屋里,好像月光有透视作用,照得见他心灵任何一个角落。后来,陈当喜欢在月下田间散步,当他仰起脸,承住清澈至极的月光时,他已经安静,任自己一点点揭开以前的惶恐和焦躁,感觉痛快淋漓。
很长一段时间,陈当的行李半开着,衣物东西半乱着,是舍不得清空,又没法收拾的样子。他给女朋友打电话,在女朋友的哭诉和描绘里厌烦又无措。
他们怎么能这样?女朋友的声音变得尖利,把你拖死在那里,怎么能这样?
陈当说,不关别人的事,脚在我自己身上,是我自己的事。
关你什么事?你是救世主?你是政府吗?你有责任吗?女朋友一句一句追问,声调一层一层扬上去。
陈当说,看起来没有责任,实际上有,我骗不了自己的,我捂上耳朵,闭上眼睛,合上嘴巴也骗不了自己,因为心灵还没有死。
你别说这些又虚又空的,我听不懂也不想听。女朋友的哭声破喉而出,对我,你的责任呢?
对不起。陈当感觉腰背猛地压了重物,压得他整个人往下一弯。
坚硬的沉默。
陈当把话筒死死扣在耳上,他怀疑女朋友已经停止呼吸。对不起,对不起。他在胸口狂喊。
不知多久,他听见那边什么被摔碎的声音。
又不知多久,他听见女朋友的声音,游丝一样,有意义吗?你念这个医科大学,就为回去看个感冒发烧,开点维生素或止疼片?
意义不是这样衡量的。陈当说,说得很小心,说完就开始后悔了。
果然,女朋友追问,那怎样衡量?你至少说服我吧。
不知道。陈当说,我还不知道,也许以后我会知道的。
陈当对阿爸阿妈说出留下的决定时,阿爸阿妈的表情他至今说不大清楚,又轻松又痛苦,又欣喜又惭愧。事过境迁之后谈起这事,阿妈垂下头,手在陈当手背上一拍一拍地,说,当年,我和你阿爸自私了,把那样的事全丢给你,没给过你一把力,连给你撑一撑都没有,我们太弱太懒了,不配当阿爸阿妈。
阿妈,这是我自己的事,别人没法的。陈当说。
现在,对圆木,陈当还是这句话。圆木听不太懂,对他睁大双眼。陈当说,我自己的事,该我自己做,做了,我就不会梦见自己不见了。就像圆木现在,在梦里,你自己再不会不见了。
圆木似懂非懂,但他笑着说,我不害怕了。
我也是。陈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