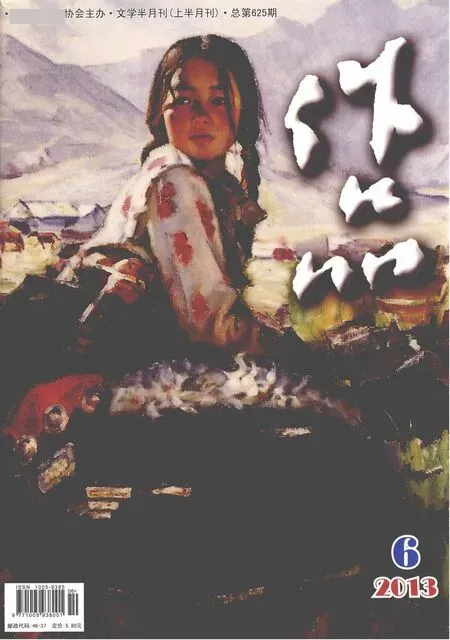我曾如此孤独
◎张其鑫
葬 礼
火车缓缓停下,月台上竖立的木头站牌还没换,木溪镇几个字已经褪去了原有的墨迹,但却旧得很好看。
走出站口,夏答迎了上来,接过行李,拍拍我的肩膀,说,秋伐,就差你了。这话听起来像是等待着我去参加一个婚礼或是集会,但都不是,我这次回来是为了参加祖父的葬礼。
我瞄了一眼手机,凌晨四点。新交的女朋友给我发来一条信息,铃声是《常回家看看》。我觉得回去参加葬礼好像有些别扭,就随手把铃声换成了《大悲咒》。
夏答把行李放进后备箱里,给我递来一根烟,拿出打火机咔嚓为我点燃。然后递来车钥匙,揉了下浮肿的眼,说,秋伐你开吧,我想睡会。从火车站到镇子里的距离是一个小时,为了让夏答睡得安稳些,我开得很慢,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擦亮了。日出的红霞照射在紧合的大门上,门上还是旧年的门神。除了因南方潮湿的天气变形得更厉害的木门,其他似乎什么都没有变——只是平添了一个崭新的白灯笼与两串纸钱。
我定定神,打开车后门,拍拍夏答,说,哥,起来了,我们进去。
刚踏进厅里,母亲就迎了上来,倒不像以往一样满脸带笑地说你回来了,只是神色平淡地说了一句回来就好。我想大概是由于祖父的死去。
祖父的棺材摆在厅中央,还没钉上。我走过去望了下,祖父脸上有点异常的乌青,像是中了毒一般。我想大概是我职业敏感惯了,我又细细看了眼祖父,死亡丝毫掩盖不了他的安详。
往棺材旁边看,凳子上窝着个人,是守夜的父亲,应该是累了,直接趴在凳子上睡着了,团成一团,越发显得佝偻。我慢慢走过去,把衣服脱下给他盖上,对着棺木跪了下来,叩了三个并不响的首。
前来吊唁的人陆陆续续进门,但并不多。母亲唤醒了父亲,示意我和夏答跪在父亲旁边。主持葬礼的是祖父的一位老友。和电影里演的一模一样,来宾先点香,然后主持者会宣布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家属打理。
祖母在旁烧纸钱,并不大哭,只是嘴里低低念叨着一些难以耳闻的絮语。
法师按部就班地盖上棺木,围着四周走了三圈,嘴里念起咒语,右手中指食指不停地在画着看不见的符咒。咒语停止时,法师从包里拿出四颗长钉,一下一下砸进去,声音又沉又响。我跪在地上,不知道为何觉得法师钉的不是棺木而是祖父的脑壳。
出殡就在当晚。随着吱吱嘎嘎的鼓声的响起,棺材被抬进了大卡车上。鼓乐班子的人像小丑一般手脚并用地爬上卡车后厢,有的坐在了棺材上方。我和父亲则在前方默不作声地撒纸钱。随着卡车的引擎发动,跟在后面的送葬队伍开始嚎啕大哭。
最后一块盖棺砖准备盖上时,一座新坟墓就完工了。
祖母迈着并不流畅的小碎步绕坟墓走了几圈,指着近旁的一块空地,对父亲说,等我死了就埋这里。
祖 父
祖父是一名强盗。倒不是我曾看见他在哪个人烟稀少的路口扛一把大刀对过往的行人说什么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只是大家都这么说。
在我小的时候,祖父经常骑着那辆老凤凰自行车带我去小县城或小镇里逛荡。谁遇到祖父都会忙不迭地向祖父打招呼,祖父总是眯着眼睛笑笑。家里经常都有客人来访,借钱的,还钱的,带礼物来讨好的都有,把祖父捧得活像现在的领导。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怪象,小时候我总以为强盗就是一种很受人尊敬的职业,还曾暗暗发誓长大就要学着祖父一样当一名出色的强盗,称霸一方。
祖父被警察带走的那年,我十三岁。是在秋天中旬,恰好是我的生日。虽然古话说从来邪不胜正,坏人总会受到法律制裁。但我从不认为祖父是一名坏人,因为我不曾见过他调戏过某个良家妇女,哪个三岁孩童。
胡屠夫带着警察搜我家时,祖父还悠闲地在内屋里坐着和老友对弈喝茶。对于这样的搜查,祖父早已习惯,像是妓女从良般,就算有些见不得光或者有失颜面,也不至于担心受怕。
警察一阵翻箱倒柜后,终于还是不辜负他们的涔涔汗水,在阁楼里搜出了一把猎枪和一个很旧的瓶子。用胡屠夫的话说那瓶子是他家里祖传的价值一百万的古董,之所以在我家阁楼里出现,是因为他早上在西岸小巷里撒尿时被祖父用猎枪顶着头抢去了。一个屠夫为什么去巷子里撒尿这个问题并不滑稽,滑稽的地方在于一边撒尿一边还带着一个价值百万的瓶子,我想不通,我觉得警察更应该百思不得其解才对。
但警察只讲求人证物证,即使我跟他们说祖父早上并没挑着枪去西岸当强盗而是和我去东岸钓鱼去了,即使父亲一再强调说瓶子是祖父的一位已故老友送的,一直藏在祖父床头柜里,但警察只是留下了两个字:狡辩。
亲手押走白发苍苍的祖父的是警察大队长王五,他离开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房子和瞄了一眼母亲。或许他觉得要是房子也是抢来的就好了,这样的话就可以有理由查封,用来当警察局。布局都想得很好,门的上方可以挂着烫金的“木溪镇警察局”的牌子,门里面镶上各种荣誉证书和锦旗。两边白墙上印刷着红色宋体字——“忠于祖国,为人民服务”。
当然,这只是我小时候的异想天开。
警车开走的时候,引擎声像喝了兴奋剂般变得格外刺耳,警笛声也毫不示弱地强有力伴奏。父亲缩在一旁大口大口地抽着旱烟,而夏答则躲在角落里放声大哭。
也就是那天,邻居小胖悄悄地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一拳揍了过去,说了句操你妈。
流言蜚语总盛行在一个家庭由盛转衰之后。祖父被判了五年。也就从那时开始,家门前一改往日络绎不绝欢笑纵横的样子,忽然就变得冷清起来。只是偶尔还是会收到一些礼物,例如一些臭鸡蛋或是炸得四分五裂的鞭炮。
我的同学朋友们间开始传唱一位在市里登过征婚启事的大作家新写的童谣:
强盗强盗真可笑
抢到粮食就大叫
大叫累了就睡觉
一觉醒来继续叫
警察叔叔真好好
把那强盗抓入牢
抓入牢啊抓入牢
父 亲
祖父被判刑的那天晚上,父亲在里屋歇斯底里地喝斥着母亲,那样子像极了一头幼子被欺侮的野兽。当父亲举起巴掌要向母亲扇去的时候,祖母拉住了他,并白了一眼母亲,一字一句地吐出四个字,不守妇道。
祖母大字不识,小字不会。但在她自认为除了字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懂,如果谁质疑她的话,祖母都以一句“我吃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长”来回应。
关于母亲有外遇且外遇的对象是胡屠夫的事就是由祖母推理得来的。她说只有这样,把母亲代入婚外情公式里计算,猎枪和瓶子在阁楼里出现的事情才会顿时变得合情合理起来。而且还能顺带说明了为什么带警察来搜查的不是街口卖菜的刘二而是胡屠夫。
母亲蹲下来哭泣,豆大的眼泪往下冒,死咬住嘴唇不肯发出声来。
父亲好像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不顾祖母的冷眼也蹲了下去,叹了口气,用衣袖一下一下擦干了母亲的眼泪。
从小就不喜欢看悲剧,我没有看下去,独自一个人去了东岸的榕树上。趴着用石头刻着那些对我唱强盗童谣同学的名字,名字后面还加了去死二字。刻累了,抬头望了一下四周,发现不远处的小树林丛里有两个人在亲嘴,男的还用手抚摸着女生的胸部。仔细看才陡然发现,是夏答和胡小语。
胡小语的爸爸是胡屠夫。
父亲坐牢那年,我十六岁,在他所在监狱的城市就读。坐牢的原因是因为毒品。
他出狱那天是我接的,瘦弱的身子,小小的缩成一团,与之搭配的是近乎祖父般苍老的容颜。
在饭馆为父亲洗尘时,我们父子俩生平第一次坐在一起喝了酒。醉酒的他说出了这么一段话。
在我骑自行车的时候,别人还都在走路。在我骑摩托车的时候,他们骑起了自行车。在我开起私家车时,他们开始骑上摩托车。但在他们都开上私家车时我却连摩托车也没得骑了。如果关于因果报应什么的我也就信了,可虽然老头是强盗土匪,谈不上劫富救穷,可是,谁做的好事又多过他呢?
祖 母
祖父出狱那年,家里经济已经稍微喘过气,父亲已经戒除了毒品。夏答在小城里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而我则考上了北京一所医科大学法医系。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送我去火车站的是夏答。祖父母和父母都在家门口为我送行。那天最爱流泪的母亲倒是以微笑的姿态挥手告别的,而从没掉过眼泪的祖父倒像个孩子一样号啕大哭。
我离开了家整整一年。祖父中风倒下,卧床不起。我这才知道离开家的那年家里过得并不好。
回来的那天,进门看到的第一幕是祖母在为祖父换尿布。凳子上摆着一盘热水,正腾腾地冒着热气。我停了脚步,站在门边,看着祖母先把祖父的衣服脱下,然后娴熟地拧干湿毛巾,把祖父的赤裸的深纹道道的皮肤仔仔细细擦了个遍。祖父不知道是因为水过于烫还是祖母擦拭得过于用力,痛得哇哇大叫。
祖母一边把毛巾往热水里浸一边大声喝斥,都几岁了还叫,不怕你孙子笑话啊。说完对着我笑着笑着就哭了。祖父已经不能说话了,一双深凹的浑浊的老眼干巴巴地望着祖母,伸出干枯得如柴木的手笨拙地擦去了祖母的眼泪,又哇哇地叫着。
我不懂他们的爱情,但却让我刻骨铭心。
待祖母出去后,我上前握住了祖父的手,说,爷爷,我是秋伐,你的孙子。
祖父呵呵地笑。顶着白发左右晃动着头颅,越发显得他像个小孩。
我离开他房间的时候,我分明听到了一句,哦,秋伐回来了。
那一年,我十九岁。
夏 答
夏答的名字是祖父起的,本来是飞黄腾达的达,只是祖父去登记时忘记了那个“达”怎么写,就改成了“答”,夏答。
最后,娶了胡小语的不是夏答。胡屠夫死在了胡小语结婚的那天晚上。
胡屠夫的尸体是第二天早上被街口卖菜的刘二发现的。那天正好刘二他老婆生了一大胖儿子,想着早点去胡屠夫那买些新鲜的猪心煮点粥给他老婆补下身子。可是当他推开门时就吓得半死,屁滚尿流连滚带爬地跑出了老远,大叫着死人啦死人啦。
警察封锁了现场,不过街坊还是围满了门口。
胡屠夫的尸体像他所屠杀的猪一样七零八落地摆在案板中,手臂,大腿,都被一一砍下,整齐排放着,连心脏都被挖出用刀劈成了两半。
杀人诛心啊。一老头说。
一中学生在旁回嘴,爷爷,你这是望文生义。
由于胡屠夫得罪的人太多了,无从查起,但警察还是第一个想到了祖父。
当警察在我家见到了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连水也要人喂,口水还一直往下冒的祖父,终于不折腾地离开了,似乎多多少少带着些许遗憾。因为离开之前王五大队长还是像当年抓走祖父时一样望了下房子,以及瞄了一眼在旁静默着的母亲。
胡屠夫的案子成了一宗悬案,最后因为上级压得紧直叫着赶紧破案,木溪镇警察局反复思量与考证后,最终还是给出了结论——
死因,自杀。
秋 伐
大四那年,秋天中旬,我二十二岁生日,那天接到第一个电话是夏答的。我按了接听键,没听到祝福,倒听到了夏答冒出的简单的四个字:老头死了。别无其他。
扶着祖母从祖父坟前回去家里已是响午,我饿得找遍了全家却没找到一点食物。最后在祖父房间里发现了一大包的麦片,我把麦片倒进碗里,倒进开水——
似乎并没有过期,麦片听话地与水相融,变成了热腾腾黏糊糊的麦片粥。唯一和以往不同的是,麦片粥上漂着一层蓝,近看似乎是未完全溶解的颗粒。我也顾不上,准备把麦片送进嘴里时被祖母抢了过去,说,你祖父的,不吉利,等下就有饭吃了。
我顿了顿,应声倒了,只捏了一点,放口袋里,以要上课为由当天晚上就坐上火车赶回学校。
回学校我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直奔去了化检室。那一点漂着蓝的麦片残渣化验出的结果是,剧毒。
于是从那一刻起,我又多了一个秘密。又多了一个。
我想立刻回宿舍去和女朋友相拥,纠缠。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我才能忘掉那两个我本不应该守着的秘密。可是回去的时候,宿舍被搬得剩下一张破椅子,连女友的一根头发也找不见。我万念俱灰,拿起了解剖刀,在左手动脉处比划着一条能最快死去的线路。

世界经典插图选登托马斯·克利1926年为西佛吉尼亚波尔普纸业公司设计的广告插图。
这时,手机响了,铃声是大悲咒。
后来,主持为我剃发时,我还想着那两个秘密。
再后来,为夏答超度时,我念叨着自己也不懂意思的经文,痛哭声大过诵经声。主持在一旁冷眼看着,说了一句,七情六欲尚未断。
夏答是死于车祸。
父亲把夏答葬在了祖父的旁边,也就是当初祖母所说死后要葬的那里,而挖掘出的洞穴里,从祖父盖棺砖旁挖出了一个瓶子。
——是那个胡屠夫说的价值一百万的、原本属于祖父的瓶子。
葬礼结束,祖母拄着拐扙迈着小碎步,围着那一旧一新的坟墓转了三圈,指着两座坟墓旁边的一块空地说,死了,我就埋在那里。
我有两个秘密,一个来自已入土为安的夏答,一个来自即将长眠的祖母。
母 亲
夏答葬礼的当天,母亲生了一个大胖儿子。我家大门还是老样子,白灯笼留着一边,只不过另一边添了一串红灯笼,一喜一忧。
当我抱起名为春新的弟弟时,发现眼睛并不像父亲,倒像警察队长王五。
我忽然想起,小胖在我十年前和我说的那段被我揍他的话。
“嗨,秋伐,我早上爬上警察王五院子荔枝树上偷荔枝时看到了你妈和王五在亲嘴还有两个人光着身子抱在一起打架呢,这比功夫片好看多了,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下面会硬邦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