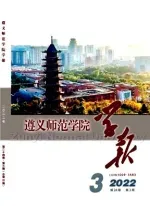《赛德克 巴莱》的阳刚美学
陶 然
(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魏德圣的台湾史诗电影《赛德克 巴莱》历时筹备12年之久,2011年9月在台湾上映,次年5月在大陆上映,获得了广泛好评。这部电影展现了台湾电影的阳刚气质,这种雄浑健壮的阳刚气息是近年来的台湾电影所缺乏的。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崇尚温良恭俭让的主流旋律,对暴力和死亡的表现大胆而彻底。在这部电影中,以莫那鲁道为首的赛德克族男人们纷纷赤膊上阵,无论是为猎场还是为信仰的战斗,都异常真实而激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赛德克族人雄浑的男儿气概,为本片阳刚美学的电影风格奠定了基础。在电影中,魏德圣的镜头运用及取景深具巧思,无论是电影开场为了夺取猎场的赛德克人之间的战斗,还是故事发展到中段,赛德克人为了民族信仰而发动对日军的斗争,几乎都是用的大全景。这种史诗般宏大的视角,不单只是表现这个特殊的时代环境里的个人,更多的是让人物的群像融合在台湾高山心脏地带的密林里,让原始的人与景互为交融,令观众获得一种粗粝的力量美感与崇高美感。
《赛德克 巴莱》以台湾历史上的“雾月事件”为蓝本,讲述的是1930年,台湾高山原住民赛德克族人被日本统治后,自己的文化和信仰被日本人严令禁止;在信仰面临灭绝时,赛德克人选择了捍卫尊严,在头目莫那鲁道的带领下奋起反抗。影片长达4.5小时,分上下两部(《赛德克 巴莱[上]——太阳旗》和《赛德克 巴莱[下]——彩虹桥》)。这里主要讨论的对象,是《赛德克 巴莱[下]——彩虹桥》。清代桐城派文论家姚鼐形容阳刚之美为:“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1]虽然姚鼐在这里针对的是文学中的阳刚风格做讨论,但是对综合了文学在内的电影艺术也是同样适用的。本文拟从电影的人物角色塑造、电影的悲剧性两个方面来探讨《赛德克 巴莱》所体现出来的阳刚美学。
一、《赛德克 巴莱》的人物角色塑造
《赛德克 巴莱》讲述了赛德克族人为了自己的民族信仰而浴血反抗的历史故事。在角色塑造上,导演魏德圣采取了重点塑造赛德克族头领莫那鲁道,让他成为贯穿电影的一个精神核心;另外还塑造了起义六大社头领、集体自杀的赛德克妇女儿童、起义的赛德克族人等人物群像;其间贯穿了继承莫那鲁道英勇无畏气质的15岁的赛德克少年巴万等人物的侧面烘托。这样点面结合的角色塑造方式,既打造出了一个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又有主有次,叙事线索十分清晰。值得注意的是,魏德圣在这些角色的塑造中,几乎没有一个突出的女性人物存在。女性角色都被群像化了。她们仿佛是赛德克族赖以生存的土地,宽厚博大,无声无息地存在,把荣耀全归属给了男人。同类的电影中,在电影叙事主线或分支中总是会出现一个或几个女性,以阴柔之美的视觉去审视战争与文明。《赛德克 巴莱》在角色上的抉择,不难看出魏德圣的用心:他就是要拍一部充满了阳刚与力量之美的振聋发聩的史诗电影。
赛德克族的头领莫那鲁道是整部电影的重点人物,被浓墨渲染。影片一开始,就是青年时的莫那鲁道在丛林里发足飞奔。他手起刀落,取了敌对部落战士的头颅,避过箭羽和枪弹,扛了山猪跃入湍急的河流中。少顷,他从水中一跃而出,在水面上密集的枪弹中奔跑,并迅速隐入丛林中,只留下一句话:“听好了,我叫莫那鲁道!以后听到这个名字可要小心了!”这组镜头只用了2分17秒,镜头剪辑非常流畅利索。
在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中,阳刚之美与雄伟、崇高、壮美等是相近的概念。在中国美学中,阳刚之美又一贯被视为艺术风格美的一个与阴柔之美相对的基本类型。它可以在不同的艺术形式里分别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具体艺术风格。在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将这种阳刚之美以《劲健》、《雄浑》等品来集中讨论。《劲健》品中,可以考察出阳刚之美还有一个美学特征,即力量气势精神的蕴蓄、充盈、贯注、健行不息、畅行无阻、往来无迹,骏利快捷,并由此而展现为一个充盈着力量与气势的壮阔的艺术境界。在上述镜头中,骏利快捷的画面叙述的节奏感和速度感非常好地表现出了这种劲健的风格。导演将其深养厚培了十二年的劲气健力贯注于电影中,令其中气势遒劲健行,最终展现出高峻横阔的艺术境界。而神、气的健行和壮阔境界的展开又往往是在骏利快捷的节奏中实现的。
另一组镜头是日军占领台湾,进入赛德克人居住的深山密林。混战中,莫那鲁道的父亲被打死。他背着死去的父亲一路狂奔,眼中的怒火烧干了泪水,口中发出如野兽般的嘶吼长啸声,悲怆有力,将原始的介乎于人性与兽性的美学观渲染出来,既震慑人心又传达出悲壮的力量。这两处故事的配乐也不一样,时而铿锵有力,时而悲壮低沉,原生态的土著歌谣和舞蹈在电影中也极具美感和力量感。
在处理人物群像时,几处战斗充满了苍莽意味,营造出一种古意悠远的杀戮。战争场面的技击动作,与好莱坞特效电影不同的是,在技击上还原真实,表现出一种最原始的力量。电影中所有赛德克男人颀长而肌肉结实的四肢,刚毅的面部表情,如豹子般迅捷的奔跑速度都以一种充满力与美的阳刚风格让人印象深刻。
司空图在《雄浑》品中,又具体概括出了“积健为雄”的主张。“健”,刚强有力,“积健”,就是不断蓄积健气健力,长期蓄积,就达到了“雄”的境地,也就是强调阳刚之美具有无比巨大的力量。这一特征和西方近代理论家们对“崇高”的特征的看法相当接近。西方美学家们认为,力量的巨大是崇高的一大特征或根源。博克说:“没有一个崇高的事物不是力量的某种变形”[2]。
台湾版本的电影开场有莫那鲁道饮血吃生鹿肉的镜头,也有许多砍下人头的镜头。赛德克人不仅不觉得残忍,反而将砍下的头高举过头顶,以示荣耀,砍下高官头目的头的,便会成为英雄,被大家称颂。人类文明的发展,必不容这样野蛮的方式,然而这是从整个人类和文明的角度来看的。我们的原始部族,都是以打猎为生。可以想象到的是人类在对抗凶险的野生动物时的危险性,野兽、自然灾害都能对这些原始人造成巨大的威胁,如果不崇尚力量和速度,以图腾和祖灵信仰为精神护佑,很难相信原始人类能生存下去。于是乎砍下凶猛野兽的头的人成为了英雄,能有勇气在部落征战中砍下对方人头的人,也便成了英雄。如果不这样,族人便没有动力去磨练身体和意志在这危机四伏的丛林中生存和战斗。于是乎原始部族也发展出了原始狩猎部族的生产方式和信仰,他们的信仰比很多信仰神的人更甚,更真切,他们一定相信他们会回到祖灵的身边,越过彩虹桥,进入那肥美的猎场,获得永恒的生命。
因为这样共同的信仰,所以六社的头领放下了部落之争,联合起来谋划雾月事变。在这里导演塑造了一个群像,每个人都是画面的主角,共同支撑起这场腥风血雨的历史。赛德克人虽然靠着猝不及防获得了雾月事变当天的胜利,但当日本重兵和飞机炸弹到来时,灭族的命运是不难预见的。为了节约粮食,不分散男人们的精力,妇女们带着幼小的孩子来到大山深处,从容赴死。镜头里,这些面部纹身的女人虽身形各异,但却都拥有共同的神态:从容自若。她们次序井然地结好了自尽的绳索。没有哭泣,没有哀声。雨无休止地落下来,整个场面安静肃穆。画外响起悲凉高亢的原住民女声,唱着一支祖灵的歌。
十五岁的少年巴万,以莫那鲁道为自己尊崇的英雄,他也加入了这场抗争。这个拥有稚嫩面容、清澈眼神的孩子拿起刀,割下被生化武器折磨得生不如死的同伴头颅;拿起枪,扫射数倍于己之多的日军。这样稚弱的躯体下,藏着如此高昂的斗志,怎能不让观众看到一种对比强烈的崇高之美呢?被日军的飞机、大炮轰炸了四十天,最后的决战到来时,赛德克人与日军遭遇在一座吊桥旁。日军早已架起了数门大炮。莫那鲁道问:“达多,告诉我,怎样才能越过那些大炮?”此时从莫那鲁道的身后站出来一个男子,说“头目,让我这个鬼魂来开路吧!”说完,便飞身迎向炮火。
从莫那鲁道到巴万达多,电影的角色塑造都呈现出了慷概激昂的审美风格。除了电影角色塑造的雄浑劲健,魏德圣的取景也非常具有深意。镜头自上而下俯拍险峻的高山、怪石嶙峋的山间窄道,使之都充满一种力量之美。
二、《赛德克 巴莱》的悲剧性
悲剧产生于社会的矛盾。著名的希腊悲剧盗火者中,普罗米修斯与以主神宙斯为代表的专制神权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悲剧的基础。冲突双方分别代表着真与假、善与恶、新与旧等等对立的两极,却总是以代表真善美的这一方的失败、死亡、毁灭为结局。
悲剧和阳刚之美有着不绝的联系。因为悲剧不仅表现冲突,而且表现抗争、拼搏。悲剧的毁灭是抗争、拼搏以后的毁灭,是惊心动魄、轰轰烈烈的死。莫那鲁道联合六大部落发动雾月事变,无视日军的重兵,在残酷的镇压下,英勇斗争,直到死亡。抗争因此是悲剧的重要特点。越是无望的抗争,越显示出悲剧的厚度。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令人伤悲的。因此,现实的悲剧只能在客观上具有悲剧的审美性质,它们必须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成为欣赏的对象。因为艺术形式建立了悲剧与人的心理距离。从现实的悲剧到悲剧艺术,电影创造了一个时间间隔和空间间隔。几十年前的台湾原住民与日军发生的那场雾月事变是我们不熟悉的,因此,狂暴与摧残,苦难与血泪,都因拉开了距离而使观众能客观地看待。在欣赏中,我们可以加入悲剧冲突,体验悲剧主体的抗争和悲痛,从而获得悲剧美感。
在《赛德克 巴莱》中,导演魏德圣认为这个悲剧矛盾源于信仰彩虹和太阳的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面对日本人的“文明”异化,莫那鲁道愤怒地回应:“什么叫文明?男人被迫弯腰背木头,女人被迫帮佣陪酒。邮局、商店、旅馆,只是族人看见自己有多贫穷而已!再过二十年,就没有猎场,没有赛德克,孩子全都是日本人了!”我们可以注意到,他说的不是我们就灭族了,而是孩子都是日本人了。这个老族长所担心的不是日本人会将他们全族屠尽,而是日本人的教化使得族人都不信仰祖灵,反而信仰文明,以后长大了去上学求知而不是去猎场打猎。他担心的是祖训全无,赛德克的灵魂死亡,这就是莫那鲁道的“道”,他所要守护的不是族人的性命,而是族人的信仰和赛德克的图腾。没有了图腾,赛德克便于其他人无异,赛德克等同于自取灭亡。
与经过维新变法的日本人相比,1930年的台湾原住民赛德克人看上去还处在“文明世界”之外。他们勇武善战,狩猎为生,把敌人的头颅作为自己的荣耀。但在日本人所谓现代文明的推动下,以枪炮为逼迫,原住民被奴役,孩子们都被迫接受日语教育。赛德克人的猎场被日军变成伐木场,传统的生存方式和信仰正在一点点被“文明”摧毁。隐忍了二十年,见识过日本人的坚船利炮的莫那鲁道首领,在明知道反抗必死,甚至有灭族危险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了保留“野蛮的骄傲”,让自己的灵魂通过彩虹桥到达赛德克人祖灵的圣地,而不是做一个卑微的文明人。一个“野蛮人”保留着自己不屈的价值观,让自己在骄傲中死去,而不是让生命在奴役下终结。他喊道:“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带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
在族人信仰的坚守下苦苦挣扎的莫那鲁道,独自一人来到先人逝去的密林中。在巍峨的高山下和潺潺的流水边,莫那鲁道看到了已经逝去的父亲的灵魂。父亲的灵魂和他一起唱了一首歌,那雄浑深厚的吟唱带出了全片的精神内核:
我来到这里
我曾英勇守护的山林
真的啊是真的
怀念过去的人们啊
我来到这里
我曾英勇守护的山林
这是我们的山
这是我们溪
我们是真正的赛德克巴莱啊
我们在山里追猎
我们在部落里分享
我们在溪流里取水
我愿为此献出生命
溪流啊,不要再吵了
祖灵鸟在歌唱了
唱个好听的歌吧
为我们族人歌唱
巨石雷光下
彩虹出现了
一个骄傲的人走来了
是谁如此骄傲啊
是你的子孙呐
赛德克巴莱!
父子二人慷慨悲凉的一唱一和呈现出了一种悲怆之美。莫那鲁道隐忍几十年,最后在与父亲灵魂的唱和中做出抉择,让肉体死亡,精神通过那彩虹桥来到祖先为赛德克们准备的丰美猎场,去到祖灵所在的地方。他说:“日本人比森林的树叶还繁密,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可我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定!”因此悲剧主体对待痛苦和死亡的方式便是抗争。在这抗争中显现了人的伟大。死亡,意味着肉体力量的失败,却并不意味着精神力量的失败。悲剧表现的不是人生的欢乐或全然的幸福,而是受难与痛苦、抗争与拼搏,它展现的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中最重要的、最严肃的一面,展现的是悲剧主体对待痛苦的和死亡的方式。冲突双方力量对比越是悬殊,主体的抗争越是艰难,我们从中体会到的人的精神越是强大。悲剧表现的实际上是对伟大崇高的人的摧毁,但更表现出了无法摧毁的人的精神的崇高伟大。正是这人的精神的伟大与崇高,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审美愉悦,感到了振奋,感到了难以言喻的升华。面对强大的敌对力量毫不退缩,敢于抗争的行为,为民族的信仰勇于献身的精神,都会放射出崇高的光芒,这是生的崇高。
有意思的是,“赛德克巴莱”在土语中,意思是“真正的人”。在这幕文明扫荡野蛮的历史中,他们无疑是悲剧的主人公。因为他们的力量与强大的日军力量相比弱小,还无法相抗衡。赛德克族的落后文明在现代文明面前,必然要遭到挫折、失败、牺牲和毁灭,维持民族信仰和自尊的要求在历史巨轮的推动下难以实现,甚至无法实现。这正是其悲剧所在。在文明异化了一切的现代,如赛德克巴莱一样固守自己的信仰、内心的纯净,视死如归的“真正的人”,也终于消亡而不可寻了。这是文明的悲哀。
在采访中,魏德圣说,这是一部争取灵魂自由的英雄主义电影。诚然,这阳刚之美给人以雄强奋进、积极向上的艺术享受,是我们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的象征。《赛德克 巴莱》洋溢着浓厚的刚健有为、舍生忘死情调,形成了全片推崇阳刚的美学精神。
《赛德克 巴莱》一上映就获得了广泛关注,被认同为高山民族争取灵魂自由的史诗巨制。《赛德克 巴莱》中的莫那鲁道为了捍卫自己的民族自由自尊,以弱小之力去对抗日本重兵,明知无生还机会仍然奋勇前行。他身上无不散发着一种刚强的不畏强暴的气息。莫那鲁道无疑是美的,他的美来自对民族、对祖先“彩虹猎场”信仰的坚守,来自于面对死亡大无畏的人格魅力。这种美是动人心魄的美,这充满阳刚力量的美,让人备受震撼。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庸庸碌碌地走完毫无意义的人生,而应该去实现自身的价值,有一番作为,才不枉度此生。《赛德克巴莱》的出现,让人们仿佛看到了一种勃勃的向上奋进的力量。这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催人不安于庸碌无为的生活,而应该活出自己的价值来。《赛德克 巴莱》中彩虹勇士们用他们的生命告诉人们:生活中最有价值的就是那可以超越生命的信仰。唯有追求信仰,才能使终将衰亡的个体生命永恒不朽。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汝信,夏森.西方美学史丛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