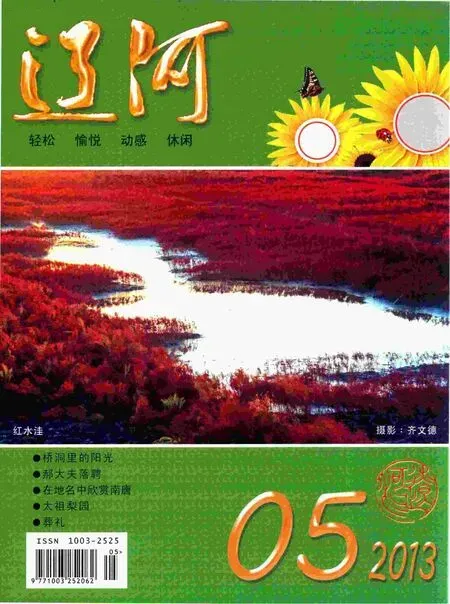村里那些树
曲京溪
六月初十那天,我回家给母亲烧三周年,却怎么也找不到住在同村的三妹的家。原先三妹家门东的小巷里,有棵高大的槐树,这棵槐树就是我到三妹家的参照物,过春节时它还活得好好的。可如今小巷变成了水泥路,那棵槐树也不见了踪影。我们村的农房,是经统一规划建设的,我无法找到三妹的家门,只得打电话让三妹出门引路。三妹说:“甭说你了,一年回不来几趟。就是王超(三妹的儿子)放假回来,没有了那棵树都找不着家了。”没了一棵树,儿子回家连家门都找不到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记忆中,老家的村子是被大树掩映着的。只有在冬季,树叶落光了的时候,才能看清农舍一排排整齐地排列着的模样。其他时候,大树就像母亲,环抱着村子;农舍就像孩子,依偎在大树母亲的怀中。
我们村庄很大,在我小的时候,东西距离就有一华里还多,户数近千。家家户户,门前栽树,房后种树,院子里还有树。榆树、槐树植于门前,取“门前一棵槐,不是进宝就是招财”之意。如果槐、榆相抱,呈现缠绕生长的景象,那可是大富大贵的征兆,预示着户主家不是要出达官贵人,就是出乡贤名流,是要光宗耀祖的。房后一般栽些枣树、香椿树之类。院内栽的树种,以农户家庭的经济条件和户主的个人喜好而定,家庭条件好一点儿的,多栽杏树、石榴、毛桃、苹果等果树,栽这些树不但能赏花,而且在那个水果匮乏的年代,还能给老人、孩子解解馋。家庭经济条件差一点儿的,院内一般种些白杨、梧桐什么的,长大后可当房梁、檩条盖新房子用。梧桐板子晒干后,不易变形,还是娶媳妇、嫁闺女打家俱的好材料。记得我家门前有条排水沟,靠街的乡亲,就在自家门前的水沟边上,栽上柳树。村外的道路两侧,由大队民兵和学校的学生,组织义务劳动,全部栽上了钻天杨,高大挺拔的身躯,一直与邻村的树木相接。在我的记忆中,村里村外种花的极少,我小时候在村里,只见过地瓜花和光光花两种花,觉得单调而乏味。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在那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年代,乡亲们哪有心思去观花赏景呢?但树木给人带来的欢乐,就够乡亲们享受一番的了。
当二月的春风,剪绿了柳树枝条的时候,村子里便响起了孩子们的声声柳哨。三叔是做柳哨的高手,他通常剪下一截直而疤疖少的柳枝,捏紧枝条的一头,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扭动树皮,然后抽出其中的白色木条,再拿把小刀,将圆筒的两端裁齐,削去一端的青皮,一个柳哨就做成了。圆筒粗的,吹起来声音浑厚,细些的声音高亢,懂些音律的,还能吹出好听的旋律,引得女孩子羡慕不已。
夏天到了,清晨或黄昏,当炊烟升起的时候,烟霭在树林里弥漫,根本分不清炊烟是从哪家升起的。人们下工回来,如同走进仙境一般。一场夏雨,浇开了知了尖尖的嗓门,从独唱、重唱到大合唱,知了们唱醉了乡村的夏季。中午,我们跟着大人去粘知了,通常是找一根向日葵杆子,上头插一节直溜的条子,接头处用麻绳勒紧;抓一小把黑面,加水和匀,再放嘴里嚼一嚼,就成了面筋,然后抹到条子的顶端。到树下,小心翼翼地粘住知了如纱的薄翼,知了怎么蹦跶也甭想挣脱。掐下知了的双翅,拿回家在咸菜瓮里腌上几个钟头,在大铁锅里焙熟,咬一口,满嘴生香。入夜,我跟着哥哥去找知了猴,因当时我们家里还没有手电,只能用手摸索着找,所以我们的收获常常不多,如今想起都觉得有些遗憾。
那年月煤炭短缺,液化气还没有。多半农户,一年里,总有那么几个月缺粮少草的日子。清秋时节,风吹黄叶落,是我们拾草的好季节。天还没明,我们就一骨碌爬起来,到沟边湾沿,用小笤帚扫树叶,有柳树叶,槐树叶,还有杨树叶。那碗口大的白杨树叶,是我们的最爱。因这种树叶,不管是在树上,还是在地面,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我们叫它“哗啦叶”。遇上刮大风,我们会起得更早。扫树叶的人多了,我们就抢占地盘。扫的树叶篓子装不下,我们会到生产队的场院边上,扯几根半干不湿的地瓜蔓子,一头横拴一节树枝,一头竖接一段细树条,用来穿树叶。那时候烧柴不足,我们拾的草,一年能补充一个家庭三四个月的缺口。
屋后那棵大枣树,是我们的最爱。屋是百年老屋。枣树就生长在老屋后面的夹道里。它枝繁叶茂,能遮挡半个屋顶。从枣树扬花的时候,我就天天瞅着枣树咽口水,盼望枣儿快快长大。等树上挂满了青果,每逢刮风下雨,我放学回家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后窗,爬进夹道,捡拾落在地上的青枣,也不用水洗,填进嘴里,就嘎嘣嘎嘣地吃起来,常常招来奶奶的一阵骂声。打枣的日子,是我们孩子的节日,也是奶奶最开心的日子。秋深了,满树的枣叶泛了黄,那红红的枣儿压弯了枝头。清早,太阳还没爬过屋顶,大哥就拿一根竹竿子,爬上树杈,使劲儿敲打,枣儿就哗哗啦啦、噼噼啪啪,从天而降。我们小一点的孩子,就拿着瓢、搪瓷盆等物,在地上捡拾。这一棵枣树,一年能结五六十斤,奶奶就放到天井里晒。待晒干了,奶奶拿个小一点儿的瓢,摆动着那双小脚,给本村的亲戚,左邻右舍挨家送去,让他们过年时蒸枣饽饽用。那棵枣树,是奶奶一年的念想,也是她在人前能挺起腰杆的希望。
相对于人类来说,树木的生命是卑微的,它们不能预知厄运什么时候降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建设连村路,村外的道路要拓宽,一棵棵十几米高、两人合抱粗的白杨树被贴地皮锯断,庇护村人们几十年的绿荫长廊从此消失了,只留下长长的一行树墩。我觉得一个个年轮清晰的树墩,就像是树们盖在大地上的一枚枚印章,证明着它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过辉煌的生命历程。直到有一天这些树墩腐烂了、消失了,它们的灵魂仍在大地里,萌动新的梦想。即使它们自己不能破土而出,也要托举起新的生命。
前几年,村里硬化主路时,那沟边房后的树木也一棵棵倒下了,有的倒在了推土机无情的铁铲下,有的倒在了乡亲们自己的手中。树木无言,可人是有心的。
一棵树倒下了,也许并不太可怕。可怕的倒是农村里的传统和文化的消失。搞建筑的大外甥,听说我回来了,找我又谈起了招工的事。外甥在老家村里成立了建筑队,专门盖民房、厂房什么的。用的人员都是守家在地的乡里乡亲,日工资,干大工的120元;小工90元。每当麦收、秋收时节还放农忙假。外甥为留住人员,工资是每月按时开的,逢年过节还得宴请他们吃喝。我问:“咱当地有那么多的建筑工匠,怎么非要舍近求远招外地的呢?”他心情郁闷地说:“你说的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如今瓦匠可成‘香饽饽了,搞建筑的争工人争得都快打破头了。我的那些工人,工资全发了,还得年前登门送礼稳住心;年后再送礼拜年定下来。”“村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他们整天没事儿干,怎么不学瓦匠呀?”外甥叹了口气:“嗨,现如今的小青年谁还乐意干这个呢!我用的70多个人,大工年龄最小的59了;最大的都72岁了。小工也没有一个掉下60岁的来。现在都是机械化了,根本累不着人,一天90元,小青年宁可在街上闲逛,也不愿意干这个,真是没办法。”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想我年轻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要学个瓦匠那可真不容易,得生产队长挑选优秀青年,还要安排师傅带徒弟才行。要是真能出息把好手,不但可以吃到“百家饭”,而且娶媳妇还能挑着捡着地找。现在的年轻人这是怎么啦?眼下农村30岁以下的孩子,还有几个会盖屋打墙、会种庄稼的呢?要是再下去几年工夫,农村还能有工匠吗?恐怕连能分清小麦、玉米的年轻人也很少见了。对土地的不敬,对劳动的鄙视,就是对生活的不热爱,这是自毁生命之根啊!
下午五点半,我们要去母亲的坟上。头上,太阳炙烤;脚下,水泥路滚烫。此时,我更加怀念村里的那些树,就像是怀念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