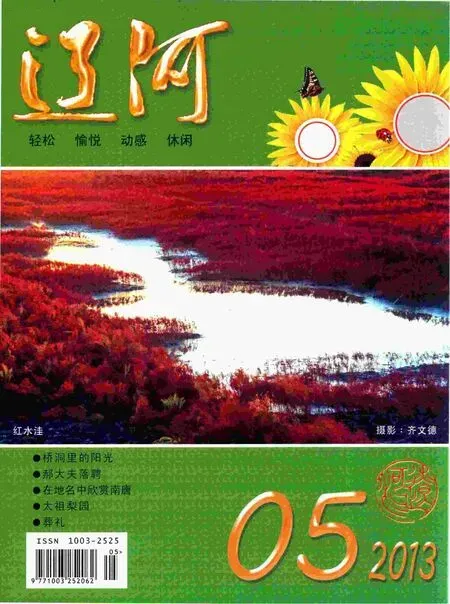小顺的愿望
史有山
半夜,小顺闹肚子上茅房,一会儿出来顾不上系裤带跑进屋说,爸!外面西墙头上有人。老程下地抄起火枪,拉开屋门跳到院里,就势一蹲,瞄瞄西墙头,嗵的就是一枪,墙上黑影哎呦一声缩了回去。老程提着枪在院子里巡视一番,没见异常回到屋里。
小顺紧张地问,爸,是啥人啊。
老程说,是老抢(盗贼)!让我打跑了。
小顺听老人们说过,老抢专抢大宅门,趁月黑风高翻墙头进入有钱人家,都睡觉了就偷,有人醒着就拿独撅龙冲人轻声喝道,别动!我们只要钱财,不要命,敢嚷,连财带命一起要。独撅龙是土造枪,一次只能打一发子弹。后街的三德子也有一只,小顺还摸过呢,两只手握着还直往下坠,挺沉。小顺不明白盗贼们怎么看中自己家的,院里有五只羊,屋里除了一个破板柜,就是一铺炕,炕席四边开花,有什么值得抢呢?一眼看到板柜上放着的一袋高粱面,小顺心说,是为爸挣来的这一袋面?
老程在村南新开的煤局子挖煤。小顺他们村叫乔家庄,村南不远是一片平地,小顺十岁时来了一拨子人,在地里东看西看,这群人大都长袍马褂,还有穿朝服却是高鼻梁,蓝眼珠,黄头发的洋人。人群中一个瘦高个,看长相四十多岁,春绸长衫,琵琶襟坎肩,尖口黑缎鞋配白布袜,骑在毛驴上满地里跑,指手划脚的呵斥人,奇怪的是所有人都听他的,连洋人也嘟噜嘟噜地说着洋话点头。清朝末年,小顺十五岁,这年这里建起了煤井。
三德子把自家的羊和小顺家的羊轰到北山坡草密的地方,羊群四散开来吃草。三德子四脚八叉地躺在草地上,小顺和四德子一边一个也躺在草地上,小顺看着远处的井架子说,这个煤局子不知是哪个大户人家开的。
三德子说,是朝廷的官家买卖,大清国建煤井咱村拔了头筹了,这里地下的煤好烧,挖出来卖给天津卫。
小顺看着蓝蓝的天问,天津卫在哪?
三德子说,嗬!远了去了,要坐船从海上走才能到。
四德子扭脸问,哥,你去过?
三德子红了脸说,我也是听人说的。
三德子比弟弟大五岁,但说话总让弟弟问住。
小顺支起身对四德子说,长大后咱俩坐火轮船去天津卫。
四德子也支起身说,肯定去逛逛。
小顺十八岁时,一个大官来煤矿巡视,八人抬大轿,前呼后拥,说是从京里走了一个多月才到的呢。问爸,爸说这个大官是直隶总督,在朝廷里挺吃香的。小顺不知总督是多大的官,问,比总甲大吗?爸照他屁股给了一脚说,总甲算个屁!爸对乔总甲没好感,见面就怒目相对,乔总甲说,老程,你不用和我较劲,你老婆死和我没关系。小顺的娘在村里算是有姿色的女人,县衙门给煤局子征地,乔总甲到家里来串门,和老程有一搭无一搭的唠嗑,看到小顺娘眼睛就放光,总甲说,老程,你看你这日子过得,穷气冒多高,瞟一眼小顺娘又说,去煤局子刨煤吧,每月挣一袋高粱面,不比土里刨食强?你把地交了,咱村给了几个名额,我给你留一个。小顺爸不说话闷头抽烟。小顺娘说,托了总甲的福了。小顺爸蹭一下站起身说,哪这么多废话,去烧大灶做饭!乔总甲没趣地站起身说,老程,这个名头给你留着了,地交不交你掂量掂量。
一天小顺爸去赶集,走到半路想起没拿烟袋,折回来进屋正看到乔总甲抱住女人在亲嘴,小顺爸大吼一声,一甩头,把辫子绕到脖子上,到院里去拿镐柄,乔总甲慌得从后院翻墙溜走,小顺爸把怒气撒在老婆身上,用鸡毛掸子抽女人,女人跺着小脚边逃边说,是他强迫的,我……女人羞愧难当,半夜悬梁自尽了。从娘死后,小顺夜里解手心里总发毛,老觉得后面有人跟着。
四德子说,小顺,看我给你做的弓箭,边说边摇晃着手中的家什。小顺凑上去,见四德子手中拿一把桑木做弓牛筋做弦的弓箭。四德子只比小顺大一岁,很聪明,挖个烟袋锅,做个弹弓都很像样,连大人们都夸他手巧。四德子说过,长大要做一把比他哥哥三德子独撅龙还响的手枪。小顺很相信这点。家里来了老抢,小顺和四德子说了,四德子说,我给你做一把弓箭,上茅房时防身用。桑木弓修理得很光滑,弦绷得很紧。小顺说,我射一箭试试!四德子从裤腰里拽出一支柳木箭杆,递给小顺。小顺说,咱们去煤局子冲井架子上的天轮射,看能不能射上去。四德子说,肯定能,我这弓箭射天宫寺塔上的铜铃都射的叮当响。天宫寺塔在乔家庄村北的山顶上,相传是唐王东征时镇压恶蛟留下的。村里老辈人都说,唐王东征路过这里,见有恶蛟危害百姓,愤怒之下用剑砍伤恶蛟,恶蛟复痛逃回海底,唐王把剑插在海眼位置,使恶蛟不得复还。天长日久宝剑化成宝塔,因为是宝剑化成的,所以天宫寺塔是封闭的,没有门。小顺每天放羊都路过那里,看塔尖要使劲仰脸,每次都把飞了沿的草帽滚地上。
两人相伴着走出村口向南趟过一条河,过一个土坡就到了煤局子,一座高高的铁架子矗立在眼前,上面有两个大铁轮在不停地转动,小顺总是不明白,铁轮子是怎样转动起来的,用牛拉也要十头牛来拉吧,小顺想。原先是一座沙岗子的高粱坨被铲平了,盖起了一溜青砖大瓦房,戴着柳条头盔的人们进进出出,辫子在脑后一晃一晃地。以前这片土地没被圈起来时,小顺常到高粱坨去逮蝈蝈,老远听到蝈蝈叫,蹑手蹑脚走过去,蝈蝈贼精,听到动静一下止住声,悄悄从豆稞子顶上往根爬,换一棵豆秧子继续叫。小顺知道这套把戏,耐心等着,汗水从脊梁上往下流,把贴在上面的小辫子都浸湿了。等找到蝈蝈的准确位置,两只手一合把蝈蝈拢在手心里。现在那里没有蝈蝈叫了,只有一台铁家伙的排气声,嘶嘶响。四德子说,别太靠近铁蒺藜网,矿警会开枪的。小顺说,没事,他们开枪也是冲你脑袋上面打。
搭着弓走两步停下,瞄瞄铁塔,觉得不正,又走。四德子说,别走了,对正了。小顺举起弓对着天轮闭起左眼,憋住气,刚要射箭,一声断喝响起,小孩!你干啥?四德子说,小顺,快跑!回身就跑了。小顺放下弓箭,看到眼前站着两个矿警。不由地把弓箭对准他们比划了一下。一个左眼有些疤瘌眼的矿警说,这是要搞破坏了,这一箭射出去,中人人倒,中机器机器卡死。回头对另一个年长点的矿警说,快!快吹哨子,有大案子了。老年矿警说,一个小孩子,值得大惊小怪吗,轰他走就是了。疤瘌眼说,不行,哨长说这两天让咱们看紧点,村民被征了地,有心里不服要闹事的。说着,吹响了哨子。一会儿来了七八个矿警,其中一个人问,啥事,谁吹的哨子?疤瘌眼举手说,报告哨长,是我吹的!哨长问,逮住刁民了?老年矿警说,就他多事!哪有刁民啊,只是一个小毛孩子。小顺认识这个哨长,是本村的,论起来还得管他叫三叔呢。小顺说,三叔,我正在这玩儿呢,疤瘌眼说我搞破坏,我手上只有一把弓箭,射人都射不死,不信,你瞧,说着,对准疤瘌眼就是一箭,疤瘌眼躲不及,胸口中一箭,吓一跳。哨长问,疼不疼?疤瘌眼说,不疼,觉得不对劲又说,好像被人杵了一下子。其他矿警都笑了。哨长说,这么一个鸡巴箭射人都不疼,还能搞破坏了。疤瘌眼说,那,这不算案子?哨长说,要不你找总办大人去禀报一下子。疤瘌眼说,找总办大人,我可不敢去,那不是王麻子的膏药——没病找病。哨长对小顺说,快回家去吧,别老在矿井周遭转悠,哪天我不在时,别人把你抓起来,可是让你蹲小黑屋去。疤瘌眼说,先别走,我看看你的弓箭,一把从小顺手中夺过去,咔嚓一下撅成两截,扔在地上。小顺狠狠地瞪他一眼,拾起断弓走了。
三德子说,你要是有我这样一把手枪,就不怕他们了。说着从腰里掏出独撅龙在小顺面前显摆。独撅龙用一块红绸子裹着,解开,手枪黑亮黑亮的。四德子说,哥,你净说些不着边的话,小顺用两手还拿不住枪呢,再说了,真打死人,还不得吃官司呀。小顺说,我要拿得动枪我就敢用,照疤瘌眼的右眼来一下子,让他俩眼都是疤瘌眼。三德子说,对!就得和他们干,把咱的田圈过去,挖窟窿捣洞地折腾,弄得咱们没有地种了,咋活!小顺说,我爸也总念叨说,挖煤没有种地舒服。不过,我可以天天吃现成高粱面呢。四德子说,就是,哥,你也去煤局子做工吧,那样我也有现成面吃了。三德子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辫子在身后甩来甩去说,饿死我也不去挖煤,我要跟他们斗,要把土地夺回来。
一晃,老程在煤矿挖煤五年了,月晌拿到了两袋高粱面,有五十斤。这天,爷俩围坐在炕桌前吃饭,压饸饹条、豆油炸的红辣椒、小白菜卤,一起拌在碗里,看着就解馋。爷俩吃的正香,三德子闯进门来,一屁股坐在小顺身后,正对着老程说,程叔,你听说了吗,矿上要修铁路了。老程咽下一口面条说,早听说了,井下嚷嚷动了。三德子说,你瞧你,听说了,还有心思吃饸饹,这次可是把咱村的土地都占了。从腰里拔出小烟袋挖一锅烟用火镰点燃,深吸一口,烟都吞进肚里竟一点没冒出来。咂巴一下嘴又说,咱村南面一马平川,土地肥沃,如今开了矿,北面是山坡子,没法种庄稼,西面是碱洼子地,只长蒿草,东面虽说是坡楞子地,但种啥长啥。一修铁路把东面的地又占了,程叔你说,这还让人活不,明天都去煤局子问问他们去。老程放下筷子抹抹嘴,找烟袋点上一锅,闷头抽烟,一会说,我也不操那份心,我的地早给矿上占了,如今一个月两袋高粱面,够我们爷俩活了。三德子跳下地把烟袋锅往鞋底上磕磕,腰里一插说,一个个都这么没出息,都这么没气没囊!说着往外走。老程头说,你不坐会儿了?顺子,送送你德子哥。小顺放下饭碗,追出去。到了大门口三德子小声对小顺说,明天你去不?你要去,我就让你放一枪。小顺说,真的?三德子说,不哄你,你去准让你放。
煤局子大门关得严严实实,一溜矿警站在门前,七八个庄稼人缩手缩脚地站在对面,三德子说,都往前靠,还没上阵就草鸡了!没人动,只有小顺跟上前来。疤瘌眼冲小顺说,这是当首领来了,几年前,你就射过我一箭,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又来挑头闹事。小顺说,我是来打枪的。疤瘌眼说,呦嗬!你小子越发野的没边了,你敢打枪,老子先崩了你。说着,把手中的汉阳造一端,哗啦一下顶上火。三德子说,咋呼啥,老子也有枪。说着从腰里掏出独撅龙,在手里掂着。小顺刚想说给我,谁承想,嗵的一声,独撅龙走火了,疤瘌眼扑通倒在地上。小顺一激灵,三德子吓傻了,拿枪的手僵在半空,浑身直抖。矿警们齐声喊,打死人了,开枪啊!啪啪几声枪响,三德子一头栽在地上。小顺吓得抱着脑袋蹲下,觉得裤裆湿乎乎的。其他人吓得都爬在地上。大门一开,出来一群人,哨长挥着手说,别开枪!别开枪!总办大人来了。矿警们分成两排站立,一个穿长袍马褂的人从门里走出来,问刚才是谁开的枪?哨长上前一步看看倒在地上的三德子,又看看疤瘌眼说,禀报总办大人!是匪类冲击矿上大门,疤瘌眼英勇抗击,将匪类击毙,他本人不幸中弹身亡。总办又问,其他人是干什么的?哨长说,其余人是乔家庄的良民,是来看热闹的,与此无关。远处跑来一个人,老远就喊着什么听不清。到了近前,哨长认出是乔家庄的总甲,就说,乔头,你看你办的什么事,不把村民看管好,来矿上闹事,总办大人生气了。乔总甲点头哈腰地说,总办大人息怒,小的这就把属下赶回去,回头冲着村民喊,还不快走,还等着吃席呀!踢一脚小顺说,你照你爸脾气各路!这事你也掺和。小顺站起来,脸吓得惨白。总办大人看着小顺说,娃子,你叫啥?小顺刚要张口,哨长接过话头,他叫程福顺,是矿上老程头的儿子,是个良民。小顺看一眼总办大人,认出是几年前,骑个毛驴在地里绕世界跑的那人,只是更瘦了,高颧骨支着,两只大眼倒是挺有神。总办大人说,你还小,参与这事干啥?小顺说,我不是来闹事的,是三德子说我要来就让我开一枪。总办大人对小顺的直爽挺喜欢,说枪在哪,我让你开一枪。哨长赶快上前拾起地上的独撅龙,双手递给总办大人,总办大人示意给小顺,哨长又从三德子身上搜出几粒花生米大小的子弹,给小顺枪里装上一颗。小顺接过枪说,我要冲天轮开一枪,总办大人回头看看说,行。小顺两只手捧着枪,闭上左眼瞄准天轮,嗵地开了一枪,子弹不知飞哪去了,再看天轮,依然不停地转动。总办大人冲乔总甲说,别说是土造枪,就是连珠快枪也打不停我的煤矿。回去管好你的属下,再来闹事我就对你不客气了。乔总甲点头像鸡啄米,连声说是!是!是!叫俩人把三德子的尸首抬上走了。小顺也跟着要走,总办大人叫住他说,娃子,你愿意到我这里做工吗?小顺看一眼哨长,哨长说,他愿意,平时他总跟他爸磨着要来矿上挖煤呢。总办大人说,你要是愿意来,就给我做个跟班吧。原来,总办大人从家乡广东带来个小跟班,前些日子,母亲病故,回家奔丧了,按制要守孝三年。总办大人身边没人伺候,生活很不方便。一眼看到小顺,就喜欢上了,又通过刚才的对话,甚是喜欢他的直爽性格。哨长说,小顺,还不快谢谢总办大人,你这是走道捡到块狗头金。总办大人边往屋走边对哨长说,你到柜上支几两银子,给死者做安葬费。哨长说,请总办大人放心,我这就着人去办。
小顺很快就适应了矿上的生活,穿一身矿警的制服,也学他们的样子,将辫子盘在头上,把帽子支起老高。只是没有配枪,是小顺不要,目睹了打死人的场面,把小顺摸枪的胆子吓没了。有啥事,总办大人都是让小顺去通知哨长,哨长凑趣说,你小子倒成了我的上司了,连洋人见了小顺也点头。
铁路铺的挺顺利,失了地的农民都到矿上来做工了。铁路铺成那天,总办大人要乘车验路,开天辟地头一遭有了铁路,当然要亲自体验了。小顺也跟着去,心里美滋滋的,长这么大连马车坐的都少,赶集都是爸用独轮车推着去,这下要坐火车,可得好好享受享受。火车呼隆呼隆地向前跑,行驶得很平稳,一个时辰就到了运煤码头。以前,用马车运煤,这条路要走一天才能到,煤都堆在矿上,误了装船。以后用火车运煤,跑得快,拉的也多,总办大人眉头舒展开了。
冬去春来,春风像长了小手,拂在人脸上痒酥酥的。这天,总办大人正在井口听领班的禀报井下的生产,小顺急匆匆跑来递上一个折子,总办大人展开看一会说,小顺,快去告诉乔哨长做准备!直隶总督大人要来视察了。小顺答应一声跑了。第二天晌午,又一个折子到了,上面说总督不来了,让总办大人去直隶府领旨。
翌日清晨,总办大人和小顺加上一个矿警做保镖,三人三骑上了路。路上,小顺不时地摸一下背在背上的包袱,里面是总办大人的朝服。跑了一节路小顺说,这次我可以见见总督大人啥模样了吧?总办大人笑了说,做梦吧,眼下还轮不到你,能让你进大门就不错了。中午时分,三人到了直隶府,找个僻静处,总办大人换上朝服,小顺帮着整理好,三人步行来到大门。守门的军士问明情况放总办大人进入,小顺也想跟进去,军士说,随从在门房侯着。
一个太监引路,到了大堂前,太监说,请总办大人稍候,待小的进去通报,一会出来说,请大人觐见。总办大人抖抖衣袖,躬身进入大堂,叩首请安。总督大人说,平身吧。站起身,到右侧入座。总督大人说,原本太后老佛爷要亲自过问的,然身体有恙,传旨我接见你。总办大人诚惶诚恐的心放松了许多,拱手施礼道,大人,不知有何钧旨?总督说,太后听说你修建了铁路,怕跑起火车来震动皇陵,让我了解详情。总办大人说,皇陵浩大,火车渺小,蚍蜉怎能撼大树,何况远离百十里地呢,请禀报太后尽管放心。总督频频点头说,你把详细情况写成折子呈报上来。
回到矿上,总办大人连夜写好奏折,鸡叫头遍就让小顺快马送去,叮嘱说,回来后到修造厂去见我。总办大人想新开一个井眼,得增加机车,去查勘材料准备的如何。
小顺递上折子后,马不停蹄赶到了煤矿南面的修造厂,把缰绳丢给工厂杂役,交了差事,在厂区随意地走着。这里到处是钢铁构件,有的大房子里叮叮当当响,有的大房子里机声隆隆。在一个宽大厂房里,意外地碰到了四德子,四德子穿一身工装,脑后的辫子变粗了,以前晒得黢黑的脸变白了,两手沾满油污,正在忙碌。见到小顺顾不得手上的油,一把拉住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不跟总办大人了?小顺也高兴地说,今天就是跟总办大人来的。问四德子每天都干啥,四德子说,我们正准备再造一台机车呢。小顺说,嗬!你到这里真正是有了用武之地了。四德子打趣说,真是没白跟总办大人跑,说话都会用词了。小顺说,你也长大了,再也不是跟在三德子身后跑的小屁孩了。说到这里,小顺忽然停住了,四德子也低了头。
小顺又说,你们造出新机车后,有时间咱俩坐火车去运煤码头。
四德子擦着手上的油污问,去那干啥?
小顺说,从那里坐轮船去天津卫啊。
四德子眼睛一亮说,对呀,去天津卫逛逛。
(责任编辑/刘泉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