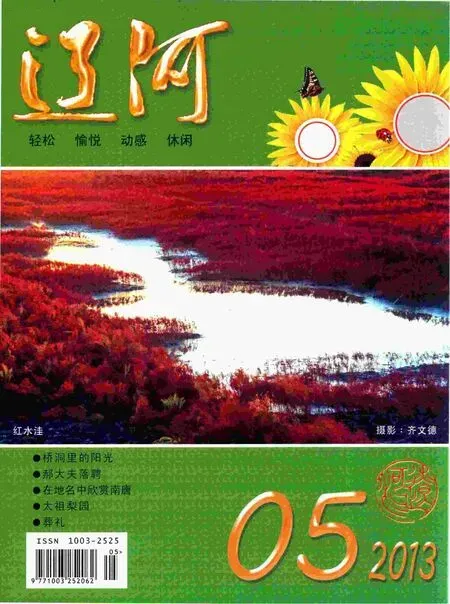文学艺术家的精神双影
余辔扶桑
成为公众人物的作家艺术家,必遭遇社会的品头论足;这是现代文化人的宿命。
可作为人类少数派的文学艺术家与常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是由“现实性主体意识”和“艺术性主体意识”两部分建构起来的。而这“一身双影”之怪,既是人类这“白马群落”的潜素质的必然,又是平庸广众对其疑惑审度的客观必然。
这“两个世界”同在一个生命体中,既融通又相排斥,差距幅度甚大;大致表现有如“通灵的贾宝玉”与“泛痴的贾宝玉”、“疯狂割耳的梵高”与“割耳后自画像的梵高”之别。这样,也就可能常常在他们身上出现一种此消彼长的“二律背反”之势(事)。而客观舆情中,如果只用广众局限的视域来挑剔“现实主体性”显笨拙的文学艺术家们,就必然忽略他们的“艺术性主体”。这也就是常听人们说作家画家是“疯子”“精神病”“怪人”的缘由。且他们又怪癖多多,有时无法让常人(包括亲友)忍受。然而,他们“通灵艺术的非凡”乃至对人类贡献之大之久,也是常人遥不可及的。
于是乎,世间留传下种种常人不解的文人“怪事”——屈原为什么投汨罗江?海子为什么卧轨?普希金为什么为轻浮的冈察洛娃决斗?司马迁为什么顶着风头替李陵直言?顾城为什么杀妻自尽?周作人海德格尔为什么附逆?郑板桥为什么说“难得糊涂”?高更为什么不惜在原始群落中染一身性病而作画?莫言小说的内涵为什么与其现实身份言行有差距?这些在常人眼里都有些神兮兮的不可思议。而这些,我们皆须在他们的“现实”与“艺术”的双维精神里剖析之,才有可能接近某些“真实”。
当然,这也就提示我们对“异常又理解不爽”之事之人,不要先以自己的习惯之眼排斥之,甚至党同伐异。多元世界与邃密人事是在被人类发现与理解中才更精彩的。而鸷求统一求单色求恒定,将导引人类退化。我记得周国平先生形容“超人”时有句话——“即使面对恶人也像欣赏荒野的风景一样”。这话听似乖谬,却常常引我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