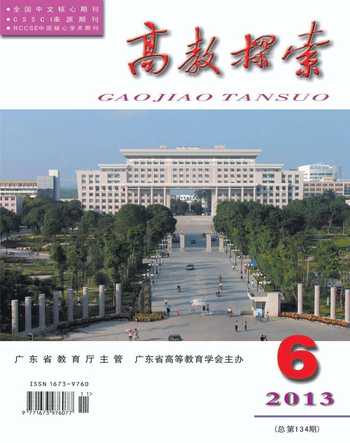大学知识生产“动力源”解读
朱冰莹 董维春
摘要:基于伯顿·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构建大学知识生产“动力源”理论模型。政府、产业界两大外部主体,及大学的学术群体构成现代大学知识生产动力源。对美国研究型大学演进的分析得出:科研的崛起,是学术主体、政府和产业界力量逐步渗透、共同作用的结果。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有效衔接,是整合三方力量,推动其科研崛起的制度基础。促进政府、产业界及学术主体建构协同创新机制,也是中国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动力源;科研崛起
一、 研究背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世界中心”地位
美国高等教育学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认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边缘与中心”的格局。几种对世界顶尖大学的排名都表明,主要的研究导向的大学集中于极少数国家[1]。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自2003年以来发布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近9年的数据表明,美国大学在世界大学Top100排名中所占的比例均超过半数。进一步分析得出,排名越靠前,美国大学所占比例越高。前50名中,美国大学所占比例在70%左右;前20名中,除2003年为75%以外,2004-2011年所占比例均高达85%;前10名中,美国大学一直稳占8席(如表1所示),只有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可以跻身其中。其他排名系统,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中,美国大学均遥遥领先。
在“边缘与中心”的格局中,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群在世界高等教育中的绝对领先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在众多促使美国大学获得成功的因素中,科学研究的卓越,无疑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本文将以美国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的崛起为脉络,对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的“动力源”加以解析。
二、分析框架:知识生产的动力模型
从哲学理论上讲,知识生产亦可分为个体知识生产和社会知识生产,知识生产是个体知识生产与社会知识生产相互作用的产物。个体知识生产遵循合理性(rationality)原则,即知识有其内部的逻辑标准(“真理标准”),个体知识生产以这一标准为前提。社会知识生产遵循合法性(legitimization)原则,即在好奇心驱动下的个体知识在符合客观事物的逻辑必然性标准的基础上,还需经过一个知识的社会评价与选择过程,以符合人类需求和社会需要。[2]个体知识生产是知识生产的源泉,社会知识生产则是对多样化的个体知识整合的结果。
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基于政府、市场以及大学对高等教育影响不断增强的趋势,将国家权力、市场力量和学术寡头作为通过其相互作用,决定协调高等教育系统的三种势力,并把这些势力合为一个图形,称作协调三角形。[3]基于这一视角,笔者认为,大学知识生产的动力亦可界定为由政府、产业界和学术主体构成的“协调三角形”(如图1所示)。
图1大学知识生产动力模型
学术主体(以教授、学生等为主的学术群体)作为大学知识生产的内在动力,所从事的知识探究活动是促进知识存量增加的根本力量。同时,随着大学的知识生产对科研条件和外部资金要求的不断提升,以及社会各领域对知识依赖程度的不断增强,大学知识生产不再仅仅是好奇心驱动下的个体自由探索活动,也是回应社会需要,承担相应职能分工的必然结果。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轨迹,充分验证了不同历史时期内,三方力量对大学知识生产的推动作用,而其最终形成的合力,成为促使科学研究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以及美国研究型大学“世界中心地位”形成的内在机理。
三、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缘起:学术主体的主导作用
在20世纪初至二战以前,研究型大学在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上所做的努力,被一些学者所忽略。有研究认为:“二战是基础研究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发展的起源。”[4]事实上,在二战以前,科学研究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已趋于成熟。在德国大学理念的深刻影响下,19世纪末,众多美国学者赴德留学,他们成为日后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奠基人和学术界的巨人,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巴纳德(Frederick Barnard)、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亚当斯(Charles Adams)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丹尼尔·吉尔曼(Daniel.C.Gilman) 等。学术主体成为这一时期推动大学知识生产发展的主导力量。
(一)吉尔曼“学术研究中心地位”理念:学术主体主导知识生产的思想渊源
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建,它的创立,使授予博士学位和开展研究生教育成为一所学院提升为大学的标志。学者们第一次能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把教学和研究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由学院时代进入大学时代。首任校长丹尼尔·吉尔曼在就职演说中宣称,“学术研究将是这所大学教师和学术的前进指南和激励器,知识的获取、保存、提炼和整理将是这所大学的主要目标”[5],从而为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职能的崛起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研究生院的创办和博士学位的设立:学术主体主导知识生产的组织建制
基于对研究的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成为大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之初,吉尔曼便在学习德国大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同时,“结合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和社会现实需求,设立专门的研究生院和博士学位,开始了研究生的大规模制度化培养”[6]。据统计,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成立时,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总数为389人;到1900年,研究生数量升至5831人。[7]这为研究型大学规模化地知识生产提供了制度基础和人才保障。
(三)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学术主体主导知识生产的路径选择
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机制也成为知识生产发展的有效路径。“在大学,教学是关键的,研究则是重要的。”[8]“教学”和“研究”是互为补充的,“学术研究可以造就更好的教师,教学可以造就更好的研究者”[9]。习明纳(Seminar)、研讨班、研究所等培养模式在研究生院的组织建制内,在规模化的研究生培养层次上得以实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认为:正是吉尔曼创造了自那以后在美国被广泛采用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模式,才使得科研,特别是基础研究成为美国大学的一个突出和首要的特征[10],为研究型大学规模化地知识生产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
(四)科学选聘标准与客座讲授制:学术主体主导知识生产的人才保障
高水平大学及科学研究的崛起,必须将大学有限的资金用在“人”上。[11]因而聘任科研型教师成为以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又一重要举措,吉尔曼在聘任一流教师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可能不太懂得培养青年人的技巧,但是在科研领域却有广阔的发展前景”[12]。霍普金斯大学办学之初便组建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正是优秀的研究型教师群体的声望和他们在研究生教育上的巨大投入,才使得霍普金斯大学成为研究型大学的象征。”[13]吉尔曼采取的最为重要的策略还在于引入客座讲授制。许多外校的教授和学者接受邀请来霍普金斯大学的讲堂举办了很多讲座。众多学生被邀请到讲座中来,一些公共讲座也吸引了部分校外公众的参与。[14]通过这些著名教授学者的学术声望,不仅可提高学生们的学术能力,还能从整体上提升大学的影响力,为研究型大学从事高水平科学研究提供了人才基础。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影响下,美国大学通过两条路径,逐步走上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道路。一是传统学院的改造。如,哈佛大学于1870年开始彻底改造旧学院,通过引进选修制,发展研究生院;耶鲁大学也提倡增设专门学院和研究生院,在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过程中,实现了成功转型。二是新大学的创办。克拉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霍普金斯大学的直接影响下创立。芝加哥大学在建立30年之后便成为美国一流大学中的领袖(被认为接过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接力棒,作为美国大学成熟的体现[15])。建校于1868年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20世纪30年代以杰出和均衡的学科建设跻身于美国研究型大学之列。斯坦福大学、康乃尔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也在某种意义上一步到位地达到高起点,很快进入世界最高水平大学的行列。[16]
20世纪初,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扩张,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显现出从总体上抑制本科教学和服务功能的增长,把资源集中在研究生院的扩大和基础研究上的趋向,从而形成了以高级学习和研究为优先的制度。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种更为根本的分化”,它以大学是否能在高一级水平上探索知识为界限。[17]可以说,美国早期研究型大学的群体性崛起,一方面,学术主体以提升大学知识生产能力为目标,是对大学组织结构调整和改进的不断尝试;另一方面,学术主体的知识生产能力伴随大学知识生产组织框架的不断发展而持续提升,从而成为大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内驱力。
四、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全盛:政府力量的强制输入
以二战为界,美国研究型大学迎来了其重大转折。二战以前,大学科学研究虽已趋于成熟,但几乎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任何资助,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以1862年《莫里尔法》(Morrill Act)颁布为标志,联邦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资助大学传授和研究与农业、机械技术相关的分支学科,奠定了联邦政府科技政策的实用主义倾向。当然,这种政策导向在世俗经济事务中对知识和技术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却使得联邦政府远离了基础研究。[18]然而二战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二战期间大学科研为战争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美国研究型大学一跃成为国家科研体系的核心,也验证了政府是大学知识生产(特别是基础性知识生产)的最重要的支撑力量。
(一)管理制度完善:政府推动知识生产的架构
1940年6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提交的“建立推动科学发展的联邦机构”的建议,由此,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The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NDRC)正式建立,组成了由布什任主席的八人委员会,以及由非军方委员会成员负责的五个研究部门。以充分利用非军事科学家的研究力量为目标,大学、研究所、工业试验室等的研究伙伴关系在政府的推动下形成。[19]从1940年6月至12月,国防研究委员会批准126个研究项目,分别与32所大学和19个工业试验室签订了科研合同。[20]在此基础上,1941年,其附属机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Th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SRD)成立,它由国会直接拨款,拥有从武器开发到武器生产的特权。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国防研究委员会,特别是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为美国军事研究和发展提供了18个月的准备(1940年6月至1941年12月),为政府推动大学知识生产提供了完整的组织管理体系。
(二)政策体系建构:政府推动知识生产的措施
战后,美国政府更意识到借助大学的科研力量改善军事系统的研究与开发基础的重要性,开始更多地关注研究型大学及其科学研究。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向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具有时代意义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疆界》(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为战后美国科学发展树立了目标、指明了方向。报告指出:如果给基础研究以重要的支持,美国的社会繁荣、人民健康、国家安全便会成为可能。[21]这份报告特别提出,联邦政府要给大学提供资金,以便它们不断地产生新知识,培养出大量的科学、工程人才。
战后的国际格局也进一步强化了联邦政府对大学知识生产的推动力度。随着“冷战”时代的到来,在科技领域,“美苏争霸”集中体现在争夺空间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从而向世界宣告:从1920年起居世界科学中心“宝座”之上的美国,其空间科学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受到严峻地挑战。美国政界、军界乃至科技界将其称之为科技领域的“珍珠港事件”。在这一激烈的国际争霸中,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发展被联邦政府置于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从而直接促使1958年《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ce Education Act of 1958)的诞生。该法案将提高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作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最终落脚点,加快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步伐,以确保美国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1960年《西伯格报告》(The Seaborg Report)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责任和投入力度。该报告指出:科学研究作为一项重大投资,应不断增加。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是美国科学发展的关键与核心,加强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是联邦政府的重要责任。
(三)资助力度提升:政府推动知识生产的路径
伴随组织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政策法规体系的逐步落实,众多的国家实验室“落户”到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战时的大量的科研项目落实到研究型大学内。雷达研制、原子弹研究、固体燃料火箭研究、无线电引信雷达研制等四大科研项目主要依靠研究型大学研发。其中,雷达研制和原子弹研制(通称“曼哈顿工程”)作为“大科学时代”的地标性事件,使一批大型政府科学实验室在各大学纷纷建立起来,动员了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其中。战后,随着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国防战略地位的确立,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的资助力度又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强化过程。1958至1968年的10年间,也就是通常所称的研究型大学的“黄金时期”,大学研究的多项指标均达到了历史上的“峰值”:1964年,大学基础研究经费占大学经费总额的79%,联邦资助的大学研究经费占研究总经费的74%;1968年,大学研究总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达到历史之最(1986年才被超越)。[22]
布什报告所形成的“布什时代”和《国防教育法》所形成的“国防教育时代”,作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转折点,在证明了研究型大学所具备的科研强力的同时,见证了联邦政府的战略性调整所创造的奇迹。这说明,政府力量在大学知识生产,特别是基础性知识生产中发挥了支撑作用。
五、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调整:产业力量的渗透
产业界对知识生产的渗透主要是使知识生产的成果不仅用以证实理论、获取知识及服务于国家需要,且应用于开发能投入生产并获取利润的产品。基于研究型大学所处的制度环境的进一步变迁,产业界渗透大学知识生产的格局最终形成。
(一)共同的诉求:产业界渗透知识生产的现实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所处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变迁。一方面,随着冷战结束,军事研究的地位逐步下降,以及80年代美国的经济衰退,联邦政府财政紧缩,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主要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高等教育政策进一步变迁,国家对研究型大学的拨款开始大幅度地减少。与此同时,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生产的规模、范围却不断地拓展,对经费的要求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在经济环境上,美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优势正面临严峻的挑战。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迫使许多国内企业进行重组、收购和兼并,企业内部研发经费开支预算不断缩减。历来美国产业界应对外国竞争的主要策略,即是通过开发新技术减低成本,但这对研发经费有着极高的要求。因此,如何寻找合适的研发机构替代企业内部研发成为产业界亟待解决的难题。
“以知识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到来,则为产业界渗透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提供了可能;而产业界和研究型大学各自面临的困境,为产业界渗透大学知识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联邦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出台的一系列知识产权法,最终促使产业界与大学合作,知识生产格局开始形成。
(二)政策的建构:产业界渗透知识生产的催化剂
197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启动了“企业和大学合作研究中心计划”。这种合作研究中心,以企业的要求为基础开展课题研究,每一项目由基金会赞助5万美元,企业界赞助不少于30万美元。根据法律,国家科学基金会不能为营利性组织提供研究资助,但可以资助校企合作中的学校部分。这一试行计划促进了其对大学两类研究组织(工程研究中心和科技研究中心)的长达11年的资助。到1995年,全美共成立了49个这样的合作研究中心,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复合物加工研究中心,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集成感受器研究中心,伦塞勒工学院的计算机制图研究中心,罗得岛大学的机器人研究中心等。[23]
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为鼓励高校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颁布了著名的拜杜法案(Bayh Dole Act,1980),成为企业与大学合作的重要法律保证。该法案规定,高校使用联邦政府科研经费所产生的科研成果,其专利属于大学。大学有权将新技术转让给公司、企业,所得收入由大学支配,不再缴纳联邦政府。[24]这有效地调动了大学研究高新技术的积极性,改善了政府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促进了私人企业就研究成果分享问题与大学积极合作,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应。1994年,卡内基梅隆大学做了一个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工业企业联系方式的调查。研究发现,美国大学与工业的联系广泛,在1990年,美国共有1,056个大学—工业合作建立的研究中心,总费用41.2亿美元,其中29亿美元直接用于研究和开发。
综上可见,政府、产业界和学术主体在发挥各自对大学知识生产的推动力的同时,也相互作用,形成了大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场。政府和产业界作为两大外部动力,对大学知识生产推动经历了从资源供给到资源供给与制度供给相结合的历程;大学则在回应这种发展趋势的同时,不断完善知识生产组织结构,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学术机制共同融入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形成大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场。
六、相关启示:协同创新机制的建构
英国高等教育学家阿什比指出,“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25]。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不但得益于其自身的“遗传基因”一开始建立在强调“学术研究”这一高深学术水平的基础上,而且也得益于美国社会科技发展这一“制度环境”,从而形成了各主体共同推动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的格局,使其最终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这对于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而言,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从基础研究到基础与应用相结合的轨迹
科学研究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经历了从基础研究到基础与应用相结合的轨迹。以德国大学模式为样本形成的美国早期研究型大学,建立了以高级学习和基础研究为优先的制度。二战中,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又在国防军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奠定了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在科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迁,在大学与社会的链接中,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逐步形成了基础与应用相结合的模式,但美国研究型大学以基础研究为核心的根本特征没有改变。有关资料表明:美国大学基础研究占大学科研总量的75.1%[26]。而中国大学恰恰没有经历过基础研究的长期体制化进程,一开始便以应用研究为主要内容。因而,如何进一步提升基础研究的比例,是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环节之一。
(二)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衔接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在制度环境层面上,体现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有效衔接。社会结构犹如一个桶,能够决定社会实践所能达到的容量。这一哲理已被近代科学的成长所证明。不同的社会结构对科学技术的容量是不同的,到了容量的极限之际,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被束缚。[27]同样,一国大学所能达到的高度也将取决于该国社会所具有的对学术教育的容量。在开放的社会结构以及高度分权的宏观管理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美国研究型大学,能够保证学术主体在推动大学发展、科学进步中能动性地充分发挥。对于中国大学而言,特别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政府以正式制度的形式保证了大学的科研基础和条件,但要发挥学术主体在原创性、基础性知识生产中的能动性,社会结构的变迁、高教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样十分重要。
(三)政府、市场、学术力量的协同
综上所述,科研职能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体现出政府、市场以及学术力量在推动大学知识生产中作用的整合。作为基础研究的天然场所,研究型大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学习、自由探究的家园;同样,学术主体也是产生原创性、基础性研究成果的最直接力量。随着制度环境的变迁,研究型大学必然需要与产业界加强合作,在推动大学与社会链接的过程中,稳固基础性知识生产的基础和条件。在产学的合作中,政府以各类政策、法规的出台,营造有效合作的制度环境,也是促使各方力量协同的基础和核心。可见,无论研究型大学所处的制度环境如何变迁,建构起政府、产业界及学术主体协同创新的发展格局,是美国研究型大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也是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必然路径之一。
参考文献:
[1] 菲利普·G·阿特巴赫. 高等教育变革的国际趋势[M]. 蒋凯主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0.
[2] 茹宁.国家与大学关系的哲学分析[D].天津: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19-20.
[3] Clark,B.R. Academic Culture,Yale University,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Group,Working Paper,1983.42.
[4] 梁彤,李驹.美国研究型大学及其基础研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2):69-70.
[5] 沈红.美国研究型大学形成与发展[M].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32.
[6] Deighton L. The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Vol 4)[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The Free Press,C1971. 185.
[7] Rudy S. 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1865-1900[J].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XXI(1951):169.
[8] [10] Flexner,Abrabam. Daniel Coit Gilman: Creator of the American Type of University [M]. Harcount,1946. 63,101.
[9] Hugh Hawkins.Pioneer: A History of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874-1889[M]. 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60. 63-65.
[11] Richard Hofstadter & Wilson Smith.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Vol.Ⅱ)[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649.
[12] [13] Bishop C. Teaching at the Johns Hopkins: The First Generation [J].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1987,27(4):503,511.
[14] Francesco C. Daniel Coit Gilman and the Protean Ph.D.:The Shaping of American Graduate Education[M]. Leiden: E. J. Brill,1960.102.
[15] William Clyde Devane,Higher Educa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42.
[16] 贾永堂,徐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群体性崛起的机制分析——基于社会进化论的视角.[J] 高等教育研究,2012(5):81.
[17] [18] Roger. L. Geiger. To Advancement Knowledge: The Growth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1900-1940[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86.
[19] Roger. L. Geiger. Research and Relevant Knowledg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Since World WarⅡ[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 Y1993.3.
[20] Daniel. J. Kevles. The Physics: Th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Modern America. Alfred A. Knopf Inc. N Y. 1978.198.
[21] Vannevar Bush.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The Endless Frontier. Unite States Government Pringting Office,Washington D. C. July 1945.7.
[22] Roger. L. Geiger. What happened after Sputnik? Shapi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 the Unite States,Minerva 35,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rinced in the Netherlands,1997.356.
[23] 朱斌. 当代美国科技[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60.
[24] [美] R·阿特肯森,W·傅兰皮得. 科学研究与美国研究型大学[J]. 余慧萍编译. 复旦教育论坛,2009(3):10.
[25] [英] E·阿什比.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7.
[26] 文部科学省·科学技術要覧·2008.28,230,231. 转引自:胡建华.大学科学研究与创新型人才培养[J].现代大学教育,2009(4):3.
[27] 刘青峰.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59.
(责任编辑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