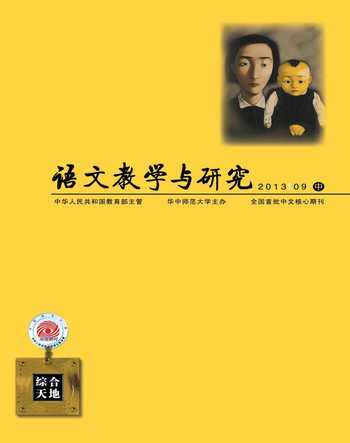“乌集”色彩之辨
郭岩岩 牛晓雷
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史记选读》选有《淮阴侯列传》。文章叙述韩信临死悔恨自己不用蒯通自谋天下之计,刘邦因此诏捕了蒯通,要将其烹杀。蒯通辩解:
“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
刘邦闻言,赦免了蒯通之罪。蒯通不愧齐之辩士,死罪在身,振振有词,居然能死里逃生。学生感慨之余,提出疑惑。蒯通辩驳中,用了“异姓并起,英俊乌集”一句。既称逐秦天下者为英俊,为何又将其形容为“乌集”?英雄豪杰如乌鸦集散,这让人觉得不大舒服。因为人们观念中,乌鸦乃不祥之物,总与“凶”、“恶”、“灾”、“险”一类概念相联系。民间也有俗语“乌鸦叫,灾要到”“乌鸦嘴,事事毁”等等。感情色彩是否恰当?
笔者考证以为,乌鸦于上古时期是一个中性词。
《诗经·北风》中有“莫赤匪狐,莫黑匪乌”一句,译为:红的都是狐狸,黑的都是乌鸦。有些《诗经》出版物将狐狸和乌鸦当成不祥之物,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认为“红的都是狐狸”含贬义,就难说通。《诗经》系周代民歌,周王朝是崇尚红色的,说狐狸是红色的,怎么会是贬义?屈原《九章·涉江》有“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译为狐狸将死时,头必朝向出生的山丘,喻不忘本,暮年思念故乡。《礼记·檀弓上》(战国·楚)有“狐死正丘首,仁也”。这里的狐分明都是褒义。同样,“莫黑匪乌”中的黑也不能理解为含贬义色彩。比如,秦就是崇尚黑色的。秦距周不远,应该说“莫赤匪狐,莫黑匪乌”一句,狐与乌都该是中性词。另外,战国宋康王舍人韩凭妻美,王欲夺之。其妻作歌明志,“乌鹊双飞,不乐凤凰”,①将凤凰比作周天子,自比乌鹊,色彩也是中性。
乌鸟被用作褒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中时时出现。
如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其中以乌鹊喻贤才。又如,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被废,侍妾夜间闻乌啼声,扣齋阁曰:“明日应有赦。”于是作曲《乌夜啼》。又如《乐府诗集》引李勉《琴说》,三国魏何晏在狱中,有二乌止于舍上,晏女曰:乌有喜声,父必免。于是作曲《乌夜啼》。这里都是褒义,把乌鸟看成吉祥之鸟的。高中语文苏教版选修四选了晋李密的《陈情表》,其中有“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进节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这里,将乌鸟视为孝鸟。
古代含有乌字词素的连绵词不少,如符定一编著的《联绵字典》就收入十三个,其中九个与乌鸟有关。它们基本是中性词,个别也有贬义色彩。如乌合,《联绵字典》释义:
谓如乌鸟之群合也。《后汉书·公孙述传》中“驱乌合之众”。又《刘玄传》中“汉起驱乌合之众”。又《耿弇传》中“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又《邳彤传》中 “驱乌合之众”。
这里的乌鸟群合,明显带有贬义色彩。
现当代,乌鸦一词应用,色彩各异。民间也有谚语:“山老鸹,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白脖子老鸹——胆大。”还有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乌鸦喝水》,赞扬了乌鸦的聪明,并将故事背景安排在乌鸦带小乌鸦去姥姥家探亲路上,添加了孝的成分。还有的报刊版块设置“乌鸦嘴”意在广为“纳谏”等等。
由此看出,无论古今,乌鸟或曰乌鸦一词的色彩以中性为主,其具体运用因其语境而有褒有贬。
太史公的“异姓并起,英俊乌集”显然不是贬义,据其语境,更有别样一种韵味:一是极言天下英俊如乌鸦之多之广,二是极言英俊如乌鸦忽聚忽散。出自蒯通之口,是非常能够替自己辩护的。试想,自陈胜吴广起义,天下英雄并起,逐鹿中原,到项羽兵败自杀,八年间,象刘邦一样想要面南称帝者不是真的像天下乌鸦一样忽聚忽散,忽生忽灭吗?既如此,他蒯通劝韩信自立而取天下还能算什么谋反呢?“乌集”一词,《史记》其他处也有使用。《鲁仲连邹阳列传》有“故秦信左右而杀,周用乌集而王”一句,译为秦始皇宠信左右而招来荆轲行刺之险,周武王如招呼天下乌鸦一般,邀集四方诸侯的力量灭商兴周。邹阳的“周用乌集而王”更能形象地反衬出“秦信左右而杀”的弊端。
郭岩岩,牛晓雷,教师,现居山东临清。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的其它文章
- 语文铺砌的心灵之路
- 课堂教学模式:合理的阶段性产物
- 致诗友
- 班级管理工作中的严与爱
- 浅谈新生的班级管理策略
- 我的语文教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