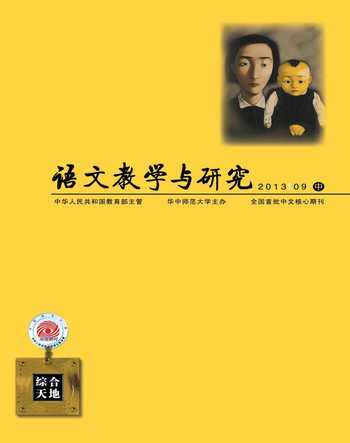一根刺
陈然,原名陈论水。江西湖口人。1986年毕业于都昌师范,1991年又毕业于九江教育学院中文系。曾任教于江西湖口马影中学。1998年起任杂志编辑,现供职于江西省文联。1991年开始发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集《幸福的轮子》,长篇小说《2003年的日常生活》等,发表中短篇小说200万字。作品选入多种选本。
吃午饭时,他不小心把一根鱼刺弄丢了。
这条鄱阳湖里的鱼,俗称翘嘴白。这种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就是刺多了一些。报纸和电视里都说,吃鱼益智,他心想,幸亏自己小时候吃了不少的鱼,才不至于显得太笨,不然,在这样的时代面前,人就要更加自卑了。鱼吃多了,就发现,鱼刺和鱼的味道之间似乎有某种隐秘的联系。比如刺多或刺少的鱼,味道都比较好。而刺不多不少的鱼,味道也平庸。头大或头小的鱼,味道也比身材过于匀称的鱼好吃。按照吃什么补什么的理论,有一种大头鱼在这个城市里很流行,莫非许多人都怀疑自己智力不够?看到别人在抢着买大头鱼,他不由得暗暗发笑。这翘嘴白就属于脑袋小的一类,只是刺还多,而且嘴阔,鳍长,面相凶猛,有点像海鱼。湖里的鱼长得像海里的鱼,就是异类。没想到,鱼里面也有异类。这湖里还有一种鱼,样子跟翘嘴白类似,但皮肤华丽,更像海鱼,名气很大。他老家就盛产这种鱼。据说有一年,国家领导人路过小城,特意点了一尾该鱼,它也算是受到了召见。那天下午,他下班路过菜市场,看到门口有卖鱼的渔民,竟然惊喜地发现了翘嘴白,一下子动了思乡之情,就买了两条。
老婆把鱼烧好端上桌。他胃口大开。他跟她讲小时候吃鱼的事情。那时,他差点因为钓鱼没去读书,是祖父操一根瘦竹棍把他赶到学校去的。祖父是一个捕鱼也是吃鱼的好手。他吃过了的鱼,鱼刺被摆放在桌上,完整生动,只是被抽象了一下。一般的小鱼,祖父是从不吐刺的。祖父上半年去世了,他会经常想起祖父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尤其在吃鱼时,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也在摆鱼刺了,也在试着把整条小鱼连刺吞下去。但这翘嘴白的刺,是既无法摆成鱼形,也无法吞下去的。它们绵软,细密,绣花针似的。好像翘嘴白那如锦似缎的身子,就是它们一针针绣出来的。他只好把它们一根根地放到小碟子里去。真委屈它们了。有一根刺,轻若游丝,仿佛被风一吹,掉在桌子上。老婆正说着什么,转移了他的注意力,等他回过头想把那根鱼刺捡起来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他说,咦,明明在这里,怎么不见了?
老婆问,什么东西?
他说,一根刺。
他侧着脑袋,朝桌面打量。桌子很结实,很沉。当初买的时候,专卖店宣传的是实木材料。看上去那么结实,也像。他们便买了这个牌子的全套:餐桌、座椅、沙发、茶几、床和柜,一万多块钱。一把椅子就花了三百多。有一天他们掀开床板放换季节的东西,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后来床板受了潮,一只角竟然卷了起来,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原来也是胶板做的,并不是所吹嘘的原木。这使得他觉得屋子里的甲醛含量一下子高了起来,他赶忙去买了吊兰、仙人球和芦荟之类。有一段时间,他觉得咽喉和胸部也难受起来。的确,装修和家具污染的事情,电视和报纸上时有报道。那完全是看不见的杀手,即使是冬天,他也不敢把窗子全部关上。自从知道了这些家具是“伪劣”产品,他对它们就不愿那么爱惜了,恨不得快点把它们用坏,好重新去买。偏偏这胶板似乎比木料还结实,看来他要达到目的还需等很长一段时间。桌子中间是一块大玻璃,周围镶着金属。一不小心就会有食品残渣掉进去。老婆经常埋怨这个地方没设计好。他抽了根牙签,在那缝隙里掏,并没掏到那根刺,只掏出了半瓣瓜子壳,一点糊状物,还有一根短短的头发丝。他又检查自己的衣服和脚底,站起来把衣服抖了抖,把鞋子脱下来看,还是没找到它。
它到底哪里去了呢?他着急起来,蹲在地上继续寻找。虽然是一根鱼刺,虽然它看起来那么柔软,可万一要扎到身体的什么地方,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小时候,他听母亲讲过,有个人不小心把鱼刺掉进了摇篮里,后来孩子不停地哭,想了种种办法也不能让他停下来,大人急得恨不得狠狠打他几巴掌或把他扔出去。后来才发现是一根鱼刺扎进小孩的肉里了,从此他对小而尖的东西都很小心。还有一次,母亲说,一个小孩在医生给他打针的时候又哭又闹,结果针头断在屁股里,吓得他以后让医生打针时一动不动,成年了亦是如此,而且还把这个故事传给了下一代。
鱼刺跟针当然不一样,但再怎么柔软,也是尖利的。或许,它的柔软会为它的入侵创造更多的机会。针扎了你一下,你马上有反应,也很容易把它找出来,即使它扎进了你的肌肉里。可鱼刺更有隐蔽性,更不知不觉,说不定,它进入了你身体,在里面移动或游荡而你毫不知情。什么时候游进你的致命部位(比如血管或心脏)完全由它说了算。想一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这跟小鸟飞进了机舱是一样的道理。鱼刺卡死人的事情不是没有过。市电视台的都市现场节目就播出过这样的新闻,一个人被鱼刺卡了,送到医院,已经大出血了。等医生开刀把鱼刺取出来,人也跟着断了气。听说有的人吞进了鱼刺,要到几天后才发现。那一般是比较柔韧的刺,像弓一样弯曲着,但也更危险。谁知道它什么时候一跃而起呢?大概是受了电视的影响,有时候老婆不小心被鱼刺卡了,便马上眼泪汪汪地望着他,眼神很复杂,他不禁也慌乱起来,虽然表面强装镇定。所以每次吃鱼时,他都告诫家人不要说话,万一被鱼刺卡了喉咙,便赶紧灌醋,灌醋。今天不知怎么的,还是说话了,结果一走神,鱼刺没卡喉咙,却从饭桌上不翼而飞了。本来,抓住它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比一个病毒木马什么的混进了电脑操作系统要简单,他无意中点了一下什么,鼠标马上失灵了,或屏幕马上漆黑一片。
当然,他的思想也有斗争。人就是这样,每个人体内至少有两个“我”。他们互相监督,暗暗较劲。如果一个人体内只有一个“我”,那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要么刚愎自用,要么死心塌地。现在,他体内的另一个“我”就试图否认那根鱼刺会带来什么伤害,指责这一个“我”杞人忧天发神经。这一个“我”当然不肯服输,他到桌上的碟子里拿了一根鱼刺,往手上一扎,大概也没用多大力,指尖马上渗出了血珠,一缕麻辣的感觉顺着指尖往上爬。这一个“我”就对另一个“我”说,看到了吧,会出血的吧,如果它扎中的是要害部位,那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看到指尖出了血,他才悚然惊醒。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看看,这刺对人是有威胁的。他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不知道是否也可称为血淋淋的事实)。
他在手指上贴了个创可贴。他背着老婆,没让她看到,不然她又要唠叨,问他要不要去打破抗。因为她不唠叨,他就要唠叨。有一次,他不小心弄伤了手指,在为要不要打破抗这件事上纠结了好久。打还是不打,这是个问题。在医院里打还是小诊所打,也是个问题。他怕打针,更怕破伤风。可如果那个破抗疫苗本身就有问题呢?这样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那他岂不是引狼入室?直到第二天,眼看二十四小时快过了,他才冒着被什么击中的危险似的朝楼下的小诊所奔去(医院里程序太复杂,恐怕来不及了)。
地板有反光。他们在房间里装的是复合板,客厅里装的是瓷砖。装好了之后,才知道无论什么样的地板对身体都没有好处。复合板如果质量不过关,甲醛很可能超标(质量过关不过关谁说得清楚,还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如果那个标准本身就有问题呢?就像网上说的,现在国内很多产品的质量标准跟国际上都有很大距离)。就是原木地板,那些胶水和油漆,也仍免不了污染。以前他认为瓷砖是最安全的,但一次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说瓷砖里含有氡,释放出来会被肺部吸附,造成严重后果。他屏住呼吸,侧着脑袋往地板上瞄,寻找那根刺的蛛丝马迹。桌脚、椅脚旁边都寻遍了,又把餐桌和椅子都挪动了一下,依然没找到。
他有些慌了。桌上和地上都没有,那就只有一个答案:它躲进了他的衣服里。它为什么要躲进他衣服里去呢?这太令人气愤了。他把外套脱下来,摊开在沙发上,想仔细翻找,但马上又把衣服提了起来。干嘛放在沙发上呢?沙发是布面沙发,要是鱼刺从衣服上转移到沙发里,那不更麻烦了?沙发是他们经常坐的。有一次,他和老婆还在上面亲热了一番。若再这样时,鱼刺从里面伸出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好在为了便于清洗,老婆在沙发上铺了几条大毛巾。他是个有洁癖的人,每次在外面坐公交之类回来,都要先换上在家里穿的衣服。来了客人,他要暗暗注意客人的衣服是否很脏,等客人走了,便赶紧打扫卫生,并要老婆把沙发上的大毛巾扔进洗衣机去搅拌,自己则耐心地把桌凳椅子全抹一遍。
他仔细检查了一遍沙发。把大毛巾(其实是浴巾)抚平,没发现鱼刺。鱼刺有闪光,有如匕首。沙发虽是乳白色,但鱼刺掉在上面,还是能看得到的。再说他还不相信它有那么狡猾,难道它比人的智商还高吗?难道它不知道,只要他把沙发一拍,那弹性良好的海绵便要把它蹦得晕头转向,乃至无影无踪?且慢,若真的把它弄得无影无踪,那他永远也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了,找不到答案,那它就永远寒光闪闪地躲在某处,威胁他们的生活。所以他必须把它找出来,不能马虎了事。他把外套套在椅背上,这样它就撇开两袖,任他搜身。这时他看着自己的衣服很陌生,仿佛它的确是一个包庇凶手的嫌疑犯。他开始给它搜身了。他认真检查衣服的每一处皱褶。把皱褶拉开,露出里面的隐私(如果它有隐私的话),可它仍然不肯把东西交出来。他不禁狠狠抽了它几巴掌。如果能刑讯逼供,如果它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个人,说不定他早就这么干了。谁不会刑讯逼供呢?如果它是钉子户,他就要用推土机把它推平。如果它要上访,那就把它抓起来或送回原籍,即使跑掉了,跳了立交桥或卧了轨,那也是它自己的事。如果它是个顽固不化的学生,他就狠狠扇它耳光,要它写检讨书保证书,让它跪石子抽自己的耳光。他以前教过书,而且可能教得还挺好,但后来,教书教得好的都不教书了,改了行,跑到机关里去了,其中就包括他。这跟现在大学生毕业了就一窝蜂去考公务员是一样的道理。
可他凭什么断定,鱼刺就一定在这件衣服上面呢?说不定,它早已跳过外套,躲进里面的衣服里去了。那是一件毛衣,地形复杂,有足够的空间让它游弋。对于它来说,毛线衣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像当年的口号,可以大有作为。他也曾经被那个口号撺掇得跃跃欲试。幸运的是,毛衣是红色的,与鱼刺有色彩对比,就像褒义词和贬义词。这使他充满信心。那时候看过一部电影,敌人在追一个孩子,孩子躲进了芦苇丛,敌人气急败坏,下令放火。芦苇熊熊燃烧起来,眼看要吞没那个孩子,但他忽然急中生智,抽出腰间的柴刀,很快割倒一片芦苇,躲过了大火。他猜想那个导演肯定不知道火到底有多厉害,肯定不知道火中心的温度到底有多高。现在他要像敌人找到那个孩子一样找到那根刺——老天,他这不是敌我不分了吗?不分就不分,鱼刺可是个中性词。不用那么危言耸听。他叫老婆帮忙来找。老婆说,不就是一根鱼刺吗,何必这么大惊小怪?他说,你这个人,就是个马大哈,一根刺,难道你还嫌不够吗?它已经够危险了!这不仅关系到我,也关系到你,关系到我们整个家庭。它会给我们整个家庭的命运,带来不可知的影响。说着说着,他很激动,几乎要生气了。老婆只好丢下手里正在织的毛线——又是毛线!他大喊一声,说你先把它拿远点。在他看来,现在什么都可能是那根鱼刺的窝藏者。
老婆忍受了他的神经质,但她也没能找到那根刺。由于着急,她反而显得笨手笨脚。他说,还是我自己来吧。看来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他把毛衣脱了下来。然而刚脱下来,他就后悔了。刚才,鱼刺顶多还是藏在前胸部位,现在,它趁机往下一溜,穿透了屏障,很可能藏到他腰间或者更深一层的地方。他这个人,总之还是太好说话了。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单位,都有点唯唯诺诺或逆来顺受。不,或许他很早的时候就这样了,只是他没意识到,对自己,他老是抱着无所谓或不作为的态度,习惯于听之任之。父亲又在电话里抱怨母亲只顾打牌,其他什么也不管。母亲倒没有抱怨父亲什么,只说自己头痛犯了,腰痛犯了,脚痛也犯了。按道理,他完全可以对母亲说,老是熬夜打牌,血液不能流畅地循环,不腰痛或脚痛才怪。但他只是好性子地劝慰她,吃好,休息好,有空散散步。有一次,他当面说过她打牌的事,结果父亲和母亲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啊,好久没打牌了。现在,他要是说了,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仍然会那么说。在单位上,别人挤兑他,暗中使手脚,他也懒得理。每次走进那栋阴森森的大楼,他总是像个小偷似的一阵小跑。的确,他就是一个小偷。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那天,主任给他一篇稿子,说是某个退下来的领导写的,要他赶快编好。他照办。虽然那稿子谈不上错字连篇,但语句不通的地方比比皆是。刊物出来后,主任叫他赶快拿几十本给那个领导送去,领导看了杂志,说文章后面的作者介绍,把她的级别写低了半级。她说,怎么搞的嘛。他挠挠头皮,说那怎么办呢,领导说,要不,重印一下吧。他回来如实汇报,主任赶快安排了重印。印好后,那个领导到北京去了,她在北京也是有房子的。主任叫他找那个领导在北京的地址。电话是秘书接的,秘书说,你是谁,找领导干什么?他结结巴巴解释了一通,好像在说明自己不是坏人。秘书说,那好,你就寄这个地址吧。他搂了一大堆杂志去邮局。主任说,一定要寄快件啊。他说,按印刷品挂号寄也不会丢的,何必寄快件?主任说,这样就显得我们对这件事很重视嘛。他刚从邮局回来,主任又说,你还要跑一趟。原来,领导的秘书打电话来,说领导刚才传真了一个要寄刊物的名单,望早点寄。那边说。他一看名单,有十几个人,都是该领导以前的老部下或朋友。他只好又跑邮局。挂号,挂号。每天,除了和同事们一起消耗大量的办公资源,重复一些毫无必要的劳动,他想不出,他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像他们这样的单位,消失了,才是社会的进步。看着单位上的同事明争暗斗,他感到好笑。就像在一艘快要沉掉的木船上,船上的人还在打情骂俏或争风吃醋。他冷眼旁观,不想去掺和。可那一次,他跟另一个部门的同事一起出差,对方的话让他大吃一惊。同事说,你其实是个很怯懦的人。而他,居然还以为自己是一块硬骨头并为此沾沾自喜呢。仔细一想,可不是吗?虽然他不掺和,可不也一直在配合着吗?按时上下班,工作一丝不苟(虽然有人在背后捣鬼,挑他的种种毛病)。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也要想妥当。还有烧开水、拖地板、跑邮局。加班也毫无怨言。开会鼓掌。投票按领导的暗示画圈或打钩。他也想过不举手或不投票,但那样,岂不显得他认为这是一件庄重认真的事情?他必须也鼓掌或投票(当然还要投同意票)才显出自己的满不在乎。鼓掌也鼓得没头没脑,热烈无比。他真的是完全配合了。大概正是因为许多人都像他这样完全配合,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才得以继续发生。而且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那么的支持,那么的没有异议,仰脸若渴。
是啊,不能让一些人得逞得那么容易,那么舒舒服服。要给他们一点难度,给他们一点阻力,要成为他们的刺。什么?难道他要做一根刺?不,或许,在一些人眼里,他早已是刺了。一根刺,在鱼的身体之内,人家不觉得是刺,而一旦脱离了鱼体,就成了刺。谁喜欢刺呢?就是他,不也容不下哪怕是一根小小的、绵软的鱼刺吗?难道他现在,是要把自己给找出来?是要把自己给剔除掉?这简直是二律悖反啊。
可是,他成不了鱼刺。他的确是个儒弱的人,他缺乏拒绝的力量(那得要多大的勇气)。比如,对于那些他很讨厌的人,他无数次地设想跟他们狭路相逢时昂首而过,好打击他们的气焰,可实际上,他还是笑容满面地跟他们打招呼,甚至还微微颔首哈腰,过后又对自己生闷气。他唯一可做的,就是把自己紧缩。不跟他们一起开那些无聊的玩笑,不跟他们下馆子觥筹交错,不跟他们沆瀣一气。可这对他们又有什么损害呢?一点损害也没有,说不定,正中他们下怀。
他干脆把衣服全脱了,开了热水,准备去洗个澡。他脱得一丝不挂,站在水莲蓬下。要是永远这样站着就好了,什么也不用管什么也不用担心了。人一脱了衣服,就是世外桃源。
他洗了老半天,老婆都在外面叫他的名字了。老婆的声音好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有几次,老婆想跟他一起洗澡浪漫浪漫,他都拒绝了。如果洗澡时中毒怎么办呢?孩子们都在外地,那可没谁来救他们了。他们洗澡是一个个地洗。如果老婆洗了很长时间还没出来,他也会在外面叫她。哪怕,有一会儿没听到水响,他也会忽然推门进去看看。那样子,有点如临大敌。
他换上老婆递进来的干净衣服,把脱下的衣服都泡进塑料盆里,洒上洗衣粉。现在,那根刺无处可逃了吧。老婆要给他洗,他不肯。老婆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不做声。他要亲自把那根可恶的鱼刺清理掉。他哪是不会洗衣服呢?以前在学校后来在单身宿舍不都是自己洗衣服?而且他还洗得挺有章法。塑料盆挺大,他都可以坐在里面泡澡。他放满水,再小心地把衣服一件件漂净。他用了差不多一吨水,才歇手。他把卫生间的门关上,免得老婆心疼。平时,漂衣服的水,老婆都留在那里冲厕所。把衣服拧干,拿到阳台上用力抖。抖了好几下,才把它们晾起来。
出门上班前,他叮嘱老婆,不要收他的衣服。
然而等他回来,却发现老婆忘记了他的话,把他的衣服也收了。不但收了,还叠好放进了柜子里。他很生气,说你怎么回事,我的话你总不上心?老婆也生气了,说,难道我收衣服也收错了?他说,万一那根刺还在衣服里呢?本来,我想等它们晾干了,再找一找或抖一抖的,你倒好,把它们放进柜子里,现在,谁知道那根刺跑哪里去了?柜子里全是衣服,到哪里去找?
老婆说,你这不是发神经吗,一根鱼刺,犯得着这样吗?
他说,发神经怎么啦,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由神经病们掌控的,你又能怎么样?他在网上看到一本书,外国人写的,书名就叫《病夫治国》。那些伟人元勋,有的脑中风,有的梅毒,有的内分泌失调,有的严重便秘,有的干脆就是神经病。可当时,谁敢说自己国家的元首是神经病呢?谁又能制约这个神经病呢?这比故事传说里那几只老鼠商量着怎么在猫脖子上挂一只铃铛还难。有几次,他坐在公交上,发现司机一会儿自言自语,一会儿又跟乘客东拉西扯,甚至干脆停下来把车门用力拉开又关上。过桥时,他真的很担心司机忽然心血来潮加大油门把车开到滚滚江水里去。
他头痛。这段时间,他老是头痛。他想,自己肯定是得了什么病。为此,他还偷偷到医院去检查了两次。他先是怀疑自己的头部。说不定里面长了个瘤子,那就麻烦了。他上网查资料,上面说呕吐,他就真的想呕吐;上面说发热,他就真的觉得自己发起烧来。不过他宽慰自己,可能是血压或血脂上升的缘故吧。单位统一体检时,医生说他这两项偏高,要他注意饮食,多喝水,少喝酒,少食肥甘之物。接着又怀疑肺部。他一抽烟就咳嗽。别人每天抽一两包烟都不咳嗽,怎么他抽一两枝就会咳嗽呢?他不敢怠慢,还真的去医院拍了片子。还好,医生把捂着自己鼻子的手拿开,说你肺部没问题。有点咽喉炎,可能是当老师时落下的职业病。粉笔灰哪是那么好吃的呢?这次医生叫他少抽烟,少吃辣。最近他又怀疑自己的胃出了问题。起因是毫无征兆的胃出血。读书时他就患过胃病(那时,学生得胃病的很多,更别说大人),后来治好了,怎么现在又出问题了呢?他上网一查,吓了一跳,怀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他买来一台电子秤,严密观察自己的体重变化。他最怕别人说他瘦了。谁要是说他变瘦了,他便十分惊慌,甚至恨上了那个人。他想,他真得找个时间,到医院去把那个不吉的可能排除掉。后来,他去了。医生让他去检查了大便,检查了胃,说没什么大问题,有点胃溃疡。现在,他除了不能抽烟喝酒吃辣大块吃肉,连茶也要少喝了。本来,他是很喜欢喝茶的,每天要喝三大杯。可这也不能那也不能,人活着还有什么意趣?看来,人生到了做减法的年龄了。那鱼刺,不刚好就是一个减号吗?它象征性地跳到他身上,潜藏在某处,准备着随时再给他做几道减法。他不把它找出来是不行的。
半夜,他忽然翻身坐起。他养成了新的睡眠习惯,上床时,要把自己脱个精光。仿佛不这样,等他睡着了,那减号就可趁机发挥作用了。脱光了衣服,那减号就没有了依附,无处藏身。老婆往他怀里钻,他下意识地用胳膊挡住。本来,他是喜欢抱着她睡的。但现在,他似乎怕老婆身上有刺,说不定,它早已狡猾地藏到她身上去了,在那里等着他扑上去呢。当它噗的扎进他的身体,它会冷笑着说,这只能怪你自己啊。老婆往他这边蹭了蹭,他把自己抱得更紧了。老婆问他怎么回事,他不肯说原因。老婆就生气了,把背对着他,他也懒得管了。他们像两个仇人一样睡在一起。
他做了许多噩梦,噩梦里又套着噩梦。他梦见母亲的手臂被雷劈开了,血淋淋的,但他却躲避着,怕雷也击倒他。又梦见自己浑身瘙痒,像小时候得的荨麻疹。开始仅仅是一个小红包,但挠了几下,它马上扩散、增生、叠加。手臂、胸脯、大腿,乃至全身都是了。那时不知道吃什么药,母亲便按着土方子用热饭粒在他身上擦,擦得通红。饭粒很烫,但擦得他很舒坦。可现在热饭粒根本不起作用,反倒越擦越痒,越擦红包越大,越多,像是身体上开了无数的小孔,每个红包里都有一根鱼刺,它们蠢蠢欲动。红包在溃烂、汇合,鱼刺无遮无挡,在他的体内生根,疯长。他看着自己的身体在迅速发酵变化,眼睛瞪得老大,他快要成一只刺猬了。
他和老婆之间,似乎开始了一场冷战。老婆认为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不然,怎么解释他跟她这么刻意保持距离,井水不犯河水呢?她说,什么鱼刺,我看是我们之间有了刺,你不用找借口,有什么话你别憋着,直接说出来好了,我也不一定接受不了。老婆的话不软不硬,倒似乎是在为他着想。他以前真的有过别的女人,也为此跟她闹过。他一边跟她闹离婚一边却世界末日似的跟她疯狂做爱。后来,觉得没意思,又不闹了。如果他真的有了别的女人,不会跟她冷战,恰恰相反,他会对她分外柔情。所以有时候,她会惊诧地望着他,说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是不是……老婆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内心总有一种不安全感。眼神也似乎有一丝卑怯。想到这里,他有些心酸,从后面搂住她。他不管那根刺了,要扎就扎吧,怕什么。他让老婆和他都激动起来。他要把那根刺赶得远远的。他才不在乎它。不就是一根刺吗?他曾笑着说他是一只蜜蜂,老婆则笑他是一只蚊子。她说,你这只蚊子真大。来吧,来。老婆呼吸越来越急促。快到达顶点了。老婆快不认识人了。但突然,他一松弛,从老婆身上滚了下来。
老婆愕然,说,怎么回事?
他翻身爬起,想继续努力,然而使不上劲。
老婆温度在降低,说,别勉强,伤身体。
挣扎了几次,他停了下来,一动不动。
接下来几天,都是如此。他既像色情狂,又像性无能。
后来,不是他不让她靠近,而是她不让他靠近了。他把手伸出去,想绕进老婆颈下,抱住她,她把他的手拉了出来。或者,干脆离得更远一些。
看来,那根刺,还在那里,而且越来越大,像一道山梁,横亘在他们中间。
按他的估计,他们的冷战很可能继续下去,直至酝酿出更严重的后果,比如,离婚。他也还可以更神经兮兮,比如把家里翻个底朝天,或买一只放大镜回来,每天像个甲虫似的趴在那里把地面、沙发、衣服及其他所有东西都放大一遍,以期找出那根鱼刺。他一遍遍想象着这样的情景。事情不往往是这样吗?鱼刺都成了他们生活中的象征性事件了,为了剔除鱼刺,结果还是为鱼刺所伤。想驱除它,它却逆向着越发长驱直入。实际上,现在,不管它是否真的还存在,他也不能彻底清除它了。他越是清除它,它往里钻的越深。记得那时,孩子们每次从寄宿学校回来,几乎都要拿着一本语文老师让他们看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大多一事一议,结尾画龙点睛。据说多读这些文章对作文很有帮助,但他们的生活并未朝着寓言的方向发展。这天,他下班回来,老婆主动打破了僵局,兴奋地说,她找到那根鱼刺了,原来,它在鞋底下,被鞋底严重地窝藏了。那是一双布鞋。真的,他怎么就没想到呢。虽然事发那天,他穿的并不是布鞋,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它窝藏那根鱼刺。
一切似乎都合情合理。看来,喜剧仍然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他当然不知道这根刺其实不是他掉的那一根,但这一点也无损于生活的喜剧性。甚至,它本身就是喜剧性的一部分。
生活又回到了此前的正常轨道中。他每天早晨跑步去买早点。回来,老婆已经煮好了豆浆。吃了早餐,坐公交去上班。中午吃快餐,然后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睡一觉。如果有事情睡不成午觉(应酬啊,聊天啊,准备下午的检查或开会啊),他就忍受一下,回来时在公交上打个盹,也不管司机是否喝醉了酒或真的有神经病了。他有个本事,就是可以坐着睡觉,而且总能及时醒过来。只有极少数时候,他多坐了一两站。吃了晚饭陪老婆出去散步。有时候也去超市买点东西。回来就看看电视,上上网,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然后和老婆分次分批洗澡。他们的夫妻生活(这个词,有点故作正经或道貌岸然啊)也恢复了正常,每星期两到三次,像完成谁下达给他们的任务。有一天,他回来喜滋滋地告诉老婆,他又要加工资了。
老婆也很高兴。毕竟,这个月,开销比上个月大了许多,很多东西都涨了价。但马上,老婆又忧心忡忡起来,说,工资不加还好些,一加,东西涨得更快了。的确,每次不都是这样吗,工资还没加到手,物价就已经闻风而动,涨起来了。晚上,他们躺在床上,商量着怎么给他们那点可怜的存款保值。再买一套房子?现在欠着银行的按揭都要到十多年后才能还清。再说已经有了限购令,他们也不能买房了。虽然限购并未使房价出现想象中的降低,反而使周边区县的房价也涨起来了。买股票?他们不懂。有人说自己炒股赚了很多钱,他都不太相信,他怀疑,那些人肯定是亏了本,想拉别人下水,就像他有个朋友,买了辆电动车,老是出问题,有一次把他掀翻在地差点让汽车压死,但他一直在想办法说服自己那辆车的质量没有问题,而且还到处向别人推荐,说它怎么怎么好。
吃了晚饭,他们又去超市。见很多人在买食用油。有个人推了满满一购物车。别人看到了,也去抢,食用油很快被抢购一空。他们幸运地也抢得了一壶。
(选自《天涯》2012年第2期)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的其它文章
- 语文铺砌的心灵之路
- 课堂教学模式:合理的阶段性产物
- 致诗友
- 班级管理工作中的严与爱
- 浅谈新生的班级管理策略
- 我的语文教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