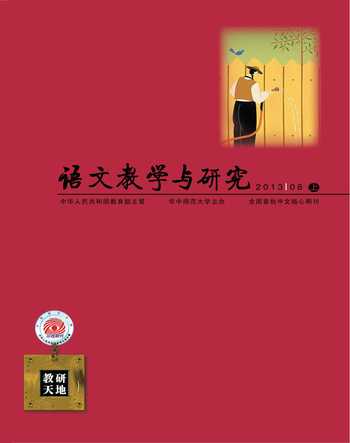对《孔乙己》的别样解读
孙伏园在《关于鲁迅先生》一文中说,《孔乙己》是《呐喊》中鲁迅最喜欢的一篇。自该小说进入教材后,对这篇经典作品的解读可谓百花齐发,但大多是从小说的三要素或众人“哄笑”的角度来解析的,并不能真正走进小说的文化心理层面。因为,“酒”才是作者安放在文章中的一个精神包裹,唯有从“酒”的角度,才能更好地品味出文本内外的诸多滋味。
咸亨酒店,是小说中人物的活动场所,也是鲁迅笔下的一个文化代码。翻看鲁迅的其它小说,其中见到的有“鲁镇”“S城”“故乡”等,这些都是以绍兴为背景的。小说《孔乙己》中以咸亨酒店为中心的环境设置,“呈现出了江南黄酒之乡绍兴的浓郁的饮酒习俗及其城镇的格局,……众所周知,咸亨酒店正是以鲁迅故乡的同名酒店为原型的。正是在这一‘温馨而又凉薄的酒店氛围中定格出越地潦倒沦落的读书人孔乙己穿着长衫却站着喝酒,到最后坐着蒲包用两手撑着前来喝酒的两幅永远的身影……”这种扎根于真实生活经历的创作取向,显示出小说虚构体式外的一种真实性存在。孔乙己的际遇及其周围人物的形态,就有了基于现实生活场景的观照。于是,有了短衣帮的“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的酒俗勾画,有了穿长衫的“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的身份彰显,也有了孔乙己借酒化解人生百味的痴迷与执着。
许慎说:“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从水从酉,酉亦声。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杜康作秫酒。”他从酒字的本源义入手,阐明了酒与人类的主观意识相关联,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和精神价值。对于身处具有“浓郁的饮酒习俗”环境中的孔乙己来说,酒是他与自己、与世界对话的媒介,他的喜怒哀乐都借助“酒”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消隐或显露。
一是以酒释苦。孔乙己的“苦”是多维的,有社会层面的,有个人际遇层面的,有时代层面的,等等。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文化心理层面,孔乙己最大的“苦”其实是一种没有尊严的“合群”。在酒店内,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站着喝酒”本应该与“短衣帮”有共同语言,可是从他两次出场饮酒的状况来看,他与“短衣帮”们的对话只有嘲笑与辩解;而“穿长衫”标示着他应该与“长衫主顾”有共同话题,可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往往只有“拳头”。就连“第三者们”——小伙计与小孩子们,也是不把他纳入自己群体中的。他脚跨两头的双栖身份与现实中两不相容,使得他的这种“合群”特别让人觉得心酸。在酒店外,“鲁迅省略的气魄很大,那些决定孔乙己命运的事件,使得孔乙己之所以成为孔乙己的那些场景,一件也没有写”。关于“皱纹间的伤痕”、“人和书籍纸张笔砚的一齐失踪”及“打折了的腿”等的现场情况都没有正面的直接描写,而是把笔墨集约到孔乙己的饮酒活动上,锐化他“合群”的苦涩感。对于孔乙己而言,排遣这种苦涩的方法,恐怕是唯有杜康了。
二是以酒解酸。寻觅文章的角角落落,始终没有发现任何一位女性的身影,甚至那些他一定曾有过的女性亲友也未曾出现,这在鲁迅的小说中并不多见。文中女性形象的缺失,深刻地表达出一种男性角色的悲凉与孤独。女性的缺失使得文章失去了性别的调和,失去了人性的柔软与文气的舒缓。这种境况与“酒”的特质非常相似,高度提纯的白酒乙醇含量在40多度以上时即能由阴而阳,神奇地燃烧。作品营构的孔乙己的生存环境如同提纯了的黄酒,通过量的累积与温度的提升,由“阴”而“阳”,使得孔乙己的身心始终处于“烧灼”状态,酒中的他留给读者的是蚀烈的深层酸楚。我们没有理由嘲笑他的这种酸楚,相反,在以旁观者或审视者的眼光打量孔乙己时,更应该记住他以男性身份在那个社会里的抗争与没落。
三是以酒掩咸。咸,是泪水的味道。文章未见孔乙己的一滴泪,也未见他人的一滴泪。不是没有伤心处,也许是他“泪泉差不多枯竭了,眼睛闭两闭就表示心头一阵酸,周身经验到哭泣时的一切感觉”。在孔乙己身处的世界里只有笑声,除了孩童们不谙世事的天真笑声外,剩下的就只是挖苦与嘲笑了。泪在哪里?在他的心里,这其中的咸涩味道,孔乙己自己最能读懂。在文章的后半部分,还“欠着酒店十九个钱”的孔乙己,已经被丁举人打折了腿,但还是用手走到酒店,用仅有的“四文大钱”“温一碗酒”。谁又能读懂他坚持喝完也许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碗酒的举动?谁又能读懂喝完酒后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的孔乙己的内心世界?也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以酒掩盖心底咸涩的泪水,或许是其唯一的选择。
四是以酒抗辣。辣不属于味觉范畴,是一种痛感。文中孔乙己挨打之后来到咸亨酒店饮酒,寻求的不是简单的自我麻醉,他精神深处的意愿是用酒的辛辣来抵抗和抚平伤痛。喝过酒的人都知道,对于经历坎坷和身受痛苦的人,酒后不但不会忘却过往,反而会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文中的孔乙己,肉体上有“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与被“打折了腿”的痛楚,精神上有“长衫主顾”的万般凌辱与“短衣帮”的百般挖苦。这样的经历是一种别人无法完全体会得到的痛楚——是尴尬,是惶恐,是自责,是逃遁不得,是挥之不去,万般滋味在心头,以酒之辣方能暂且抵抗这种苦痛。
五是以酒养甜。甜的滋味在孔乙己的生命里并不多见,他需要用酒来养育,把它幻化为愁苦际遇中的心灵安慰剂。1.对读书人衣着的保持。在“短衣帮”群体中,孔乙己是“读过书”的,尽管没有“进学”。但对于“短衣帮”来说,他是一位读书人。这也就给了他以一种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尽管这种美好的感觉总是被他们的挖苦与嘲笑淹没,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他“穿着长衫”来喝酒的举动,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自我欣赏与陶醉,这种看似无意中的刻意,是他内心深处的“甜”。2.对奇特语言风格的坚持。孔乙己的语言是与众不同的,他“总是满口之乎者也”,辩解时也多是使用“窃书不能算偷”与“君子固穷”之类的文言语词,他用这样的语言方式包裹着自己的失落与孤苦,就像裹着糖衣的苦果,苦涩的内核之外毕竟有着标示自己是读书人的甜蜜存在。就是这一点点“甜”,让他在面对尴尬时可以进行自我“包裹”,以求得心理上的自恕。3.对“一笔好字”的依赖。孔乙己“写得一笔好字”,“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一笔好字”是他能够勉强安身立命的仅有的合法生存技能,这能给他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更为深刻的是,他往往在下意识中用它来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在与小伙计谈论“茴香豆的茴字”这一情节中,小伙计的百般不屑之后懒懒地说:“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而孔乙己则是“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孔乙己没有使用语言来摹画“回”字的其它三种写法,而是下意识地准备用写字的方式来交流,除了便于说得更清楚的目的之外,这其中也暗含着他潜意识中对自己有“一笔好字”的认同感。以上这些都是与饮酒相连着的,只有在饮酒时他才能小心翼翼地养护着这仅有的一丝“甜”。
酒中的孔乙己是落寞而又不乏坚持的,这种复杂情态的呈现,则缘于孔乙己身上隐藏着作者的自我观照。因为,鲁迅也是酒中人。在东京神保町,有一间叫“兵六”的居酒屋见证着他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的饮酒生活,其第一代掌柜老“兵六”就是当年与鲁迅常在一起饮酒的朋友,酒屋墙壁上至今还挂有鲁迅的照片。在他从日本回国后的1912年至1936年的日记中,每逢饮酒也是必有记录。有一次鲁迅去看望一位朋友,“饮酒一巨碗而归……夜大饮茗,以饮酒多也,后当谨之”。又一次,“夜失眠,尽酒一瓶”。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记述,1925年端午,他喝了烧酒六杯,葡萄酒五碗,等等。林语堂曾这样艺术化地描述鲁迅:“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于是鲁迅复饮……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由此观之,他对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对自身际遇与创作时期心理状态的隐喻式投射,“有鲁迅自己的为生存的艰难呐喊,为自己的生活辩护”,“折射出越地知识分子落拓寂寞但又永不屈服的精神特征”。正如蓝棣之所说:“通过解剖孔乙己,鲁迅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合法性——人得要生存——这也是鲁迅的基本观念。”我们在研读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时,应该以“酒”为抓手,洞烛幽微,体味人物命运抗争的深层意蕴,审视作者投射在小说主人公孔乙己身上的现实重影。
对于作者,酒是他生活和行文的用具;对于孔乙己,酒就是他的灵魂。唯有通过“酒”才能真正走进孔乙己的内心深处,也才能从字里行间体察出鲁迅先生对孔乙己的那种“在调侃中又隐含着忧郁的同情”。
王小东,语文教研员,现居江苏泰州。责任编校:高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