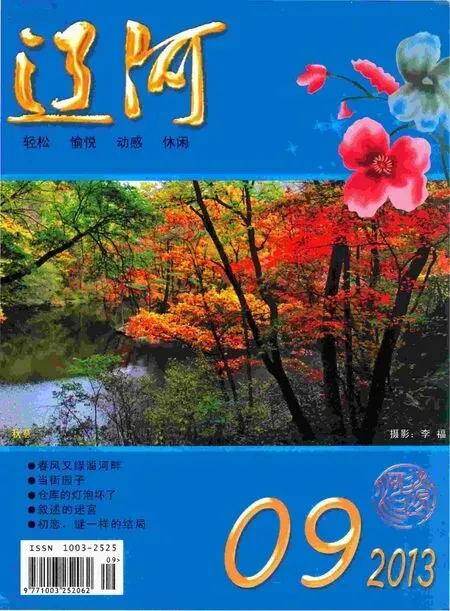当街园子(外一篇)
王颜军
屯儿东,我家有个园子,家人都管它叫当街园子。这么叫,大概是和当院儿那园子相区别吧。
它不大,三分来地。园墙不高,淘小伙儿骑墙头,两脚刚着地。
那儿有不少园子,都不大。它们密密地挨着,像方格本似的。园墙有单独的,也有两三家一个的。
我家和四表舅家就共用一个园墙、一个园门儿、一条水垄沟。园门儿在他家园子那边。进出园子我们都顺他家水垄沟走。没水时,走沟儿,有水时,走台儿。那台儿上通常栽辣椒,一撮儿一撮儿的。秧矮时,我们从它头上迈,高了,我们踩沟沿儿,小心叉腿过,从不伤他家苗。
水垄沟上,有棵雪桃儿。那桃儿先从尖儿红,像漂亮的小姑娘抹着口红使劲向你努嘴儿。每次从树下路过,我都不敢抬头,恐怕忍不住向桃儿伸手。可就像情窦初开的男生路遇漂亮的姑娘,我正视难为情,不看又放不下,最终还是偷看它一眼。
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有一天,我给自己找个理由:人爱采花,不怨人痴,那是因为花艳!谁让他家桃儿诱人呢!于是,见四外没人,我假装摔倒,跌撞在那树上,随着那猛力一撞,“啪、啪”,桃儿纷纷落下。我赶紧捡起,袖着,躲到背角儿,美美一口儿,那才甜呢!
其实,不做“贼”我也能吃到那桃儿。桃儿熟时,四表舅先走村窜户叫卖,傍晚,他准来我家,从卖剩的桃儿中选些好的送给我们。通常,他先把桃儿放在我家外屋锅台上,挑开门帘儿,看看屋里有没有外人,若没外人,他再回身把桃儿拿进来放在柜盖上。那年月,给谁送俩桃儿,就算是很厚重的情谊了。大多选在傍晚,怕被人看出来,还用毛巾遮掩。
新进俩钱儿,四表舅满脸喜悦。坐在我家炕头,和我父亲话语滔滔。我早都困了,可那桃儿香阵阵,我怎么也睡不着。
没有家长的许可,那桃儿我们是不敢动的。那年月,好东西少,孩子多,有啥像样儿的,分配要讲秩序,论长幼。哪像现在,好东西有的是,家家就一两个宝贝。好吃的家长给送到嘴边儿,人家都懒得张口。
桃儿卸完后,我这馋猫儿就可以从容在树下望寻了。在那枝叶掩映间,每每会发现星星般的小桃儿崽儿,偶尔还会发现一两个鲜香欲滴的大家伙。于是,我便奋不顾身地躥上树,美美一番享用,顺势像小猴儿似地在树上一阵戏耍!
浇园子,我印象特深。园外有条渠直通东河,东河连着毛道河,毛道河连着六股河。那时的河水清亮清亮的,日夜在村前“哗哗”流淌。若浇园子,只要在渠和东河交汇处,放几捆柴草,压几块石头,河水就沿着渠汩汩来到园边。父亲在园门儿那儿抠个坑儿,担块板儿,在园墙上掏个洞,放块麻袋片,他双腿叉开站在板儿上,用水桶一舀一舀,那水就沿着垄沟一荡一荡的涌进园子。每每,我都被父亲抓去拨池口子。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当时东北农村最小的童工,没半截锹把儿高。园子外头就是欢快的玩伴儿,半天半天被困在园子里,我跑又不敢跑,在那儿又不情愿,只能恨恨地嘟哝。偏偏,头顶不时飞过自由的蝶呀鸟儿的。有时,水都跑半截垄了,我还没发现。有一次,我正冲欢闹的当街出神,忽听脚下噼哩啪啦!原来,一条大鲶鱼“误入藕花深处”,正急急地找寻出路。我一见,立时来了精神,扔了锹,手忙脚乱地去捉,弄得满身满脸都是泥。父亲见了哈哈笑:“忙啥呀!水渗下去它早晚不是你的!”
母亲一有空儿,就到当街园子忙。那园子东南有一大片水浇地,乡邻们来来往往都从我家园外路过。园外有条道儿,不宽,妇女挎个筐儿领个小孩刚能过。母亲人缘好,谁路过都在那儿站一站,跟母亲打声招呼,唠一会儿,顺手递过来一把豆角,母亲随手送一绺香菜。东西不一定多,但都捡新下来的、自己认为可心的东西给对方。当时,我还小,听不懂她们的对话,但从她们或微笑或哀伤的表情,我知道她们在互相倾诉的同时,已深切地走进了彼此质朴而丰富的内心。她们间的情谊是那样深!本来唠了很久,已经走开了,又意犹未尽地拐回来,半天半天续谈。
经营园子,父亲非常吃苦。他买土豆种都跑二百来里地,有时都走两天两宿。因种儿好,再加上父亲精耕细作,那土豆儿个个硕大,跟小孩儿脑袋差不多。
年年起土豆“出事儿”。往家挑土豆儿,得路过半条街。满怀丰收的喜悦,父亲兴冲冲地挑着担儿!可不知啥时,几个侄儿悄鸟儿跟在后头,互相使一下眼色,一拥而上,又是晃筐儿 ,又是压扁担。父亲连连央求:“别逗,别逗!”可他们哪肯罢休,弄得土豆叽哩咕噜。父亲放下挑儿,操起扁担要追,他们早叽叽嘎嘎逃之夭夭。
秋白菜大了,要用马莲扎起来“镀心儿”。那白菜,个个小胖墩儿似的,齐刷刷站一园子,过往的人都夸:“哎呀!这白菜长得真干净!”
运白菜,是我家大事儿。满地大白菜,父亲一个人运不过来,就得举全家之力,挑的挑,挎的挎,连我都被动员参战。我抱一小棵儿都踉跄!可每每,还能看见父亲欣慰而又鼓励的目光!
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中,少不了那个“编外人士”,小憨儿哥。他是我四表舅的儿子。口吃、语迟,说话“啊”半天,就是词不达意。他30多了,还没寻上媳妇。他想让我父亲保媒,又不好意思直说。三天两头儿到我家来,借口因由半天半天不走。没办法,害得我父亲还得编瞎话:“南沟老纪家有个姑娘,浓眉大眼的,可水灵啦!”那时,小憨儿哥就张着嘴、痴痴地听,有时口水都流出来!看他那心驰神往的样子,父亲故意不往下说。“吧嗒”、“吧嗒”抽烟。把他急得脸通红:“看你,二……二姑父!咋……咋不往下说……说了呢?”于是,满屋人都开心大笑,包括我!
倒不是我父亲逗他,父亲是热心肠儿。他看谁家姑娘小伙儿般配,就惦着给牵线,南北二屯经他撮合成的,不下一个排。为小憨儿哥,父亲没少磨鞋底儿,可给提几个,人家都嫌他家穷,再加上他多少有点拿不起个儿,30多了还没混上人儿。
细究起来,四表舅跟我家没啥血缘关系。他是我姑姥爷的侄儿,姑姥爷没后人,就过继他当儿子。原先,他在那家排行老四,论屯儿中我们管他叫四舅,有了这层关系,就改叫老舅了。我几个姐会来事儿,嘴儿甜,称呼早改过来了,我小,不大懂事儿,有时还顺嘴叫四舅。那时,他老人家可不高兴了:“得管我叫老舅,不许再叫四舅!”
四舅跟我家可向近了。对我母亲,从来都“妹子、妹子”的叫,像称呼亲妹妹似的,可亲了!对我也特别好,在街上遇着我,就眉开眼笑地摸我小脑袋!有时,我挨欺了,他领着我就找人家,像宠护自己儿子似的!
春天,见父亲扎墙头,四舅也凑热闹。开始,俩人还各干各的,边干边拉话儿。唠唠的,越唠越近,最后,俩人干脆合伙儿。通常可我家先来,然后再扎他家的。完活儿,咸菜条儿就酒,老哥儿俩也得整两盅儿!别看没啥菜,那兴致却异乎寻常的高!
两家人好,两家秧苗也跟着来往。有时我家豆角盘他家苞米上,有时他家黄瓜顺着墙头就溜过来!四舅和我父亲都那脾气,该谁的就归谁!若对方诚心不要,就爽快留下,从不客套!
后来,四舅把园子给他二哥一小块儿,从此,我家园子多了个伴儿。四舅的二嫂,我叫二娘,她说话、办事儿毛愣,屯儿里人私下都管她叫“二慌慌儿”。那老太太有点手“粘”,恰巧那年我家自己开园门儿,就有人逗我父亲:“你单独开园门儿是不是防二慌慌儿?”
这话纯属笑谈。二娘就老两口子,啥菜都不缺。只是她爱开玩笑,闲下来就挎个筐儿绕,见好不错儿的茄子、豆角她就给捋!有一天,当街闲坐一大帮人,二娘掐一小把儿豆角,笑嘻嘻凑过来让大伙儿择!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她在整事儿。就有人笑骂她:“二老娘们儿,从哪儿神来的?”二娘没吱声,不屑地冲骆叔努下嘴。骆叔早看出了她的鄙夷,“嗖”跳起来就去薅她。骆叔爱开玩笑,跟屯中儿很多嫂子都有“户头儿”,跟二娘更是老“关系户”。见骆叔扑来,二娘“妈呀”一声,顺便使个眼色!几个女人“哄”一下就把骆叔围住,没等她们下狠手,骆叔就半推半就倒在二娘的怀里!他根本没被怎么着,就妈声嘎气地叫唤!二娘她们就骂:“让你浪!让你浪!”拳脚像下雹子似的,还不解气,正巧跟前儿是生产队粪堆,她们扒开骆叔裤子就往他裤兜子扬粪。
其实,我家另开园门儿,是有原因的。一呢,一桶一桶地舀水,我父亲早嫌累了。二呢,让我拨池口子,父亲也看出了我的不耐烦。三呢,我一家族侄儿正需土垫地,刚好可以从我家园子就近取土。园子里的土被卸完后,父亲在墙根掏个豁儿,秧苗儿口渴的时候,把口儿一开,水渠的水就长驱直入了。此乃一举三得。更主要的是,从此我再也不拨池口子了,此欣喜则何如!
父母去世后,那园子就归弟弟了。他常年在外打工,那园子清一色大苞米。近些年,县、乡号召栽薄皮核桃,那儿早成核桃园了。
如今,四舅、二娘、我的父母,他们那代人大都走了,只给我留下那个年代依稀的记忆。可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去看看那园子,看着那园子,我就会想起他们,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种深深的眷念就会涌上心头!
祖传乐器
我有三件乐器。大镲,铙,小镲锅儿,青黑青黑的。不知底儿的人,一定以为它是刚出土的古代青铜器。
它是我们老王家祖传的。啥年代的,说不清。我大爷在世时,说它是我们祖辈用寡妇踩街赎罪钱买的。他讲的含糊,我听了糊涂。看他讲述时的表情,咋看都像编瞎话儿。
据说,刚置备时,不只这三件,还有锣、鼓和小水镲儿。我小时,这六件家什还挺好。敲起来,山响,那声音如万马奔腾。在当街敲,炕都跟着忽闪。一听那响动,我激动得心都要蹦出来,放下碗筷就往外蹽,啥好的也顾不上吃了。屯里大人小孩儿也都跟我似的,闻声从四面八方往鼓场跑。
这套家什,当时可是我们屯的稀罕物儿。那时,一块彩纸,一个像样儿的小瓶儿,都难得一见。春天,绿树短笛,就堪称我心中绝美的乐器了。捧着那笛子,迎风吹奏,俨然尽抒了我少年的情怀。
这家什,曾险遭不测。“破四旧”时,红卫兵说它是剥削阶级的旧文化,要把它砸了。所幸,当时它被二大爷保管着。二大爷把它锁在柜里,趴在柜盖上拼命护着。红卫兵碍于他苦大仇深,根正苗红,没敢硬来。它才得以保全。
怕弄坏,它,轻易不让小孩儿碰。我就无比羡慕地站在大人中间,看他们欢快地敲打。儿时的勃勃激情随着那优美的旋律纵情绽放。有时,忍不住弄根细棍儿,悄悄儿伸到鼓面上。忽儿,那棍儿就欢快地跳荡,振动的波儿酥酥传到我的手上。麻麻的,痒痒的。每每,那鼓手就会友好地冲我一笑,刹那间,他的温情就永恒地注入到我少小的心上,暖暖的。有时,能摸会儿小镲锅儿,微翕双眼,和大人手中的鼓、镲一起相融相和,何其快哉!
鼓场,尽出乐子事儿。一次,祥哥擂鼓,摇头拧腚的。他刚当新郎,正陶醉在甜蜜幸福中,故意整浪样儿。三叔白他一眼,出他洋相。拎来大锣,紧贴他屁股,“咣咣”,爆炸似的敲。边敲边盯他裤裆,大呼小叫。那样子,好像祥哥裆里有啥情况似的。在场的人,都捧腹大笑。
小时,我常纳闷。当街锣鼓一敲,南山根儿就跟着响。这儿锣鼓刚住,那儿就停。南山根儿是张家老坟茔。我就怀疑那儿的鬼神,在和人赛热闹。远远望去,那儿,影影绰绰的,真好像有鬼神在手舞足蹈。
按照习俗,只有正月,人们才把它拿出来,敲敲,耍耍。平时,它就被静静地放在二大爷的柜子里,一大年见不着。想到它往日欢奏的乐音,我时常望那柜子出神,有时,禁不住偎靠它。听到它里边“哗儿”一下,别提多高兴了,好像在幽谷听到了琴声。
可有时,好几年都见不到它。我们小队没办热闹家什,办,就得借我们的。可一借出去,有些毛愣小伙子,喝点酒就给糟践。本来,把东西借出去,我们王家孩子就有一种施予的优越感,瞅他们不知轻重的敲打就來气。大人们也觉得为它生闲气不合适,索性不外现了。于是,我好久见不到它。怀恋它的心,就像落日作别晚霞。
每逢正月,当邻屯的锣鼓响起,我就会痴痴地驻望。时常,忍不住弄两根木棒儿,在墙头或碾台上叮叮当当,把手震得都酸疼,但似乎只有那样,才能抒怀。淋漓的,仿佛正吟唱着心中憧憬已久的歌儿。
正月,没有热闹的夜晚,太冷清了。那时,乡村没有电视,没有音响。长夜,孤独地望房巴,实在没趣儿。偶尔,一声狗叫,我一阵欢喜,以为来秧歌儿了,可跑到当院儿,除了远处依稀的吹打声,什么也没有,房檐根儿那只狗正焦躁地在原地打转儿,不时听听、望望,空叫几声,冲那声音传来的方向。
没有这套家什,我们屯秧歌儿就办不成,外屯的秧歌儿来得就少了,秧歌儿也讲礼尚往来。为看场秧歌,有时,我都等到深夜。母亲怕我错过那一年一度的好热闹,边做针线,边陪我聊天,有时,在灶上烤俩豆包,香喷儿的,吊我精神。终于,有人喊:“来秧歌了!”夜深人静,那声音分外响亮。我赶紧从热被窝儿爬起来。很快,秧歌进屯了。吹打声,欢笑声,连同红红的灯笼,一下子沸腾了街巷,醉了山庄。我撒欢儿追着看。看外屯秧歌儿,有意思。在那千娇百媚的秧歌丛中,不时会扭来涂脂抹粉、风情万种的大姑娘。可曲终舞罢,当她摘下头饰,和你打招呼,却往往是瓮声瓮气的大男人。秧歌走了,我余兴未尽地返回家。外屋门竟大敞着。着急看秧歌,出门时,我忘带门了。屋里烧了一天的热气,都被我放跑了。
这些年,我人在外地,却时常想起那套家什。去年腊月回老家吃杀猪菜,席间,我叹恋起三叔、二大爷,提起那套家什,没想到人们对它竟漫不经心:“谁知那破东西扔哪去了?”我心一沉。人们在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怎么把过去那些好东西都忘了?而我偏不能忘却。我要找寻,找寻它和它曾带给我的美好记忆。谁知,那鼓、锣和小水镲儿早都没了。大镲、小镲锅儿和铙倒还有,竟被散落在谁家的角落里,那铙早不成样子了,全身开纹。
我把这三件家什精心收藏起来,给老家又置备了一套新的。愿它崭新的乐章,能在家乡人的心中世代传承,永远畅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