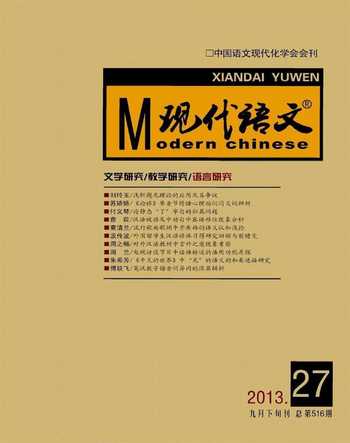从最近发展区理论看不同纠正性反馈方式对汉语习得的效果
开天 李柏令
摘 要:二语教学中的纠正性反馈方式可分为“形式协商、重复和明确纠正”三类,不同纠正方式所获得的学习者纠正效果不同。本研究对比了不同纠错方式在一对一汉语教学中的纠正效果差异。与重说和明确纠正相比,形式协商确实可以获得学习者更积极的态度反馈以及更有效的错误修正。对于产生不同理解回应率的原因,本文从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以及支架式教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形式协商处在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内,符合“支架式”教学原理,因而符合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自然发展条件,并且在感情上更受学习者青睐,故获得了更好的理解回应。
关键词:纠正方式 形式协商 最近发展区 支架式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
一、引言
对语言学习者语言偏误的回应,即对于语言学习者不规范言语所提出的信息回应,叫作“纠正性反馈”(corrective feedback)。Van Lier(1988)等学者指出,偏误纠正是语言学习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二语学习中的一项非充分但必要条件。
国外二语教学界针对纠正性反馈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不同纠正性反馈方式的效果研究及对比研究,如Ranta & Lyster(1997)、Lyster(1998)、Oliver(2000)、Morris(2002)、Philp(2003)、Lyster(2004)、Ellis(2007)、Sheen(2008)、Lyster & Izquierdo(2009)等。
国内对纠正性反馈的研究多集中在英语教学,主要涉及课堂中不同纠正方式的使用及其效果。在对外汉语教学界也有少量研究。例如,邵娜(2011)通过课堂观摩、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了新教师的纠正性反馈方式。
大量的研究表明,不同的纠正方式所获得的学习者纠正效果是不同的。Lyster & Ranta(1997)通过对“浸泡式教学”课堂的纠正反馈语的调查研究,将教师使用的纠正性反馈方式归纳为6种:明确纠正(explicit correction)、重说(recasts)、请求澄清(clarification request)、诱导(elicitation)、元语言反馈(metalinguistic feedback)、重复(repetition)。根据其统计分析,重说和明确纠正之后学习者的理解回应率较低,而其他4种反馈方式实施之后均伴随了较高的理解回应。Lyster(1998)进一步分析了各种纠正性反馈方式与学习者理解回应及修正之间的关系,发现“请求澄清、元语言反馈、诱导、重复”等4种纠正方式能够引发学生较高的理解回应及自主修正,可统称为“形式协商”(negotiation of form)。由此将教师的纠正反馈方式分为三大类:明确纠正、重说、形式协商。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词汇和语法偏误,形式协商比重说和明确纠正能更有效地引发学习者修正偏误。此后,Lyster(2002)对加拿大成人英语课堂进行研究,再次印证了上述结论。
施光(2004)借鉴Lyster & Ranta(1997)的实验方法,考察了英语课堂中教师的纠正性反馈方式与学生回应间的关系。类似研究还有赵晨(2005)、雷蕾(2008)、朱雯洁(2008)、徐立群(2008)、蔡少芹(2009)等。张欢(2006)通过课堂教学语音资料,分析了对外汉语教师纠正性反馈的方式和效果,并发现元语言反馈、请求澄清、重复是引发学习者理解回应最高的三种反馈方式,这一结果与Lyster & Ranta(1997)、Lyster(1998)的研究结果类似。
综合国内外诸多实验与研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元语言提示、请求澄清、重复等几种纠正方式获得的学习者理解回应效果明显优于重说与明确纠正。
对于不同的纠正方式产生效果相异的原因,国内也有学者做了实验研究,涉及学习者心理、偏误类型、教师偏好等许多方面。例如,孙宁宁(2010)、杨燕飞(2011)、夏苇、阙红玉(2012)、王典(2013)等。
目前国内外鲜有从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以及“支架式”教学角度来解释纠正性反馈效果的探索与研究。Aljaafreh & Lantolf(1994)曾研究了“最近发展区”中“负面反馈”(negative feedback)的影响,发现二语学习者能够在其“最近发展区”内随专家提供的负面反馈作出调整。但该研究尚未对负面反馈的不同效果进行解释。
根据“最近发展区”理论(Vygotsky,1978),语言学习者个体的语言发展包括两种水平:现实的发展水平(即学习者目前已经掌握的语言知识)和潜在的发展水平(即学习者个体在专家的帮助下所能达到的语言水平),这两种水平之间的区域即语言发展的“最近发展区”。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Bruner,1978)根据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提出了“支架式教学”(Scaffolding Instruction)。他借用“构建支架”(Scaffolding)作为概念框架的形象化比喻,认为该框架应按照学生智力的“最近发展区”来建立,通过这种“支架”的支撑作用,不停地把学生的智力从一个水平提升到另一个新的更高水平。
我们认为,包括元语言反馈、请求澄清、诱导、重复等在内的“形式协商”方式是符合“支架式”教学原理的。
本文选取汉语学习者进行一对一教学的个案研究,对形式协商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并尝试从“最近发展区”理论及“支架式”教学角度,对纠正性反馈的不同效果进行分析。
二、个案研究
研究对象是一位母语为英语的美国汉语学习者Julia,女性,40岁左右。学习时间为4个半月,学习课程主要为口语。教学形式为一对一教学。
我们采用多种纠正方式,引导该学习者学习或复习基本的句型及语言点,并对其产生的偏误进行纠正。选取重说法和诱导法作为主要对比内容。通过观察学习者、分析教学录音和笔记,研究不同纠正性反馈方式下学习者的反应及错误纠正效果,并从“最近发展区”角度对结果进行解释。
通过观察发现,学习者通过教师的引导式教学产生较为浓厚的学习兴趣,偏误修正效率较高。采用形式协商对学习者进行引导,可获得更为积极的反馈,尤其是在诱导法与重说法的对比之下。
(一)对话语料
以下是从教学录音及教学笔记整理材料中摘录的片段(按时间顺序排列),共有九组对话:
对话一
Julia:明天我们去豫园,你忘吗?
教 师:Dont forget the past perfect.(诱导)
Julia: ……了……吗?
教 师:对。
Julia:你忘了吗?
教 师:对。
对话二
教 师:你开空调了吗?
Julia:不,我不开空调……了。
教 师:You mean you dont use the air-conditioner or you just havent turned it on?(请求澄清)
Julia:I havent yet. How do you know whether you mean you never use it or you just havent?
教 师:I said“你开空调……了……吗?”The“了”means having finished the action.
Julia:Ok,so I can answer“我不开空调。”
教 师:When answer such question,you should use“没有”instead of“了”。(诱导)
Julia:我没有开空调了。
教 师:“没有”can also refer to the achievement of the action,so here“了”is unnecessary. (诱导)
Julia:我没有开空调。
教 师:Right. If you use“不”,well think you dont use such machine.
Julia:Yeah,I got it.
对话三
教 师:你会打高尔夫吗?
Julia:不,我不会打高尔夫。你呢?
教 师:我会啊。
Julia:Ah……你打高尔夫经常吗?
教 师:When you use adverb, put it before the verb.(诱导)
Julia:你经常打高尔夫吗?
教 师:是的,我非常喜欢打高尔夫,我经常去南京路的球场。
Julia:南京路的球场很好吗?
教 师:很好,人很少,很安静。
Julia:哦,周末,this weekend……
教 师:This?(诱导)
Julia:这个周末,我们去打高尔夫。
对话四
教 师:你吃过扬州炒饭吗?
Julia:我吃了扬州炒饭。它是了,it was,很好。
教 师:“是”doesnt have tense. (诱导)
Julia:So it was good,I can say,它是很好。
教 师:Do you remember the structure of Sentences with an adjective predicate? “Subject+adj.”,no verb. (元语言反馈)
Julia:So I can say“它很好”。
教 师:它很好吃。(重说)
Julia:Ok.
对话五
教 师:Please translate“Chinese music is very beautiful.”
Julia:中国的音乐是很好。
教 师:好听。(重说)
Julia:中国的音乐很……听。
教 师:很听?(重复)
Julia:很好听。
教 师:Can you make it more complete?(诱导)
Julia:中国的音乐很好听。
对话六
教 师:Please translate“Americans are nice.”
Julia:美国人很好。
教 师:Very good.
对话七
教 师:Please translate“Im very hungry.”
Julia:你很好喝?
教 师:“饿”refers to hungry.(诱导)
Julia:很好饿?
教 师:(笑)(诱导)
Julia:太饿了。饿极了。饿死了。
教 师:Right.
对话八
Julia:你帮我打合同吗?
教 师:You can say “Can you help me to…”or“please help me to…”.(诱导)
Julia:请帮我打合同。你可以帮我打合同吗?
对话九
Julia:我要四份复印……我还要四份复印,4 copies。
教 师:“复印”is a verb,not a noun.(诱导)
Julia:我还要你复印这个合同。
教 师:对。Add how many you need.(诱导)
Julia:我要四份。
教 师:我还要你复印四份合同。(重说)
Julia:Ok.
教 师:Can you say it again?(诱导)
Julia:我还要你复印四份合同。
(二)结果分析
首先,该学习者对教师的引导与启发,亦即符合“支架式”教学的形式协商的语言点纠正方法,表现了积极的学习态度。
例如,教师使用诱导或元语言反馈进行纠错后,学生会主动对说过的句子做出更正或重组,如对话一“Julia:你忘了吗?”;对话二“Julia:我没有开空调。”等。而教师使用重说法明示正确句型时,学生反应相对消极,很少主动重组句子;如对话四“——教师:它很好吃。(重说)——Julia:Ok.”又如:对话九“——教师:我还要你复印四份合同。(重说) ——Julia:Ok.——教师:Can you say it again?(诱导)——Julia:我还要你复印四份合同。”
该学生积极的反馈表明了其对形式协商式法的认可。该模式下学生顺着教师给予的提示思考与记忆,是一个主动学习与发展的过程,因而表现积极,会主动重组答案,说出正确句子。而在非重说法引导下,学生对教师输入的内容仅作简单答复“Ok”。
其次,该学习者在教师循循善诱的引导过程中,即教师在与其交流中所构建的“支架”上,较快地习得了大部分语言点,重复出错率较低。例如在连续对话四、五、六、七中,对简单形容词谓语句的学习,学生一般能根据教师提示马上对自己所说的句子做出调整,其后遇到类似句子时会有意识地注意,即便可能因为习惯原因有偏误的重复出现,学生会有意识地主动做出更正。详见下例分析:
对话四:——Julia:我吃了扬州炒饭。它是了……it was……很好。——教师:Do you remember the structure of Sentences with an adjective predicate?
对话五:——Julia:中国的音乐是很好。——教师:好听。——Julia:中国的音乐很……听。(按:学生主动做出更正,省去习惯用的动词“是”。)——教师:很听?——Julia:很好听。——教师:Can you make it more complete?(诱导)——Julia:中国的音乐很好听。
对话六:Julia:美国人很好。(按:学生迅速给出正确句子,未出现偏误。)
通过上述对话记录可以发现,学生跟随教师的步步引导,在短时间内成功地掌握了该语言点。教师从构建“支架”(阐释语言点,进行较为具体的提示),到逐渐拆掉“支架”(粗略提示,仅进行点拨,直至给出问题,省去提示),采用了较为典型的“支架式”教学。而学生则在教师构建的“支架”上步步攀登,逐渐习得语言点,达到不经提示便能答出正确且完整句子的水平。整个纠正过程体现了形式协商对该学生汉语习得的明显促进作用。
综上,该汉语学习者在形式协商纠正反馈语的辅助下对基本语法点的学习达到了较好的习得效果,学习过程十分顺利。学生的学习态度相对积极,对教师的引导与提示迅速思考,反应较快,正确率高。
以上材料验证了不同纠正性反馈方式获得的不同效果,尤其是诱导法与重说法相比所产生的更强的理解回应。究其原因,可根据“最近发展区”和“支架式”教学理论来解释,“提供支架的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学生与同伴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也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教师提供丰富、有效的概念支架是促进学生认知发展、使学生有效地实现知识意义建构的有效方法”(Vygotsky,1986)。诱导法在施行时,处在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内,符合“支架式”教学原理,因而符合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自然发展条件,并且在情感上更受学习者青睐,故能获得更好的理解回应。
三、结语
上述结果是基于“最近发展区”理论的“支架式”教学对于引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其语言认知发展并实现语言知识意义建构的有效性体现。
根据Lyster & Ranta(1997)的定义,明确纠正是指教师明确地告诉学生他们所说的话中有错误,如“No,what you said was wrong”,或者是“you cant say…”,接下来教师会给出正确的形式。“重说”是指教师并不直接指出学生的错误,而是将学生话语中的错误更正并重复他们的话。
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点,在于直接将正确的语言形式告诉学生,不能引导学生自己纠正错误,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只能重复教师提供的正确形式,无助于培养学生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因而违背了“构建支架”的原理。
而形式协商法,包括请求澄清(教师要求学生澄清自己话语中的语言错误,“Pardon?”或“Excuse me?”)、元语言反馈(教师对学生的回答提出评论或问题,从语言学的角度让学生分析话语并找出错误)、诱导(教师用一些方法诱导学生更正语言错误,如引导其补充自己的话、提问、让其重组话语等)、重复(教师用升调重复学生的语言错误),教师并不直接提供正确形式,而是通过“支架”的构建,使学生有机会自己纠正错误。
本研究验证了不同纠错方式在一对一汉语教学中的纠正效果差异,并从“最近发展区”理论的角度进行了原因分析。与重说和明确纠正相比,形式协商可以使学习者获得更积极的态度反馈以及更有效的错误修正,这种区别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溯源分析。从“最近发展区”理论的角度来看,形式协商,尤其是诱导,主要在学习者“最近发展区”内进行错误纠正与引导,构建支架帮助其习得语言点,修正口语中的偏误,不仅使学习者更深刻地认识与记忆语言点知识,并且在心理上更受学习者欢迎。对学习者来说,这样的纠正过程是一个引导学习者主动学习、认识自身偏误并寻找修正方法的过程,符合他们的语言学习发展规律,因而比重说等非形式协商纠错方式的理解回应率更高。
当然,对于形式协商纠错反馈方式更具体的使用语境、需考虑的学习者水平、个性等其他因素,亟待进一步研究。对于形式协商是否适用于各个阶段的汉语二语学习者以及适用的课程,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Van Lier,L.The Classroom and the Language Learner[M]. London: Longman, 1988: 182.
[2]Lyster.R,& Ranta L.Corrective feedback and learner uptake:negotiation of form in communicative classrooms[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997,19:37-66.
[3]Lyster,R.Recasts,repetition and ambiguity in L2 classroom discourse[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998,20:51- 81.
[4]Oliver,R.Age differences in negotiation and feedback in classroom and pair work[J].Language Leaming,2000,50:119-151.
[5]Morris,A.Negotiation moves and recasts in relation to error types and learner repair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G].Foreign Language Annals,2002,35:395-404.
[6]Philp,J.Constraints on ”noticing the gap”:Non-native speakersnoticing of recasts in NS-NNS interaction[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003,25:99-126.
[7]Lyster,R,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rompts and recasts in form-focused instruction[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004,26:399-432.
[8]Ellis,R.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corrective feedback on two grammatical structures[A].In Mackey,A (Ed.)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A series of empirical studies.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7:339-360.
[9]Sheen,Y.Recasts,language anxiety,modified output, and L2 learning[J].Language Learning,2008:835-874.
[10]Lyster,R.,& Izquierdo,J.Prompts versus recasts in dyadic interaction[J].Language Learning, 2009,59:453-498.
[11]邵娜.对外汉语课堂中新教师纠错行为的调查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2]Lyster,R.Negotiation in immersio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2002,37:237-253.
[13]施光.纠错与接纳:中学英语课堂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14]赵晨.不同水平英语教学中的教师纠正反馈语——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3).
[15]雷蕾.显性反馈、隐形反馈与二语习得——针对一般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动词词素变体的实证研究[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16]朱雯洁.高中英语口语教学纠错方式调查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7]徐立群.论英语课堂纠正性反馈的类型及其作用[J].疯狂英语(教师版),2008,(2).
[18]蔡少芹.初中英语课堂上教师纠错方式的调查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9]张欢.对外汉语课堂教师纠正性反馈研究[D].北京语言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06.
[20]孙宁宁.关于留学生对教师教学反馈态度的调查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0,(7).
[21]杨燕飞.二语语用教学中的显性和隐性纠正性反馈研究[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1,(2).
[22]夏苇,阙红玉.不同纠错方式对高中生英语学习效果的影响[J].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基础英语教育),2012,(1).
[23]王典.对外汉语听说课纠错行为研究[J].时代教育,2013,(5).
[24]Aljaafreh,A.,& Lantolf,J.Negative feedback as regu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94,78(4):465-478.
[25]Vygotsky,L.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76 .
[26]Bruner,J.The role of dialogue in language acquisition[C] / /In S.Jarvell & W.Levett (eds.)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Language.New York:Max Plan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 1978:214.
[27]Vygotsky,L.Thought and Language[M].Cambridge MA: MIT Press,1986:45.
(开天 李柏令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20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