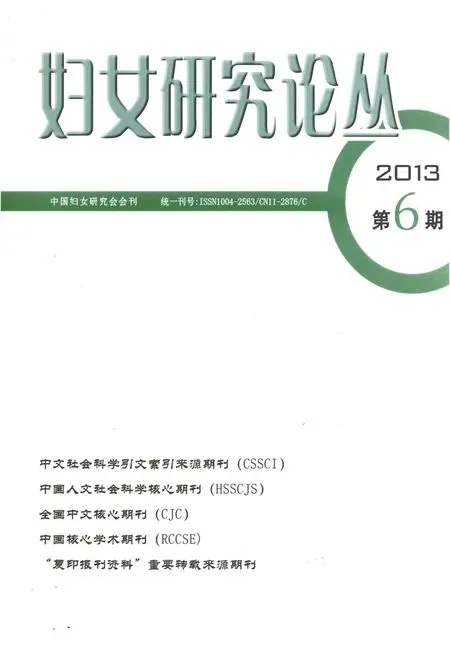汉代女性阅读活动述评
顾丽华
(嘉应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阅读活动作为承载着人类精神需求的文化现象由来已久。在中国古代,因诸王朝文教政策、社会风尚与印刷技术等因素的变迁,阅读活动并非一成不变。汉代阅读活动不仅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且成为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从事的重要文化活动。但因性别及公私领域分工不同,女性在阅读取向、方式和目的上皆与男性有别。本文拟从阅读史①在对阅读史领域开拓上,当推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领军人物罗杰·夏蒂埃,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将书籍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推进,主编了《西方阅读史》(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在夏蒂埃看来,阅读是一个充满创造和活力的过程。最近研究成果则以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为代表。当然,西方史学界对于“阅读史”的探索仍存在诸多争议,暂略。和社会性别史角度分析汉代女性阅读活动的特点、原因及影响,由此透视这些历史现象所源出的汉代社会秩序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所彰显的历史文化内涵。②对于中国古代妇女阅读问题,目前学界研究主要在唐以后。如铁爱花《宋代女性阅读活动初探》(《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宋代社会的女性阅读——以墓志为中心的考察》(《晋阳学刊》2005年第5期)、韩淑举《明清女性阅读活动探析》(《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年第1期)、陈秀钦《唐代女性阅读活动浅析》(《兰台世界》2011年第5期)。而关于汉代女性阅读活动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
尽管阅读活动由来已久,但汉代阅读的社会条件已与前代不同,它是在国家集权统治加强、经学广为流传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女性阅读活动自然具有时代特征,表现如下:
其一,汉代女性阅读内容宽泛多元,但并未涉及为男性看重的实践性较强门类。就汉代女性整体而言,其涉猎领域颇为宽泛,主要有以下4类:一是儒道史百家之言。阅读道家典籍的如汉初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1](《外戚传》P3945)汉末钟会之母尤好《老子》。[2](《魏书·钟会传》P785)也有诵读儒家经典的,明帝马皇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3](《皇后纪》P409)顺帝梁皇后“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3](《皇后纪》P438)东汉巴蜀地区的季姜“少读《诗》、《礼》”。[4](《汉中士女》P616)也有好史书的,如西汉成帝许皇后“聪慧,善史书”。[1](《外戚传》P3974)通百家之言的也大有人在。两汉之际崔篆母师氏“通经学、百家之言”。[3](《崔骃传》P1703)二是箴戒类读物。阅读古箴戒之书的如西汉孝成(成帝)班婕妤“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师古注曰“《窈窕》、《德象》、《女师》之篇,皆古箴戒之书”。[1](《外戚传》P3984)也有习阅当世女诫之书的。班昭《女诫》即是为其女所撰。[3](《列女传》P2792)三是音乐算数天文书法类书籍。史载:“蔡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3](《列女传》P2800)另和帝皇后邓绥“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方、算数”。[3](《皇后纪》P418)又东汉灵帝妃子王美人“聪敏有才明,能书会计”,师古注曰“会计谓总会其数而言”,显然涉及对数学的研读。[3](《皇后纪》P450)东汉章帝窦皇后“年六岁能书”,[3](《皇后纪》P415)和帝阴皇后“少聪慧,善书艺”,[3](《皇后纪》P417)可见汉代女性亦有阅览书法读物的。四是医学方术类书籍。汉代有颇为(负)盛名(的)女医,高超医术或与阅读医药类书籍有关。如西汉义姁“以医幸王太后”。[5](《酷吏传》P3144)汉代方术盛行,③据《后汉书·方术传》载:“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录,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子长(司马迁字子长)亦云:‘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忌。’盖为此也。”([宋]范晔:《后汉书》卷82上《方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05页)亦有习阅此类书籍女性。东汉和帝时“明于风角”的李南之女“亦晓家术”。[3](《方术列传》P2717)尽管汉代女性阅读内容丰富多元,但与男性比,诸如刑名学④“刑名学”,泛指秦汉时期人们对法律进行学习和传授的活动。关于这一活动和学问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史学家对秦汉时期法律学习和传授模式一般称为“刑名学”或“法律学”;现代法学界则一般将秦汉时期的法律研究、注疏和传授活动称为“律学”;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提出了“律令学”的概念。秦汉时期不仅社会上盛行学习“律令”,而且国家也重视官吏对法律的学习和使用,从性别角度而言,则研习者皆为男性,现有资料未见有女性研习法律知识者。这样实践性较强的领域则未曾涉猎。
其二,汉代女性阅读阶层广泛,但不同阶层女性所阅内容有别,底层两性阅读亦各有偏重。汉代各阶层女性皆有一定阅读行为。贵族家庭妇女大多要研习典籍。前文提及的熟习儒家经典和史书的顺帝梁皇后是大将军商之女,博览群书的和熹邓皇后是“太傅禹之孙也。父训,护羌校尉;母阴氏,光烈皇后从弟女”。[3](《皇后纪》P418)儒学世家女性亦尚阅读。西汉大儒刘向尤重对《左氏春秋》的传授,“下至妇女,无不读诵”。[6](引桓谭《新论》P2770)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家奴婢皆读书”。[7](《文学》第4P105)普通家庭妇女亦有诵读。河南乐羊子之妻以“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劝其路不拾遗,后又以“夫子积学,当日知其所亡”劝其专心求学,此皆《论语》中典故,可见必有相关习阅。[3](《列女传》P2792)尽管汉代各阶层女性皆有一定阅读活动,但文化水平和环境因素致不同阶层女性所侧重内容并不相同。与贵族世家女性涉猎甚广相比,文化素质不高的底层女性以诵读通俗易懂鉴戒类书籍为主。如敦煌(汉代?)残简中有“□□分列女传书”字样,不仅说明《列女传》流布甚广,且揭露了阅读者为底层边郡随军家属。[8](P256)女性阅读阶层差异与不论出身境况、志在通晓经术的男性阅读形成较鲜明对比。⑤尽管家庭经济条件会影响到男性外出游学和受教育情况,但这种影响并不是非常显著,因为汉代雇佣劳动较发达,使一些无经济实力者可以依赖作佣工来维持游学活动。如公沙穆“来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祐赁舂”。([宋]范晔:《后汉书》卷64《吴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00页)
其三,汉代女性阅读态度不尽相同,与各阶层男性主动求学状态不能同日而语。从态度上看,汉代女性既有主动阅读者也有被动阅读者。主动阅读兴趣多在蒙幼时期就已显露。前文提及的顺帝梁皇后即在9岁时已表现出对阅读典籍的浓厚兴趣。[3](《皇后纪》P438)邓皇后6岁已熟读《史书》。[3](《皇后纪》P418)与主动阅读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某些女性接受教育的被动性。东汉韦逞母宗氏因家中无男性可继承家学《周官音义》,不得不接受父传。[6](《宗亲部·女》引《后汉书》P2361)一些庭训尤严的明儒世家女性要被动阅读规训读物。如东汉大儒马融很欣赏《女诫》,“令妻女习焉”。[3](《列女传》P2792)为利于政教,宫廷妃后需接受一定经学训练。汉昭帝去世后大将军霍光以为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宜知经术,白令胜用《尚书》授太后”。[1](《夏侯胜传》P3155)宫廷中有专门的女官学事史负责督教皇后。西汉成帝时宫女曹宫“为学事史,通《诗》,授皇后”。[1](《外戚传》P3990)为矫正风俗一般宫女也要接受经学教育。和熹邓皇后曾“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3](《皇后纪》P424)
其四,汉代女性阅读空间局限于家庭,与男性游学明经的动态阅读相比属于静态阅读,并展现出阅读的家族性。“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9](P131)故口耳相传是汉代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由于汉代各阶层男性皆可外出游学寻师,并不受家庭条件限制,但囿于家庭空间的女性则受制于家庭文化氛围。在这种情况下,有更多机会接触典籍的当属贵族与士人家庭女性。如前文提及那些诵阅典籍的妃后(后妃)们就多出身贵族。以传《尚书》为业,士人家庭家学渊源与氛围亦深刻影响了女性阅读。几乎与两汉王朝相始终的伏氏家族女性就继承了家学。史载文帝时“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1](《儒林传》P3124)东汉蔡文姬能诵忆其父散逸书籍“四百余篇”,[3](《列女传》P2801)蔡文姬之才学亦有深厚家学渊源,其父蔡邕“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3](《蔡邕传》P1980)世家大族往往一门多才女。以修撰《汉书》传世的班彪家族作为文武世家,在西汉成帝时即有以辞赋见长的才女班婕妤,东汉有“博学高才”的班昭,班昭之妹及子媳“俱以能文名”,能文的背后必然是大量阅读的支撑。[3](《列女传》P2792)又东汉大儒马融之女马伦“少有才辩”,“有名于世”,马芝“亦有才义。少丧亲长而追感,乃作《申情赋》”。[3](《列女传》P2796)可见,就空间和状态而言,汉代女性阅读囿于家庭,与男性在广阔空间游学的动态诵读相比属于静态阅读。
其五,汉代女性阅读被(受到)主流文化深刻影响,但就阅读目的及其学识所能发挥空间而言则与男性有别。从纵向动态看,历经两汉,与男性一样,女性阅读内容亦紧随主流文化的变动而变化。汉初官方力倡无为而治,黄老之学⑥汉初的黄老之学,尊奉黄帝,本于老子,与战国末期齐国慎到、申不害等人的稷下学派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成为当世显学,这自然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对黄老之学的重视和研习,女性概莫能外。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量包括黄老学在内的帛书,推测应为死于公元前186年的墓主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之妻生前所喜爱和阅览的。⑦此次出土仅《老子》就有甲乙两种抄本,其中,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据唐兰先生考释,这四种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黄帝四经》。(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卷本前古佚书的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又汉初窦太后亦“好黄帝、老子言”。[1](《外戚传》P3945)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取代黄老学一跃而为汉代统治思想,政府不仅大力倡导经学教育,并以经取仕(士——朝廷是取士、士人是取仕),形成持久不衰的明经习儒社会风尚。汉代女性亦以各种方式参与到这一风尚中。[10]但因汉代女性被阻隔于明经入仕的正途之外,故女性研读目的不同于男性的明经仕进,而偏向于道德修养和家庭教育。
二
汉代女性阅读活动丰富多元,并表现出独有的时代特点,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尽管汉代女性阅读内容、方式和目的不尽相同,但和主流文化及官方意识形态联系密切。因而汉代女性阅读深受经学教育普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及家庭氛围等外在因素影响,同时亦与女性自身因素息息相关。
汉代以传播经学为主的教育之普及是女性阅读活动的文化环境。西汉肇建之初虽继承了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但对教育已有所重视,此后随着统治者对儒家“教化”实用价值的认可和提倡,在贾谊“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故是以明君之于政也慎之,于吏也选之,然后国兴也”[11](《大政下》P348)及董仲舒“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1](《董仲舒传》P2512)等主张的推动下,通过学校教育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文教政策形成,并逐渐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办教育机构。从汉武帝时期起,中央设立太学,地方郡县设置地方官学,至东汉时出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3](《班彪传》P1368)的官学林立的局面。除官学外,汉代名师授业的私学亦相当发达,名儒动辄“弟子以千数”,[3](《郭太传》P2226)“著录且万人”。[3](《儒林传》P2553)汉代以传播经学为主要内容之官私教育之兴盛,不仅推动了对蒙学的重视,部分女性得以在蒙幼时期接触《史书》《孝经》《论语》等,⑧《后汉书·皇后纪》引师古注曰:“《史书》,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前书》曰‘教学童之书’也。”([宋]范晔:《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18页)《孝经》《论语》则是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虽未入五经之列,“然两书在两汉所发生之作用,或且超过五经,实质上汉人即视之为经”。(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见《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启蒙了汉代女性的阅读兴趣,也有利于女性多方面接触经学,同时亦左右着女性的阅读取向。可见,经学教育的发达是汉代女性阅读的文化环境。
汉代官方移风易俗之教化思维及其渗透是女性阅读的政治思想背景。如前所述,汉初统治者重教兴学是建立在对儒家“教化”实用价值之青睐基础上的。通过传播经学直接移风易俗乃是这一教化思维的实践方式之一。这一教化实践是全方位的,不仅有前文提及的针对社会各阶层而设立的官私学之兴盛,还有针对宗室及外戚的专门教育。东汉开国之初,即令刘昆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施氏易》。[3](《儒林列传》P2550)汉明帝时创办了“四姓小侯学”。⑨“四姓”指外戚樊(光武帝母家)、郭(光武帝后家)、阴(光武帝后家、明帝母家)、马(明帝后家)四氏;“小侯”是因为这四姓都不是列侯,故以此称之。邓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3](《皇后纪》P428)邓太后曾言“所以引纳群子,置之学官者,实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不有化导,将遂陵迟,故欲褒崇圣道,以匡失俗”,[3](《皇后纪》P428)道破了官府通过教化而规范贵族行止进而矫正时俗之真正目的。就此而言,汉代针对宗室贵妇、宫廷妃后乃至普通宫女的教育不过是这一教化网络的一环而已。
汉代官方旌表行为亦是推动女性阅读的重要因素。作为传统社会维持时俗风教方式之一的旌表制度,肇端于先秦时期,历经两汉形成定制。汉代旌表原则是“举善而教,旌德擢异”,[2](《吴书·陆绩传》P1329)那些德行卓异的女性亦在国家旌表之例。据文献所载,汉代以不拘一格的方式对包括(具有)孝行显著、贞义、母德突出及才华横溢的各阶层妇女进行了旌表。被旌表的母德(内容)之一即教导子弟有方。西汉武帝时期的金日磾之母就因“教诲两子,甚有法度”而被旌表。[1](《金日磾传》P2960)此类教诲多指明经取仕。东汉寿张县人女子张雨被旌表即因“留养孤弟二人,教其学问,各得通经”。[3](注引《谢承书》P2714)被表彰女性的才华指精通经学。两汉之际的崔篆之母师氏“通经学、百家之言,(王)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即为一例。[3](《崔骃传》P1703)在汉代,受到国家旌表是非常荣耀的,不仅有图画其形⑩将旌表对象的形象画于石或砖上,在画像旁写明其事迹以供瞻仰品评,此即图画其形。如东汉蜀郡手刃杀父仇人的敬杨由“涪令向遵为立图,表之”。([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0下《汉中士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7页)和刊石表闾⑪将刻有异行的石头立于其居住的闾里,此谓刊石表闾。汉灵帝时庞淯之母赵娥积十余年终雪刃杀父仇人李寿后从容自首,一时之间“州郡叹贵,刊石表闾”。([晋]陈寿:《三国志》卷18《庞淯传附母娥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48页)等名誉上的表彰,亦有诸如赏赐帛、谷,免除徭役等实际奖励。这对家族乃至女性个人而言皆有相当诱惑力。尽管汉代国家旌表妇女实践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期待,对妇女实际生活的影响是有限度的,但国家尊崇此类母德(以上张雨事迹非“母德”)所形成的这种氛围,却是女性阅读活动能够发展的重要条件。
周围人对女性阅读的赞赏与期待是汉代女性阅读的家庭条件。正如前文所述,在政府教化思维的渗透及明经当仕的利禄吸引下,汉代形成了研习经学的风尚。这一风尚必然影响家庭教育取向及人们对女性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对女性接触甚至研习经学的开明态度。前文提及的和帝邓皇后6岁时就表现出了对阅读典籍的极大热情,其母虽以“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非之,但在她“昼修妇业,暮诵经典”之后便默许了;其父则信任并重视她的才华,“异之,事无大小,辄与详议”;诸兄更在共同研习之余,“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表现出爱护和认同。[3](《皇后纪》P418)如果说邓家还仅限于基本认可与赞同,那么后来的梁家则流露出更高的期许。前文提及的顺帝梁皇后幼年即表现出对儒家典籍的热衷,以致使其“父(梁)商深异之,窃谓诸弟曰:‘我先人全济河西,所活者不可胜数。虽大位不究,而积德必报。若庆流子孙者,傥兴此女乎!’”[3](《皇后纪》P438)梁商不仅嘉许女儿阅读行为,还表露出对其兴族显家的热切期待。家庭的支持无疑是对女性阅读的有力推动。
自我满足感是汉代女性阅读活动的内在动因。尽管外部环境深刻影响着女性阅读活动,但女性个人因素也是不容抹杀的。如前所述,汉代兴学目的之一为培育能够教化一方的官吏,不仅“明经当仕”成为时人通念(流行观念),且“经明行修”成为检验士人行为的标准。这一通(观)念不仅客观上为女性阅读架构(筑)起相对宽松的弹性空间,也是女性自我满足的内在动力之一。虽然女性被阻隔于明经入仕正途之外,但女性自然也有获得社会尊重的强烈愿望,并以自己的方式来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女性阅读与这种追求自我价值和社会尊重的满足感紧密相关。当女性通过研习典籍而或像钟会之母那样成功培养出优秀有为的儿子,或如崔篆之母师氏因通经学、百家之言而获得政府表彰,她们实际是在实现自己所追求的“被尊重”及“有价值”的愿望。无论是通过成功教导子弟明经而获得家庭乃至社会的认可,还是加入对“经明行修”美誉与名节之追求行列,女性皆需首先研读儒家典籍,就此而言,自我满足感可谓汉代女性阅读活动的内在动因。
总之,除外界环境对女性阅读活动的导引外,女性内在需求也极为关键,部分女性阅读乃是其在有限社会生存空间中的积极选择。
三
汉代女性阅读活动深受主流文化推动,反过来,必然对当时经学传授、教育普及乃至文化风尚有所影响。但阅读活动的意义更多地则在于对女性自身的影响,表现如下:
第一,提高女性自身素质的同时亦强化了女性对自我行为的约束。东汉班婕妤阅读皆为古箴戒之书,尤其注意依礼行止,史载其“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甚至一次与成帝游于后庭,帝“尝欲与婕妤同辇载”,婕妤也以古代贤圣之君的故事拒绝说:“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1](《外戚传》P3983)东汉顺帝梁皇后“深览前世得失,虽以德进,不敢有骄专之心,每日月见谪,辄降服求愆”,她刚入宫为贵人时“常特被引御”,这对于其他妃后(后妃是)求之不得之事,她却从容辞于帝曰:“夫阳以博施为德,阴以不专为义,螽斯则百,福之所由兴也。愿陛下思云雨之均泽,识贯鱼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谤之累。”[3](《皇后纪》P439)梁皇后这番辞对引用乃《诗·国风序》与《易》中典故,可见其对这些典籍不仅熟悉,且已内化为约束自我的价值观。⑫据师古注曰:《诗·国风序》曰:“言后妃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诗·大雅》曰“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也。《易》曰:“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宋]范晔:《后汉书》卷10下《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39页)东汉名儒桓鸾之女亦以儒家价值观念为行为指导,在夫子相继离世后她企图割耳自誓,以不辱“男以忠孝显,女以贞顺称”家风及《诗》中“无添尔祖,聿修厥德”德行训诫。[3](《列女传》P2797)总之,阅读在提高女性整体素质的同时,亦推动了女性对官方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的内化及践行。
第二,汉代女性阅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部分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上文述及的班婕妤和梁皇后皆因受所诵阅典籍影响而依礼进退从而提升了政治地位。班婕妤拒绝同辇后博得成帝与太后的敬重和喜爱,成帝“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1](《外戚传》P3983)梁皇后拒绝顺帝后,“由是帝加敬焉”,后终立为皇后。[3](《皇后纪》P438)班昭不仅凭借才华博得皇室重用,而且还带动了其子政治地位的提升:“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3](《列女传》P2784)和帝邓皇后幼年就因对书籍的兴趣而使其父与之商议家庭事务,显然其家庭地位因此而非同一般。[3](《皇后纪》P418)汉末遍览典籍的钟会之母张氏少丧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礼不动,不仅“为上下所称述”,终为定陵成侯太傅钟繇之命妇。[2](《魏书·钟会传》P785)总之,汉代女性诵阅活动确有助于其家庭、社会地位的提升。
第三,汉代女性阅读亦是其寻求和证明自我社会价值的方式与途径之一。“阅读不但只是种技能而已,更还是一道寻求意义的途径。”[12]汉代女性阅读,一方面深受社会环境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女性自身不断努力,以迎合社会需求、证明自我的积极行为,甚至可以说是“妇女们利用有限然而具体的资源,在日常生活当中苦心经营自在的生存空间”[13](P9)的表现。与汲汲于功名的男性一样,汉代各阶层女性都在寻求着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具有渴望被尊重、被认可、被奖励与赞誉的内在需求。汉代女性诵阅儒家典籍,也是其内在需求的外在表现。尽管汉代社会制度没有给女性预留实现自我的正规制度化途径与机会,但儒家并不反对女性对文化的掌握与精通,汉代社会也对那些具有一定学识修养的女性给予尊重与赞誉,客观上为女性架(建)构了一个比较宽松、尚可以寻求与探索的文化空间。汉代女性往往以成功教诲子幼学问而间接实现自我价值。如东汉邓训之子邓阊之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为阊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3](《邓寇传》P618)前文提及的钟会之母“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觐见规诲。年四岁授《孝经》”,后遍及儒家经典,钟会弱冠而显名,众皆知其母教诲之功。[2](《魏书·钟会传》P785)班昭这类凭借自身学识而获得社会认可者则称得上是藉由自身努力对自我价值的直接实现。虽然这一人生价值未能超出固有的狭隘,仅是儒家“学而优则仕”价值观的内化,但女性在阅读活动中所展现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却令人称道和赞叹。
第四,阅读也促进了女性间的互相交流。如班昭《女诫》书成后,昭女妹曹丰生“为书以难之,辞有可观”。[3](《列女传》P2792)这种因阅读而带动的女性间的唱和与批评,无疑丰富了女性文化生活。
综上可见,在汉代,尽管阅读对女性个体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其限度亦不容忽视。汉代女性深受主流文化影响之阅读取向,仅是对时代风尚的顺应,并未触动原有社会规范,且不可避免地使女性将主流价值观内化为一己人生追求和行为指南。就阅读目的及学识所发挥空间主要在家庭内部而言,女性阅读则不仅未能突破儒家“男外女内”性别秩序,反而强化了女性对为母角色的认同与实践。
[1][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宋]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7]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陈直.汉书新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9]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顾丽华.汉代女性好儒风尚述评[J].妇女研究论丛,2008,(6).
[11]贾谊.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J].新史学,2005,(3).
[13][美]高颜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