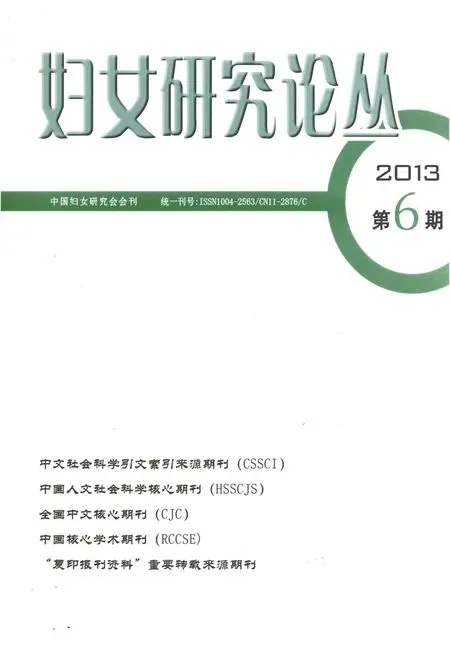近代中国女性人体艺术的解放与沦陷:再论民国“人体模特儿”事件
曾越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由废除缠足、束乳的女性解放运动推向社会前台,成为人们评头论足的对象。先进的艺术家从艺术领域出发,试图建立女性人体的审美独立性。这一冲决女性传统身体禁忌的尝试遭到了封建势力的坚决抵制。其间,以上海图画美术学校①该校1912年由乌始光、张聿光和刘海粟在上海创立,初名上海美术学院。1915年改名为上海图画美术院。1916年又改名为上海图画美术学校。1920年更名为上海美术学校。学生公开展览人体绘画作品为导火索,引发了关于女性身体公开展示和观看合法性问题长达十年的社会争论。学界一般认为,艺术家通过这场论争建立了独立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肃清了女性人体艺术在审美与道德之间的界限问题,进而推动了近代女性新的身体审美观的建立和发展,对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解放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论争过程及以后大众媒体和民众对女性裸体图像的围观,显示出这一艺术事件的男性话语色彩。女性的身体以艺术的名义沦为公开消费的对象。
一、事件回溯
民国时期的“人体模特儿”风波,是在1916年到1926年间,由艺术家3次公开展览人体绘画作品而引发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历史事件,其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女性人体艺术的合法性问题上。
事件起自1916年夏,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学生在作业展览会中陈列人体习作,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群众见之,莫不惊诧疑异,随甚迷惑,第隐忍而不敢发难。”[1](P30)某女校校长“为文投之《时报》盛其题曰:《丧心病狂崇拜生殖之展览会》……又趋江苏省教育会告沈君信卿,请上书省厅下令禁止,以敦风化。”[1](P31)此次公开反对对刘海粟和上海图画美术学校人体写生课程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时报》既没有采用该校长的辱骂文章,江苏省教育会对告状信也不予回应,首次交战不了了之。时隔3年,1919年8月,刘海粟、江新、汪亚尘、王济远等人在寰球学生会举办展览,陈列人体画。当地媒体斥责其有伤风化,呼吁政府予以制止,然而“工部局派碧眼儿来观,未加责言,盖亦知其所以然也”。[1](P31)这两次展览总体上是成功的。刘海粟认为,此时社会对人体艺术已经司空见惯,群众“有以人体美为流行之风尚矣。数年来对于人体模特儿似已无怀疑,展览会时时陈列裸画,亦无非之者。且也,每届美术展览会之时,群众鹜趋,方谓社会爱美之观念渐深,将与欧人之艺苑、观众可并驱驾”。[1](P31)
但事实并非如此乐观。1924年,上海美专学生饶桂举画展因陈列人体习作而遭到了江西警厅勒令禁止。警方陈其原因为“裸体系学校诱雇穷汉苦妇,勒逼赤身露体(名为人体模特儿)供男女学生写真者,在学校方面,则忍心害理,有乖人道;在模特儿方面,则含垢忍羞,实逼处此;在社会方面,则有伤风化,较淫戏、淫画等为尤甚。”[1](P32)刘海粟致信教育总长黄郛、江西省长蔡成勋,驳斥警方谬论,指出人体艺术与色情图像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异,并请求政府出面打击以艺术名义贩卖色情图片的不良商贩。其诉求初步得到官方支持。1926年,上海市议员姜怀素又谓“窃维世风不古,礼纪荡然,淫佚放浪,于今为烈。沪地为华洋杂居,欧俗东渐,耳濡目染,不随善化,只效靡风。而智识阶层中含有劣根性者,复绘为裸体淫画,沿路兜售,青年血气未定之男女,因被此种淫画诱惑而堕落者,不知凡几。在提倡之者方美其名曰模特儿、曲线美……造恶无量”,[2]特请当局禁止人体模特儿并惩处刘海粟。继姜怀素呈文之后,上海总商会、上海县长危道丰相继撰文谴责。在多方施压之下,官方最终判定上海美专暂缓使用人体模特儿,并对刘海粟处以50元罚款,事件基本平息。
这3次论战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长达10年的“人体模特儿”风波。反对者的身份历经个人、媒体、政府,打压层层升级,艺术家阵营最终以刘海粟及上海美专受到官方惩戒而宣告失败。
二、人体艺术的话语权建立及其意义剖析
在近代中国艺术向西方寻求新突破的时期,先进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在国内积极推进西方艺术,以扫除明清艺术传统的陈腐之气。“人体模特儿”论争集中展现了进步艺术思想与传统势力的交锋。它对近代中国社会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不但使中国艺术呈现出全新气象,在艺术范畴之外,对近代中国女性身体观念挣脱封建传统束缚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人体模特儿”的论争过程是中国社会人体艺术生长、发展、壮大的过程,10年间,围绕人体艺术展开了多种多样的艺术实践活动,艺术家通过美术教育、创作实践、参展参赛、媒体宣传等多种途径培育了中国人体艺术创作和接受的社会土壤。在这一时期,除了上海美专之外,其他如上海美术学校、北京美术专科学校、上海神州女校等均采用人体模特儿进行教学;1911年到1920年期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亦由李叔同主持开设了人体写生课程。西式美术教育使人体写生成为近代学子向新式艺术家道路迈进的必经阶段。美术教育领域中的先行者往往充当了一般民众人体艺术欣赏的启蒙者,如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撰文推广英国人麦克劳德(Macleod)夫人的美术展览,介绍说“人体写生计九十三件,有西洋裸体妇人及中国戏剧、妇女、旗女、小孩、贫民等各画。其中以裸体妇人及赤身力士为多……西妇之裸体者,皆以极简略之笔出之,而色彩之浑厚,肌肉之凹凸,均显豁呈露”。[3](P26)李叔同也曾于1920年在《美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女性人体油画《女》,是民国时期较早登载于公开刊物上的女性人体画作品。1928年1月,林风眠在首都第一届美展中展出以女性人体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油画作品《人道》,“连日参观者均在千人以上”。[4]
总体上看,艺术家阵营主要从艺术场域的独立话语权和女性人体艺术的审美纯然性这两个方面来建立女性人体艺术的合法性。首先,从专业角度提出人体写生是艺术进步的必要手段,话题主要围绕着观察方式、结构比例、技法技巧等方面展开。如针对民国初期中国人体绘画创作因缺乏写生而人体比例、结构特征不准确的弊病,汪济川在1918年撰写了《洋画指南》一书,采用人体插图的形式系统地介绍了女性人体的特征和比例,展示了东、西方女性身体比例上的差异。艺术家指出,进行人体写生是学习西洋画的基本方法,人体模特儿写生能够直接帮助从艺者提升创作技巧和艺术水平。“最初研究西洋画的人,一定要晓得西洋画的门径和格式。西洋画中,应当注意的是写实、写真、写自然的几种东西。有了这几种东西,所以就有模特儿的发生。”[5]从模特儿入手描绘人物,使作品人物“不至有头重脚轻,四肢不相配,不合学理之种种缺憾”。[1](P40)“人体曲直线极微,隐显尤细,色致复,而形有则。习艺者于此致其目光之所及者,聚其腕力之足追随者,毕展发之。并研究美术解剖,以详悉人体外貌之如何组织成者。”[6](P409)艺术家必须通过人体写生才可能实现画面对人体的准确和真实表达。汪亚尘指出:“画人体,不一定要像西洋人的身体就算是美。中国的女模特儿,只有六分之一的躯干,但是我们研究的时候,能够把全部美的要素综合起来,也未尝不能见到优良的地方。”[7]他希望运用西式艺术创作手段,通过对中国模特儿的写生,挖掘中国女性身体的审美价值,在中西艺术合璧的前提下实现人体艺术的本土化创作。艺术家借鉴西方观念对人体艺术进行客观、严谨的论证,奠定了国内艺术场域建立女性人体审美话语权的专业理论基础。它是艺术家最为有力的武器,也是封建卫道者在抨击人体艺术时难以根本动摇的。其次,在人体写生“工具论”之外,艺术家竭力强调女性人体的审美纯然性。他们撇清人体艺术与色情图像的关系,要求人们剥离长期以来将女性裸体视作淫秽之物、将女性裸体公开展示和观看视作道德沦丧的观念束缚,还艺术以“纯真之眼”。“一般人之所以反对裸体画,固有以前的遗毒。但是现在一般研究艺术的人们不去把人体美详详细细地用文字说明给一般人,实在也是一个大原因。”[8](P12)艺术家撇开身体的社会属性,专注于其自然生理的外在形式,详细地分析了女性人体之美。倪怡德提出,女性裸体的美不但表现在由身体构造所形成的“曲线美”上,还表现在它变化统一的形式之美以及“人体之肉感、圆味、色彩而引起之美”,“尤其是妙龄丰盛的女性的肉体,她那高高隆起的一对乳峰,她那肥大突出的臀部,她那玉柱一般的两条大腿,是何等的能引起我们生的愉快,爱的活跃”人体“外有微妙之形式,内具不可思议之灵性,合物质美之极致与精神美之极致而为一体,此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也”,而最能表现这些美的,乃是女性的人体。[1](PP47-50)在近代中国,艺术家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将女性身体从传统文化的层层包裹中剥离出来,还原其自然形态,不但为艺术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同时也是对封建社会以身体社会属性来划分人群尊卑等级的传统制度的反叛。人体艺术的支持者坚持从艺术场域论证女性身体审美纯然性,为近代中国社会女性身体观念的解放提供了专业的思想及话语武器,并奠定了扎实的审美基础。它与女性解放运动领域对女性回复健康自然身体的要求相互呼应,从审美角度论证女性自然身体的价值,拓展民众的接受度,培养并提升其审美能力,使女性身体从废缠足、束胸等改造实践当中得到观念和心理层面的升华,促进女性身体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论争的艰难反复使艺术家意识到社会整体观念对建立艺术独立话语的重要影响。“身体是人人具备的东西……现在一般以裸体为可羞耻的观念,大约还是受礼教的遗毒的缘故,这是非赶紧打破不可的。”[7]封建思想观念不肃清,人体艺术作品即便广泛传播,也只能“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以致于“学了体格还未匀称的裸体画,便画猥亵画”。[10](P346)必须从艺术领域中走出来,投身于道德伦理观念的重建工作,才可能实现艺术的自律性发展。唐隽指出,“裸体的本身无丑可言,他是具有很纯洁,很高尚的美趣的”,认为裸体为丑的人无外乎“有道德迷的”和“有遗传和习惯性的”两种,前者“拿道德做中心”,后者“拿道德做陪衬”,[11]都与裸体本身无关。艺术家阵营提出女性艺术人体纯粹的审美价值,极力撇清它与“诲淫”裸体画的关系,切断了男性权力中心社会赋予女性裸体与情色诱惑的必然联系,为人体艺术博得一条独立发展的途径,也为女性身体挣脱传统观念束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提供了契机。刘海粟尖锐地指出,如果“见女性而肉体颤动,性欲勃起,岂必杀尽天下女性,方能维持所谓风化耶?然而天下女性仅为导淫之具矣,岂有此理乎”?他揭示了卫道者的无耻虚伪,敏锐地指出男性因自身的欲望而谴责其欲望对象这一思维逻辑的荒谬。在传统礼教思想根基受到撼动之际,卫道者悍然以礼教思维逻辑来抵制人体艺术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也是他们在事实上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
三、“艺术家的春天”——人体艺术创作的蓬勃发展
1926年7月《北洋画报》第7、8期登载的主题漫画《模特儿之今昔观》,表现了女人体模特儿“昔日”荣耀,“今日”却受到官方禁令的“砍杀”。但1926年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女性裸体在大众媒体中大量出现,与这一漫画表述的女人体模特儿遭禁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矛盾正体现了“人体模特儿”受到官方禁止而人体图像却在社会中大肆流行的事实。
《北洋画报》和《良友》杂志的表现较为突出。天津的《北洋画报》刊载女性人体作品相当积极,在1926年到1928年间,陆续刊载了众多作品。除了前述的《模特儿之今昔观》(1926年7月),还有《艺术界之双十》(1926年 10月)、《女子三百六十行之十——“模特儿”》(1927年4月)、《画家与模特儿》(1927年10月)、《模特儿姿势之研求》(一共九幅,在1927年11月第139期到12月第150期上不定期地连载)、《艺术家的工作》(1928年3月)、《画室中之模特儿》(1928年 8月)、《艺术家的春天》(1929年4月)等等,画中模特儿全部是女性,集中表现了人们对女性模特儿的关注。其他类型的女性裸体也以艺术之名频频出现。《北洋画报》从1926年创刊到1937年停刊,一共出版1578期;同时,在1927年7月到9月间,发行副刊共20期。据笔者统计,在这近1600期当中,该画报共登载女性人体作品500余件,基本达到平均每三期便有一件女性人体出现的频率,所登载的女性人体作品数量,在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中无出其右者。《北洋画报》编辑部“自证清白”式地指出:“裸体画一物,在研究艺术者之目光中,只见其曲线之美,绝无淫邪之念可言;其观为诲淫之具者,适足以见其心目之不正而已。……吾报毅然刊载裸体画片,完全为介绍世界美术起见。”[12]《良友》杂志登载的裸体图像相对较少,但是它自1926年起的10年间共有135期出现女性全裸或者半裸的各种摄影、绘画、雕塑等图像两百多幅,从绝对数量上看仍是相当多的。此外,其他刊物也纷纷响应,登载女性人体成了这一时期报刊杂志的突出特征,几乎无裸体不成刊(报)。正如刘海粟所说:“今者模特儿之訾讼纷纭,变本加厉:流氓伪模特儿以诈财;迂儒谤模特儿以辅道;官厅皇皇颁发禁止模特儿明文以示威;报馆记者冷刺热讽以模特儿为论资;画匠画贩亦能学说模特儿、人体美、曲线美以影射。”[1](P29)尤其在该事件基本尘埃落定的1927年,媒体登载女性人体图像数量急剧增加。如图1所示,《北洋画报》、《良友》在1926到1929年间对女性人体的刊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高潮,直到1937年之前,它始终作为社会的热点话题而受到普遍关注。

图1 1926-1937年《北洋画报》、《良友》登载女性裸体图像数量单位:件
可以说,正是“人体模特儿”风波促成了近代中国社会表现及观看女性裸体的热潮,它造成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人体艺术在中国艺术领域中的强劲发展,并带动整个社会对女性人体的围观。
四、以艺术之名:性别控制的新途径
从艺术场域来看,艺术家在为人体艺术正言的同时,对女性身体初步体现出抛弃传统束缚的客观和理性。但是,站在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来看,艺术家对艺术独立场域的坚持,一方面使艺术朝着更加专业化的道路发展,另一方面“画地为营”,也使人体艺术成为艺术家在艺术场域内部的自娱,显示出艺术家对其反对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妥协。“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基础,使人体艺术在面对社会广泛的质疑时,出现了观念意识和表达语言的局限和贫乏。
事实上,这场论争至始至终贯穿着强烈的男性权力色彩。将“人体模特儿”事件正反双方的交锋层层剥离可以看到,其矛盾的核心是国族语境框架下近代中国新旧意识形态的斗争。它不以女性解放为目的,相反,论战双方实际上表现了同样的男性立场。艺术家与封建卫道者一样,并不真正关注身体的所属者——女性本身的思想、观念、情感等等。他们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将女性身体视作“物”来进行视觉形式上的表述,后者则更加关注女性身体反映的社会等级和权力意志。艺术家强调女性人体美是纯然的美,展示或观看女性人体艺术非但不是道德的沦丧,相反是进步、文明的行为。他们深愤于“一般轻薄少年,以及无业流民,利用时机,乃大印其荡妇娼妓之裸体照片,名之曰模特儿,招徕贩卖;无耻画工,乃亦描绘其似是而非之春画,亦名曰模特儿,四处兜售,每见报纸广告,连篇满幅,不曰提倡人体美,即曰尊崇模特儿,盗取美名,淆乱黑白,以之诈骗金钱”,[1](P36)指责部分民众的无良、礼教观念的虚伪,但是作为男性精英,他们批判使女性人体在艺术领域之外演化成低俗欲望对象的封建礼教思想,却无法看到这一思想归根到底是为包括性别在内的等级权力控制所服务的。刘海粟等人一再强调人体艺术不是“裸体少女”画,而是大众媒体中出现的“人体艺术”作品,正如其反对者所言,绝大部分是年轻女性的裸体。社会舆论在赞赏或者抨击“人体艺术”时,所指称的对象也往往是“女性”的裸体,而非“人”或“男性”的裸体。“人体艺术”成了“年轻女性人体艺术”的代名词。他们的“权力”仅能触及艺术场域之内的女性身体,在场域之外,剥离了艺术高尚外衣的女性身体并不受其庇护。对性别权力问题的不自觉或者回避,使艺术家们无法真正应对歧视和丑化女性身体的传统思维和行为惯性。人体艺术作品对女性身体的展示,非但未能从根本上为女性及其身体解放提供平等、自由的机会,相反,在性别权力问题未能厘清的前提下,它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对女性裸体的围观和消费狂欢,导致了女性身体在艺术名义下遭遇新的沦陷。
事件中作为争论焦点的女性,其声音的缺失,进一步显示出这仅仅是一场不同立场的男性权力之争。女性的身体是“人体模特儿”论战双方争执的焦点,然而无论是标榜文明进步的艺术领域,还是坚守传统道德阵地的卫道者,都没有从女性作为独立的人的角度审视其身体。作为被观看、讨论的主体,女性本身的意识并未得到双方的关注。在这场男性精英的权力争夺中,女模特儿经历着怎样的心路历程、现实遭遇?她们的赤身露体是出于本人意愿还是被男性话语绑架?面对如自己的镜中影像一般的女性裸体,女性观众又有怎么样的心理感受?在男性主导的进步话语“胁迫”下,女性几乎完全失去了发声的机会,她们的思想、认识、情绪在史料文献中难以寻觅。女性的身体实际成为新旧阵营中男性精英斗争的工具。论争双方相互为对方扣上“不道德”的帽子,但无论是卫道者将女性身体视为淫秽,还是艺术家试图从建立艺术场域之内独立、纯洁的女性身体从而与艺术场域之外的其他女性身体相区分,归根结底都是将女性置于由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男性精英设置的标准之中。可以看到,在民初这场缺乏性别权力自觉的“人体模特儿”事件中,在对女性身体的“显”、“隐”争辩间,双方都并没有跳出男性权力控制的意图,他们的出发点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
人体艺术的争论反映出女性身体观念在近代中国社会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角力,最终显示的不过是新旧社会转型中不同阵营男性精英的对峙。新的男性精英在通过这场女性身体“解放”运动夺得话语权的同时,也重新建立了对女性的掌控途径。延续着男性权力中心的思维模式,“人体模特儿”之争因而必然会出现人体艺术获得胜利和女性身体重陷困顿的矛盾结局。
[1]刘海粟.人体模特儿[A].沈虎编.刘海粟艺术随笔[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2]姜怀素请禁模特儿[N].申报,1926-05-05.
[3]刘海粟.参观法国总会美术博览会记略[A].朱金楼,袁志煌编.刘海粟艺术文选[C].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4]首都第一届美展[J].良友,1928-01-30.
[5]周勤豪.模特耳[J].美术,1920,4(2).
[6]徐悲鸿.节录徐悲鸿君由法来信[J].晨光,1921-06-01(1).转引自李超.中国早期油画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
[7]汪亚尘.人物画与研究裸体之解说[N].时事新报,1923-01-31.
[8]刘开渠.禁止展览裸体画[A].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
[9]倪贻德.论裸体艺术[A].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
[10]鲁迅.随感四十三[A].鲁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唐隽.裸体艺术与道德问题[J].美术,1921,3(4).
[12]裸体画问题[N].北洋画报,1926-02-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