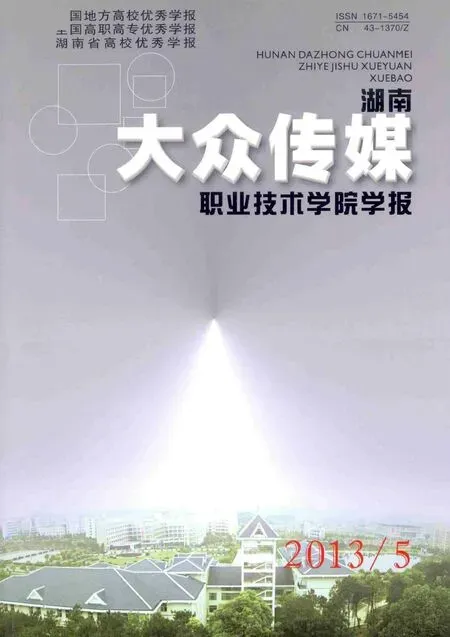用解构主义解读克鲁亚克的《在路上》
司梦云 章玉龙
(1,2.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杰克·克鲁亚克(1922~1969)是一位美国小说家、作家、艺术家与诗人,是美国“垮掉派”重要作家,其生活方式放浪不羁,作品大多具有自传性色彩。虽然他的作品相当受到欢迎,但是评论家并没有给予太多喝采。杰克·凯鲁亚克的主要作品有《乡镇和城市》、《在路上》、《达摩流浪者》、《地下人》等,但是最知名的作品还是他创作于1957年的小说《在路上》。《在路上》和金斯堡的《嚎叫》一起被公认为“垮掉派”文学经典。 “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作家克鲁亚克提出, 是指美国二战后一群松散的年轻诗人和作家。在英语中,“beat”原意“敲击”“拍打”,而克鲁亚克赋予 “欢腾”或“幸福”的含义在其中,就像音乐中“节拍”一样,形容他们狂欢、自由、随意的生活。“垮掉的一代”中的大部分成员玩世不恭,笃信自由。他们推崇自发的文学创作理念,不遵守传统的创作常规,甚至结构和形式杂乱无章,非常混乱,所以其作品通常受到争议。但是“垮掉派”文人颠覆了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体验极端的生活方式,其对主流文化的态度严重影响了后世人们对文化的理解。有些文人也对东方文明充满了兴趣,他们向西方传播关于“禅宗”和“佛教”的知识,也影响了西方的文化。
《在路上》这部作品描写的是青年学生萨尔为追求个性自由,与狄安、玛丽露等一伙儿男女开车横穿美国,一路狂喝烂饮,耽迷酒色,流浪,吸毒,性放纵,在经过精疲力竭的漫长放荡后,开始笃信东方禅宗,感悟到生命的意义。本文将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学说从这部作品的结构、写作方式、内容以及主题上分析这部小说。
一、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通常被认为是稳定的文学结构的消极倾向,也迎合了进入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们对于模式化,规范化的普遍厌恶心理。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的全面复苏和飞速发展以及科技的高度进步,使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工业生产飞速发展的时期。大工业社会中生产的规范化、产品的规范化和模式化进一步加深了西方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造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相脱节带来的精神危机。在探求摆脱这种精神危机的途径的过程中,整个社会也产生出一种对于规范化、模式化的普遍的厌恶心理。于此相应反应在人文学科乃至艺术上,对于所谓恒定不变的结构、中心,以及终极意义的全盘否定,对于人的主体能动作用的突出强调,便使西方6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文化朝新的走向发展。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结构主义思潮的发展都反映了这一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是现代形式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最先提出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首先就是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即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为了反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乃至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解构运动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换言之,它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哪怕这种自由仅仅是一曲“带着镣铐的舞蹈”。 解构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抗,反非黑即白的理论。
德里达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无中心的系统,结构也是不固定的,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就不是一个规定明确,界限清楚的稳固结构。文学作品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它的意义总是超出文本范围而不断变化游移,在有限的结构中不断地解构自己。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分别是开放性和无终止性。
后来耶鲁学派接受并发展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观点,其中杰弗里·哈特曼突出强调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强调语言在符号领域中由于符号的相互替代而具有自我结构性质,使我们无法将它看成一个结构稳定、意义明确的对象。语言不确定,所以文学文本意义也会不确定。
二.解构主义在《在路上》的体现
(一)情节上的体现。解构主义提倡打破逻辑、连贯、封闭的故事情节,用一种开放的情节结构取而代之,使其充满不确定的多样性,这样,就呈现出淡化情节、打破完整性、强化碎片和开放性的结构特点。而这种松散结构就是为了全面解构作品,散乱的文本对应了混乱的世界和破碎的生活,打破了传统价值观念中稳定统一的秩序。《在路上》的情节就不具有完整性。[1]作者自发性地写作,任意而为,叙述了“我”和旅途伙伴们几次横穿美国大陆并且最后南下墨西哥的的旅行经历,酗酒、吸毒、性放纵、高速开车以及旅途中的零碎事件相互穿插构成了小说的主体。总体结构松散,叙述杂乱,没有固定的中心,使人摸不着头脑,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可以说是作者对头脑中超越时空的自发性思绪进行了拼接而成连接起来的。
(二)叙事技巧中的体现:“自发性”写作。杰克·克鲁亚克推崇 “自发性” 的写作手法。 他任意而为,对其自发性的思绪进行拼接从而构成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形乱意不乱,忠实记录了40年代末、50年代初“垮掉的一代”生活方式,算得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垮掉的一代”的浪漫传奇。自发性写作实际上是把理性和非理性、把随意性和深思熟虑有机结合起来,并不是玩胡乱创作。克鲁亚克本人觉得,抛弃那些所谓的语法和章法的限制,以内心来独自叙说,为自己书写回忆,才是文学创作的真谛。所以,“垮掉的一代”的作家会吸食毒品或者致幻剂,使意识混沌,在极度兴奋中写作,也就不难理解了。[2]
杰克用一部打字机和一卷120英尺长的打印纸,花了不到三个星期就完成了此书的初稿。这样的写作速度还遭到了“本末倒置”的批判。克鲁亚克随兴而至, 不顾及结构,其作品充满了思维的碎片和时间的碎片,[3]从这两段引文中可以看出:“第二天早上埃迪亚去了,我没去。梅杰买来了许多食物,作为交换,我只得做饭,洗碗。我的时间安排得很满。一天晚上,罗林斯家要举行一个大型晚会,他母亲旅游去了。罗林斯邀了所有的朋友,并让他们把威士忌带来,然后他又给一些认识的姑娘发了邀请。他让我主持晚会。晚上来了很多姑娘。我给卡罗打了个电话想知道迪安现在干什么,因为迪安清晨三点总要去卡罗那里。晚会后我也去了。”[4]51“在此期间,我开始频繁地去旧金山;我试遍了书上说的怎么搞定姑娘的办法。我甚至同一个姑娘在公园长椅上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天亮都没有结果。那姑娘来自明尼苏达,长着一头金发。那儿有许多同性恋者。有几次,我带着枪去旧金山,当一个同性恋在酒吧里凑到我面前时,我就取出枪。[4]77”他的写作并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具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整体感, 完全是按照作者亲身经历的顺序以及记忆的流动进行书写。
(三)在主题中的体现。德里达认为文本没有固定的意义,没有中心,没有本质,一切都在同一个平面上。作者在《在路上》中一一记述了主人公萨尔与朋友穿越美国的一次次旅行经历,记录了沿途的自然风景和人们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方式。不批判,不歌颂,不探求,不解释,事无巨细地呈现在读者面前。[5]而且在这部小说中没有一个确定的主题,读者可以理解到不同的主题。一是宗教主题。迪安和萨尔及他们朋友的旅行,实际上是多次内心冒险的旅程。“垮掉的一代”对于上帝有着广泛的概念,其灵魂紧紧与他们自己的经历息息相关。他们发起旅行,穿越美国,就是在寻找美国,寻找美国人内心的美德。这实际上就是两个天主教徒游遍美国寻找上帝的故事。二是20世纪50年代的男性概念和迁移性思想。这些词语看似无关,但是克鲁亚克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成为反抗社会规范的另一种方式。萨尔和迪安试图用植根于美国的征服和自我发现的模式来代替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男性主导的模式,旅行则非常具有象征性,尤其是对于男性。但是他们不仅认为遵循社会规范是一种限制,而且在很多方面认为女人也是这样。重新分配权力使父权制下对于女性统治的权力丧失,他们试图把道路上的自由作为男性身份的主要判断。这部小说内容相互交错归根结底是在平衡男性力量的得与失,即使他们否认传统的界定,但是迪恩和萨尔依然依赖于他们自我界定中的男性身份。最后他们的分别,反映了萨尔理解了他们在路上寻找的完全自由的局限性,它是从属于文化和身份的。三是成长的方式。萨尔并没有忽略他的青春期和成熟期,而是努力地去度过,努力地平衡着这些反对力量而迪安正好相反,他就像个孩子,总是在路上,追求自己所谓的自由。
杰克·克鲁亚克也是“垮掉的一代”中最有名的作家之一,本文试图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学说从这部作品的结构,写作方式,内容以及主题均具有不确定性,打破传统模式和规范化,以其解构的形式解释50年代的美国垮掉派对美国传统和权威的反抗以及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
[参考文献]
[1] 马新国. 西方文论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 陈城. 后现代语境下对凯鲁亚克《在路上》的解析[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
[3] 董艳华. 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解读《在路上》[J]. 黑龙江科技信息.
[4] [美]克鲁亚克. 在路上[M]. 文楚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
[5] 罗全. 论《在路上》的叙事技巧和主题意义[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