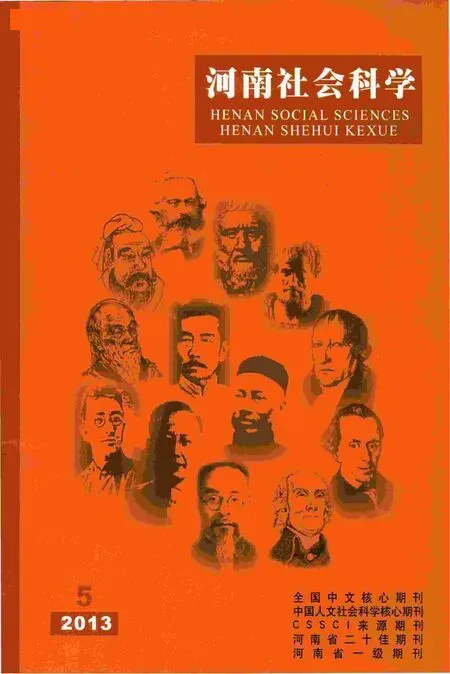理性破裂与世界重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评析
罗建平,王亚萍
(1、2.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在西方哲学史上,无论是本体论阶段追问存在是什么也好,还是认识论阶段追问如何认知存在也好,更不论是语言学转向后追问用什么认知存在也好,贯穿始终的一个根本性的命题就是理性,或曰对理性的坚守或质疑。而把哲学理性与人类社会进步的现代性问题加以综合考察的思想家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既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社会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哈氏的哲学社会学研究就是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他以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在社会主体交往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与矛盾,并提出了解决现代社会困惑的方案。虽然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带有明显的“乌托邦”的色彩,但这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及其本质,采取措施防止并消弭异化现象,构建完善的社会交往系统还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因之,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的研究与述评尽管常常见诸学者视野之内,但从社会学角度对之进行再评述也许并非完全多余。
一、理性之维及其现代困惑
西方近代哲学是从笛卡尔开始的,当笛卡尔提出怀疑开始、思维至上与天赋观念时,实际上是重新确立了被中世纪宗教神学压抑了上千年的理性意识,因而“我思故我在”具有几近振聋发聩的意义,自此以后西方哲学研究尽管在研究范式上几经变迁,但康德以来的哲学家们大都趋向从理性的角度来认识、调控世界及人的自我意识和人的思维,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转向也不过是理性意识的一个矫枉过正的反映罢了。诚如人们所言:“尤其的存在者(指人)的这个无限的宇宙,本身是一个理性的宇宙,它可以通过一种与之有相互关系的普遍科学彻底加以掌握。”[1]以至于韦伯也用理性观念来剖析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本质,在韦伯看来,欧洲资本主义化亦即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经典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对金钱的欲望和尽可能多地获得利润,韦伯考察了世界各主要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希腊、印度、中国、罗马等的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得出结论:欲望、金钱、商业、经营、获取利润存在于所有人身上,因而所有这一切并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或者说它们“与资本主义本身并不相干”,“对财富的婪欲,根本就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2]。因而韦伯把近代意义上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称为理性资本主义,而现代性的动力就来源于理性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在韦伯看来,理性将导致世界发生革命性的变革——社会将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向运用工具理性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工具理性成为西方所有社会活动主导的价值取向。
工具理性无限地延长了人的手,延伸了人的眼,开阔了人的脑,工具理性使得科学兴盛、技术发展、物质富足,使得西方社会由前资本主义进入资本主义,由前现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韦伯恰恰把理性资本主义的过程称为现代化的过程,但工具理性对人的控制也进而带来一系列消及问题,消费主义盛行,权力意识膨胀,主客体对立,人类社会相互疏离而破碎原子化,作为个体的人的相互对立而“单面化”。究其原因,韦伯认为是人们把理性归之于“目的—工具”之一维,重视外在世界而忽视内在自身,强调法律意识而放弃伦理诉求,人类世界与人类生活的分裂,人对外在世界产生疏离感,世界成为人的异己力量,他人也成为自己的异己力量,人们感到“自由的丧失”(韦伯语),在韦伯看来,这种异己力量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及当代世界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中,人们被囚禁在工具理性的牢笼里而无法逃脱,人们无法克服理性给文明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具有鲜明批判意识的学术团体,早期法兰克福派的代表霍克海姆、阿多尔诺等人一直致力于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在他们看来正是工具理性的胜利导致现代西方社会的种种矛盾和物化现象,韦伯也把多元理性仅仅局限于目的理性,从目的合理性这一视角来剖析资本主义的发展,哈贝马斯一方面秉承了早期法兰克福派的批判意识又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克服了韦伯的悲观意识而有对现代性的坚守,“现代性——一项未竟的事业”是他的重要观点之一。按照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的观点,理性意识早在前资本主义甚至在人类的远古时期就成为人类意识活动的根本,人只有在理性引导之下不断地认识自然把握自然,从自然中获取人类生存必要物质条件,人类社会才能进步,这是一个理性工具化与合理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不断地对自然斗争的过程,与自然的斗争是人类生存与进步的前提,与自然的斗争也带来人与世界的对立与异化,这实在是人类自身的一个二律背反,因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必须导致“一种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文化批判”[3]。哈贝马斯同样反思了韦伯的悲观思想,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之所以以理性精神解释资本主义而又陷入悲观情怀之中是因为他还未从传统意识哲学的基本框架中摆脱出来。传统意识哲学重视人的主体意识,但却从主客体二元对立之中来洞察人的理性能力和主体性,其目的合理性的本质表现就是选择工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正是建立在主客体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哈贝马斯认为,要克服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所陷入的危机就必须超越意识哲学,意识哲学的致命缺陷就是“把人的精神活动同人的行为、生活环境、‘生活世界’以及把人联结在一起的最普遍的语言中介物分裂开来”[4]。这样的理论不仅无法解决认识论本身的基本问题,而且对于认识论以外的更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也束手无策。因而哈贝马斯试图在哲学之语言学转向的学术背景下,以语用学方法论为基点,把人的行为与行为主体联系起来,把具有主体意识的不同的人联系起来,摆脱形而上学的窠臼,挽救理性的分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其学术努力的结果就是建立影响深远的具有对话意识的交往行为理论,以期进一步推进已然发展的现代化事业。不过,交往行为理论的前提是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观。
二、“生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者是现象学奠基者胡塞尔,他认为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以一种漠然、冷静、客观的姿态分析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从而使世界成为客观化、数字化、理论化、逻辑化的世界。这实际上是挥舞科学主义的大棒横扫人的自然本性,是对人的主体意识的极端漠视,是把世界变成一个仅供科学分析的对象而忽视人的意识的无限丰富性,因而晚年的胡塞尔“主张从科学的世界和逻辑的世界向前科学的与前理论的‘生活世界’的回归”[5]。哈贝马斯沿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进而从波普的三个世界理论入手把“生活世界”分为三个维度: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是人置身其中的物理世界,这是一个以主客对立表现的世界,客观世界的呈现以真实性为原则;社会世界是人与人互动交往形成的属人世界,这是一个主体与主体协同行动的世界,社会世界的稳定以规范性为前提;主观世界是人经验到和经验过的内心情感世界,这是一个主体内心独语的世界,主观世界以经验性为特征。三种世界相互区别,也相互贯通,相互渗透,客观世界是物质载体,社会世界是意义生成,主观世界是精神显现。生活世界的三个维度要求相应的行为角色,相对于客观世界的是目的理性行为,相对于社会世界的是规范协调行为,相对于主观世界的是戏剧性行为。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这三种行为涉及不同的世界关系网络,但它们都是理性的行为,受理性的支配,有着不同的有效性标准,存在于客观世界的目的理性行为要求真实,存在于社会世界中价值理性行为要求正当,而存在于主观世界的实践理性行为要求真诚,三者统一于人的交往行为理论之中。
哈贝马斯同意韦伯的观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合理化与理性化过程,但他进而认为合理化是逐步推进的,人类的前行也是永无止境的,理性化是多元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不是对立的而是交融互渗共同推进的,但是当代资本主义却过分强调工具理性,运用工具理性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没有实现经济、文化与个性的全面发展。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哈贝马斯提出了系统——与生活世界相对的物质生产——这一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主要依靠两个系统,一个是经济系统,一个是政治系统。经济系统表现为货币统治世界,政治系统表现为法律取代伦理。货币统治世界使世界异化,人成为物的奴隶,人的主体性丧失;法律取代伦理使道德在社会生活中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使社会仅凭权力运行,合法性仅凭权力来决断,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自由的丧失”。哈贝马斯把两种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统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他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就是“将道德因素从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中驱逐出去”,就是“生产关系自主的系统从外部侵入生活世界,就像殖民的主人进入部落社会一样”[6]。
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像韦伯那样对现代文明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在他看来,遭到系统入侵的生活世界中仍然会蓄积着某些能量,这些能量也在改变着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并不只听凭经济和行政上所采取的措施的摆布。在极端情况下,则会出现被压制的生活世界的反抗,出现社会运动、革命”[7]。哈贝马斯进一步为人类社会发展勾勒出一种新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没有暴力的共同生活使个人的自我实现和自主权有了可能。这不是靠牺牲团结和正义,而是借助于团结和正义”[8],它就是“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他认为,这个未来社会之所以美好,不是因为它同某种具体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相关,而是因为它与形式上完好的主体性有关,是一个通过语言理性来维持的理性社会。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就是要“在日常实践自身中,在交往理性被压制、被扭曲和被摧毁之处,发现这种理性的顽强声音”[9]。
三、交往行为与理性重构
“语言学转向”是西方哲学在20世纪的一次“华丽转身”,自此之前一直上溯到笛卡尔总体来说可以称之为意识哲学,意识哲学的困惑不是忽视人的主体价值而是从形而上学、二元对立观出发强调主体客体的对立,不是从行为主体与行为对象的联系而是从两者的对立中认识世界。意识哲学也忽视不同主体间的双向沟通,强调主客体之间的单向的认知与被认知,行为主体成为孤立的个体,这种哲学观念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作为统一体的精神世界片面化。哈贝马斯正是看到了当代社会合理化进程中的局限和意识哲学的困惑才步许多语言哲学家的后尘转向语言哲学,并且哈贝马斯突破了格里斯、弗里泽、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语义学哲学观,提出了语言学哲学观并把它运用于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抓住天生就与那些通过语言中介的交往行为有关的语用学,从对话和行动能力方面来考察并界定理性,使理性不再是传统主体哲学以意识作为框架的认知理性,而是在语言沟通活动中的互属互动理性。与之相应,人的主体也不再是一个仅具有认知功能的主体,而且还是一个包容着其整个交往和活动的实践主体。正是由于将传统哲学的所谓自我反省的认知理性能力演变成语言交往的理性沟通能力,社会化的个体才在其语言与行动的客观联系中,必然作为‘交互主体’或‘大型号的主体’而得以存在和发展”[10]。
哈贝马斯认为主体与世界、主体与主体之间不是独语而是交流,不是独白而是对话,这是一种“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为了实现有效的交往与交流,每一个主体表达内容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对他人的表达应是能理解的,相互之间应该是互理解的。不同的主体之间应是平等的,每一个主体都应该有权独立地发出声音、提出质疑、作出回应,都应该有权独立地作出解释、判断、说明、论证和反驳,也应该有权独立地表达思想、意识、情感、好恶和意愿。交往行为得以有效进行须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是真实性原则,真实性原则要求言说者以客观中立的立场正确地陈述外在客观世界的真实状态,使之变得具体可理解;第二是真诚性原则,真诚性原则要求言说者把自己内在的思想、意见、愿望和情感真诚地表达出来,使交往在互相信任中进行;第三个是正确性原则,正确性原则要求言说者遵循社会共同遵守的价值伦理规范,使交往行为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
交往行为比独白行为更有其合理性,蕴含在交往行为中的交往合理性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交往合理性是建立在主体间的关系基础之上的。它的核心是主体间的关系,与传统的囿于主体——客体关系的理性概念相比,它所研究的是主体间达成一致的可能条件。第二,交往合理性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语言或人的交往资质内在地包含一个真正的主体间一致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4]。在此,哈贝马斯把语言提升到哲学本体论地位,也提升到人的本质属性的地位。第三,交往合理性遵循一定的操作原则,操作应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依一定的先验原则和伦理规范进行,因而操作是程序性的。第四,交往合理性是具有可误性的。由于主体间的交往都是带有主观性的,归根结底都可诉诸理由,但这种理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其本身也是具有批判性的。
总之,这种把理性放到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中去考察的交往合理性与传统的理性概念相比,尤其与韦伯将理性理解为实现目的之手段的观念相比则更加广泛、更加全面地阐释了理性的观念,使得不同主体可以通过协商与对话实现理解与共识,把生活世界从“殖民化”境遇中解救出来,实现生活世界的重新整一和理性的全面发展。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始终不渝的一个信念就是如何凭理性把人们从蒙昧意识中解救出来,这实际上也就是西方人苦苦追寻的现代性之路。如今,现代化似乎已然完成以至有人宣称历史已进入后现代时期,然而对哈贝马斯来说,一方面现代化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另一方面他深刻地认识到理性现代化越来越显示出片面性与局限性,从交往行为出发重新审视人类的理性意识,实现理性精神的全面均衡发展,重建破碎的世界,这种理论在非理性思潮占据哲学世界主导地位的20世纪实在是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
[1]张汝伦.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批判[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6):5—10.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哈贝马斯.政治短论集[M].法兰克福:舒尔坎普出版社,1981.
[4]艾四林.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评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37—39.
[5]刘志丹.交往如何可能: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新探[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34—39.
[6]J.Habermas.TheTheoryofCommunicativeAction[M].Boston:Beacon Press,1987.
[7]哈贝马斯.生产力与交往[J].哲学译丛,1992,(6):57—60.
[8]哈贝马斯.追补的革命[A].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9]得特勒夫·霍尔斯特.哈贝马斯传[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10]王振林.评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