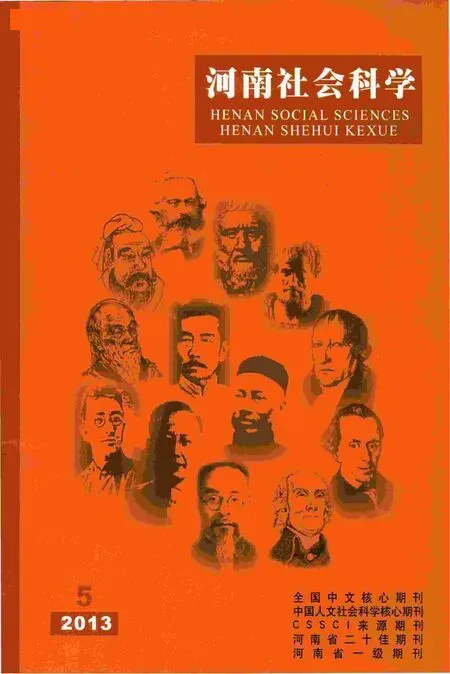亚文化心态视域的我国“下半身”诗歌研究
冯万红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1990年代以来,身体在诗歌中成为频繁的表现对象,但诗歌中的身体成为最有冲击力和最能引起争议的话题,恐怕还是应该归功于2000年以来的“下半身”诗歌。这个诗歌流派在其理论宣言里将身体定位成单纯展示性活动和性心理的肉体,这种肉体写作遭到评论界的诟病,被认为这是诗歌放弃精神维度的坚守,诗人放弃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持有的精英意识和人文关怀的具体表现。但笔者认为应尽量还原当时“下半身”诗歌肉体写作的原生场景,即以“下半身”诗歌流派的理论宣言和诗人具体的诗歌作品作为考察对象,从这批诗人的文化心态上对“下半身”诗歌中的肉体写作给予分析,具体论述这种亚文化心态的体现、原因以及带来的问题,以期对“下半身”诗歌中的肉体写作能有一个更全面辩证的认识。
一、何为亚文化心态
在“下半身”诗歌中,展现的是一种肉体写作,而这种肉体写作折射出这批诗人的一种心理状态,笔者将其称为“亚文化心态”。所谓“亚文化”,正如迈克·布雷克所说:“亚文化是随着试图解决由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引致的集体经历的问题的努力而产生的。”[1]也如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揭示并解决(尽管有些不可思议)母文化中隐藏的或解决的矛盾。”[1]这与“下半身”诗歌流派登上诗坛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吻合。2000年,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入,社会转型进一步加剧,改革和社会转型会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动从而引发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在尚未解决之前会催生出一种“亚文化心态”,这种心态的显著特征就是冷漠、嘲弄、无价值立场、无善恶美丑之分,甚至在矛盾综合体中游刃有余、自得其乐,抱着一种游戏和无所谓的心态,完全放逐和逃离意义。反映在“下半身”诗歌中,诗人表现出对道德的蔑视,对性的大肆渲染,并由此而获得一种宣泄的快感。
二、肉体写作:亚文化心态的体现
2000年7月,一批“70后”诗人沈浩波、尹丽川、朵渔、南人、李红旗、巫昂、盛兴、轩辕轼轲等创办了《下半身》刊物,并且开辟了诗江湖网站发布同步网刊。在其《创刊号》上,刊载了沈浩波的发刊词《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发表了在当时来说是惊世骇俗的流派宣言。在这篇宣言中,沈浩波认为:“‘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注意,甚至是肉体而不是身体,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而回到肉体……意味着让我们的体验返回到本质、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我们是一具具在场的肉体,肉体在进行,所以诗歌在进行,肉体在场,所以诗歌在场。仅此而已。而我们更将提出: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2]显然,宣言里将诗歌创作中的肉体写作就简单等同于人的“下半身”,是性心理、性活动的展现,并且这种心理和活动的展现成为诗歌中唯一的内容,这样的内容呈现的是一种极端形而下的日常生活状态,其背后折射出诗人宣泄的快感。正如陈仲义所说:“浏览宣言、文本、争论、访谈录,包括网上帖子,剔除某些极端成分,我们将‘下半身’社团所推行的东西,定性为一种肉身化写作。其核心取向可概括为:第一点,诗歌写作是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第二点:诗歌写作遵守快感(广义)、性感(狭义)原则;第三点:诗歌写作直指形而下日常性在场状态;由此引发语言技术层面问题,则可再补充—第四点:游戏‘段子’为言说特征的后口语。”[3]这便是笔者认为“下半身”诗歌中肉体写作的含义。下面就结合这批诗人具体的诗歌作品和理论宣言来看看这批诗人的肉体写作。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些“下半身”诗歌流派的诗人所创作的一些带有肉体的诗歌。在沈浩波那首和他的理论宣言《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同样带有震撼效果的诗歌《一把好乳》中,沈浩波用调侃的、口语段子般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场景,作者坦然地意淫着一位带着小孩的母亲,这样的场景虽然有着“我”为自己之前意淫猥琐样“不知羞耻”的坦然辩护而让人目瞪口呆,更有着直面事物而让人心惊的勇气,以及单刀直入说出事物真相而让人胆寒的锐利。这种坦白和锐利是让人害怕的,因为没有任何的遮蔽和委婉的表达,而是直接就这么赤裸裸地被诗人表达出来,是现实社会中大部分普通的个体都会在内心深处所拥有的,只是不过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心理阴暗角落,被所谓的文明和理智压抑住,不会被公布于众,更遑论在诗歌中这样坦诚地表达出来。
还有一些纯肉体展现、纯生理活动的诗歌,这些诗歌多半都是性活动的展现,在“下半身”诗人的诗歌中大面积并且公然存在,以至于“下半身”诗歌流派被丁友星在半岛诗坛网上的半岛诗帖里给予了一个评价[4],即被评为中国诗坛的两大黑暗之一(另一个是垃圾诗派),其创作的这些纯肉体的展示性心理、性行为的带有黄色和意淫色彩的诗歌被集中挑选了28首并被命名为“下半身”最淫秽的作品(下流版),这些诗歌正如王世强所说,“性活动、性生理、性心理、潜意识等被赤裸裸地张贴、展览出来,黄色、类黄色话语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语言手段,性的快感、狂欢似乎成为了他们追求的唯一目标”。这些诗歌中的肉体也符合笔者在本文开头所给出的肉体写作的定义,在这种肉体写作中,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在这里已经被抽空,思想的内涵被归结为零,我们看到的只是简单的肉体狂欢,以及完全没有美感和精神内涵的动物般的单纯生理活动,生命本该有的厚度和意义在这里全部被抹掉了。
而在沈浩波的理论宣言《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中,一开头就写道“强调下半身写作的意义,首先意味着对于诗歌写作中上半身因素的消除。”[2]而上半身在沈浩波看来,意味着“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年轻得还没有来得及去受更多的压迫,我们就已经觉醒了,我们已经与知识和文化划清了界限……我们用身体本身与它们对决,我们甚至根本就想不起它们来了,我们已经胜利了”[2]。在摆明了对这些几千年来我们在进行诗歌创作时都奉为圭臬的知识文化传统等的厌恶和不屑以后,沈浩波的这篇宣言紧接着对一些东西展开批判、宣布决裂,首先是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中华几千年来的唐诗宋词的传统,他认为“传统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你们都认为我们的写作必须跟它有关?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身体,有我们自己从身体出发到身体为止的感受。这就够了,我们只需要这些,我们已经不需要别人再给我们口粮,那会使我们噎死的……唐诗宋词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可笑地拥有了一种虚妄的美学信仰,而这,使我们每个人面目模糊,丧失了对真实的信赖”[2]。然后就是西方现代艺术的传统,对于这种传统,同样也是给予全面的否定,“源自西方现代艺术的传统就是什么好东西吗?只怕也未必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一代中国诗人是怎么匍匐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直起身子来。这个东西一旦成为传统为人们津津乐道,它腐朽的一面便越来越暴露出来,更多的时候,它已经作为一种负担而必将为我们抛弃”[2]。诗歌所赖以生存的中外传统都摒弃了,接下来就是对诗歌所应该坚持的艺术上的范畴即诗意进行了否定,“这个一点现代感都没有的酸词只能被那些学院派的冬烘先生奉为至宝。而对于现代艺术来说,取消诗意将成为一个前提。我们不光不需要传统的,来自唐诗宋词的所谓诗意,我们干脆对诗意本身心怀不满。我们要让诗意死得很难看”[2]。接着就将思想、抒情、大师、经典、承担、使命统统贬损了一遍,在这样的贬损和否定中,下半身诗歌将这么多年以来对优秀诗歌的要求、标准和定义都全部推翻,将一直被奉为诗歌创作的准则也抛弃,于是,整个诗歌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被我们为之维护的血肉和骨骼全部在一瞬间坍塌了。这份宣言接着亮出了他们认为诗歌需要坚守的,或者说他们认为一首诗歌所应当具备的核心要素是什么,那就是“追求肉体的在场感,意味着让我们的体验返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2]。最后还不忘强调一下“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唯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2]。这一带着很多武断词语的、充满极端口气甚至是有些歇斯底里般神经质样的总结,表明这批诗人对以往诗歌的传统和诗歌艺术进行了彻底否定,对诗歌所应坚守的精英意识和精神内涵完全回避,是一种不容回旋余地、斩钉截铁的告别,肉体写作由此被这一诗歌流派奉为唯一的宗旨。这些由诗歌和宣言所呈现的“下半身”诗歌中的肉体写作,是这一诗歌流派亚文化心态的具体体现。
三、亚文化心态的原因
“下半身”诗歌流派的诗人所表现出的这种亚文化心态是有一定原因的,笔者认为这种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追逐自由和觉醒的策略
由上述沈浩波的理论宣言以及这批诗人的一些诗歌,我们看到诗人们想通过肉体写作而达到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个人正视自己的肉体,以此达到自我的觉醒和追逐自由的目的,也许为达到这种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太过于偏激和极端,但这种偏激和极端在当时的诗坛或许是他们不得已为之的一种手段。毕竟文学发展到2000年已经黔驴技穷,甚至说黔驴技穷都显得有些高调,因为文学更甚至是诗歌本身已经在社会处于边缘之边缘的地位,已经不足以引起重视和轰动,而这批诗人当时还只是刚刚离开大学校园,这群初出茅庐的后生要在诗歌领域争得话语权,要让自己的诗歌创作所喻示的思想观念引起文坛轰动,引发社会关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在宣言里,还是在诗歌中引入肉体,切合了当时整个社会注重个人欲望这一社会思潮。更何况当时整个大的社会环境相较于“十七年”甚至“文革”时期已经有所松动,并没有“十七年”甚至“文革”时期用以控制创作的极端规则和制度,也没有1980年代那种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使诗歌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一部分。而同时,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已经有女性诗歌中的身体铺路,而这些女性诗歌中的身体,在精神内涵上还是有所坚守的,在表现的身体形态上,还没有扯下最后的“遮羞布”,这样就让“下半身”诗歌流派的诗人可以在将策略锁定为肉体时还有可供开拓的空间,予内予外都是条件具备的,但也正是这种因为予内予外条件都具备的现状迫使其策略要更极端,甚至达到一种偏激或者说偏执才容易引起更大的轰动,这样必然就会造成一些诗歌中确实出现如外界评论那样的纯肉体之作。
(二)文化断裂的反应
联系到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社会转型进一步加剧,旧有的文化已经坍塌,而新的文化、观念并未完全建立,新旧文化之间有些还无法承接,从而给人在精神和思想观念上带来矛盾和迷惑,导致对于传统文化、传统观念解构后的迷茫和无所适从的状态,这样的状态让这批出生于1970年代,成长于1990年代末的诗人难免会在诗歌中以一种冷漠、揶揄、嘲弄、反讽的面目示人,而在这种面目的背后,其实是内心的迷茫和空虚,在面对很多问题没有答案和无法解决时,只能在精神上向下滑落,用更深的堕落来麻醉自己,但其实这种拯救是徒劳的,这种徒劳背后其实代表的是一种绝望,因为采用上述的方式对于解决问题于事无补。所谓越空虚越堕落、越堕落也就越空虚,人在两者的纠缠和裹挟中,只能迷茫和坠落地越来越深。这种状态其实有一定的代表性,折射出在当今,一部分人在社会进一步深入改革,面临进一步转型的过程中,很多文化观念和传统道德被解构得分崩离析,而在传统的碎片中我们却无处可依,于是离经叛道的张牙舞爪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落寞和无助,失去所谓令人可笑的思想深度和厚度以后,似乎只有人的欲望和本真的生活状态是唯一可以信赖的,正如郑述裕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也面临着一个精神的危机阶段,现存的一切法则都失去其权威性,文化不再成为值得夸耀的身份标志,只有本能和欲望才是唯一的实在。本能和欲望构成一种文化语境,人们行为的法则。人仿佛又重新从洪荒的年代开始跋涉,沿着本能欲求去获得一切”[5]。
四、亚文化心态所带来的问题
对于这种亚文化心态的评价,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停留于好和坏的判断,而应该结合这种心态产生的原因给予客观的、多维度的评价。
首先,产生这种亚文化心态纵然是因为这派诗人所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但这种策略带来一定负面的影响是事实,诗歌是文学中的精品,也是文学中最能体现文学品质的体裁,也许1990年代以来,文学已经边缘化和无人问津,但是如果为了让自己借助诗歌宣扬的自由与觉醒的观念引起重视,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实际某种程度上牺牲的是诗歌的精神维度与艺术追求,而失去这些因素的诗歌还能否称为诗歌呢?这种客观上的牺牲,造成了损坏诗歌本身的做法是不是有欠斟酌?而在这种策略中,抛弃一切只为自己惊艳出场的极端做法,甚至将诗歌创作的现在和过去断然切开,并且还是断得干干净净,不但不可能,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为了改变几千年来中西方皆有的用道德、文明以及其他种种去压抑人的肉体的现状,这批诗人的这一策略“首先确立一种平庸的身体伦理,然后通过对身体某部分的怪异强调与变形,挑衅这种平庸伦理,试图通过一种触犯众怒的伦理暴力,来使自己的写作获得意义。此时,身体成为不折不扣的工具,在对抗一种道德专制中建立起另一种道德专制”[6],即从过去的伦理暴力走向如今的身体暴力,这样的境况就像一面镜子的两面,其实其内在的逻辑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样不但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觉醒,反而会使人重新陷入一种蒙昧的洪荒状态中。更何况追逐自由和觉醒,也不能以完全放弃任何积极层面上的文明为代价,任何的自由不是绝对的,任何的觉醒也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前提之上。
其次,这种心态所带来的客观效果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即达到对过去文化中个人欲望遭受压抑现状的祛魅,但笔者认为这种祛魅应该把握一定的限度,更不应该只停留于此,还应该更往前走一步,即怎么去构建和提升更好的社会文化。
这种粗陋的肉体写作客观上也导致诗歌内容的粗鄙化,艺术上的平实化,诗歌在精神和美学维度上的逃亡,不利于诗歌在保证自身质量的基础上再向前发展。而尽管这一流派的诗人所带来的肉体写作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反抗之前文学中对人的身体、人性的过度压抑,追求自由,为了表达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不满,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承认,压抑是文明的必要代价,如果文明驯服不了横行冲撞的欲望,社会的基本秩序将走向失序”[6]。同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出现一些问题和矛盾是必然的,但为此而表达不满的方式是一种冷漠、嘲弄、揶揄、放逐意义甚至无所谓的态度,本身也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自残方式和自杀行为,更是一出贼喊抓贼的荒诞场景。而有担当的诗人们,出于敏感的天性,也出于良知和责任,他们开始介入时代现场……去与现实的残酷作短兵相接的碰撞……当很多人在现实的压力下归于乡愿和犬儒时,作为“时代的孤儿”,诗人们依然要背负沉重的担子前行,以寻找到更为坚实的地基和更富理想主义精神的公共价值观(刘波,2011)。而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策略。
[1]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J].诗刊·上半月刊,2002,(8):78—80.
[3]陈仲义.肉身化诗写刍议[J].南方文坛,2002,(2):36.
[4]白云饶孤城.昏评现在的垃圾派下半身派诗歌[EB/OL]http://club.bandao.cn/thread-1245174-1-1.html,丁友星贴,2009-10-24.
[5]郑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53.
[6]王岳川.肉体沉重而灵魂轻飘[J].美苑,200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