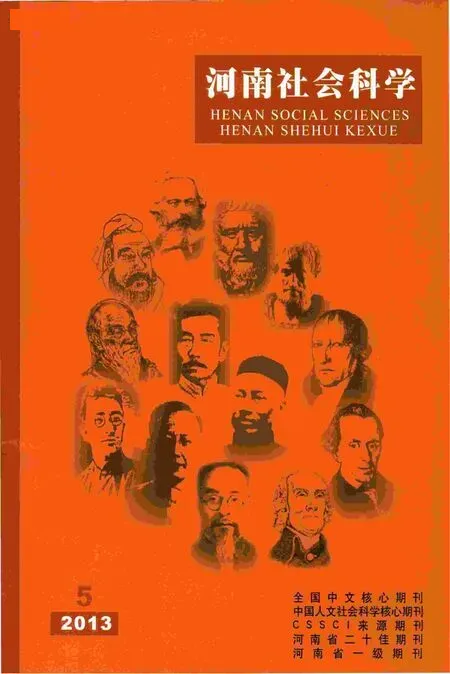论李大钊的“自觉”意识及其当代意义
何亚娟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自清末鸦片战争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降,“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难题摆在了中国人面前。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的李大钊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作了艰难的探索。在他探索的思考和实践历程中,贯穿着强烈的“自觉”意识。
所谓“自觉”意识,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基于问题的反思、批判,从而自我创新、自我建构的一种意识。李大钊从当时中国的情势出发,由爱国自觉到青年自觉、阶级自觉、文明自觉至人类自觉的“自觉”意识发展、演进,实践和勾画着未来中国和世界的理想蓝图。梳理、分析这些“自觉”意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李大钊的思想发展脉络,也为今天“中国往何处去”、“世界往何处去”和“人类往何处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爱国自觉
近代世界,西方资产阶级的胜利,叩响了封建制度的世界历史性的失败丧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被强迫纳入世界体系格局中,被迫开眼看世界。传统的天下观逐渐瓦解,民族国家意识开始萌发。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建立。然而,新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只不过是“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1],国家“内政俱废”,人民“生机断绝”。辛亥革命后每况愈下的现实,使得许多人对国家的观念和心态发生调整。
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心态的,要算陈独秀提出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陈独秀试图辨别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什么是自觉,应该爱国还是应当自觉。在陈独秀看来,爱国是“爱其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2],自觉是自觉“国家之目的与情势”。“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弊一也”[2]。若国家为民则可爱,否则不可爱。如不知这一目的而爱之,则为盲目;其后果只能是被野心之君利用,给人民带来灾难而不会带来幸福。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奥、日等国人民的爱国主义都是盲目的、错误的。不认识国家的情势,像朝鲜、土耳其、日本等国家,结果是“爱国适于误国”。“爱国是出于情感,而自觉是出于理智”[2]。因此,不能保障人民幸福的国家,不爱也罢。而基于当时中国的情势,他认为中国不可爱。“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2]。这样,陈独秀以辨别爱国、自觉之义,将自觉心归结为有国家不为喜,无国家不为忧,得出了“残民之祸,恶国家胜于无国家”的结论,以“自觉心”否定了“爱国心”。
笔者认为,陈文的分析固然有其合理之处,然而,或许由于过分悲观痛苦,该文无异于助长了国内悲观厌世之风。李大钊以《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批驳了陈独秀的“自觉心”,阐明了他的爱国“自觉”。首先,李大钊认为陈独秀的所谓的“爱国心”实际上就是“厌世心”——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李大钊认为,陈文中“厌世之辞嫌其泰多,自觉之义,嫌其泰少”[3]。按此种“自觉心”去做,中国将坐而待亡,人民只能做亡国奴。其次,李大钊提出了不同的“自觉”观念。“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3]。李大钊与陈独秀一样,反对盲目爱国,但李大钊强调,人们应有“自觉”的“爱国心”。国家好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绝不能因其国家不足爱就不爱之。“与其于恶国家而盲然爱之,诚不若致国家于善良可爱之域而恬然爱之”[3],不能以从未享有过可爱之国家,自暴自弃。国家由人创造,要发扬爱国心,努力建设。因此,今日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自觉近世国家之真意义,而改进其本质,使之确足福民而不损民”。改进国家本质,为人民谋利,使人民真心诚意地爱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谓所逢情势,绝无可为……慎勿灰冷自放也”[3]。应发扬“公民”之新精神,无论现状如何,都应努力奋斗,积极改造国家以爱之,不能放弃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文明之人,务使其环境听命于我,不使其我奴隶于环境。太上创造,其次改造,其次顺应而已矣。国家之存立,何莫不然”[3]。在李大钊看来,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一种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就是自觉力。这也是李大钊乐观进取的人生观的体现。李大钊这一努力创造的爱国自觉心,澄清了当时人们的错误思想,给人以锲而不舍、自强不息的力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起到了激发斗志、鼓舞人心的作用。
二、青年自觉
爱国自觉之心需要爱国主体之自觉。民国建立后中国的一般国民素质并不尽如人意。在时人看来,唯有那朝气蓬勃的青年们才能担负起当时建设新国家的重任。自新文化运动以后,李大钊逐渐形成了一种“青年情结”,他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新生命诞生之努力》、《青春》中向青年发出了奋起自觉的呼唤,把国家振兴的希望直接寄托于青年身上。
青年是青春的别名,不仅仅是年龄的象征。在李大钊看来,宇宙无尽,青春无尽,青春是美好的,青春常在是一种幸福。青春的本质是一种生命活力。中华民族已是白首之民族,已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垂死的中华民族希望“不在白首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3],即青春中华的再生。青年是国家之魂,一切新创造、新机运是青年独有之特权,青年的文明是奋斗之文明,但今日之中华仍是老辈把持之中华,“非老辈之强乃青年之弱”,因此,青春中华再造“不能不求青年之自觉与反省”。故青年自觉,一要自觉具备青年精神——断头流血牺牲之精神、慷慨悲壮之精神、起死回天创造之精神、主体性之精神,二要自觉承担其使命——青春中华创造之使命,三要自觉承担其责任——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觅新国家,拓新世界,实现创造青春中华之使命。
为此,他还希望青年建立这样一种自觉:“一在冲绝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去来无罫。全其优美高尚之天,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此固人生唯一之蕲向,青年唯一之责任也。”[3]
也就是说,青年一方面应冲破历史观念的重压,尤其是冲决代表专制主义,打破“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3]的孔学罗网,打破偶像的权威,保持无拘无束的青春创造活力;另一方面应当摆脱机械生活的负担,不为物的奴隶,保持独立人格,从而保持今日和明日的青春,与进化的宇宙竞进。这一思想也为他以后呼吁青年到农村去作了思想铺垫。
三、阶级自觉
如果说,李大钊的爱国自觉、青年自觉更多倾向于天演公例、新胜于旧的进化论思想,而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进而逐渐形成了基于唯物史观的自觉阶级意识。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的发表,体现了李大钊阶级意识的萌发和初步形成。尤其是1919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发表,暗合着李大钊自觉阶级意识的形成。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大体可分为过去、现在、将来三个部分,即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其中唯物史观最为重要,“离了他特有的历史观,去考他的史观,简直的是不可能”[4]。而将三部分联系起来的是阶级竞争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4]。
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李大钊认为,由于现代经济组织的发展,促进了劳工阶级的自觉,从而产生了阶级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命运。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4]。
阶级意识的形成和确立,改变了李大钊考察中国问题的视角。中国国民运动手段在李大钊那里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著名的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认为,中国社会具体实际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生机、一切机能都已闭止的社会,“遇着时机,因着情形”,中国问题必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作一个根本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也才能得到解决。“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4],但如不去用“阶级竞争说”作工具,消极坐等,那么经济革命的实现和成功,恐怕遥遥无期。至于中国国民运动的主体,李大钊也从早期注重知识分子群体的力量转向工农大众的力量,早期唤醒青年的自觉相应转为唤醒劳工的自觉、庶民的自觉、工农大众的自觉。在1919年发表的《青年与农村》和1925年发表的《土地与农民》文章中,李大钊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是劳工阶级的主体,解除农民的苦痛、愚暗,就是解除国民全体的苦痛、愚暗,农民的解放才是国民全体的解放。若能把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动员并组织起来,使之投入国民革命,那么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必有希望。他呼吁青年到农村去,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唤醒愚暗的农民,唤醒农民的阶级自觉,帮助农民树立阶级意识,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产生阶级觉悟,从而改造农村,并进而改造社会。此外,他在提出青年到农村去的同时,还领导和指导了北方工人运动。
同时,李大钊对世界问题的分析,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的评价等,都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这些都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用的借鉴。
四、文明自觉
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离不开自身的文明建设。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被迫以西方文明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撼动了中国的思想界,促发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中西文明关系的深入探讨。李大钊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在《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李大钊较系统地分析了东西文明的特点、对待东西文明应采取的态度和新文明的取向,在指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4]的前提下,分析了东西文明的不同之处。他认为,东西文明“平情论之,互有长短”[4]。东西文明为世界进步不可或缺的左右两翼。他同时指出,东洋文明的缺陷是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疲命于物质下。面对西方文明的剧烈冲击,李大钊认为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拒绝西方文明是不可能的。西方之动的文明“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因此他主张“割除种族根性的偏执”。“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4]。中国当务之急要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同时他又认为,“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4]。故为挽救世界危机,就必须开掘新的文明,有新文明的崛起 ,这种新文明就是“第三文明”——俄罗斯文明。
李大钊的“第三文明”观是其文明自觉意识的体现。“第三文明”观独特、深刻又有前瞻性。具体讲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它打破了以往文明发展观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是亦此亦彼。“第三文明”观是其调和思想的体现。“调和”不是东、西方文明的简单叠加,非折中主义,非一锅煮式的搅和、化一,更非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开放状态下平等交流,是并立竞进。它是多元思维的自由调适,反对人为地撮合、融通,不以单方标准和思维模式规范对方,而以双方的互补、相牵为鹄的,即不同文明在并立中互补,在互补中竞争,在竞争中发展。
其次,它是动态的文明,是文明的创新。“第三文明”作为一种新文明,一种新事物,是对旧事物的既保留又克服,既继承又发展,是变革和扬弃,是辩证的否定。“第三文明”即非东方中心论,也非西方中心论。“第三文明”是动态的文明,是具体内涵不断与时俱进的文明。“第三者,理想之境,复活之境,日新之境,向上之境,中庸之境,独立之境也”[3]。俄罗斯文明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尚存向上发展之余力”。
再次,它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容纳、超越。“第三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东方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4],西方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4],俄罗斯文明是对现代性的容纳、超越。文明并没有终结。
最后,它是人道主义、自由的文明,理想文明,具有普世意义。在李大钊看来,俄罗斯新文明是建立在人道主义、自由基础上的文明。俄罗斯经过十月革命的风云“而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4],俄国人因此将能够创造出“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的新文明,人道主义、自由的文明必是世界人民“翘首以迎的”。
五、人类自觉
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更多的是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李大钊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他是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但他关心的不仅是简单的救亡图存、富国强民,更关心人的解放、人类解放;他认定只有人与世界才是真正的目的,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具有自觉的人类意识。
李大钊深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毕生奉献于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中国当时的情势下,他认为“直接行动”、“根本解决”是求得解放的根本之道,但他并未像后来的有些人那样,将阶级斗争绝对化。相反,他认为马克思只是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的前史,而非历史的全部时期或阶段。阶级斗争仅是获得解放的手段,而非目的。人道主义对李大钊有根本的影响,“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4]。李大钊认为,马克思所讲的人类真正的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而不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在过渡的时代应该特别注意伦理感化和人道的运动,以铲除人类在前历史中所受的恶习。经济问题的解决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但物质进步不能自动提高人的素质。因此,李大钊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要“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4]。在李大钊看来,社会主义不是穷的,是要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自由是真正自由,社会主义是增加自由、保护自由的,社会主义与纯正的平民主义Democracy是一种精神,社会主义是互助、相爱的,社会主义不仅要使人们过上富裕的生活,更要使他们享有更多的自由与民主,同时,也将一扫资本主义的恶俗的气氛和商贾的倾向,劳动将是愉悦的,艺术与个性也将得到真正的发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是李大钊追求的价值目标。
李大钊关爱中国和中国人民,同样关爱世界和世界人民。“我相信人间的关系只是一个‘爱’字”,不仅要爱自己的家、同胞、国家,还要像爱自己的同胞一般爱世界的人类,“爱世界人类的全体比爱一部分人更要紧”[4]。在李大钊看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爱或恨某一个特殊国家,它首先是反抗强权的运动。因此,中国的学生运动不是爱国运动,我们“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可爱的道理”,“我们只承认学生运动,是反抗强权的运动”[4],这也是李大钊对自身前期爱国观的超越。反抗强权,就要主张公理;哪里有强权压迫公理,不管是什么人,都应该反对。“压迫亚人的亚人,我们固是反对,压迫亚人的非亚洲人我们也是反对;压迫非亚洲人的非亚洲人,我们固是反对,压迫非亚洲人的亚洲人,我们也是反对。强权是我们的敌,公理是我们的友”[4]。他反对帝国主义,并不因为他们是西方人,是“非我族类”;也不仅是因为他们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员所规定的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4]。显然,李大钊的主张不是排外主义、闭锁主义、种族主义,而是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李大钊看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的时代,故而他认为中国应主动进入世界体系,成为其中富有竞争力的一个成员,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希望以改造中国为基础,通过对中国问题的解决,不仅尽到对中国的责任,更尽到对世界和人类的责任。人类永远在国家和民族之上。李大钊热诚地向人们呼吁:
不要受狭隘爱国心的拘牵。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们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我们的家庭范围,已经扩充到全世界了,其余都是进化轨道上的遗迹,都应该打破。我们应该拿全世界的生活作家庭的生活,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生活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的一部分的责任。[4]
基于对世界经济时代的考察、对人的关怀、对人类未来发展的终极眷注,李大钊设计了新的世界组织——联治主义。这个世界组织“应该是自治的,是民主化的,是尊重个性的”[4]。它不再以多数强制少数,乃是靠着共同的认可;彼此间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他认定,人类是朝着天下一家的世界大同进化的,民主主义、联治主义是其中的一个程级,将来的世界必是世界的联邦。联治主义是个性的自由和共性互助的统一,自由和秩序的统一,“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的统一。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就要“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4],即建立一个没有阶级、人人平等、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理想社会。李大钊这一设想恰恰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初衷相契,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界说的未来的理想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自由人联合体。
纵观李大钊的自觉意识的演进,可以说,他的自觉意识从根本上看,是对现代性的容纳和超越,其价值取向是对中国命运、对整个人类命运和可能性的自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语境已发生巨大变迁。就中国而言,现代民族国家已基本建成,民众的绝对贫困状况已根本改变,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世界而言,全球化、信息化迅猛发展,世界格局有了巨大变化。在人类享受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时,现代性的负面影响也在考量着人类的智慧和价值追求。随着世界历史向纵深发展,“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逐渐生成,人类也必将于自己正在经历的新的阶段,发展出新的自觉意识。笔者认为,这也是李大钊的自觉意识给予我们的当代启示和意义。
[1]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4]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