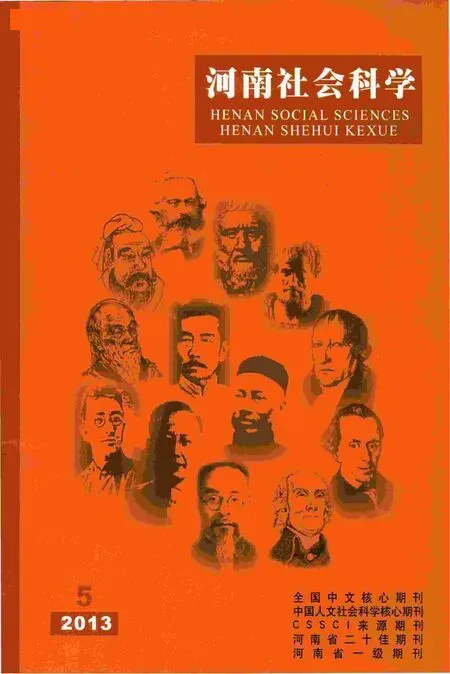清代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
马 珺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2)
任何形态的社会要想正常存在和发展,都需要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但是,不同的社会与历史发展阶段,社会控制的方式和手段是不同的。从早期人类社会的禁忌、习惯,到后来的道德、宗教、法律、行政等,任何社会时期社会控制的方式和手段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因为社会是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虽然近代以来法律的作用与地位日趋凸显,逐渐成为最有力也最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但是,由于社会和法律自身的局限性,它同样离不开其他手段的配合与支持。
中国历朝的立法,大多属刑事立法,民事立法的内容相对较少。而在民间大量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尤其在宋之后,更多地适用以习惯法为内核的家族法规、乡规民约等。而且,凡属轻微的刑事纠纷未必按国家司法管辖去告官审理,大多也是听由民间依习惯法调处解决。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在我国的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形成了种类繁多的习惯法,并被全面传承下来,加之统治者的积极态度,使其在广泛的领域内得到运用。清代习惯法已有相当规模,“民事法律不仅表现为国家制定法,更多地表现为传统习惯法”①。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在社会控制中互动并进。
一、清代习惯法发挥社会控制作用的时代背景
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经济体制、浓厚的血缘宗族伦理与组织、“无讼”的思想意识等因素是清代习惯法发挥社会控制作用的历史原因。清代特殊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则是习惯法发挥社会控制作用的现实因素。
(一)经济的发展使新的生产关系亟待调整
首先,地权分化,永佃权②和“一田两主”③等新的经济形式产生。清代,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到鸦片战争爆发的道光二十年,人口已过4亿④。而耕地面积的增长未能跟上人口的增长速度,结果造成人与人、人与地关系的紧张,各种因土地关系而产生的矛盾凸显。特别是明清时期,非身份性的私人地主获得长足发展,土地买卖频繁,定额地租、货币地租流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步为租佃契约关系所取代;农业生产率和商品化程度显著提高,土地收益不断增加。这些都是佃农向地主争夺土地所有权、佃农经济独立性提高的有利条件,也是促成地权分化的历史动因。自明中叶以后就开始流行于东南地区的永佃权和一田两主,到了清代和民国时期,已蔓延全国,在若干地区甚至成为主要的租佃制度和土地制度。永佃权和“一田两主”的形成,虽然没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但通过地权分化,割断了地主与土地的联系,限制了地租剥削量。然而,因此产生的新的生产关系所引发的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是以《大清律例》为核心的法律控制体系难以预料和应对的,这就为调整此关系的习惯法的存在留下了发挥作用的自由空间。
其次,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清代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为农产品商品化提供了前提。这种变化的产生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变化的性质是农业中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渐破坏,为小商品经济所替代,并由小商品经济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发展的方向就是资本主义对整个农业的统治。在许多农业生产部门中,出现了富农、经营地主、资本主义租地农业家式的新的农业经营方式。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的手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流入市场,商品经济更加活跃。广大农民也积极投身于商品交易活动中,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商业性的浓厚,使广大乡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的“义利之辩”、“重义轻利”的伦理思想受到冲击,人们开始追逐利益,强调公平,寻求保障,杜绝隐患。
再次,社会关系日益契约化。清代伴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和人口流动的频繁,契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纽带,并且日趋复杂。与此同时,人们之间相互的依赖性和信任感受到了新的挑战。所有这些,导致了此阶段民事矛盾、冲突和纠纷剧增。尽管社会结构、经济形式、法律关系已经变得日益复杂,然而官方并未做出适当的回应。大清律例体系还是仅仅满足于道德训诫,仅仅满足于日常生活秩序的理想梦幻,从而导致国家法律与社会生活,尤其是与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和日常生产、生活严重脱节。所以,清代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以调整“户役、婚姻、田土、钱债、继承”为核心内容的习惯法,获得了发挥社会控制作用的广泛空间。
(二)皇权衰落与法律的失控
随着“康乾盛世”的过去,皇权渐渐失去昔日的威严。原有的以《大清律例》为主轴建立起来的法律控制系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因素迅速变动的情形下,已经渐渐不能适应社会的变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
首先,以《大清律例》为中心的法律系统庞大混杂,科条繁多,自相矛盾,妨碍了官员执法的积极性、主动性;律典文字表述的晦涩难懂便利了贪官污吏欺压百姓,进一步恶化了阶级矛盾。尤其是法律规范中的不合理条款与规定,致使民众对清廷更为反感。如旗人明显的特权地位引起了汉人的怨恨与不满。
其次,法律控制系统执行过程存在弊端。主要表现是:(1)国家的司法运作往往不能满足主体基于伦理道德评价的利益要求。加之晚清地方官吏利用民间争讼获取不当利益的行径,也引发百姓对诉讼的厌恶心理⑤。人们往往将进入衙门提起诉讼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救济途径,极少和极不愿意与官府和官衙发生任何关系。(2)中国社会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并存。“宗族处理继承、立嗣、祭祀等事务,行会管理贸易和公平竞争,而乡村负责地产诉讼及买卖契约或租赁契约”⑥;“民间可以根本不理官府已经做出的裁决,而重新进行调解。并且,民间调解的效力可以否定官府的裁决”⑦。于是,民间社会自发形成了一套适合自己运行机制的规则——习惯法,形成了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社会机构与组织——宗族与乡绅,以大家共识的方式约束和管理自己,追求共同的目标,实现整体利益,协调各方面关系,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实现民间社会自治。
二、习惯法与国家法互动的体现
马克斯·韦伯曾说,中国历史“乃是一部皇权试图将其统辖势力扩展到城外地区的历史”,但实际中的情况是“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了,乃至消失”⑧。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古代社会民事立法的薄弱,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民间具有一系列非官方制定法存在的传统和社会现实基础。正如梁治平所说:“国家没有、不能也无意提供一套民间日常生活所需的规则、机构和组织,在国家法所不及和不足的地方,生长出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法律。”⑨所以,清代在运用划一的法律促进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和中央集权强化的同时,也不得不允许习惯法的存在,甚至在法律上予以确认。
(一)给予少数民族一定限度的自治权
首先,清朝统治者采取因族制宜、因俗立法的原则,对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立法。如对蒙古族有《理藩院则例》,对藏族有《西藏通制》,对回族有《回疆则例》,对青海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有《番夷成例》(《番例条款》),对西南民族有《苗例》,等等。这些法例,都是对各地方各民族习惯法的整理与总结,符合各民族历史传统及风俗习惯。比如,在诉讼程序及证据制度方面,蒙古、青海、宁夏、甘肃地区少数民族重视“设誓”,因此《理藩院则例》规定,允许当事人在所属佐领或管旗章京处“设誓具结”作为判决依据,保持其神明裁判色彩。
其次,清朝统治者注意尊重少数民族地区首领对发生在本族本地区内案件的审判管辖权。清廷通过中央派遣的官员对重大案件进行上诉审或再审、复审进行一定的监督。最后,清朝统治者在制定和运用法律时,注意中央法律和民族地方的特别法律之间的协调和融合,逐渐增进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共性。例如,在《蒙古律例》中的“盟长扎萨克出缺报院限期”条中引用了《大清律例》的“迟误公事例”的规定。
(二)对民间旗民交产习惯的认可
清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封建政权,为了维护旗产的所有权,确保旗人在经济上的优势,法律严禁旗民交产,不许汉人典买旗地、旗房。康熙朝曾经明确规定:“官员、甲兵地亩,不许越旗交易;其甲兵本身种地,不许全卖。”⑩雍正七年(1729)颁发上谕重申上述禁令。旗民交产的禁令,违背了民间自由买卖、互通有无的自然规律。特别是入关以后多数旗人不事生计,生活困窘,不得不将旗地自愿典押、转卖于民人。因而,民间汉人依据习惯法自由典买旗地的现象不断发生。为此,康熙皇帝曾出内帑为旗人赎回典卖土地。雍乾朝,采取对业已典卖的旗地,由官方付给一定的地价,强行取赎。仅乾隆一朝,大规模“回赎”旗地共有四次,总计回收旗地3.7611万顷。但回赎旗地并未能按预期目的解决旗人生计问题,贫苦的旗人无力购买政府“回赎”的旗地。屡禁不止的事实,一方面反映了旗民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旗地私有化不可阻挡的趋势。咸丰二年(1852),颁布《旗地买卖章程》,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允许“变通旗民交产”。同治四年(1865),进一步规定顺天直隶所属旗地,“俱准旗户民人互相买卖,照例税契升科”[11]。从此,“旗民交产”正式合法化,以往旗田因“官有”而“免粮”的特权,也随之被取消,变成一般私有民田,八旗土地制度基本瓦解。
(三)对宗族组织、宗族法规的认可与支持
清王朝建立之后,统治阶级看到宗族组织在基层社会的普及以及宗族意识在广大民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地位,也看到宗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战争稍息,最高统治者即向宗族共同体伸出寻求联盟与合作之手,并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表示对宗族共同体的重视、认可与支持,在国家政权与宗族共同体之间形成合作关系。宗族共同体利用自己所具有的特殊力量维护宗族秩序,协助政权机关巩固地方统治;国家统治者则支持宗族组织并在一定范围内授权宗族,依据宗法族规实行有限度的自治。
顺治九年(1652),颁行上谕:“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12]康熙九年(1670),又颁行“上谕十六条”。其基本精神都是肯定宗族共同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标志着国家统治者对宗族共同体支持的态度。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四十六年(1684—1707),康熙皇帝先后六次南巡,抚慰地方巨族大户。雍正朝,这种有限度的宗族自治权得到国家法律的明确肯定。“族长”入律,各项权力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国家政权与宗法族权的结合达到高潮。嘉庆以后,各地普遍出现宗族组织将制定的成文宗族法送交州县衙门,正印官阅后即发文批示,以官府名义赋予宗族法效力,并保证其执行。这说明,统治者一方面加强与宗族的联系以及对宗族的控制,另一方面明确承认宗族法的强制效力,更多地利用宗族法,以稳定地方社会秩序[13]。
鸦片战争中,社会危机加剧,国家统治者无暇他顾,在地方秩序的维持上,更加依赖宗族共同体,放任宗族势力的增长。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国家统治者允许宗族共同体组织地方武装,以协助围剿太平军,靖乡安里,维持治安。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其他各类乡兵、团练。地方政府亦支持宗族武装,放任其发展。在此政策下,宗族武装、宗族产业、宗族法规,三位一体,自我膨胀,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14]。
(四)对典卖女子民间习惯法的认可
清代法典中有对买卖女子行为惩处的规定。如“典雇妻女罪”、“略人略卖人罪”等[15]。但是,事实上,在封建父权、夫权制下,妻子完全从属于丈夫,女子完全丧失其独立的人格,失去其应有的权利,更不用奢谈受法律保护。清代法典在地位和意志上都把女子看成是男人的附属品,无论是已婚还是未婚。所以,清代买卖女子仍十分普遍。从巴县和宝坻县档案馆搜集的131件清代“婚姻奸情”的案件中,买卖女子的案件占了68件。清代司法者承认、宽容了买卖妇女的行为。丈夫如因贫困所迫出售妻子将不会因违反法律规定而被处刑;当贫困的妇女情愿被卖以图活命时,无论她们还是她们的父母都不会受到惩处[16]。另外,对于童养媳的习俗,清代法典从来没有正式承认它,但在清代司法实践中却认可了这一现象。《刑案汇览》中记述了道光二年(1822)处理的一个案件,判语清楚地表明执法者把童养媳契约等同于订婚。法律包容了民间买卖女子的习惯法[17]。由此可见,清代妇女被广泛地当作商品处理,为她们所可能获得的代价或被买或被卖,这一习惯法得到国家法的默许。
(五)对民间契约的认可
传统中国社会里,旨在解决民间纠纷的各种契约文书,其权力来源不是官方强制力,而是民间的自发力量。人们订立契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结信”。清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交易空前频繁,在各类经济交往中,契约的种类、名称相当繁多,几乎每单交易都要书写契约。这说明清代人们对于契约文书的高度重视以及法律意识的增强。相当部分的契约因涉及产权归属、性质,双方当事人为取得合法权益的确认与保护,往往于订立契约后去官府登记注册,并缴纳契税。民间纠纷凡涉及私约者,官府也总要“调契查验”,以为判断依据。鉴于契券的重要,各地政府明文告谕百姓,凭契约执业,并将“虚钱实契”[18]等破坏交易正常秩序的行为,斥责为“例禁”行为加以禁止。而对于民间契约的管理与控制,国家主要是通过规定税契以及钱粮推收过户的登记和注册手续等手段来加强约束[19]。
所谓“有契斯有业,失契即失业”、“官有政法,民从私约”[20],一方面表明在民间社会中,契约对于确定普通百姓的权利归属以及解决相互之间纠纷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表明官府在解决产权争执中对于民间私约的倚重。它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民间契约与国家法律之间的相互关联,体现了契约所具有的维系民间社会秩序的“私法”特征。
(六)从官方判语看国家法对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与认可
《汝东判语》“桂如禄呈词判”中提到:有一弟弟为了阻止兄为其夭亡之子进行冥婚而提起诉讼。法官针对其引用《周礼》论证冥婚之非,首先表明了“生今之世,不能援古礼以妄改王章。安能执古制以妄补今律乎”的原则,然后指出,对于冥婚这种虽无礼制的根据,但民间盛行的风俗,律文中并未禁止,因此不能取缔,从而驳回了该诉讼[21]。
《问心一隅》中记载:道光末年,山东博平县七十多岁的老寡妇高姜氏,以前将三亩地以四十五千文的典价出典给小叔子高书行及其儿子高东岱、高东山(三人共同名义),现又请求高书行每亩再加五十千文将土地买断。高书行予以拒绝,而且周围也没有肯出这样高价购买的其他人。于是高姜氏捏称高书行既不肯买断土地还妨害自己将土地卖给他人,向官告状。高姜氏显然无理,然而考虑到老寡妇困穷的境况,知县胡学醇利用该地有“值十当五”的习惯[22],使老寡妇撤回了过分的卖价要求,同时也说服对方当事人在兼顾扶养亲戚的意义上作出了让步[23]。
像这样依据习惯法所作的判语在清代很多。当时,许多有心的地方官及其幕僚为了更好地进行审判,总是努力了解所在地的风俗习惯。如汪辉祖作幕友所著《佐治药言》和他任知县后所著《学治臆说》中,都提到要注重风俗习惯,以达到审判效果的“情法兼到”。
清代,法律和以道德为内核的习惯法,并行共进,互相弥补,相辅相成,共同实现社会调控的目的。国家一方面在一定社会领域内,时常放任习惯法调整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则将以道德为内核的习惯纳入法律规范之中,转变为内含习惯法的成文法规则,即“以德入律”。这些都是国家法与习惯法良性互动的表现。
三、从清代习惯法与国家法互动关系中得到的启示
当今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大量的习惯法顽强地存留在民间。中国乡土社会的法制现代化,应在整个国家法制建设的背景中进行。因此,国家法和习惯法的良性沟通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应首先依靠国家法解决问题,强调国家法的科学性、权威性、稳定性、规范性,强调执法者的职业化、程序化、规范化。其次,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即便把需要解决的问题纳入国家法的体系中,也不能完全就法论法,就审判而审判。必须尊重习惯法中合理、有效、积极的因素,在整个国家大和谐的背景下,力促办案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再次,科学、有效地消解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冲突,达到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良性沟通、互动与融合。努力提高基层民众的法律意识,更好地实现“送法下乡”,以求乡村法律秩序构建的完善与规范。中国特殊的法制语境要求我们的执法者不仅要有法律职业道德,要有较高的理性认识和司法智慧,还必须对民生有深刻的社会体察,对人民群众拥有深厚的真感情。对于案件机械套用法律条文,片面强调法律上的处理结果,只会使法律完全脱离社会和民众的期待,这必然导致裁判结果虽然形式上合法,却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情感。所以,我们既要借鉴、吸收、变通世界上先进的法制经验与技术,为我所用,又要尊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仍然存在且发挥巨大社会功效的精华。只有如此,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法治,才能真正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注释:
①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②永佃权是指佃户履行交租的义务以后,永远耕种或使用地主的土地。即使地主出卖地产,永佃人也不丧失其权利。永佃权人有交租的义务,但没有转佃、典押、出卖、继承“田皮”之权,否则即构成撤佃的理由。
③“一田二主”是指同一块土地的上层称为田皮、田面,由佃户享有它的使用收益权,是为皮主;下层称为田根、田骨,由原田主所有,是为骨主、田主。骨主从皮主处收取地租,由骨主向国家交纳粮银。皮主与骨主可以各自处分其田面权与所有权。“一田二主”使得原有田主的所有权不断地弱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土地所有权转移的复杂性。
④曹树基:《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卷,第832页。
⑤刘广安:《中华法系的再认识》,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7页。
⑥[英]S.斯普林格尔:《清代法制导论》,张守东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⑦徐忠明:《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⑧[德]马克斯·韦伯:《经济和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8页。
⑨梁治平:《清代习惯法:国家与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⑩[清]典馆会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卷,第187页。
[11]张晋藩:《从晚清修律官“固有民法论”所想到的》,《当代法学》,2011年第4期。
[12][清]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卷,第246页。
[13]朱勇:《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167页。
[14]朱勇:《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199页。
[15]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户律、婚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卷,第205页;第25卷,第404页。
[16]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17]判语写道:“民间于未成年之先,将女送至夫家,名曰童养,自系女家衣食缺乏,不能养膳,不得已为此权宜计,所以法令不禁,听从民便。”[清]祝庆祺,鲍书云:《刑案汇览》,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卷,第744页。
[18]“若虚(写价)钱实(立文)契典买……罪止杖八十徒二年。”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户律、田宅、盗卖田宅》,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卷,第195页。
[19]杨国祯:《明清土地文书契约》,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20]郭建:《中国财产法史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21][日]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范愉、陈少峰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1页。
[22]指卖价为十的土地则典价为五。
[23][日]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范愉、陈少峰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