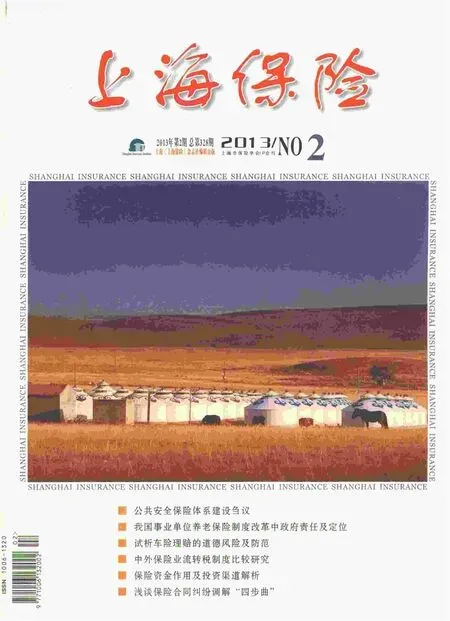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责任问题探析
□吴诵芬 向 婧
原告:上海金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直属支公司。
第三人: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案情]
2010年7月1日,原告上海金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直属支公司签订货物运输保险协议。双方约定,原告在发货后第一个工作日通过邮件或传真方式向被告及时投保。被告在收到原告投保要求后,逐笔开单,并向原告出具保险单。2010年11月25日,原告委托第三人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快递“金一版”、“第五套人民币珍藏册”一套至河北廊坊客户耿某,同时向被告投保,被告出具了保单。次日,第三人将包裹运送至耿某处。在交接验收货物时,发现“金一版”缺失,客户拒收。原告知情后,即向被告申请理赔,同时向公安部门报案。但是,被告以运件外包装完好无损,原告无法证明货物是在运输途中被盗为由作出拒赔决定。因双方协商未果,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保险金212,000元。
被告辩称:按照合同约定,被告承保的货物在运输途中灭失的,被告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案外人耿某收到货箱时,其外包装是完好无损的,在原告没有举证说明货物是在运输途中遗失的情况下,被告按约定不承担理赔之责。此外,涉案的托运单上仅记载了货物的重量,没有品名,仅凭重量无法证实原告已将货物交付给了第三人,原告对此负有举证义务,不然,只能说明原告在订立合同时对保险公司未尽如实告知义务。
第三人辩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双方合同约定,如果原告在托运货物时,向第三人申报了货物价值并支付了附加费,一旦货物的短缺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第三人将按照货物申报的价值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本案原告未购买保价,故而即使第三人应承担责任,也是在最低限额内赔偿。
[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原告是否完成了快递货物交付义务?第二,被告主张的原告应对货物在运输途中灭失承担举证责任的意见是否成立?第三,原告在事故前与第三人关于赔偿限制责任的约定是否导致被告免责?
关于货物是否已经交付的问题。庭审中,被告以证人耿某、刘某、第三人出具的情况函件及涉案的货箱为由,主张包装箱的外观完好无损,未发生盗窃事实;又以原告提交的视听资料存在盲区、托运单存有瑕疵为由主张灭失的“金一版”未被交付出去。原告认为,11月25日当天,第三人出具托运单据并取走货物的事实,可以证实原告已经交付完毕。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未对运件的包装作特别约定,涉案的货箱仅是一般的封箱包装,被告以耿某及刘某仅凭肉眼作出的判断便认定货箱的外包装是完好无损的,缺乏证明力,更无法以此推导出货箱在运输途中未曾被打开过这一事实。何况,通过庭审质证,货箱的正面和底部共有四道封口存在破损,而耿某陈述当时是从底部打开货箱。所以,被告以上述证据认为货物在运输途中未发生灭失的观点,一审法院难以支持。
关于托运单证明力问题。被告认为,托运单是原告交付货物的直接证据,但是托运单上未记载货物的品名,无法证实原告交付托运了灭失的货物。对此,原告及第三人一致认为,为了降低运输风险,双方在履约时变更了原来的约定,不要求原告填写具体的品名。那么,原告未填写货物品名是否必然导致原告未如实交付?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视听资料是原告公司内部监管所需,不是原告对被告及第三人的合同义务。如果涉案合同约定原告须对运件从装箱到托运进行全程监控,则视听资料存在盲区,原告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运输合同的立法规则,托运人应如实申报货物,承运人对货物在运输途中的灭失等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其能证明托运人在托运中存在任何过错。因此,在承运人举证不力的情况下,承运人的签收行为应产生托运人已交货完毕的法律后果。本案诉讼中,作为承运方的第三人没有提出更为有力的证据证明原告在托运中存有过错。在交接涉案运件时,其将托运单寄件人联交存原告并提取货箱的行为应视为签收。此后,第三人又对货箱的长宽高重新度量,在托运单取件地联签收16.5公斤。这一重量已高于原告原来的称重——13.05公斤。因此,一审法院确认第三人在托运单上签收行为的效力。而原告提供的视听资料证实灭失的“金一版”已被打包装箱,这节事实可作为第三人签收行为的证据补强。鉴于上述分析,原告虽未在托运单上填写货物品名,但这一形式要件的缺失并不能从实质上说明原告未如实托运、未如实交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已经按约履行了交付义务。
关于被告主张的原告应对货物在运输途中灭失承担举证责任的意见是否成立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作为被保险人只要证明其交付的货物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了短少,其举证义务即告完成。被告作为保险人应对其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按照涉案保险合同可以得出,如果被保险货箱内物品的短损不是发生在运输途中,则被告免责。因此,被告须对此承担举证义务。庭审中,被告认为货箱的外包装是完好无损的,说明货物的短少不是发生在运输途中,其中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在上文中已经阐述。因被告主张的免责事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述意见一审法院无法采信。
原告在事故前与第三人关于赔偿限制责任的约定是否导致被告免责?
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的请求赔偿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依照该条法律规定,被保险人放弃权利的时间须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原告与第三人关于货物灭失后第三人赔偿原告每笔100元或每公斤20元并取高者为准的约定,是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一种合同行为,并非是原告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权利。因该条款在涉案货物灭失之前即已存在,因此被告的抗辩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投保时,依法应将运输合同中的责任限制条款如实告知被告,但是该义务的履行须满足被告在缔约时对原告有相关要求为前提,否则便无法认定原告未尽如实告知义务。由于双方没有上述约定,被告在订约时也未对相关情况提出询问,所以被告无法就此免责。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作为保险人,完全可以在订立合同时要求投保人告知影响保险人风险的事项,从而降低自身的风险。但其疏于行使上述权利,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就涉案货物向被告投保后,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发生货物短少,价值212,000元,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赔偿原告保险金212,000元。为规范保险活动,保护保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直属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金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保险金人民币212,000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8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
判决后,被告不服上诉。被告认为原告、被告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应适用2009年邮包险的条款,仅对“整件提货不着”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由于保险协议签订在前,运输协议签订在后,被告无法询问金望公司是否保价,影响了被告对金望公司理赔后的追偿权。金望公司应对承保货物的实际交付及保险事故的发生承担举证责任。金望公司则辩称保险合同附件加盖了骑缝章,载明的附件为1981年邮包险条款,要求适用2009年邮包险的条款没有依据。为此,第三人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审法院确认的事实属实,因原告、被告双方未合意变更邮包险条款,认为适用1981年邮包险条款;对于保价,认为系投保人的商业选择,人保公司在此笔业务发生时未询问,事后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因此,对人保公司减免相应保险金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对于货物交付问题,认为已经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货物已交付。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由上诉人人保公司承担。
[评析]
一、快递行业中出现货物遗失情形下的货物交付与否的认定
货物是否运输途中遗失,这几乎是所有货运纠纷中最难处理的部分,托运人、承运人、保险公司均各执一词,货物遗失时间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由于货物遗失时间系货运保险是否承担责任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于这一时间节点的认定,对案件审理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笔者认为,确定货物是否交付前遗失,主要涉及以下因素:
(一)托运单的证明力问题。托运单是托运人交付货物的直接证据,托运单中应当明确记载托运货物的品名,完整填写托运单一般应视为货物已经交付。然而,实践中,托运单上未记载货物的品名屡见不鲜,而托运人和承运人一般均认定是为了降低运输风险,双方在履约时变更了原来的约定,不要求填写具体的品名。笔者认为,完整填写托运单上的品名及相关内容系确立双方权利义务的重要因素,亦系法院所倡导和鼓励的,但如未完整填写,并不当然地证明未交付。毕竟托运单的存在至少证明了存在托运的行为和托运的事实,应根据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判断。
(二)涉案视听材料的认定。为了防范较为贵重的物品在托运途中遗失,托运人往往会采用视听资料来证明自身已经履行了相关义务。本案审理中的难点在于,在视听资料未完整反映托运全貌的情况下,是否承担举证不能的义务。裁决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涉案视听资料是托运人公司内部监管所需,不是托运人对人保公司及第三人承运人的合同义务。如果涉案合同约定托运人须对运件从装箱到托运进行全程监控,则视听资料存在盲区,托运人需证据补强,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三)封装包装、称重行为对于灭失时间的认定。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另一个焦点在于封装包装完好无损。各方当事人未对运件的包装作特别约定,涉案的货箱仅是一般的封箱包装,仅凭肉眼作出的判断便认定货箱的外包装是完好无损的,缺乏证明力,更无法以此推导出货箱在运输途中未曾被打开过这一结论。况且货箱的正面和底部共有四道封口存在破损,相关人员陈述当时是从底部打开货箱,所以,被告人保公司以上述证据说明包装问题,进而认为货物在运输途中未发生灭失的观点,难以获得支持。托运人交货后,承运人对货箱的长宽高重新度量,在承运人公司内部保存的托运单取件地联签收16.5公斤,这一重量已高于托运人原来的称重——13.05公斤。因此,法院最终确认承运人在托运单上签收行为的效力。
二、货物运输途中灭失的举证责任承担
举证责任在民事案件中是一个动态转移的过程。一般来说,履行方应对自己履行的义务负有举证责任。如前所述,综合上述关于托运单、包装情况、涉案视听材料以及托运货物重量等的综合判定,托运方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保险公司如认为货物并非在运输途中发生灭失,则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三、托运人与承运人的保价条款对于货运保险合同的影响
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签订“保价条款”,这几乎成了货运行业中的惯例。但由于保价金额的有限以及费用的问题,不少托运人倾向于不通过约定保价条款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托运人未签订保价协议是否构成对自身权益的放弃?保价条款与货运保险的关系如何?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双方的保价条款系自由约定。笔者认为,托运人与承运人对于保价条款是否进行约定、如何约定取决于双方的真实意思。本案中,托运人未选择对托运物品进行保价,而是选择了责任限制条款,即接受货物灭失后承运人赔偿托运人每笔100元或每公斤20元并取高者为准的约定,且向被告人保公司直接投保。此系托运人自身的商业选择,并不构成对承运人权利的放弃。
(二)保价条款的约定确系影响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后追偿权的行使,是影响本案保险合同保费的因素。应当明确,有无保价条款及其具体约定影响到货物灭失后托运人对承运人要求的赔偿范围和赔偿金额,并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在承担了保险责任后对承运人追偿权的行使,进而影响到保费。因此,人保公司理应对保价条款是否进行约定、如何约定作出询问,并引导托运人进行选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保价条款是否影响货运保险合同取决于合同约定以及询问情况。如前所述,有无保价条款确系影响保费的因素。但是,鉴于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对于告知义务实行有限告知,即取决于保险公司的询问。现保险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未对保价条款进行约定,在缔约中也未进行询问,在知晓未进行保价后的法定期间内亦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本案中,保价条款不会影响到货运保险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