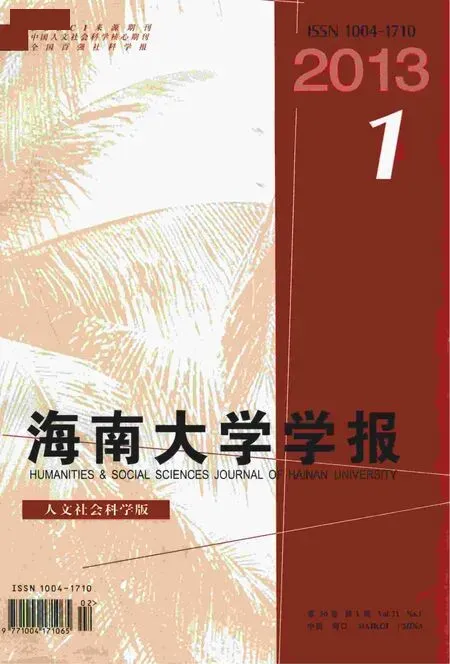赛珍珠《母亲》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朱 磊
(山东财经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山东济南250014)
赛珍珠是一位美国作家,襁褓中的她被传教士父母带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这段经历使她对中国有了深深的感情。1938年,赛珍珠由于对中国农民生活所作的史诗般的描写,以及传记方面的杰作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赛珍珠一向关注女性问题,她的早期作品,塑造了一系列活生生的中国女性形象。1934年问世的《母亲》是她的经典作品之一,该书描写了一位坚强的中国女性坎坷的命运。诺贝尔授奖词称《母亲》的女主人公在赛珍珠塑造的中国女性形象中是最完美的,这本书也是她最好的一部。母亲在小说中是个没有姓名的妇女,除了她,小说还塑造了其他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同母亲一样,她们也没有姓名,作者这样做旨在说明她们的故事并非个例,她们的遭遇反映了旧中国妇女寻常的命运。《母亲》无论从思想性、艺术性还是可读性而言,都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长期以来,虽然也有像《漫谈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和〈母亲〉》、《两位没有姓名的女性——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和赛珍珠笔下的“母亲”》、《乡村经典女性形象——分析赛珍珠小说〈母亲〉中母亲命运特征》、《母性·妻性·女性——论赛珍珠的长篇小说〈母亲〉中的母亲形象》等文章问世,但对于《母亲》的专题研究无论是从成果问世的数量,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看都是远远不够的。大家不妨多角度、多侧面地对其进行分析,不断挖掘其深藏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鉴于《母亲》中的生态女性主义特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评析这部作品,以期为《母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是较新发展起来的批评论和方法论,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女性主义·毁灭》一文中最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这标志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开端[1]。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在创造和维持生命方面,女性和自然界是联系在一起的”[2],以反对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的男权思想为核心,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环境和谐的、体现伦理文化的,以及遵循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原则的理想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在《母亲》一文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女性与自然的融合,女性意识的觉醒。
一、《母亲》中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制是造成女性一切不幸的根源。父权制下女性被视为被统治的对象,女性必须服从于男性的利益。父权表现在家长支配全体成员并对其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这使家长成为这种家庭的核心,也是人们把它称作父权家族、父家长制家庭的原因。在中国的家长制家庭里,父权的表现尤为突出。手持斧杖形的“父”字本身,就是权威的一种象征[3]。生态女性主义者注意到,在父权文化语境下,男性等同于拥有心智的人,而女性则被视为自然和非理性的化身,因此,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排斥,对女性的各种形式的统治、压迫就被认为在道德上是正当的,是父权制社会的自然法则[4]。在父权社会中,男性不仅占有女性的肉体,并且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习俗和道德标准来束缚女性的自然本性。
在《母亲》中,读者不难发现文中女性在父权制统治下的悲惨遭遇。在旧中国,男人尽可以三妻四妾地娶进门,而女性却必须从一而终。否则就会被看作是不守妇道,轻则被人唾弃,重则被逼身亡。正如林语堂在《中国人》中所指出的:“在中国,……被遗弃的妻子总是处在一种无限悲惨的境地。”[5]作品中的母亲,即使在无缘无故地被丈夫抛弃之后,也没有重新选择幸福的权力,她虽正值壮年,却不得不压抑自己自然合理的生理需求。被地主家道貌岸然的管家欺骗失身并怀孕后,母亲背上羞耻的重负,她“日夜千思万想,烦恼着那藏在肚里的孽种”[6]107,“好几次恨不得在床架上吊死”[6]105。尽管听说堕胎会让自己遭受极大的痛苦,母亲仍坚持道:“只要能去了这个孽障,只要能让我的孩子和别人不知道这回事,就是我死了我也情愿。”[6]115为了迎合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抱着从一而终思想的母亲只能独守空房,郁郁终生,所以说,是父权制造成了母亲的创伤,又在母亲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父权制”统治的家庭里,女儿的遭遇比起母亲还要悲惨,她从小害眼病,眼睛又疼又痒,红肿不堪,当母亲提议给她买眼药时,她的父亲却“很不高兴地回答说:‘她不会痛死的,为什么要用我们好不容易省下来的这么一点钱给她医眼睛呢?’”[6]14母亲想“也是的,不知有多少孩子害着同样的红眼病,可是过了孩子的时期,也还是会好的。”[6]14此时父权的绝对权威使得母亲轻易认同了丈夫不负责任的话,尽管她非常想给女儿治病,却不敢违抗丈夫的意愿。丈夫离家出走后,大儿子尚未成年前,她才有了短暂的话语权,但当她带着女儿去看眼睛的时候,却被告知错过了治疗时机的女儿已经双目失明。
从众多的关于父权的定义来看,“男权制”与“父权制”可以视为同义词。等大儿子娶妻成家,“母亲因为媳妇来了,现在必须要让出她睡了多年的床铺。”[6]144“正式的床位如今是要让给大儿子和他的女人睡了。”[6]145表面看来母亲是家里“最老,最尊贵的主妇”[6]145,实际上整个家庭开始听从大儿子的安排。床铺在这里有着明显的象征意义,正式的床位代表着家庭的权威,谁占有正式的床位,谁就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获得了话语权的儿子,在媳妇的怂恿下,开始嫌弃女孩是家庭的累赘,鼓动母亲把她嫁出去,母亲听从了此时作为一家之主的儿子的话,匆忙让女孩出嫁,最终导致女孩惨死异乡。所以说女孩一生的命运,都受到父权制的控制,如果没有父权制对家庭的控制,女孩一生的命运将大相径庭。
二、《母亲》中女性与自然的融合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物种的幸存使人们看到重新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性。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将人与自然分离,将思想与感觉分离”[1],“回归自然是人类身心健康、心态正常的必由之路,只有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形成‘天人和一’的境界,才是人类精神家园的最终归属”[7]。生态女性主义者相信女人与自然有极大的亲近性,在生理上如月经、怀孕和生产过程的经验类似自然生态的循环,有其周期性存在。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相连性。
《母亲》中的女性将自己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不管自身命运如何,都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和极力体现的女性和自然之间在本质上的必然联系相吻合。作品中的这种和谐性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母亲》对女性的生育做了最朴素的描述
生育是使自然延续下去的基础,生态女性主义者把大地孕育万物的自然现象类比于母亲哺育子女的天性。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由于女性和自然都具有创造和养育生命的能力,女性在精神上比男性更亲近自然,女性的心灵也更适合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8]《母亲》中,无论是母亲,还是堂嫂,她们从怀孕到生产,都被作者描述为自然而然的过程,这是女性与自然相融合的巧妙佐证。
例如,母亲“以往差不多每年春天母亲都会生产一次,自从她嫁过来以后,每年春天都是如此。”[6]72“每当她怀孕的时候,她总是很快乐,而且很满足。”[6]8生产时,“母亲痛得大叫起来,转过身去,背着女孩,松松腰带,倚在凳子上,堂嫂赶快跑过去,用她那敏捷的手,接住了她们所期待的孩子,又是一个胖儿子。”[6]22生产后,母亲“躺在床上休息,这种辛劳以后的休息,真是让母亲觉得太甜蜜了。”[6]22可以说,母亲完全是在享受自然所赐予的做母亲的权力,对此她从没有感觉是一种痛苦和负担。就连不小心摔跤导致小产那次,也没有特别痛苦,只是心里有些遗憾罢了。但母亲的堕胎,这种违背自然意愿的行为,却给她带来了身体上和心理上极大的痛苦。“母亲一定得尽量地忍着疼痛,汗珠像雨点一般地淌下来,失去知觉,如同死了一样。那种绞肠的疼痛,就像她被凶猛的野兽捉住,撕裂她的血肉一样。”[6]146
作者对自然分娩和堕胎的描述是大相径庭的,一个似和风细雨,一个如雷霆万钧,这种安排看似无意,实为巧思,暗示着孩子是自然赐予的,人若违抗自然的安排定会受到惩罚。
(二)《母亲》表现出女性对土地自然而然的亲近与关注
无论是中国的女娲捏土造人,还是西方的上帝创世神话,都说明人类将土地视为自然界赐予自己的生存基础。中国自古以农耕为主,土地对中国农民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母亲》中,作者把农民(尤其是其中的女性)与土地的深厚感情和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得酣畅淋漓,反映了女性与自然的融合。
例如,母亲去给秧苗浇水,她“一次又一次地灌着,看着地上的泥土慢慢变色而润湿了,她觉得像喂饱了的孩子一样,让那些干渴的土地,得着生命了。”[6]96土地在这里被比喻成自己的孩子,反映了母亲对土地发自内心的爱恋。
再如,母亲不得不带着小儿子去田里劳作,“孩子现在已经大了些,可以把他放在地上,随便他爬着玩,抓了泥土往嘴里塞着吃,他吃着吐着,吐了再吃,脸上糊满了吐了吃的泥巴。”[6]53在这里,人们看到一幅天人合一的和谐画面,孩子已经完全和土地、和自然融合在一起。
(三)《母亲》中自然景物与人物命运相互呼应
赛珍珠借助其细腻而具有象征意义的景物描写手法,以景物变化烘托和渲染主人公心情和处境的变化,表现自然与主人公之间的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例如,孤独寂寞的母亲被油滑的管家吸引时,天气的闷热与她内心的欲火相呼应,她感到“一辈子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闷热”,“她内心里的火热已经够她受的了,她血脉里的欲火好像要把血管冲破一样。”[6]95
在被管家引诱发生关系后,天色大变,“突然间,狂风如同猛兽吼叫一样从远远的山上吹过来,将那沉寂夜空里的乌云吹得随风翻腾,黯淡无光。骤然倾盆暴雨把一整天的酷热冲洗得干干净净。”[6]100酷热褪尽象征着母亲的欲望暂时得到了满足,而满天乌云与倾盆大雨则象征着母亲将面对的接踵而来的折磨与不幸。
(四)《母亲》中洋溢的浓浓的母性和母爱是维系自然发展的纽带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网,并无上下高低的等级之分。作品中的母亲喜欢一切的小生命,甚至“如果老母鸡忘了一个蛋,她便拾起来,放在自己贴肉的衣服里,做一个袋子,把蛋装在袋里,小心着,轻轻地走动,直等到小鸡孵出了为止”[6]76。对小动物尚且如此,对孩子母亲更是充满母爱,以至于“不能忍心听到孩子的一点点哭声”[6]5。丈夫的出走,使她彻底失去了再次做母亲的权力,因此她的“心灵和肉体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空虚”[6]76。
(五)《母亲》中女性安于平淡生活的人生态度反映了她们与自然的融合
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男性是把世界当成狩猎场,与自然为敌;女性则要与自然和睦相处。因此,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于为保护自然而战,更有责任也更有希望结束人统治自然的现状——治愈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这正是生态运动的最终目标。
《母亲》中女性安于平淡生活的人生态度反映了她们与自然的和睦共存。“每天的日子,对母亲都是同样的,但是她从不感觉乏味,她对于日子的轮转感到非常的满足。”[6]15因为每天的生活,对于母亲都是“滋味无穷的”[6]16。偶尔跟着男人去城里卖菜时,“城里那些稀奇古怪的景致,也真够她看,够她想的啦,但是她毫无一点欲望,她很知足很满意地跟着孩子和男人一块儿过日子。”[6]16
母亲平和知足的生活态度与她的男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对母亲那男人来说,他只会一天天挨过着日子,是从没有什么改变的,也从不会对任何新鲜事抱过希望。”[6]23而对于家庭的责任,“好像就是他最大的梦魇”[6]26,“当他兴奋地想寻找欢乐的时候,他忘了他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只一心一意地盼着能到那遥远的大城市里,找些乐趣,开开眼界。”[6]32最终,他抛妻弃子去城里寻找新的生活,从此杳无音信。虽然丈夫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这清楚地反映了男性的不安分,他们不安于顺应自然的力量,过靠天吃饭的生活,而是把世界当成狩猎场,渴望与众不同的生活,不断寻求新的刺激。
三、《母亲》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父权和男权的思想价值观,讴歌女性的本质”[1]。它借助解构主义,充分揭示和批判了父权制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赛珍珠在这部作品中将主人公母亲塑造成一位一方面深受男权制桎梏,一方面又能够顽强不屈地面对厄运挑战的女性,闪现出不甘愿受压迫的女性意识,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又一体现。母亲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小说中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母亲具有当面指责男人虚荣心的勇气
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男性中心论,文中母亲尽管一向把男人当作一家之主,但她的“坏脾气有时也会爆发起来的”[6]26,例如:当看到男人手指上戴了一个金戒指从城里回来时,母亲“大发怒火,用最愤怒、最泼辣的声音向他大骂:‘你!你也不替我们的穷日子分担点儿,难道就非把剩下的一点钱拿去,买个没用的东西戴在手指头上才舒服吗?你听见过穷人戴戒指吗?有钱的人戴着没有话说,穷人戴着有什么意思?’”[6]27再如,当男人要花光积蓄只为了买一块华而不实的布料做新长衫时,母亲叫道:“那笔钱,无论如何是不能用的!”[6]38当男人不听劝阻为买布花掉了最后的三块钱时,母亲开始和他冷战,“她冷冷地对着她的男人,两人简直像对头一样”[6]39。这几个细节,表现出母亲的倔强和抗争精神,虽然不足以帮助母亲挣脱男权制的枷锁,但毕竟显示出女性的力量,与她平日里的逆来顺受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母亲具有巧妙掩饰丈夫离家出走这一尴尬处境的智慧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人应有自己的主体性,而不只是男人的附庸,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要有正确的体验和感悟。文中母亲在丈夫离家出走后,乡邻的闲言碎语“使她必须要想出一个好法子,能挣回自己受羞辱的面子来”[6]60,在艰难又尴尬的处境中“母亲擦干眼泪,法子终于想出来了”[6]60,她编织出丈夫在外打工的谎言,请外村人以丈夫的名义写信,并把自己辛苦劳作的收入夹在信中寄回家,以此来支撑这个谎言。如此巧思,使得“从此以后,这村子里再没有人敢藐视她了,或是嘲讽她是被她丈夫抛弃的女人”[6]66,并使儿女及婆婆能够充满希望地生活下去。能镇定自若地做好这一切,表现出母亲巨大的忍耐力和承受力,也表现出她作为一个女性关键时刻闪现出的智慧火花。
(三)母亲具有顽强担负起家庭重担的毅力
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将女性视为被统治的对象,女性必须由男性主宰这一观点。文中的母亲是一位自强自立的女性形象。丈夫在家时,虽然不爱干活,但毕竟是一家人的顶梁柱。丈夫离家出走后,全部的重担都压在母亲的肩上。顽强的母亲在老人孩子面前从不流露出内心的无助与悲伤,她尽其所能,使得这个破碎的家能够维持下去。她妥善地照顾着三个孩子,把他们一一抚养成人。她也没有因为丈夫离家而厌弃婆婆,而是一如既往地孝敬老人,并在其临终之际倾其所有买来“顶好的红棉布”[6]102,熬夜为老人赶做了一件新寿袍,满足了老人最后的心愿,老人临终前,“瘪着嘴笑着,她知道她的新寿袍已经穿上,心愿满足了,可以很安心地走了”[6]103。母亲,在丈夫缺失的家庭里成功地为家人撑起一片天,她的这种自强不息的女性意识正是生态女性主义者所提倡的。
小说结尾孙子呱呱落地带给了命运多舛的母亲生活下去的新希望,赛珍珠以此作结,传达出对和谐境界的追求,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这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当前所极力主张的。
总之,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极具建设性和现实意义的思想潮流”[9],“它的终极关怀是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的精神家园和物质家园”[10]。《母亲》中“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体现在母亲和女儿的悲惨命运。女性与自然的融合,体现在朴素的生育态度,对土地的亲近与关注,自然景物与人物命运相互呼应,自然的母性与母爱和女性安于平淡生活的人生态度。女性意识的觉醒,体现在当面指责男人虚荣心的勇气、巧妙掩饰丈夫离家出走的智慧和顽强负担起家庭重担的毅力。这三点涵盖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要旨,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这部作品,可以从更深层次体现作品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极高的思想价值。
[1]生态女性主义[DB/OL].[2012-10-16].http:∥baike.baidu.com/view/1115943.htm.
[2]关春玲.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J].外国社会科学,1996(2):25-30.
[3]王治功.论家长制[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3(4):49-58.
[4]曹南燕,刘兵.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J].哲学研究,1996(5):56-57.
[5]林语堂.中国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39.
[6]赛珍珠.母亲[M].万绮年,原译.万尚澄,编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7]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
[8]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230.
[9]陈煌书.从《尖尖的枞树之乡》看萨拉·朱厄特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8):72-76.
[10]刘英,王雪.美国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中的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4):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