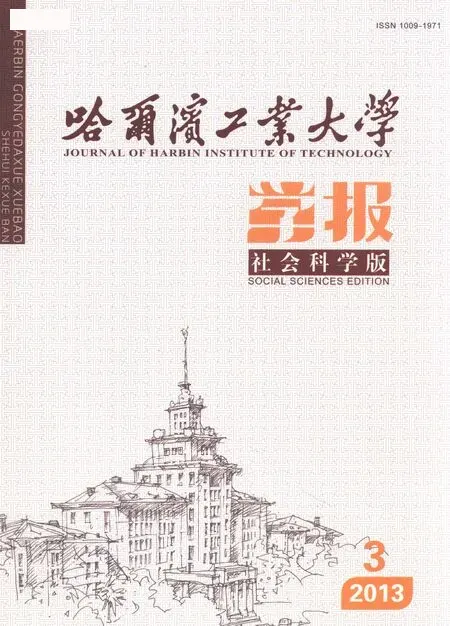慕华风,易胡俗
——前燕官学教育兴起的助推力
赵红梅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长春130033)
·史学研究·
慕华风,易胡俗
——前燕官学教育兴起的助推力
赵红梅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长春130033)
东胡遗裔,俗同匈奴,是慕容鲜卑传统的社会教育,在入居辽西、始慕华风之后,慕容鲜卑的文化教育中出现了汉文化元素。在慕容廆的助推之下,前燕“移风易俗”,渐进地出现了官学教育,而接受官学教育旋即成为慕容鲜卑人出仕为官的基础。前燕官学教育的出现,在客观上促进了慕容鲜卑在思想观念以及制度文化层面的社会变迁。
慕容鲜卑;传统教育;社会教育;文化教育;官学教育
“鲜卑”之名最早见于汉代,慕容鲜卑“慕华风”始自莫护跋迁入辽西,于棘城之北建王府之时。经木延、涉归,传至慕容廆时建立前燕政权,共历四世,凡85年[1]2858(《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前燕历史地成为了第一个入居东北、立国东北、进据中原的地方民族政权。在慕容廆的助推之下,前燕“移风易俗”,渐进地出现了官学教育,而接受官学教育旋即成为慕容鲜卑人出仕为官的基础。前燕官学教育的出现,在客观上促进了慕容鲜卑在思想观念以及制度文化层面的社会变迁。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官学教育出现之前慕容鲜卑的传统教育模式的考察,试就前燕官学教育兴起与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官学教育出现之前慕容鲜卑的传统教育模式
鲜卑人的先世为东胡人,在鲜卑诸部当中,关于“慕容”氏的记载最早见于王沈《魏书》中所记载的檀石槐中部大人“慕容”。在慕容廆草创前燕政权以前,慕容鲜卑屡有迁徙,其先世经历了从檀石槐时期居住在“右北平以西至上谷”[2]833(《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传》,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的中部大人“慕容”这样的“塞外蛮夷”,通过莫护跋入居辽西主动吸纳汉文化以及莫护跋之子木延、其孙涉归相继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逐渐使慕容部成为“渐慕华风”的东北地方民族。
(一)慕容鲜卑的社会教育:东胡遗裔,俗同匈奴
在官学教育出现之前,慕容鲜卑习俗与匈奴略同。“昔髙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次以君北夷,遂世居辽左,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西汉初期,匈奴冒顿击溃东胡,东胡遂分为乌桓、鲜卑二部,其中“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3]2985(《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退保鲜卑山的这支东胡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鲜卑。
居于东北地区的鲜卑人的东部鲜卑人,与匈奴一样,有语言而无文字.匈奴“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4]1231(《前汉书》卷九四上《匈奴列传上》)在长期的狩猎生产中,自然习得的主要是骑射教育,而非中原礼仪。
对于西汉时期鲜卑人的教育状况不得而知,主要在于彼时鲜卑之所以不通于西汉王朝,究其原委,一方面在于受乌桓所阻,另一方面在于受制于匈奴势力的影响。鲜卑经常与匈奴、乌桓一并寇掠东北边郡,此种局面持续至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鲜卑与匈奴入辽东,辽东太守祭肜击破之,斩获殆尽……由是震怖。”[3]2985(《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建武二十五年(49),在辽东太守祭彤的招抚下,东部鲜卑成功地与东汉王朝建立了朝贡册封关系[5]265-268。
(二)慕容鲜卑的文化教育:入居辽西,始慕华风
1世纪中叶至4世纪后期,鲜卑人的分布状况随着时空变化而有所不同。鲜卑这一族称乃得名于鲜卑山[3]2985(《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从《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的记载来看,“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1]2803(《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魏书》卷一《序纪》中记有,“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6](《魏书》卷一《序纪》)。既然慕容与拓跋均以“鲜卑山”为号,二者是同族不同部,其所依之鲜卑山当不是同一座山,慕容部所依之鲜卑山在柳城县西南,西汉时期此地当在汉长城之内,属右北平郡。拓跋部之大鲜卑山位于大兴安岭北段。鲜卑人最初分布于大兴安岭北部地区,西晋时期,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一带分布着东部鲜卑三部:慕容部、宇文部、段部[7]。
在《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中仅记载了檀石槐“乃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3]2989-2990(《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能够知道檀石槐时期的中部指的是“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关于鲜卑慕容部的分布地域问题,马长寿先生认为鲜卑自鲜卑山迁出后,“分布到古饶乐水即今西拉木伦河流域。慕容部此时的分布当在西拉木伦河的上游,即今河北省平泉县直北至西拉木伦河西段地区”[8]186。慕容部属檀石槐三部中的中部,公元2世纪中后期,慕容部应该分布在在“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各郡的塞外。因此,有学者认为慕容部在东汉时期“已迁居今河北省以北地区”[9]。
入居辽西,慕容鲜卑始慕华风[10]。最为有利的实例为《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与《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中关于“慕容氏之由来”的记载。史载,慕容廆的曾祖莫护跋在率部迁入辽西以后,见当时燕代地区的汉人多习惯戴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1]2803(《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在今辽宁省北票房身晋墓、北燕冯素弗墓、朝阳县下田草沟晋墓等墓葬中常出三燕时期的金步摇[11-12],在考古资料上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佐证。从这些出土的遗物来看,作为汉文化因素的步摇冠,彼时确实流行于辽西之地。
若慕容氏之名果真源自“步摇”之音讹,则慕容部名称起源不会早于莫护跋率部迁入辽西以前,亦即不早于曹魏初年,换言之,不可以上溯至汉灵帝时代,[13]这就与檀石槐三部中的中部大人“慕容”就是指慕容部的首领之说相矛盾了。见于史书记载的另一种关于慕容氏名称由来的说法是,“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1]2803(《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初入辽西的慕容氏对汉文化的了解尚难达到如此程度,不太可能取如此深奥意义的汉字为其族名。
胡三省都曾对上述两种说法作过驳斥,即“余谓步揺之说诞。或云之说,慕容氏既得中国,其臣子从而为之辞。”[14](《资治通鉴》卷八一《晋纪三》,晋武帝太康二年条胡三省注)“慕容”与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名称一样,皆出自对少数民族语词的汉语音译,固不能从“慕容”二字的汉字内涵予以解读。
尽管“步摇之说”与“或云之说”均不能作为慕容氏由来的依据,却将慕容鲜卑“主动向华”的倾向展示得淋漓尽致。不论慕容氏之名是否起源于“步摇”,自莫护跋率部迁入辽西地区后,慕容鲜卑都经历了由“秃头宴饮”到“敛发袭冠”的转变,足证慕容鲜卑已在与汉族杂居过程中逐渐接受汉文化[5]265-268。这既是慕容部在进据辽西后文化教育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后来慕容鲜卑汉化历程的起点。
二、华夷之辨:前燕官学教育兴起的根本原因
在促使慕容鲜卑迅速兴起的诸多因素中,学界对尊晋勤王、慕容鲜卑汉化、流寓前燕的中原士人等问题多有论述。诚然,慕容廆时期采取了尊晋勤王的策略、前燕统治者从慕容廆开始也进行了汉化改革,还大量启用了流寓前燕的中原士人,这些问题都是慕容鲜卑崛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慕容鲜卑能够跻身于五胡十六国之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单纯夸大某一方面因素的做法都是有欠妥当的,其中前燕的官学教育无疑是慕容鲜卑兴起的催化剂。
(一)慕容廆汉文化素养:慕容鲜卑贵族接受经学教育
正始年间,莫护跋之子木延,跟随毌丘俭征高句丽有功,曹魏赐予其大都督、左贤王之号。木延之子涉归,因“全柳城之功”,被封鲜卑单于,并率部“迁邑于辽东北”(《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进一步向辽东中心地带靠近。马长寿认为,此“‘辽东之北’当在今彰武之北、边栅以外之地”[8]187。虽然在涉归时期曾经叛晋,攻昌黎、辽西二郡,后被平州刺史鲜于婴讨破,但就整体而言,慕容部在进入辽西以后,与魏、晋等中原政权保持着比较稳定的臣服关系。此种时局为慕容廆年少时研习中原礼俗作了环境上的准备。
慕容廆,鲜卑语名为弈洛瑰[15],出生于西晋武帝泰始五年(269),在涉归去世后的第二年成为慕容部的首领。《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记载:“安北将军张华雅有知人之鉴,廆童冠时往谒之,华甚叹异,谓曰:‘君至长必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者也。’因以所服簪帻遗廆,结殷勤而别。”[1]2803-2804(《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张华“都督幽州诸军事”是在太康三年(282)的正月[1]73(《晋书》卷三《武帝纪》),此时的慕容廆还只有14岁。慕容廆能够得到时任安北将军的张华的赏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慕容廆绝不仅仅是能够熟练使用汉语,能顺畅地与张华进行沟通。
(二)“华裔理殊”:前燕官学教育兴起之原因
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不仅仅局限于民族血统上的融合,从十六国中部分统治者对其族属的认知问题来看,在民族心理上,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首领对华夏的认同,是这些少数民族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提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还是将祖先追溯到高辛氏后裔,都认为慕容鲜卑是流落夷狄之地的华夏子孙。这种比附的目的不会是只将慕容鲜卑的祖先追溯到华夏始祖黄帝身上就完结的,换言之,“华夷共祖”思想的落脚点应该是在黄帝及其子孙居住的中原之地上,也就是说,在“其先有熊氏之苗裔”的诱惑下,中原地区自然成了慕容廆祖先的居住地。
倘使慕容氏势力强大、据有中原,那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被视为回到其祖先居住过的地方,无异于重返故土、叶落归根。因此,“华夷共祖”思想无疑为慕容鲜卑政权日后得以进军中原作了舆论准备。通过这种“华夷共祖”的现象可以推测,东晋时期的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前,已经是充分认同了“华”,且急欲摆脱自己“夷”的身份。这就促使“五胡”首当其冲地选择了在族属上去寻求与“华”之间的同源共祖,但这种说法显然不是信史,而是慕容氏与汉族接触以后对族源所做的一些附会。
“华夷之辨”形成于先秦时期,“裔”与“夏”,“华”与“夷”的观念此时就已形成。有学者指出“华夷秩序”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比较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16]。慕容廆立国伊始就不自觉地被纳入到西晋王朝的“华夷秩序”中,而无论前燕统治者是否情愿。终慕容廆一世,“华夷之辨”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前燕君臣。对“华夷”之间的差距,慕容廆君臣经历了从意图冲破“华夷秩序”、漠视“华夷之辨”至认识到“华裔理殊”,恢复与西晋的朝贡册封关系以使“勤王杖义”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尽管慕容廆的辅政集团吸纳了大批中原士人,但是这些士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以“请封燕王”一事为例,“拥晋”仍是部分前燕士人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17]。
三、出仕为官:前燕官学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北方民族纷纷入主中原的十六国时期,“传统的汉民族文化不仅经受了周边民族朴素、刚健精神的冲击,而且在民族融合所造成的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下不断输入外来思想文化,出现了许多以往单一民族政权中难以想象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现象。”[18]那么,前燕政权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对其辖区范围内胡汉民族的统治?在前燕政权不断壮大过程中,是否也存在胡汉冲突呢?
(一)吐故纳新:前燕官学教育的人才储备
前燕政权向西晋、东晋王朝遣使最为频繁、朝贡关系最为密切的阶段当属慕容廆统治时期[19],前燕与中原王朝朝贡册封关系的疏密程度与前燕对中原王朝的认同程度成正比。这一时期恰恰是前燕大量学习和效法两晋王朝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重要阶段。
建兴四年(316)西晋灭亡,华北地区再次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慕容部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中记载,“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1]2806慕容廆的汉化改革不但很好地安置了中原移民,其收到的最大成效就是,使慕容部控制区成为中原移民的首选迁入区。有学者认为,“前燕的侨置流民制度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推行的措施,它有利于各民族在同一政权之下共处,从而有利于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当然也就有利于前燕的巩固和国力的增强。不过,侨置流民制度依然属于过渡阶段的政策,并不属于制度的革新。”[20]慕容廆安置归附与己的中原士人,这些流寓前燕的中原士人在慕容廆统治时期促进了慕容鲜卑对中原文化的吸纳,加快了前燕改易胡俗的进程。
太兴元年(318)春三月,“元帝即尊位,遣谒者陶辽重申前命,授廆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固辞公爵不受。以游邃为龙骧长史,刘翔为主簿,命邃创定府朝仪法”,从而使前燕棘城政权的政治制度开始走向规范化进程。太兴四年十二月(321),慕容廆尊晋命,“承制海东,命备官司,置平州守宰”[1]2807(《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
(二)选官捷径:前燕官学教育的历史作用
慕容皝十四年春正月,“皝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通经秀异者,擢充近侍。”(《十六国春秋》卷二五《前燕录三·慕容皝下》)使官学教育成为前燕官宦子弟得以选官的捷径。至慕容暐委政于太宰慕容恪时期,前燕出现了“专受经于博士王欢、助教尚锋、秘书监杜诠,并以明经讲论左右。至是通诸经,祀孔子于东堂,以欢为国子祭酒,锋国子博士,诠散骑侍郎,其执经侍讲者,皆有拜授”的局面(《十六国春秋》卷二八《前燕錄六·慕容暐上》)。经学是前燕官学教育的主流。
将前燕历史回归到3—4世纪中国的社会环境中,由于前燕对周边的夫余[21]、宇文鲜卑、段部鲜卑、高句丽等诸民族战争,在民族冲突与民族迁徙中发生着慕容鲜卑与诸多民族的交错局面,最终归于多民族之间的融合。除慕容廆幕僚体系均由流寓前燕的中原士人充任外,慕容廆受晋命置“平州守宰”、慕容皝时期前燕的文职官员、将军、地方官吏、慕容儁时期的中央文职官吏、将军、地方官吏等职官或多或少地存在者前燕官学教育的影子[22]。
综上所述,审视慕容廆建立前燕、慕容皝自称燕王、慕容儁称帝的历史轨迹,慕容鲜卑能够将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从东北一隅发展到问鼎中原,固然有前燕统治者及其辅政集团励精图治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慕容鲜卑“主动向华”的理念支撑着慕容鲜卑人一路前行,成为前燕官学教育兴起的助推力,而慕容鲜卑的“族魂”即依赖于焉。而前燕官学教育恰恰是将慕容鲜卑主动向华意识由统治者的主观层面贯彻落实到慕容鲜卑民族教育客观发展的产物。
[1]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探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J].学习与探索,2011,(3).
[6]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程妮娜.中国地方史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259.
[8]马长寿.乌桓与鲜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9]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46.
[10]赵红梅.“渐慕华风”至“尊晋勤王”——论慕容廆时期前燕的中华认同[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11]周亚利.朝阳三燕、北魏遗存中反映出的汉文化因素[J].辽海文物学刊,1996,(1)
[12]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J].文物,1977,(5).
[13]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魏晋南北朝民族姓氏研究[J].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59.
[14]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5][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M].方壮猷,译.商务印书馆,1934:47-48.
[16]何芳川.“华夷秩序”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版,1998,(6).
[17]赵红梅.前燕慕容廆君臣的华夷观[J].学习与探索,2010,(5).
[18]北朝制度与文化革新研究·编者按(专题讨论)[J].学习与探索,2009,(5):219.
[19]赵红梅.两晋在慕容廆君臣中的地位与影响探论——以前燕慕容廆遣使入晋为中心[J].学习与探索,2009,(4).
[20]李凭.民族融合与制度革新——十六国北魏的历史轨迹[J].学习与探索,2009(5).
[21]赵红梅.慕容鲜卑的崛起与夫余的灭亡——兼论夫余灭国的慕容鲜卑因素[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5).
[22]赵红梅.向慕与吸纳:学校教育在游牧民族志社会的推进——以前燕官学教育为例[J].学习与探索,2012,(4).
[责任编辑:郑红翠]
From Admiring Chinese Culture to Transforming the Ethnic Customs—On the Promotion to the Rise of the official education in Pre-yan Dynasty
ZHAO Hong-mei
(Department of National Research,Jil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Changchun 130033,China)
The study approaches to the traditional social education of Murong Xianbei from two perspectives:the posterity of Donghu and the same customs of Xiongnu.Aftermoving to live in western Liaoning,and especially after the subsequent rise of admiring Chinese culture,Han cultural elements started to occur in Murong Xianbei cultural education.Under the driving ofMurong Gui,official education gradually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Pre-yan transforming ethnics,and in turn,the experience of official education became a prerequisite for Murong Xianbei to distinguish oneself as government official.It is believed that the appearance and rise of Pre-yan official education practically promote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at has produced a great influence on history of Xianbei nationality at the level of ideology and system culture.
Murong Xianbei;traditional education;social education;cultural education;official education
K289
A
1009-1971(2013)03-01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