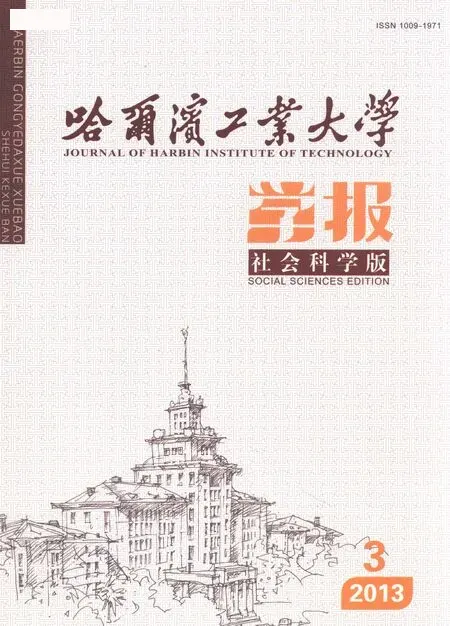元代生态思想与实践举要
赵 杏 根
(1.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215123;2.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南京210037)
元代主流社会中,蒙古民族一方面接受汉民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原来的务实等作风,以及重畜牧、好射猎、多肉食品等的生活习惯。他们对包括汉民族在内的整个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元代的生态思想及其实践,和此前相比,也有明显的发展。
一、灾异观念与蝗虫灾难的应对
作为董仲舒“天人感应”说重要部分的“灾异说”,长期笼罩中国社会。尽管唐代姚崇等和宋代社会在蝗灾应对实践上,宋代王安石等在理论上,对“灾异说”有了根本性的突破,但是,在元代,“灾异说”还有很大的影响。自然灾害发生,君臣首先从社会政治和君臣的所谓德行方面找原因,并作出相应的反应,希图以此消除灾难。《元史》卷30《泰定帝二》云,泰定三年,“中书省臣言:比郡县旱蝗,由臣等不能调燮,故灾异降戒。今当恐惧儆省,力行善政,亦冀陛下敬慎修德,悯恤生民。”[1]670同书卷39 云,顺帝年间,三年,“河南武陟县禾将熟,有蝗自东来,县尹张宽仰天祝曰:宁杀县尹,毋伤百姓。俄有鱼鹰群飞啄食之。”六年,“戊午,以星文示异,地道失宁,蝗旱相仍,颁罪己诏于天下。”[1]841《元史》卷122《塔海传》云,塔海为官多行仁政,“任庐州,时有飞蝗北来,民患之,塔海祷于天,蝗乃引去,亦有堕水死者,人皆以为异。”[1]3005《全元文》卷177 王恽《鸲鹆食蝗》云,某年有鸲鹆几乎吃光蝗虫之事。他根据汉书《五行志》,认为贪人尸禄,故感而生蝗。今鸲鹆食之,“意在位者不肖,将有因贪抵法而败者,不然,何食之既邪?纪之验他日之异。”[2]232同书卷526 程钜夫《议灾异》云:“乃若政令之或爽,天必出灾异以儆之,而儆之者,所以仁爱仁君,欲其久安长治而万物得其育也。故明君遇此则必省躬以知惧,昭德而塞违,诚格政修,天意乃得。于是灾变弥而和气复矣。”[2]99同书卷680 张珪《因灾异上泰定帝奏疏》,列举大臣们为非作歹事实和朝廷失政,云这些“皆足以感伤和气,唯陛下裁择,以答天意,消弭灾变”[2]763。这些,都完全是“灾异说”的思想。
不管如何,在元代,和宋代一样,捕杀还是应对蝗灾所普遍采取的手段。《元史》卷39《顺帝二》云,二年,“黄州蝗,督民捕之,人日五斗。”[1]835卷160《王磐传》云,巨富王磐,世业农,岁得麦万石,乡人号万石王家。某年蝗灾,王磐组织乡民捕杀蝗虫,三日而尽[1]3752。陈旅《安雅堂集》卷5《陈允恭捕蝗序》云,陈允恭受命到宝坻督促捕蝗虫,发现蝗灾严重而人力不足,乃祭祀社神和城隍,蝗虫于是大减,再加人力捕杀,蝗灾顿消[3]。陈允恭尽管行祭祀,但也不废捕杀。吴师道《礼部集》卷四《陈教授捕蝗宝坻》诗亦纪其事。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四有《捕蝗行》、《后捕蝗行》等关于捕蝗的诗歌[4]。释大䜣《蒲室集》卷二有《岳柱留守捕蝗诗有序》、王结《文忠集》卷二有《捕蝗叹》诗。王恽尽管还是不肯放弃“灾异说”理论,但是,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38《为蝗旱救治事状》,面对蝗灾,提出了若干应对措施,除了许多检讨社会政治的内容外,专门列一条,主张利用种种手段,捕杀蝗虫,清除蝗虫卵,并提出了利用蝗灾夜间趋光的习性,予以捕杀[5]。
和宋代相比,在蝗灾应对方面,元代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朝廷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对捕蝗不力者的处罚标准。《元史》卷102《刑法志》一云:“诸虫蝗为灾,有司失捕,路官各罚俸一月,州官各笞一十七,县官各二十七,并记过。”[1]2620张养浩《三事忠告》之《牧民忠告》卷下云:“故事:蝗生境内,必驰闻于上,少淹顷刻,所坐不轻。”[6]
第二,注重消灭虫卵。北宋欧阳修提出,捕杀蝗虫,越早越好,应该在蝗虫处于幼虫阶段就对它们有效捕杀。但是,他们没有从虫卵身上做文章。元人则注重消灭虫卵,把灭蝗的措施提早到虫卵阶段。《元史》卷93《食货一·农桑》云:“仁宗皇庆二年,复申秋耕之令,唯大都等五路许耕其半。盖秋耕之利,掩阳气于地中,蝗蝻遗种皆为日所曝死,次年所种,必盛于常禾也。”[1]2356元至正中敕撰《大元通制条格》卷16 在管理和技术两个方面,对尽早消灭蝗虫虫卵作了规定[7]。元代大规模的蝗灾远远比前代少,应该和这样的方法有关。这样的方法的背后,乃是人们对蝗虫生活史和习性的科学把握,而这一点,只有冲破“灾异说”迷雾之后,才有可能实现的。
二、人和动物的关系
在人和动物的关系方面,宋儒有一些著名的论述,例如“民胞物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等等,总的思想是把“仁”所覆盖的范围,由先秦儒家的人扩展到包括动物甚至万物。如此则容易在实践中产生思想上的混乱。例如,有害动物怎么办?肉食还吃不吃?元代的儒者,在人和动物关系理论方面,在宋儒的基础上,有所推进。
南北朝以下,几乎历代都有提倡杀戒的文章。《全元文》卷445 黄公绍《戒杀文》[2]44,纯粹是从佛教出发,宣扬杀戒,其理论无非是众生平等、六道轮回之类。同书卷741 袁桷《放生池祝圣文》[2]711,则完全是宋代众多的此类放生池文章的新版,站在儒家立场上提倡放生,化佛教活动为尊君。此外,元代几乎就没有什么专门提倡放生的单篇文章了,极少有人像宋朝许多士大夫那样提倡杀戒。这也许和元代主流社会的组成有关。蒙古等民族,在其传统饮食中,肉类占较高的比例。
古代政府,颁布禁止宰杀耕牛的文件,是不鲜见的事情。鉴于社会上宰杀耕牛的现象屡禁不止,王旭写了《不食太牢说》,此文从儒家“天理”、“人心”的角度,提倡不吃牛肉:“凡物有功于人者,古人皆有以报之,”牛有大功于世,人“既无以报之,又从而食之,呜呼,吾诚有所不忍者!非若世俗罪福果报之说也。顺天理而养人心,制口腹而遵国法,君子当有以戒于斯。”[2]503有利益关系在,杀戮者难以劝止。食客食用时,会觉得杀戮者非我,食之而心安理得。王旭云:耕牛不当食,劝食客不食,如此易于见功。食客数量多而杀戮者数量少,食客少一些,杀戮就会相应地少一些。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耕牛既然有大功于世,那么,对耕牛感恩,保护耕牛,也应该是劝社会行之的事情。这具有生物伦理方面的深刻意义。
在如何处理人和野生动物关系的问题上,元代儒者较之宋代儒者,也有发展在。胡炳文《四书通》之《论语通》卷四《朱子集注》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云:“仁人之本心,即天地生生之心也。其于物,有不得已而杀之者,而天地生生之心未尝不存焉。”[8]处理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这里有两条准则,一是“仁人之本心”,或者说是“天地生生之心”,也就是爱动物之心。一是“不得已而杀”。刘因《四书集义精要》卷十四《论语》十的阐述更为清楚:“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皆是心之也。然于物也,有祭祀之须,有奉养宾客之用,则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于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若夫子之不绝流、不射宿,则皆仁之至义之尽,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则王政行焉,鸟兽鱼鳖咸若矣。若穷口腹以暴天物者,则固人欲之私也。而异端之教,遂至于禁杀茹蔬,殒身饲兽,而于其天性之亲,人伦之爱,反恝然。其无情也,则亦岂得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庙,与商纣之暴殄天物,事虽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乱亡则一而已。”[9]哪些属于“不得已而杀”的范围?刘因所列举的“祭祀”、“奉宾客”,自然不足以尽之,那么这范围,以什么为标准来划定?应该是以儒家的礼为标准。先秦儒家,就已经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礼是社会文化规范,是社会文明的体现,礼的实践,必须有物质的形态,因此,人们遵守社会文化规范,必须付出物质的代价。按照礼消耗动物,这些动物就是人们遵守这些社会文化规范的代价。人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此类文化规范,维护社会文明,维护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等关系的和谐。佛教禁止杀生,在刘因他们看来,如果实践佛教文化,禁止杀动物,就无法实践儒家的礼,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等关系的和谐,也就无法维护,最终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政权的灭亡。在人和动物的关系问题上,佛教是动物中心主义,人不仅不能够杀动物,而且还要牺牲自己以保护动物;元代这些儒者,则绝不是动物中心主义者,他们主张为了人类社会,可以杀动物,应该是人类中心主义者。可是,他们认为生命的产生和存在,是天地之心,人们应该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对动物应该存爱惜之心,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杀害动物。因此,作为人类中心主义者,他们并非不爱动物,并非不尊重生命,并非认为为了满足人类的口腹之欲可以残杀动物,无条件地让动物为人类的私欲服务,乃至牺牲他们的生命。这和许多人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残害动物,具有本质的不同。
没有人类自身,当然也没有人类社会及其文化或者文明,因此,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健康,捕杀动物,也是属于必要的,也在“不得不杀”之列。人类自古就是这样做的。元代,有不少禁止捕猎的地方,但是,遇到灾荒之年,朝廷对公众开放这些禁猎区域,以便人们捕猎动物,解决生存问题。见《全元文》卷1050 元武宗《至大改元诏》[2]。至于其他地方的公共动植物资源,一般也是对公众开放的,这就也为百姓提供了一些可以利用的生活资源。《全元文》卷1815 陈恬《五乡水利本末序》,云上虞之夏盖、白马、上妃三湖之不可废,有五大理由,其五就是:“五乡细民,当青黄不接之时,家无粒粟之储,唯赖入湖采捕鱼虾,贸易钱米,以资口食之给。若以湖为田,鱼虾既不繁息,穷民不得采取,是犹扼吭而夺之食,生意微矣。”[2]500人们不为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滥捕滥杀动物,注意保护动物资源,让动物很好地繁衍,到灾荒之年,或者是别的困难时期,才有足够的动物资源,帮助人们度过难关。因此,关爱动物,不滥捕滥杀动物,客观上也是有利于人类自身。
元代,关于山泽资源的管理,大概是由于幅员广大,各地地理、物产和居民等等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规定。有些地方,是严格禁止捕杀野生动物的,而也有许多地方,山泽资源中的野生动物资源,是向社会开放的。因此,鱼鸟之类的小动物,就被大量捕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动物的了解,大大提高了捕杀的效率。王旭《黠鸟说》记载捕鸟的方法,王恽《鱼叹》、贝琼《观捕鱼记》,都记载作者亲眼所见捕鱼的绝技。《全元文》卷1725 马斯道《渔记》详细记载了他所熟悉的种种高效的捕鱼技术,然后云:“古者山泽皆有厉禁,今也民得以尽取,唯恐智巧之不足也。鱼虽欲自蔽,得乎?孔子曰:竭泽而渔,则蛟龙不藏其渊。非此之谓欤?”[2]116在这些文章中,尽管在生态理论上没有什么创获,还是承袭先秦儒家的相关思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科技发展导致动物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深深忧虑。
三、农业生态思想和实践
蒙古贵族起于游牧,入主中原后,曾经不那么重视农业。根据《元史》卷145 的记载,蒙古贵族别迭等就向掌握大权的窝阔台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1]3485,当然,这样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和实行。“但是在黄河以北,大量农田被占为牧场的情况还是存在的,一直到元世祖时,还发生官吏请求禁止农民秋收后复耕的事,理由也是‘恐妨刍牧’。”[10]94
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朝廷就开始重视农业。《元史》卷93《食货一》云:“农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初无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1]2354朝廷还在户部设立了专门管理劝农事务的司农司,这在此前的朝代是没有的。此后,朝廷和地方政府,在国家农业建设方面,多所作为。可是,在当时社会占绝对强势地位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都有重畜牧、尚武好斗的传统,加之国家崇尚武力,马匹等军用牲畜数量庞大,这些因素,明显不利于农业的发展,甚至给农业造成生态灾难。《全元文》卷1050 元武宗《至大改元诏》云:“农桑者,国家经赋之源,生民衣食之本。世祖皇帝以来,累降诏条,诫谕劝课,而有司奉行不至,加之军马营寨,飞放围猎,威扬骆驼人等,纵放头匹,食践田禾,损坏树木,以致农桑隳废。”[2]144同书卷1138 元仁宗《劝农桑》云:“诸官豪势要,经过军马及昔宝赤、探马赤、喂养骆驼人等,索取饮食草料,纵放头匹,食践田禾、桑果者,所在官司,断罪赔偿。”[2]30强势人群纵放牲畜损害农作物,竟然也会引发皇帝不止一次地下诏书禁止,这一方面说明此类现象之严重、之普遍,另一方面也说明朝廷对农业之重视。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朝廷颁布农桑之制一十四条[7],二十八年,又颁布农桑杂令。在这些文件中所蕴涵的农业生态思想和政策、技术,涉及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种植植物,绿化闲地和发展水产等。总之,这些思想或者措施,其中心是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土地和水域资源等自然资源,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
《四库全书》收录元代三部农书。一是《农桑辑要》[11]。该书分为七卷,遍及农桑畜牧林业等农村事务,以《齐民要术》为蓝本,摘取其他农书精要,而一一注明出处,凡是新添加者,都注明“新添”字样。元代官方曾经大量刊行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卷102 云:“盖有元一代,以是书为经国要务也。”“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于农家之中,最为善本。当时著为功令,亦非漫然矣。”[12]853此书的编撰者,署名是“司农司”,应该是集体编撰的。二是《农桑衣食撮要》二卷[13],鲁明善著。此书按照《月令》一类的体例,逐月记载农事。三是《农书》二十二卷[14],作者王桢,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历官丰城县尹。其书是古代一部集大成的农学著作,内容富赡,遍及当时农村种植、养殖、食品加工、器具制造等方面。《四库全书总目》卷102 言其“引据赅洽,文章尔雅,绘画亦皆工致,可谓华实兼资。”[12]853
这里不可能对这两部农书作全面的研究,仅仅将其中主要的生态思想抽出来探讨。
(一)引进外来作物
《农桑辑要》明确主张,有必要引进外来作物,以丰富物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该书卷二云:“大哉造物,发生之理,无乎不在。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遂即已试之效,令所在种之。悠悠之论,率以风土不宜为解,盖不知中国之物,出于异方者非一。以古言之,胡桃西瓜,是不产于流沙葱岭之外乎!以今言之,甘蔗茗芽,是不产于牂牁邛筰之表乎!然皆为中国珍用,奚独至于麻棉而疑之?虽然,托之风土,种艺不谨者有之,抑种艺虽谨,不得其法者亦有之。”其新添的关于苎麻和木棉的种植之法,特别详细。在某些地方种植的植物,也可以推广到其他的地方,使更多地方的人们获其利益。例如,该书卷五橙、橘、栌部分,都提倡把这些水果在其他地方种植。王桢的《农书》中,云芝麻、西瓜、石榴等都是外来作物,可见他也是同样赞同引进外来作物的。中国较多地引进外来作物,主要是在社会高度开放的汉朝和唐朝。元代,中国版图最为广大,对外交往几乎是空前的,各种农林畜牧产品,也随着人员的流动,散布到远方。各地所拥有的可以选择的物种资源,应该是非常丰富的。人们如果利用这样的资源,选择作物成功种植,那么,对发展当地经济、提高人们生活质量,肯定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当时肯定有许多人有过这样的努力。可是,我们从“悠悠之论,率以风土不宜为解”云云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引进外地作物的实验性种植,不成功者,也是较多的,于是有些人就以“风土不宜”为解,也就停止了这样的实验。《农桑辑要》认为,这样的实验不成功,未必是“风土不宜”,也许是种植者不够用心,也许是不得其法。如果种植者足够用心,且得其法,也许还是可以成功的。因此,这样的观点,不仅在当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且对引进外地物种,共享优良物种,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从选种到改良物种
物种的进化,可以在自然选择中实现。人为的选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物种的进化。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了选种的记载,选种在农业中的具体应用,肯定还要早得多。人为的选择,优胜劣汰,让物种的发展向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进行,这当然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选种层面的人为选择,只是决定生命个体的去留,并不改变生命个体自身的形态及其发展。在生命个体上的人为选择,则可以改变该生命个体的形态及其发展,使之向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生变化。《农桑辑要》等,都是提倡这样的选择的。《农桑辑要》卷三中,有对桑树上的枝条去劣存优以增加桑叶产量的技术。卷五论种西瓜,“欲瓜大者,一步留一科。科止(只)留一瓜。馀蔓花皆掐去。”这也是在某个生命体上作出选择,有所保,有所弃。弃是为了所保者而弃,以求最好效益。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中的骟树、修桑、修果树、西瓜去花等等,也都体现这样的思想。
在同一生命体上的选择,改变该生命体的形态和发展,涉及到其他生命体的选择等操作,还可以改变生命体的性质。《农桑辑要》卷三云,枝干丰大而条短叶薄的老桑树,可以截去干而留其根,然后嫁接幼小的枝条,使之焕发新的生命力。该书卷五云:“凡木皆有雌雄,而雄者多不结实。可凿木作方寸穴,取雌木填之,乃实。以银杏雄树实之,便验。”《农桑衣食撮要》卷下也详细记载了嫁接果树的方法。这些,完全是用人为的方法,改变生命体的性质。
嫁接技术乃至果木的远缘嫁接技术,《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元人予以大规模推广,并且有人将此类技术上升为理论,甚至提到哲学的高度。《全元文》卷384 张之翰《接花说》,则从理论的高度,对嫁接技术作发挥:“花,植物也,苟识其理,顺其情,能变俗而奇,仍旧而新,即此而彼,以人力之有为,夺化权于无穷。”[2]316通过人为的努力,人们可以改变生命体的性质,甚至向自然夺造化之权。
从选择生命体,到改变生命体的形态和发展,再到改变生命体的性质,这预示着人类对生命体的改变,将一步步地走向深入。
(三)“人事”胜“天时”、“地利”
王桢《农书》卷三《灌溉篇》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之说,尽管这是在论灌溉的时候说的,但是,这实际上是王桢最为重要的生态思想,这样的思想,统帅全书。“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孟子论战争的名句。在战争的语境中,天时、地利和人和,都是战争双方利用的对象,论者着眼的是对战争双方来说,此三者重要性之高下。可是,在农业的语境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之说,尽管也是说此三者的重要性之高下,但是,其中所蕴涵的“人事”战胜“天时”和“地利”的思想更为突出,因为“天”和“地”,在这里都是“人”有所作为的“对象”。在王桢看来,“人事”可以突破天时和地利的限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样的思想,在对农业灌溉问题的讨论和实践中,最为容易得到验证。该书卷三《灌溉篇》云:“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方今农政未尽兴,土地有遗利。夫海内江淮河汉之外,复有名水万数,枝分派别,大难悉数。内有京师,外有列郡,至于边境,脉络贯通,俱可利泽。或通为沟渠,或蓄为陂塘,以资灌溉,安有旱暵之忧哉!”又云:“各处陂渠川泽废而不治,不为不多。倘能循按故迹,或创地利,通沟渎,蓄陂泽,以备水旱,使斥卤化而为膏腴,污薮变而为沃壤。国有馀粮,民有馀利。”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天气晴雨是无法控制的,亦即天时是无法控制的。但是,如果地势得宜,可以有效地灌溉和排涝,那么,农业就可以不忧水旱,因此“天时不如地利”。地形地貌之类的地势,是可以通过人事来改变的,其地灌溉和排涝即使不方便,甚至不可能耕作,也是可以通过水利建设等人事来改善,创造出可以种植的良田,因此,“地利不如人事”。该书同篇又云:“复有围田及圩田之制。凡边江近湖,地多闲旷,霖雨涨潦,不时淹没,或浅浸弥漫,所以不任耕种。后因故将征进之暇,屯戍于此,所统兵众,分工起土。江淮之上,连属相望,遂广其利。亦有各处富有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地率有千顷,旱则通水,涝则泄去,故名曰围田。又有据水筑为堤岸,复叠外护,或高至数丈,或曲直不等,长至弥望。每遇霖潦,以捍水势,故名曰圩田。内有沟渎以通灌溉。其田亦或不下千顷。此又水田之善者。”该书卷十一《田制门》,用绘图加上文字的方式,详细介绍了区田、圃田、围田、圩田、柜田、架田、梯田、涂田、沙田等耕地种类,这些不同的耕地,都是人们改造自然的结果,也是战胜天时(水旱)和地利(地形地貌等地势)的证明,并且不断地体现着人们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进程。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这种人可以战胜自然的思想,还体现在王桢论农业水利之外的方面。例如,他认为,不仅地形地貌等地势是可以改变的,土质也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改变的。上文所引“使斥卤化而为膏腴”之说,就是用灌溉来改造盐碱地的技术。该书卷三《粪壤篇》,专门论述以肥料,强调土质也是可以通过施肥来改造的。许多具体的记载,尤为详尽。例如,关于肥料的种类,就有人粪、各种家禽家畜粪便、用植物制造的绿肥、用杂草或树叶等制造的草粪、用熏土和熏肥制造的火粪、用河沟池塘等水下污泥制造的泥粪和石灰粪等,此外,老墙土、草木灰、厨房下脚水及其他垃圾、粮食加工废料等等,也都可以作为肥料。其中火粪和石灰等,已经具有化学肥料的性质。把多种肥料放在一起加工并且使用,这样的肥料,已经具有复合肥的性质。关于施肥的方式,基肥、种肥和追肥,以及根据不同的作物和不同的土质施肥的具体方法等等,王桢都有详细的记载。《山东古代三大农学家》一书中说:“使我们感到这已具有肥料学的雏形。”[10]118
总之,在以人力改造自然以适合农业发展方面,在宋代陈旉《农书》的基础上,王桢《农书》又有比较大的发展。这既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战胜自然的经验总结,又有当时科技的支撑。从大禹治水以降,中国人民有非常丰富的水利实践及其理论研究,史书中一般都有《河渠志》,文人论述或者记载水利事务的文章很多,宋元更是如此。王桢《农书》中,农具是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用图文详细介绍农具300 多种。从这些记载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对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的充分信心。
结 论
尽管在理论上,元代士大夫尚未完全突破董仲舒以后几乎一直笼罩中国社会的“灾异说”,但是,在蝗虫灾害的应对实践上,元人较宋人有明显的进步,且完全突破了“灾异说”。在人和动物的关系问题上,元人明显比宋人务实,坚持人类中心论,既反对滥杀动物,也反对形形色色的动物中心论。在农业生态方面,从朝廷到士大夫,在科学研究和农业实践两个层面,其成就都卓然可观。
[1]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李修生,等.全元文[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3]陈旅.安雅堂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4]胡祗遹.紫山大全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5]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G]//四部丛刊(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4.
[6]张养浩.三事忠告[G]//四部丛刊(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4.
[7]至正中敕撰.大元通制条格(影印本)[M].北平:北平图书馆,1930.
[8]胡炳文.四书通[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9]刘因.四书集义精要[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10]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山东古代三大农学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
[11]司农司.农桑辑要[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1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3]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14]王桢.农书[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