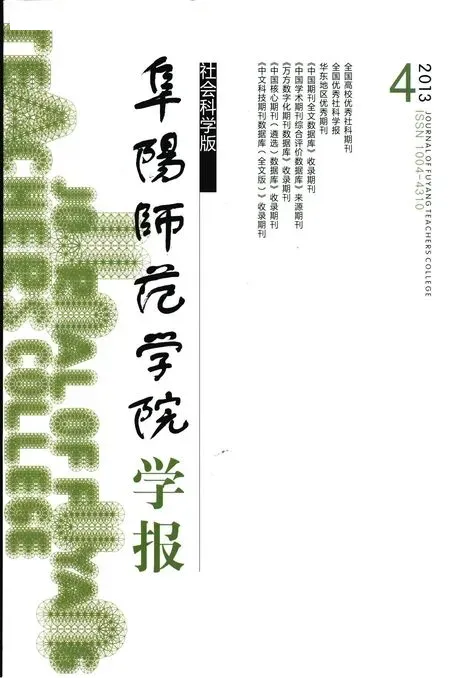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跨文化符号研究
钟晓文
(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福建 福州 350008)
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生活在一个“关于符号的符号世界”[1]。我们的社会认知与认知转移都依赖符号而进行。跨文化交际包含了异域文化认知及其跨文化转移,同样也依赖符号而进行。在异域文化认知中,认知主体通过异域文化符号认知异域文化,并通过跨文化转移,使这些异域文化符号进入认知主体文化,成为跨文化符号。根据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理论,异域文化认知实际即认知主体从其文化历史“先见”出发而进行的跨文化“视域融合”[2]391。跨文化符号不仅承载着主体的异域文化认知,而且逐渐融入主体文化的符号系统,流通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逐渐淡忘,跨文化符号只是伽达默尔所言的“不再有像自我和他者问题”的一种“历史流传物”[3]386。
研究跨文化符号,探究其符号生成,追溯其符号演变,深入其社会运用,对于重新审视异域文化的历史认知,观照当下的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社会语言构成,反思社会心理形成等等,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与理论意义。为此,本文尝试以哲学阐释学为逻辑起点,在广义修辞学视域下,运用符号学基本原理,试图探究跨文化符号的产生、修辞建构与修辞功能,呈现跨文化符号研究的多重视域,探讨跨文化符号成为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修辞、社会语言意识形态批评诸研究领域的一种理论视角的可能性。
一、符号与跨文化交际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跨文化交际就是一项重要的人类社会活动。自18 世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经贸的国际流通、政治生活的跨国影响,跨文化交际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必须基于两个前提要素:(1)正确的跨文化认知;(2)有效的跨文化转移。符号是社会交际活动的基本要素,同样是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元素,正确的跨文化认知与有效转移都离不开符号。
1.符号与跨文化认知
在跨文化交际中,正确的跨文化认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1)异域文化的认知;(2)主体文化的自我认知。
一般来说,跨文化认知的主要问题出现在前者,即对异域文化的正确认知。
异域文化的语言文字、社会现象、伦理道德、习俗礼仪、宗教理念等等,需要一个认知过程。就认知次序与认知接受而言,这个认知过程与主体文化的自我认知迥然相异。总体而言,文化的自我认知是一个伴随自身生存体验、人生经历的逐渐累积结果,而异域文化的认知则是通过对各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概念进行解读而获得。对于认知主体而言,异域的社会文化现象或概念其实是一种符号呈现,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符号的能指呈现。因此,异域文化的认知,即是异域文化的符号认知。然而,并非所有异域文化符号都能帮助认知主体进行正确而有效的异域文化认知,而必须借助异域文化的认知符号。
哪些社会文化现象或概念可以或可能成为文化认知符号并非由异域文化自身决定,而由认知主体选择决定。异域文化的认知符号选择必须基于两个向度的“否定性内容”[3]115,即该符号与同一文化系统其他符号的区别,该符号与认知主体文化系统相关符号的区别。正如索绪尔而言,区别产生意义。一般来说,差异性越大,就越有可能被选择作为异域文化的认知符号,而差异性则由认知主体的文化历史视域所“规定和限定”[2]388。因此,认知主体对异域文化的认知符号选择实质是一种主观选择。同时,异域文化的认知符号所指也并非取决于异域文化的自身认知,而将取决于主体认知。所以,异域文化认知符号其实是一种依据认知主体的选择而建构并被视为异域文化表征的核心符号,如近代西方的中国文化认知中的“龙”、“缠足”、“儒教”,近代中国的西方认知中的“十字架”、“夷”、“耶稣”。
在跨文化交际中,主体的自我文化认知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同样也包含着文化认知符号的选择问题。正确的自我认知应该是,把主体文化置于跨文化语境中重新认知,并依据重新认知进行认知符号的选择与重构,以便顺利实现跨文化转移。
2.符号与跨文化转移
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效的跨文化转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1)异域文化认知的有效转移;(2)主体文化自我认知的有效转移。
在跨文化交际中,认知主体完成异域(本土)文化认知后,还需要对认知进行跨文化转移,也就是说必须把其所认知的异域(本土)文化呈现于本土(异域)文化语境,让本土(异域)文化语境中的读者或话语接受者接受其认知。追溯跨文化交际史,我们很容易发现,早期的跨文化文本大多聚焦于对异域(本土)文化现象或概念的介绍或解释。换言之,这些文本所起的作用就是异域(本土)文化认知的跨文化转移。
认知主体为了顺利完成其认知的跨文化转移,首先通过话语或文本介绍异域(本土)文化的认知符号,通过话语或文本呈现其异域(本土)文化符号的认知过程,以获取本土(异域)文化语境的接受者对其异域(本土)文化认知的认同与接受。因此,异域(本土)文化认知的跨文化转移实质就是异域(本土)文化符号的跨文化转移,或更确切地说,异域(本土)文化认知的跨文化转移开端于异域(本土)文化认知符号的跨文化转移。
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如果说我们的交际障碍本质上源于跨文化认知及其跨文化转移障碍的话,其表现就是异域(本土)文化认知符号的跨文化转移障碍。换言之,符号的跨文化流通障碍。
从符号学视域而言,社会交际的过程其实就是符号的流通过程,跨文化交际是一种符号的跨文化流通。然而,符号的跨文化流通有其明显不同的特征。根据索绪尔的符号定义,符号由能指与所指组成,能指与所指如一张白纸的两面,密不可分[3]111。符号在同一语言文化系统中流通,能指呈稳定静态,而所指呈相对静态。符号在不同语言文化系统流通(即跨文化交际),能指与所指均发生变异。文化符号的跨文化流通,意味着符号能指与符号所指的同步转移并变异,转移变异后的符号其实是与原符号存在极大差异的跨文化符号。符号的文化属性越强,跨文化流通后所产生的变异越大,依据其所产生的跨文化符号与原文化符号的差异性越大,也就对跨文化交际产生的阻碍作用越大。
3.跨文化符号与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符号的产生源于跨文化认知与转移的需要,源于跨文化交际的需要。有效运用跨文化符号,跨文化交际则可以在更加广阔更加深入的层面进行交际实践,并进一步完善跨文化符号的建构认知与广泛接受。跨文化符号与跨文化交际呈现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通过跨文化文本或跨文化话语,认知主体对其跨文化认知进行跨文化转移,进行跨文化符号的建构或重构呈现。随着跨文化认知符号的逐渐增多,产生跨文化符号系统,认知主体运用这些跨文化符号及系统,可以有效地进行异域(本土)文化的意象或概念呈现,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跨文化文本或话语的接受者,在获得对异域文化的符号认知同时,将在其后各自的跨文化交际中运用相关的跨文化符号,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不仅如此,这些跨文化符号会被运用于社会交际的各个层面,逐渐融入主体文化,成为主体文化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其跨文化来源及本质将逐渐被淡忘。
综上所述,跨文化符号不仅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跨文化文本与跨文化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也可能成为社会语言研究的一个理论视域。跨文化交际的研究离不开跨文化符号的研究,而跨文化符号研究则更应重视其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的符号生成及其修辞建构。
二、跨文化符号的修辞建构
在探讨跨文化符号的生成及其修辞建构之前,首先对跨文化符号进行粗略的分类。根据符号的生成来源,跨文化符号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源于异域符号的跨文化转移,是认知主体向本土文化语境的接受者介绍异域文化;一类是本土符号的跨文化转移,是认知主体向异域文化语境的接受者介绍本土文化。根据符号的文化认知功能,跨文化符号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文化认知符号;一类是非文化认知符号。限于篇幅并为了论述上的方便,本文主要探讨具有异域文化认知功能的跨文化符号。
1.跨文化符号的生成
伽达默尔认为,“一切自我认识都是从历史地在先给定的东西开始的。”[2]387同样,异域文化认知也开始于认知主体的文化历史“先见”,完成于跨文化的“视域融合”,其表现即异域文化的认知符号选择并建构,而“视域融合”的直接结果就是跨文化符号。异域文化符号经跨文化转移而生成跨文化符号,跨文化符号所指是异域文化语境中的事物、现象或概念。异域文化认知符号的跨文化转移既是认知主体对异域文化认知的一种跨文化呈现过程,也是一种跨文化符号的修辞建构或重构过程。换言之,跨文化符号既是异域文化认知符号的跨文化转移结果,也是一种修辞建构或修辞重构结果。
跨文化符号的生成包括对异域文化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跨文化转移,其实质是一种新符号的建构生成。基于对异域文化符号的所指认知,认知主体在本土语言文化系统内设置或寻找相应的符号能指,进行符号能指变异,以便把异域文化符号向自己文化系统内转移,实现异域文化符号能指的跨文化转移。新的符号能指设置或找到后,认知主体在文本或话语中对新的符号能指进行介绍或阐释。这种介绍或阐释,表面上是认知主体对异域文化符号的介绍或阐释,但实际是一种基于文化比较并对异域文化符号所进行的修辞话语的“归化”[4]表述。然而,在话语深层,这种介绍或阐释则是在认知主体语言文化系统内对新符号的介绍或阐释,对新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呈现与确认,是认知主体在其文化历史“先见”下对异域文化的“视域融合”过程。当跨文化文本或话语的接受者从该修辞话语表述中获得新符号的认知,且被视为对异域文化符号的认知后,异域文化符号的跨文化转移完成,跨文化符号生成完成。
根据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符号的存在有两个基本原则:一、系统关联原则,即符号不能独立存在,任何符号都从属某一符号系统,并在该系统内与其他符号的比较区别中而生成意义;二、任意性原则,即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3]67跨文化符号的生成同样符合这两个基本原则,且在修辞话语的建构中生成。在广义修辞学视域下,修辞不仅参与跨文化符号的话语建构,而且参与跨文化意象的文本建构,使认知主体在其文化历史“先见”下实现对其异域文化认知的跨文化“视域融合”。
2.符号的系统关联性修辞建构
根据索绪尔的符号学原则,一个文化符号必须从属某一文化符号系统,并在与同一系统其他符号的区别中产生意义。[3]115跨文化符号的生成,必须基于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异域文化符号必须通过关联进入认知主体文化符号系统,即符号的系统关联建构;第二、异域文化符号必须与认知主体文化符号系统中的其他符号因区别而产生意义,与其他符号相区别而存在,即符号的差异性建构。
2.1 系统关联性修辞建构
在跨文化文本中,认知主体常引入本土文化相关符号,使异域文化符号置身于本土文化语境,通过修辞技巧改变异域文化符号的所指,在修辞话语中使异域文化符号与本土文化符号的所指产生错位与交叉,使异域文化认知符号通过本土文化的关联符号进入主体文化符号系统,以获得认知与接受。在近代西方的中国文化认知中,为了介绍中国的文化符号“龙”,首先通过跨文化转移为“dragon”,并与“devil”(魔鬼)等各种西方符号共处一个文化语境,通过修辞话语,“dragon”的符号所指“邪恶、凶兽、魔鬼”等被植入并替换“龙”的原所指“祥瑞、天命、威严”等,中国的“龙”通过“dragon”进入西方文化符号系统,西方语境接受者通过“dragon”认知“龙”,同时亦产生其文化认知:中国是一个以“邪恶魔鬼”为图腾的民族。
除一般常见修辞技巧外,“叙事”与“互文本”常成为特殊的修辞手段,参与修辞话语或文本的建构,创建异域文化符号与认知主体文化符号系统的关联。“叙事”,即“至少是一个事件或者事件状态的一个变化的陈述。”[5]“互文本”是法国当代理论家克里斯特娃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她认为,无论是文学或非文学“文本”,就文本本身并不能产生独立意义,其意义要从文本所置身的文本网络中获得,从文本间的关系中获得[6]。
认知主体常在其阐释文本中插入叙事话语,或直接运用叙事文本,对异域文化符号进行艺术性的修辞呈现,使读者在栩栩如生的叙事中感受并认知异域文化符号,认同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强制性”联系。[3]71此外,认知主体也常把读者所熟知并富含文化历史意蕴的话语作为“互文本”引入跨文化文本,成为阐释性文本里修辞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语境联想,在一个熟知的语境中获得异域文化符号认知,同时也接受互文语境所携带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可以借用并改造罗兰·巴尔特在《大众文化流行神话》中所建构的符号三维图式来描述叙事文本在跨文化符号建构中的作用:这个图表里有两个符号系统:一个是异域文化符号系统,异域符号能指与异域文化叙事建立“强制性”任意联系,建构“异域文化认知符号”,认知主体此时所见“仅仅是一种符号整体即一个整体性符号”[7];另一个是主体文化符号系统,“异域文化认知符号”作为跨文化符号能指,认知主体根据其主体文化“限制在对给定的、实在的、在场的部分进行替换”或提供包括主体文化叙事在内的所指[8],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强制性”任意联系,建构跨文化符号。

在异域文化符号的介绍或阐释文本中,这些符号同时置身于异域与主体两种文化语境中,认知主体利用各种修辞技巧,并以叙事与互文本等作为修辞手段,创造跨文化话语语境,让异域文化符号逐渐逸出其文化符号系统,在与各种主体文化符号的关联、碰撞中生成意义,从而获得读者或话语接受者的认知与接受,最后生成跨文化符号,并进入认知主体的文化符号系统。
2.2 系统差异性修辞建构
依据索绪尔符号理论原则,异域文化符号因与其文化符号系统其他符号的区别而存在,因其与认知主体文化符号系统其他符号的区别而产生意义。前者决定了认知主体对异域文化认知符号的选择,后者决定了认知主体对异域文化符号的跨文化转移。在跨文化文本中,这两种区别都通过修辞话语而确认或凸显,并使认知主体的认知通过跨文化符号的生成而合法化。
异域文化符号既从属于其文化符号系统,又与同一系统的其他符号相区别,这是异域文化符号的存在可能。认知主体对异域文化符号的认知,既通过其异域文化的认知,更是通过对该符号与其他符号的比较区别中认知。在与其他符号的比较区别中,认知主体选择那些具有异域文化典型性与社会重要性的符号作为认知符号。如美国教会近代在中国创办的英文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9]中,西方人选择“儒教”、“道教”、“佛教”作为“中国文化”认知符号,“缠足”与“妻妾制”作为中国女性的认知符号。当然,认知主体在选择异域文化认知符号的时候,也会以其主体文化作参照,选择那些与其主体文化符号差别明显的符号作为异域文化认知符号。在近代西方的“中国文化”认知中,“祖先崇拜”、“孝”常成为其“中国文化”的认知符号。这是认知主体的两个最主要的异域文化认知符号选择标准。
在跨文化文本中,异域文化符号置身于修辞建构的跨文化话语语境,通过与认知主体文化系统的其他符号相比较,其能指与所指差异性同时得以凸显,其符号所指获得认知,所生成的跨文化符号获得认可。认知主体通过各种修辞技巧建构跨文化话语,通过修辞手段建构跨文化文本,使异域文化符号或置身于文化比较话语,或呈现于历史叙事文本,或游弋于异域空间叙事文本(如游记)等各种修辞话语或文本中,异域文化符号的差异性获得充分的建构并表述,最终获得主体文化读者或话语接受者的认知与接受。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把中国“大都”修辞建构成一个美丽富饶遍地是黄金的神秘东方大国。在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通过各种历史叙事与旅游空间叙事文本,把中国“祖先崇拜”建构成为一个“自私、愚昧、保守、迷信”[9]的文化认知符号。在《教务杂志》中,跨文化文本既通过历史叙事文本,凸显中国文化认知符号的历时性差异,也通过与西方国家的比较文本呈现中国文化认知符号的共时性差异。
在种种差异性的修辞建构话语或文本中,跨文化符号在认知主体的文化中获得认知与接受。正是在这种种的差异性修辞建构,认知主体的文化历史“先见”亦在跨文化符号的生成中获得了合法性的建构与存在,但如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里所指出,修辞话语虽具“说服性”,但并“不是关于对错的一种指示,”[10]329跨文化符号先天携带了主体文化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偏见。
3.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性修辞建构
索绪尔强调,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3]115换言之,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建构的。认知主体通过修辞话语或文本,建构跨文化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逐渐完成跨文化符号的建构。
如果把异域文化符号设置为A(能指为Aa,所指为Aan),跨文化符号为B(能指为Bb,所指为Bbn),跨文化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性建构步骤如下:
3.1 异域文化符号的选择与建构:(1)认知主体通过异域文化符号认知异域文化,即通过能指寻找所指(Aa→Aa1+Aa2+…… +Aan),建构能指与所指的联系;(2)认知主体根据异域文化认知而选择或建构异域文化符号,即通过所指寻找能指(Aa1+Aa2+……+Aan→Aa),建构所指与能指的联系;
3.2 跨文化符号的能指建构:认知主体依据异域文化符号认知,在主体文化内选择或创造跨文化符号能指(Bb),实现异域文化符号能指的转移,即Aa→Bb;
3.3 异域文化符号的所指转移:认知主体通过修辞话语或文本,造成异域文化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断裂,利用符号的任意性原则,修辞建构异域文化符号所指与跨文化符号能指的联系(Aa1+Aa2+……+Aan←→Bb);
3.4 跨文化符号的所指重构:在跨文化符号的介绍、阐释或评论中,为了让符号在认知主体文化中得到认知与接受,修辞话语在原符号所指中植入新的所指,或者干脆对原符号所指进行置换,跨文化符号所指改变为Aa1+ Bb1+Aa2+ Bb2+…… +Aan+Bbn←→Bb,或进一步改变为Bb1+Aa1+Bb2+Aa2+……+Bbn+Aan←→Bb,甚至改变为Bb←→Bb1+ Bb2+……+Bbn。此时,跨文化符号建构完成。
在跨文化文本中,认知主体通过修辞话语或修辞文本,实现符号的所指,并逐渐实现对跨文化符号所指的相对固定。就跨文化符号的建构过程而言,在最初的异域文化认知中,异域文化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均置身于异域文化语境,但在其后的跨文化转移中,符号逐渐逸离原有的异域文化语境,融入主体文化符号系统,能指与所指均重新建构,生成一个新的跨文化符号。
4.跨文化符号与跨文化修辞话语
在跨文化话语或文本中,认知主体通过修辞话语呈现异域文化认知,建构跨文化符号,其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偏见也同时通过能指而获得形式固定。正是通过修辞,跨文化文本表面上成为异域文化的“客观”与“真理”认知呈现,如柏拉图所言,“(修辞学)不需要知道事情的真相,而只要发现一种说服的技巧,这样他在无知者中出现时就能显得比专家更有知识。”[10]334接受者通过修辞话语认知跨文化符号的所指呈现,接受跨文化符号,并接受符号所指中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偏见,忽略异域文化“理解的历史性原则”[2]341与符号的“效果历史”[2]385要素。
跨文化文本,在其深层,就是认知主体对其文化历史“先见”与“视域融合”的修辞化过程。认知主体运用修辞话语进行跨文化认知转移时,都会有意无意地运用修辞功能掩饰其异域文化认知的主观性特征:(1)“掩盖”异域文化认知活动中的文化历史“先见”的主导实质;(2)并把认知主体的文化历史“先见”修辞化为普适性、恒远性的价值评估参数;(3)同时,认知主体会引进一些具有普适性价值所指的概念符号,融进其价值评估体系,使其异域文化认知修辞化为“客观性”或“真理性”的认知。
综上所述,跨文化符号研究,尤其是跨文化符号的生成研究,离不开修辞话语分析,而跨文化修辞话语研究同样也离不开跨文化符号研究,因为跨文化符号的生成或建构不仅是跨文化修辞话语的一个重要目标,跨文化符号本身也具备修辞功能,是跨文化修辞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修辞话语的异域文化意象呈现,而且随着跨文化符号在认知主体社会的接受、运用与流通,其修辞功能亦显现于社会生活的各种修辞话语之中。
三、跨文化符号的修辞功能
跨文化符号的修辞功能源于跨文化符号的生成与存在特性,既具一般符号特征,亦具跨文化独特性。跨文化符号是“任意的”,其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强制性”的,因而在某种条件下也是可分离的;跨文化符号所指既包含异域文化内容,又包含主体文化价值判断,因此跨文化符号既从属异域文化符号系统,也从属主体文化符号系统;跨文化符号既因与其他异域文化符号的差异而产生意义,又因与主体文化符号的差异而产生意义。跨文化符号不仅在跨文化语境中使用,也在非跨文化语境中广泛使用,而修辞功能也因语境不同而呈差异。
在跨文化语境中,跨文化符号与其他异域文化符号一起参与话语或文本建构,呈现异域文化意象,同时又与主体文化符号一起,既凸显异域文化意象的差异性,又彰显主体文化的价值体系,产生两种文化符号系统的张力关系,直接影响读者的文化或价值认知。
一般而言,跨文化符号的修辞功能主要显现于非跨文化语境。从广义修辞学视域来看,跨文化符号的修辞功能显现于其所参与的话语建构、文本建构与主体精神建构三个层面。[11]4
1.跨文化符号与修辞话语建构
就话语建构层面而言,跨文化符号因其符号的建构、形式与所指特征而产生修辞效果,增强整个话语的修辞效果:
符号能指:跨文化符号的能指,有些未经跨文化转移,而以异域形式直接进入主体文化系统,如近年流行的“你必须hold 住”、“你out 了”;有些符号能指则通过音译简单转换而间接以异域形式进入主体文化系统,如“这个人很会做秀”、“那个学者有很多粉丝”。这两种跨文化符号以其能指形式的异域特征,在所建构话语中显现与其他符号的明显差异,制造视觉冲击,产生什克洛夫斯基所称的“陌生化”[12]修辞效果。
符号所指:跨文化符号的所指,因其异域文化内涵而产生陌生化修辞效果,如“罗曼蒂克”、“柏拉图式爱情”、“法国式浪漫”等,在所建构话语中,很容易把读者带入异域语境,使读者的阅读产生时间与空间的延展,对话语表达内容进行认知与接受。
能指与所指的联系:跨文化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因建构时间等因素而相对松散,在话语建构时适合增加新所指或进行所指置换,从而使符号所指变异,产生修辞效果。近年出现的大量“门”词汇,如“艳照门”、“东航吸烟门”、“名表门”,“门”不仅从当年美国“水门事件”丑闻的空间所指“水门”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其所指为“丑闻”的独立符号能指,而在与其他符号组合时,既隐现符号的异域色彩,又修辞化其所指。
符号的系统关联:跨文化符号从属于“双重”符号系统,既从属异域文化符号系统,又从属主体文化符号系统,参与话语建构时:(1)容易引发读者的异域文化联想而产生陌生化修辞效果,如“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式的文艺复兴”;(2)因其与主体文化符号差异而生成意义,并因文化系统差异而产生张力,增加话语修辞效果;(3)因其与异域文化符号差异而生成意义,引进异域文化参照,增加话语修辞效果。
2.跨文化符号与修辞文本建构
根据广义修辞学理论,文本建构就是,“特定的表达内容在篇章层面如何向特定的表达形式转换的审美设计”。[11]43-44跨文化符号参与修辞文本建构的常见方式,除因其所参与的修辞话语而延伸至整个文本外,还以其符号的跨文化特征,使表达内容实现程度不等地跨文化表达形式转换,实现其修辞效果:
跨文化符号参与文本建构,有助于在篇章层面拓展表达内容的空间语境,在双重文化语境的既联系又冲突的语境中,制造修辞张力,而读者则在双重空间语境中接受文本意蕴,获取内容认知。如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的时候,同时引入英国文化、美国文化、德国文化、法国文化与古希腊文化诸跨文化符号,使西方读者通过在欧美各国文化的空间视域上接受文本所呈现的“中国人的精神”,又可以通过古希腊文明历史的纵向视域上接受文本表达内容。
跨文化符号参与文本建构,常引致整个话语既具异域文化的话语形式特征,又具主体文化的话语形式特征,而文本亦因双重文化语境而呈现“陌生化”形式并产生修辞效果。如鲁迅《摩罗诗力说》,整个文本以文言论述,但间插大量跨文化符号,如“英人加勒尔曰,得昭明之声,洋洋乎歌心意而生者,为国民之首义。意太利分崩矣,然实一统也,……有兵刃炮火,政治之上,……无不腐蚀……”,[13]66“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13]70引文中跨文化符号,不仅在内容上彰显文本所述,而以异域话语形式间插文本,使整个文本隐显多重文化语境,呈现“陌生化”形式。
跨文化符号参与文本建构,因其异域文化所指,文本既表达又偏离主体文化符号系统;因其主体文化所指,文本既表达又偏离异域文化符号系统,使文本成为一种“建构和解构交织”的修辞文本。[11]57如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13]165-173,文本表面以评论易卜生《娜拉》行文,随着文本展开,“娜拉”不再是所指为“易卜生戏剧人物”的一个特定符号,逐渐脱离符号的原戏剧语境,演变成一个所指为“觉醒女性”的跨文化符号,就整个文本而言,新所指隐然取代了原所指,并参与文本建构。然而,如果读者没有“娜拉”的原所指认知,则在接受该文本内容认知时将产生困难;如果读者固守“娜拉”的原所指认知,则该所指认知会一直牵制或干扰读者的文本内容认知。因此,“娜拉”作为一个跨文化符号,事实上使《娜拉走后怎样》成为一个“建构和解构交织”的修辞文本。
3.跨文化符号与主体精神建构
跨文化符号生成于认知主体文化历史“先见”下的跨文化“视域融合”,因此认知主体所具有的主体文化的“优越性”或“自卑感”、主观价值或意识形态偏见都将置于符号所指之中,并渗透于所参与建构的话语或文本之中,也将直接影响接受者的自我文化认同或评价,对异域文化的认知或评价,影响或重构其精神价值观念。跨文化符号作为一种修辞参与主体精神建构的主要表现是:
跨文化符号的修辞运用,扩展了主体的时空视域,主体在更开阔的时空视域中建构自己的认知与自我的认知,同时也通过跨文化符号所营造的语言空间,扩展了主体的生存空间,“世界通过语言向人敞开,人借助语言倾听存在的声音,体验存在的诗意”[11]60。
跨文化符号带着异域文化语境进入主体文化系统,客观上打破了文本的单极主体世界,建构了文本的多元共存世界。
跨文化符号带着异域文化所指进入主体的文本世界,事实上创设了一个新的焦点,带进了一个不同的经验或现象,既扩展了主体的认知范围,也使主体的原有认知因所增加的参照系而获得修正,甚至包括对其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修正。
跨文化符号作为一种认知主体文化历史“先见”下的“视域融合”产物,其被置换或增加的具有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偏见的内容,也在相关的话语或文本中起着修辞作用,干扰主体的认知与判断。在当下大量的“与国际接轨”的表述话语或文本中,英语形容词“international”(国家之间的)变成了一个汉语名词“国际”,被修辞化为一个大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符号所指的同时,增添了“价值判断”所指,其原所指的“国家之间”被置换成“发达、文明、科学”等价值判断,那些标示着“具有国际水平”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充斥着“与国际接轨”表述的各种话语与文本,扭曲着中国读者的自我认知:中国一直位于“国际”之外,中国的各种水平一直“低于”“国际”。
综上所述,跨文化符号不仅因其异域文化认知所指而进入主体文化符号系统,也因其所具有的独特修辞功能在主体文化符号系统中流通,成为社会生活各种修辞话语的组成部分。作为修辞的跨文化符号不仅携带着其建构之初的“文化先见”,而且也影响着文本主体的世界认知与自我认知。因此,跨文化符号研究,应包含对其修辞功能的研究,而话语或文本的修辞分析应充分考察跨文化符号的修辞作用。
四、结语:跨文化符号的研究价值与理论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在种类繁多的符号中,跨文化符号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现代越来越频繁的跨文化交际。虽然现代的交际手段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先进,跨文化交际变得越来越便捷,然而,跨文化交际仍然有着种种技术之外的障碍,其跨文化特征清楚地显示,文化差异性仍然是这种人类重要活动的最主要障碍,包括对异域文化的认知,对异域世界的自我呈现,而所有这些必然是通过跨文化符号而进行的。因此,研究跨文化符号,探索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生成及其对跨文化交际的作用,有着非常现实的理论意义。跨文化符号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个组成要素,随着跨文化符号研究的深入,必将有助于推进跨文化交际研究。
自索绪尔以来,符号越来越获得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视。对符号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所处世界的关注,也是对我们人类自身的关注。对于符号的生成,研究者进行了大量探索,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生成模式,其中索绪尔模式与皮尔士模式影响最广。然而,就笔者浅见,这些模式并未能很好地解释符号的生成,尤其是文化符号所具有的伦理价值与意识形态偏见等判断功能。如果把广义修辞学理论引进符号的生成研究,不能说是解决了问题,但至少多了一种有理论价值的研究视域。为此,笔者大胆把广义修辞学理论引进跨文化符号研究,试图通过跨文化符号的修辞建构生成研究,探讨符号生成与修辞之间的关系,为符号的生成研究尝试一种新的视域。
跨文化符号不仅出现在大量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而且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大量使用,成为社会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运用广义修辞学的基本原理,探讨跨文化符号的修辞功能,不仅是跨文化符号的一个研究维度,也为广义修辞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观照对象。同时,跨文化符号也将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探寻异域文化对主体文化社会语言的建构,并进而对社会心理的建构作用。
跨文化符号既是一个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视域,而在广义修辞学视域下进行跨文化符号研究,可以在学理上部分解决跨文化符号的生成问题,跨文化符号本身的修辞现象及功能、跨文化符号的意识形态意义也应得到研究关注。拙文所述,只是一种粗鄙的理论尝试,逻辑论证、文本案例分析等远远不足,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尤其需要在话语文本分析实践中检验与论证。
[1]Terence Hawkes,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77.2nded.p.1.
[2][德]汉斯-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F.de.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trans.Roy Harris,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4]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ion'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8.2nd ed.p.240.
[5]Gerald Prince,“Revisiting Narrativity”,in Narrative Theory (Volume I),edited by Mieke Bal,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4.p.11.
[6]Graham Allen,Intertextuality[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0.p.1.
[7]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M].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96.
[8][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523.
[9]http: //www.china.amdigital.co.uk.ezproxy.auckland.ac.nz/Collections/doctype.aspx? doctype=1.
[10]柏拉图.柏拉图全集: 第1 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1]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2]Victor Shklovsky,“Art as Technique,”in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Four Essays,trans.Lee T.Lemon and Marion J.Reis.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5.p.5.
[1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