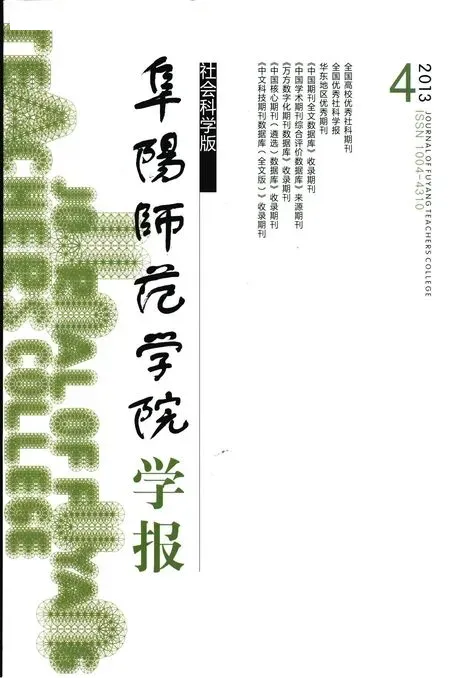关键词及其意识形态:文革文学批评话语的广义修辞学分析
肖翠云
(1.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福建 福州 350007;2.闽江学院中文系,福建 福州 350108)
从研究方法上看,对文学批评话语的研究,可以在文艺学领域展开,也可以在语言学领域展开。文艺学的研究着重探讨批评话语生成的历史语境、文化渊源、发展逻辑以及价值取向等,侧重在话语背后找寻其思想意义;语言学的研究着重探讨批评话语的生成方式、结构特征、语法功能、语用频率等,侧重于话语本身的形式研究。两种研究方法在各自领域内具有自身特色和阐释力,但也因单一视域的局限而留下了阐释的盲点。广义修辞学重在打破学科界限,在学科渗融的开阔视野中将语言学与文艺学结合起来,以语言学的形式研究为起点,既探寻话语形式自身的修辞特征,又将话语延伸到文本,探究话语的文本建构功能,并进一步发掘话语形式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构筑起“话语层面(修辞技巧)→文本层面(修辞诗学)→人的精神层面(修辞哲学)”三维立体研究框架[1],从而为文学话语(包括批评话语)研究打开了深广的空间。
文革期间(1966-1976年)的文学批评高频使用一大批特有的较为稳固的话语,如“小资产阶级”、“走资派”、“牛鬼蛇神”、“毒草”、“黑线”、“黑八论”、“三突出”、“反攻倒算”等,这些话语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意识形态色彩。本文拟从中提取两组使用频率较高的关键词,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运用广义修辞学理论,在修辞学与文学批评的融合视域中,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话语进行细致解剖,以揭示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时期文学批评话语的独特性。
这两组关键词是:“批判组”及其类义符号和“毒草”“香花”及其类义符号。“批判组”及其类义符号如“编者按”、“写作班子”等是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主体,它们的出现象征着文学批评主体由个体向集体转变;“毒草”、“香花”及其周围所汇聚的类义符号如“黑线”、“鲜花”等是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经常使用的话语,它们之间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意味着文学批评方式的两极倾向。这两组关键词是文革文学批评中最为突出的符号,烙有文革时期特有的时代印记。“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2],一方面,符号诞生于一定的历史时空,带有特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符号的广泛运用又会反过来强化时代的意识形态内涵。因此,从这两组关键词出发来考察文革文学批评话语的修辞特征以及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可行的。
一、“批判组”及其类义符号:文学批评主体的集体出场
与文革时期“公开文学”创作主体的集体出场——“写作组”[3]相对应,文革文学批评主体也呈现出集体性特征,表现为各种“批判组”及其类义符号。在“文革”前即“十七年”文学批评中文学批评主体大多数是个人,很少以集体的名义署名。从洪子诚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所附的“1949-1976年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编目”来看,在“1949-1960”的文学批评中批评主体基本上都是个人,从1961年开始出现“理论研究组”、“《文艺报》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等集体署名现象,1966年以后“编者按”、“批判组”以及化名为“初澜”、“江天”、“任犊”等写作班子开始涌现,文学批评主体的集体性特征逐渐凸显。文学批评主体的集体性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
(一)《人民日报》编者按
文革时期,在政治的压力之下,许多报刊因发表了“毒草”文章或为“毒草”辩护的文章而遭受批判,被迫停刊。能够生存下来并且获得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主要有“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在“两报一刊”中《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承担着介绍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及主张的重任,传达着党中央国务院的声音,是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是最高话语权的象征。因此,它在发表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时常常以“编者”的身份所下的“按语”,往往为当时文学批评定下了基调,引导着文学批评的政治走向。如:
1966年1月9日,《人民日报》以两个整版篇幅开始选载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编者按称:“它是近年来我国文学工作者进一步革命化,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所取得的成果之一。”
1966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北京上海西安天津工人批判影片<球迷>》,编者按称,影片导演“笑里藏刀,用‘嘻笑’的障眼法,肆无忌惮地丑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丑化社会主义社会,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1967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师红游的文章《揭穿肖洛霍夫的反革命面目》,编者按称:“肖洛霍夫、西蒙洛夫、艾伦堡、特尔挖多夫斯基之流,特别是苏修文艺鼻祖肖洛霍夫的一些作品,流毒很大。”
《人民日报》特殊的身份符号和政治地位,使它的“编者按”具有以下特征:(1)在批评标准上基本上从政治的角度对作家作品进行定性,这种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当时文学批评的方向,规范着其他批评文本的政治取向,其他批评文本也会自觉与其保持一致,形成声势浩大的批评合力,掀起一股又一股的批评浪潮。(2)在话语上多采用简短的肯定句式,显得简洁有力;也很少出现“商讨”、“讨论”等语汇,表现出不容置疑的语气。这些特征与《人民日报》在文革时期所拥有的话语权是相一致的。与文革时期《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激烈专断风格相比,文革前的文学批评中的“编者按”则显得更为温和折中。如《中国青年》1959年第2 期在发表郭开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时所加的“编者按”是:
《青春之歌》就是这些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它和其他作品一样,受到了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看了《青春之歌》后,很多青年同志向本刊编辑部来信反映,认为这是一部好书,它塑造了卢嘉川、林红、林道静、江华这些光辉共产党员的形象,给每个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本书的缺点严重,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感情,并已经在读者中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下面发表的郭开同志的意见,就代表了这种看法。
从这两种不同的反映来看,我们感觉到目前在阅读与评论文学作品中,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应该怎样来全面的估价这些反映现代生活的文学作品? 应该怎样正确对待这些作品的缺点? 这不仅是关系到对于这些作品的评价,而且也关系到人们看问题的观点和方法,是很值得大家来探讨的。我们除了发表郭开同志的文章外,还拟继续发表有关文章。
从这份“编者按”可以看出:(1)没有直接对《青春之歌》进行定性,没有给《青春之歌》扣政治大帽子,而是客观描述了当时文论界对这部作品的评价;(2)把对文学批评限定在学术争鸣的学理层面,没有上升到路线之争和阶级之争;(3)允许对同一文学作品发表不同见解,倡导自由探讨。这和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编者按的做法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这种不同正好反映了政治环境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和渗透。
(二)“XX”写作班子
在文革后期的文学批评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初澜”、“江天”、“任犊”、“高炬”、“闻哨”、“洪途”、“梁效”等署名文章,这些署名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乍一看,跟一般人的署名没什么差别,很容易把它当成是某个人的真名或笔名,但若细细体会,便会发现这些名字的政治色彩很浓。与文革时期被美化的文学作品如《决裂》、《闪闪的红星》、《春苗》、《春潮急》、《千重浪》等的命名一样,蕴藏着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实际上,这些名字是“四人帮”写作班子的笔名,“这些特定的符号,代表了集体言说的‘样稿’,出自集体写作班子的公开文本,往往成为政治策划的信息载体”[3]。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夺取政治领域的领导权,首先必须夺取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利用舆论造势,加大批判力度,是其必要手段。但光靠姚文元、戚本禹这两个“笔杆子”显然力量不够,但若全部上阵,又怕目标太大,更怕暴露自己的政治野心。因此,采取“笔名”的方式不仅达到众人造势的目的,而且达到隐匿自己身份的目的。
从1973年开始,以“初澜”为首的“四人帮”写作班子开始大量炮制批评文本,在1974年出版的署名为“初澜”的《“坚持正确方向 坚持斗争哲学”文艺评论集》中一共收录了14 篇文章,令人惊讶的是,这14 篇文章均发表于1974年,其中10 篇发表于《人民日报》,3 篇发表于《红旗》,1 篇发表于《光明日报》,一年之内竟然写了14 篇文学批评文章(这里的统计仅以“初澜”的这部文艺评论集为依据,其他文章未计在内),而且70%左右发表在当时的“权威报刊”《人民日报》上,这不能不让人惊奇,也不能不让人反思。不仅如此,其他以“江天”、“任犊”、“闻哨”、“洪途”、“梁效”署名的文章基本上都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且时间大多集中在1974年。“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成立于1973年左右,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炮制出如此多的批评文章并占领了党的机关刊物,政治野心可见一斑。
(三)各种类型的“批判组”
文革时期文学批评主体的集体出场,除了“编者按”和“‘四人帮’写作班子”这两种表征形式外,更为常见的是各种类型的“批判组”,其身份相当复杂:
北京人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新北大公社尖兵革命造反团
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
旧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
安徽劳动大学中文系写作组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复旦大学中文系大批判组
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
中共上海电影制片厂委员会
从署名来看,这些以集体名义出现的身份符号其表层能指十分明确,有“红卫兵、革命造反团、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大学中文系批判组、艺术研究所、电影制片厂委员会、京剧团剧组”等,但深层所指却相当模糊,我们很难判断其真实身份,首先,它是个人借用集体的名义还是本身就是一个集体?其次,“集体”的成员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批判组”其成员到底是学生还是老师?“文化部艺术研究所”的成员是知识分子吗?等等。这些疑惑很难解释清楚。尽管如此,这些集体符号本身就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值得探讨。
“批判组”尽管身份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来自“民间”。这里的“民间”不是一个地域空间概念,而是一种相对于“官方”的身份和立场。相对于《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和“四人帮”写作班子的“官方”身份而言,“批判组”是一个“民间”群体,包含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众。在话语权上,“官方”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因其“党报”身份而具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因江青的特殊身份和政治权势而具有相对权威;而处于“民间”的“批判组”则不具有权威,它要获得“官方”的支持和认可,唯一的选择就是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作“官方”声音的传声筒。从各“批判组”所写的大量批判文章来看,在观点上都是唯主流意识形态是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遭批判的就是自己。
文革文学批评主体的集体性出场并不意味着“个人言说”的消失,从形式看,也有个人署名的文章,但这种“个人言说,实际上只是在复制非个人化的集体话语,真实的话语主体的位置仍然是缺席的。况且,即使有的作品由个人执笔,也绝不是‘我性’言说,因为不管是‘写什么’,还是‘怎么写’,都不是自我设定”[3]。“个人言说”的集体化突出地表现在:第一,没有“我性”言说的权利和自由,由于官方话语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话语的言说内容、言说方式和言说渠道,处于民间立场上个人完全丧失了“我性”言说的自由,沦为官方言说的“傀儡”。第二,在批评中经常以“我们”来取代“我”,把微不足道的个人“小我”努力地纳入到声音洪亮的集体“我们”之中,寻求“我们”的集体力量来保护“我”自己。如,文革文学批评文本的结尾大多采用动员式呼告句,动员式呼告句的主要特点是通过激励性、呼吁性或要求性话语动员大家行动起来,期待话语能够产生实际的言后行为。句式中充满了“我们必须”、“我们一定要”、“我们希望”、“我们相信”、“我们决不能”、“让我们”等立誓言、表决心的话语,具有很强的鼓动性。这种以“我们”来言说的方式,不仅体现了借用集体的话语权威来寻求强势话语庇佑的心理,“还体现了一种疑惧被判别为与‘我们’相对立的敌对话语群体,渴慕‘归属’革命阵营的心理,这种话语立场倾向是文艺批评的写作主体屈从于主流意志规范的一种心理防御策略”[4]。如果说,“民间”集体和个人在向“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靠拢过程中,最初是迫不得已的被动选择的话,那么,随着文革时期毛主席的“神化”以及“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发行和广泛传播,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就已经自动化为大多数言说主体的自觉选择了。
二、“毒草”妖魔化、“香花”英雄化:文学批评方式的两极倾向
借用“毛主席语录”来说,文革文学批评不仅“破字当头”,而且“立在其中”,不管是“破”还是“立”,“毛主席语录”都是批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破”的是“毒草”和“文艺黑线”,“立”的是“香花”(以“样板戏”为代表)和“三突出”理论。对“毒草”和“黑线”采取的是彻底铲除的“棒杀”式批评,对“香花”和“三突出”论采取的是极力美化的“捧杀”式批评,这两种批评方式截然对立,不可调和,从而形成了文革文学批评方式的两极分化倾向。
在这种两极化的文学批评中,产生了一大批在语义上相互对立的词汇,它们与“毒草”和“香花”形成修辞汇聚和对立语义场。本文以文革时期文学批评文本的“标题”为语料①,从中抽取与“毒草”和“香花”相关的类义符号,来说明文革文学批评方式的两极化特征。列表如下:

“毒草”及其类义符号 “香花”及其类义符号身份 黑线、黑话、黑旗、黑店、黑货、黑帮、黑戏、黑会、黑碑、死敌、叛徒……鲜花、新花、奇葩、榜样、样板、新人、英雄、战歌、赞歌、史诗、画卷……性质 坏、黑、反(反面、反动、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好、新(新人、新事、新时代、新一代、新文艺)、生动、伟大、优秀、壮丽、壮阔、光辉……罪行/成就歪曲现实、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贩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货、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宣扬修正主义思想、复辟资本主义……塑造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典型、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历史、为一代新人立传、宣告了文艺黑线的破产……批评方法粉碎、埋葬、肃清、砸烂、揭露、搞垮、清算、铲除、炮打、斗倒批臭、撕破面皮、揭穿真面目……祝贺、赞扬、歌颂、欢呼、喜读、鼓舞、保卫、捍卫……
对常态的文学批评来说,本应站在唯物主义哲学的辩证立场看待问题,不管是“毒草”还是“香花”,一视同仁,不带有色眼镜,才能保持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但在非常态的文革政治语境中,在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等同,学术批评等同于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时,文学批评很难保持中性立场。从当时的文学批评来看,批评主体没有选择“批评什么”和“如何批评”的权利,对已经被“官方”定性为“毒草”的作品只能是毫不留情地“炮打”,将其“斗倒批臭”;而对“官方”定性为“香花”的作品只能是竭尽所能地“吹捧”,坚决加以捍卫。这种非此即彼、不允许存在任何中间状态的极性批评方式,在话语方面主要体现为:
(一)褒贬对立词语高频复现
这一点从上表所列出的批评文本的“标题”关键词即可看出。除了标题所显示的“贬抑性词语”和“褒扬性词语”的对立外,在批评文本的正文中更是屡见不鲜,如(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但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一直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前进的。一个时期以来,伴随着社会上的反对文艺革命,革命样板戏的大辩论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清晰地出,在文艺界大刮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那个的、党内的走资派。……
(焦宏铸《驳“一花独放”论》,《人民文学》1976年第2 期)
上述两段话语在语义上相互对立,第一段是赞扬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主要是革命样板戏)的,一共5 句话,运用了14 个褒义词,极力美化革命样板戏所取得的成就,并运用4 个排比句来加强气势;第二段是批驳“一花独放论”的,一共3 句话,运用了10 个贬义词,极力丑化走资派及其言论。批评的对象水火不容,批评的话语也针锋相对,没有调和的余地。
(二)绝对性词语高频复现
文革文学批评文本的标题和正文中经常使用语义绝对的词语,如“最”、“极”、“完全”、“绝对”、“根本”、“任何”、“一切”、“千万”、“彻底”、“坚决”、“必须”等进行渲染和夸张。如:
仅以“彻底”为例,“彻底”一词很受文革文学批评的青睐,不仅在文本中经常现身,而且在文章的标题中也频频出现。如:江青、张春桥的《文化部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周扬反动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人民日报》1966年8月6日)、“国防歌曲”的流毒》(《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7日)、电影界“老头子”夏衍的反党罪行》(《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0日)、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人民日报》1967年7月13日)、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风雷>》(《人民日报》1968年7月8日)、上海市文化系统召开的电视斗争大会无产阶级的死敌——巴金”、《两种根本对立的战争观——诋毁人民战争的一批反动影片》(《人民日报》1969年12月24日)等等,这些标题用“彻底”一词显示了坚决不让的态度和斗争到底的决心,使一大批被定性为“毒草”的作品和“死敌”的作家走向了灭顶之灾。绝对性词语的高频使用是文革文学批评思维方式片面化和极端化的体现,它抹杀了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变异性,只用简单化的方式进行处理,并且态度强硬、不容许讨论和匡正,带有很强的激进主义色彩。
(三)战争话语高频复现
文革文学批评方式的两极倾向,还体现在批评话语充满战争色彩。文革期间的“战争”主要是两条路线之间和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两种斗争在当时被看作是不可调和的、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学批评,使文学批评的话语烙上了鲜明的战争印痕。具体体现为:
名词性的:反革命集团、反党罪行、反社会主义分子、叛徒、死敌、阶级敌人、吹鼓手、总指挥、滔天罪行、黑线干将、投降派、毒箭、文艺阵地、重大胜利、战斗成果……
动词性的:高举……旗帜、向……开火、发起总攻击、炮打、彻底捣毁、捍卫成果、揭露真面目、剥下画皮……
文革文学批评话语的政治化、战争化和暴力倾向不是文革时期特有的现象,实际上从“十七年”文艺就已经开始了,根源来自战争文化心理。陈思和曾经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分析了战争因素对人们意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影响。陈思和认为“抗战爆发-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这四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特殊阶段,是战争因素深深锚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文学意识也相应地留下了种种战争遗迹,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现象。”在他看来,“文革”时期的文学艺术正是以抗日战争为起点,以新中国成熟为标志的战时文化发展到了登峰造极阶段的一种表现形态[5]。
文革时期战争话语达到巅峰状态,除了集体无意识的战争文化心理作祟之外,还与领袖权威话语的引导与示范作用有关。1942年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文化战线”和“文化军队”的概念,并且认为“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在批评标准上,坚持“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这些理论话语实际上已经开启了文艺批评使用战争话语的幕布。泓俊认为“从把文艺作为革命的一条‘战线’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毛泽东,笔者注)极为关注文艺界的思想动向与文艺家的政治立场,以及为什么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常常亲自介入具体的文艺问题的争论,并多次主动发起对文艺界‘错误倾向’的批判运动。显然,他极为看重的是文学艺术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统一全党思想、发动群众、引导舆论方向方面的功用。”[6]
周扬从30年代到文革前一直是以党的文艺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代言人的身份在场的,他深入领会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并不遗余力地加以贯彻执行和宣传,在对文艺理论批评进行定位时,采取的自然也是战争话语。他说:“文艺理论批评,是思想斗争最前线的哨兵。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往往首先在文艺方面表现出来,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的侵蚀,也往往通过文艺。资产阶级思想来影响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思想要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前哨战往往是文艺方面。”[7]
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用战争话语为文艺批评定性,而且直接介入文艺批评,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也大量使用战争话语。如:
1962年对小说《保卫延安》的批评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红旗》1967年第1 期)
1964年观看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后作的批示: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解放军报》1966年12月28日)
1965年对电影《清宫秘史》的讲话:《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红旗》1967年第5 期)
1966年8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认为: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这张非同凡响的大字报迅速在全国掀起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风潮。
1975年对评《水浒》的批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0 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这个批示为评《水浒》定下了基调,指引了方向,文艺界随之出现了大量的批判文章,但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围绕“投降”二字展开。
从上述材料来看,毛泽东的文学批评话语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大量使用战争话语,如“推翻政权”、“武装斗争”、“炮打”、“围剿革命派”、“白色恐怖”、“投降”等,使话语笼罩着浓厚的战争阴云;第二,非此即比的对立表述,如“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反贪官”和“不反皇帝”,并且加上“凡是”、“彻底”、“何其”等范围广、程度深的极性词语,使话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儿。这些都对当时的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批示都被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华收入“毛主席语录”中,成为当时文学批评的理论纲领和思想武器。文革时期文学批评话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高频引用“毛主席语录”中的话语,通过“毛主席语录”的神圣性、权威性和内在说服力来为文学批评寻求权威认证,以确保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及无可辩驳性。
三、结语
按照广义修辞学理论,话语层面的批评主体“我”被置换为“我们”、“个人署名”被替换为“集体署名”,微弱的个人言说被洪亮的集体言说所淹没,在修辞哲学层面显示的正是文革文学批评主体本真自我的丢失,隐匿自我,而以集体的姿态出场,表明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已经牢牢地控制了个体言说的权利和自由;话语层面“毒草”与“香花”相互对立,延伸到文本叙述层面,表现为“毒草”被妖魔化、“香花”被英雄化的普遍性叙述模式,这既与批评主体丧失言说的选择权相应和,也显示出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批评话语的有力统辖和强力渗透。至此,在广义修辞学视域中,文革文学批评从话语到文本再到批评主体(人)都体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注释:
①语料主要来源于杨鼎川《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附录的“年表(1966-1975)”以及洪子诚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77年)附录的“1949-1976年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编目”。
[1]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
[2]巴赫金.周边集[M].李辉凡,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50.
[3]谭学纯.文革文学修辞策略[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2).
[4]黄擎.毛语体时代文艺批评的话语风貌及其影响[J].阅江学刊,2009,(3).
[5]陈思和.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J].上海文学,1988,(6).
[6]高建平.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 200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9.
[7]周扬.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周扬文集: 第三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