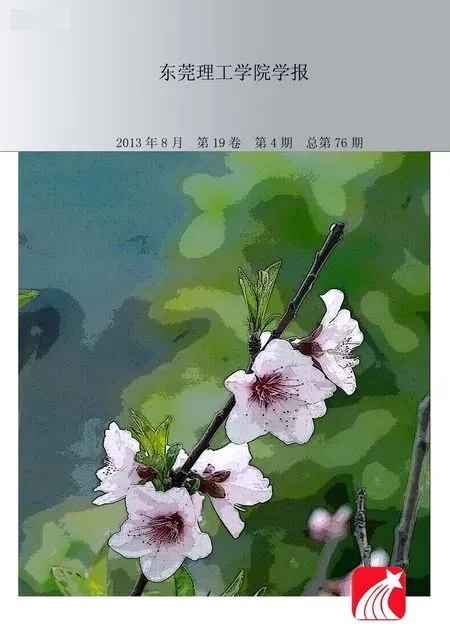空间批评视域下的《最蓝的眼睛》
孙笑非 左金梅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最蓝的眼睛》是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自出版以来便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在该作品中,莫里森以独有的女性视角审视社会,以细腻的笔触讲述了在白人强势文化下生存的黑人群体,展现出黑人在诸多空间中的边缘处境,奠定了她在美国文坛的地位,也为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铺平了道路。小说打破线性叙事规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展现人物的生存状况,一经一纬、一静一动,将文本穿插于多维时空体中,勾勒出包涵诸多社会现象和人文情感的时空版图。
空间批评兴起于20世纪末,它将文本的研究方向从线性静态的时间维度引向广阔多变的空间顺序,为从多领域多视角分析文本奠定了理论基础。主要奠基人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局限于几何与传统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不是一个抽象的逻辑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不是一个消极无为的地理环境,而是社会生产的结果和再生产者[1]172。该定义首次使空间脱离地理学的局限,得以在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层面发展。此外,列斐伏尔对叙事空间进行了文学分类,将其分为物理、心理和社会空间[2]39。本文借用列斐伏尔的空间批评理论,从地理、认知和种族三种维度解读《最蓝的眼睛》,通过探讨空间中隐含的地理图景、心理特征及社会机制来探究种族主义对黑人群体生理上的摧残与心理上的扭曲。
一、地理性物理空间展现的南北二极对立
物理空间指静态实体空间,包括具有自然属性的地理景观和带有人文特征的建筑实体,在多维时空体中处于最基层,被视为是独立于世界的时间结构和文本的顺序安排。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并非静止的容器或平台,也不是一个消极无为的地理环境[3]25。作为文本发展的基点,物理空间在文本建构中并非处于被动的地位,它是人物情感世界的外在展现,也是社会权利机构的地理再现,为故事的发生发展提供地域场所。
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勾勒出两种形态的地理图景:悲情化的北方仓库和诗意化的南方乡村意象。小说的在场空间是俄亥俄州的洛兰镇,这是美国北方的钢铁小镇,以新兴的工业发展和工作机遇吸引众多黑人从南方来到北方,包括佩科拉的父母。然而,北方并没有改变他们贫穷的生活状态,反而在精神上扭曲他们原有的价值观念,造成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迫害。他们只得住在一个废弃的、与周围房屋很不协调的库房。“它强行让路人不得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既让人恼怒又使人伤感。”正如这间破旧简陋的房子,布里德洛夫一家在整个小社区里也是可有可无、冷漠孤寂的,“他们挤在仓库的前厅里,在房地产商一时冲动而修建的劣质房子里苟且偷生。来无影,去无踪,从上到下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4]22“让人恼怒”、“使人伤感”、“劣质”构成北方黑人生存空间的符码,完成了弱势群体在异域空间可悲的定位。
相对于以工业为支撑的北方,美国南方依赖种植园经济发展而来,是黑人群体根之所系,记忆之所在,被称为黑人的第二故乡。在佩科拉父母的记忆中,南方是一个没有白人、可以生活得自由自在的地方。“在肯塔基州他们住在一个名副其实的镇子上,一条街上仅有十到十五家人家。自来水管直接接到厨房里。”[4]72南方乡村不仅提供了便利的生活,也满足了他们对爱情的向往,当又高又大的乔利从南方温暖的阳光中走来,玻琳萌动的心被俘获了,对他们来说,南方承载着他们温馨的回忆和甜美的爱情,是诗意化的温情港湾。所以到北方后,他们感到“一切都变了,“这儿的人们不好接触,我想念我的乡亲,我不习惯这么多白人。”[4]93与现实中北方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和黑即是丑的审美标准形成巨大反差和强烈对比的,是回忆里在南方幸福的生活体验和温馨的情感世界。
两幅空间图景——悲情化的北方仓库和诗意化的南方乡村共同罗织成小说的地理空间,从不同方面折射出一个外同质异的美国文化空间,在阐明地理景观与作家情感间的显性关系的同时隐现出黑白两种文化特征和情感结构的隐性联系。北方与南方,工业与农业,悲情与诗意的二元结构不仅彰显出南北的地理性差异,也折射出异质性的情感结构。
二、认知性心理空间展现的黑白二级对立
心理空间具有表意和认知性,承载着典型人物的个性特征和情感欲望,是外在地理环境和社会实践经历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反映。它将地理空间建构的文本框架深入化,为作者提供一个间接表述情感的渠道,也为读者打开一扇窥探人物内心的窗口。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种族迫害虽被法律明文禁止,但种族歧视的现象仍然普遍。白人在意识形态上操纵大众媒体,宣传并引导白人价值观,使黑人传统文化被贬低为具有奴隶特点的文化体系,并利用在社会空间中的优越地位使黑人将这种低劣性内化到自身身份中,与低劣的存在价值共存共生。
小说立体地呈现了女性个体心理从他者压制走向自我失衡继而自我分裂的过程,借助地理空间从南方乡村向北方城镇的位移,活动主体的心理从稳定的自我空间走向受控的无我空间,凸显出主体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分裂瓦解的趋势,表现了黑人主体在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逐步丧失自我的动态过程。在北方仓库空间苦苦挣扎的布里德洛夫一家[注]佩科拉一家姓氏Breedlove(布里德洛夫),原意培育爱,然而全家人相互之间没有爱只有仇恨。不仅物质上贫穷而且精神上备受煎熬,他们的心理空间在白人强势文化的镇压下被病毒化。佩科拉把苦难的根源归因于自己的黑和丑,她幻想能有一双蓝眼睛来改变一切。她的幻想一方面体现了她追求自身价值的美好夙愿,另一方面折射出她认同白人价值观,试图用白人眼睛看世界的可悲境界。对她来说,拥有蓝眼睛就能铲除她的黑人特质,因为白色代表美丽与善良,而黑色却是丑陋与邪恶。白人文化的种族主义色彩导致她产生自我厌恶的心理,使“她久久地坐在镜子面前,想发现丑陋的秘密。”[4]28可悲的是,她通过镜子找寻自我、透过眼睛得到社会认定的努力注定会失败,因为受白人文化的浸染,她已经牢牢地“把丑陋握在手里,把它像件衣服似的搭在身上,走到哪里都寸步不离。”[4]34她不得不寄希望于蓝眼睛的奇迹能发生在她身上。然而,对白人审美价值的全盘内化没有使她得到些许安慰,反而将她推向更为痛苦的深渊,在遭遇母亲厌恶、生父奸污、学校开除、邻人唾弃一连串的打击后,佩科拉精神崩溃,走向疯癫。
佩科拉的自我迷失与她母亲的人格分裂息息相关。初到北方的玻莉不仅面临如何在冷漠的新环境中与他人交往,而且面临着主体性身份定位如何进行重构的难题。当作为乡村女性的她受到北方城镇居民的凝视时,她得到的是挑剔的眼光和鄙夷的窃笑,她开始怀疑个人价值和个体身份。怀孕后的她沉迷在电影院中,被大众媒体宣扬的主流审美观同化,开始用银幕的标准来审视她的家人,认为她的丈夫和儿女丑陋不堪,而她的白人雇主则是更可爱、更可贵,由此她将白人雇主看作“能爱的一切”,把丈夫和亲生骨肉归为“能恨的一切”,[4]97企图通过疏远家人、做白人的忠实奴仆来找到自己的生存之路和文化身份。可是,不管她为白人家庭倾注多少爱,她在白人雇主眼里只是一件廉价的劳动工具,丝毫没有人的价值和尊严。
与佩科拉一家残缺的心理空间相对的是克劳迪娅一家完整的情感世界,他们住在漏风的屋子里,靠捡煤渣吃菜叶过活,但生活的压力没有压垮他们的信仰和期望,他们相互关爱、互相支撑,有意或无意地恪守黑人传统文化,保持黑人身份的个性。面对生活的艰难,女主人麦克蒂儿太太没有被动地躲藏到电影院里,而是时常唱些黑人歌曲来积极应对,使孩子们相信“痛苦不仅可以忍受,还甜蜜蜜的”[4]24。非洲人的音乐、舞蹈、歌声、语言和生活方式中存在着一种活力、激情和生气[5]52,对黑人本族文化的追溯和维系给孩子们生存的勇气,也在她们幼小的心灵里种下自尊自爱的种子,使她们相信自己的黑皮肤黑眼睛是美丽的,强化了对黑人自我形象的认定。
个体心理空间体现了白人强势文化对黑人民族文化的冲击,以及在文化侵略的阴影下黑人群体产生的两种心态,一是因盲目认同白人价值观、背弃族群传统而残缺病态的情感空间,二是抵制白人文化影响、坚守黑人民族文化而进一步获取幸福生活体验的心理空间。两种心理空间均折射出黑人主体试图追求个人价值和族群身份的不懈努力,探索了黑人价值观在美国文化价值观盘剥下发生的扭曲和异化,揭示了个体心理背后所蕴藏的社会种族机制。
三、政治性社会空间为黑人族群的未来发展提供良方
社会空间具有政治性和历史性,是通过策略和手段,依靠人类行动生产出来的产物,它不仅包含生产出来的事物,也包含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6]134。莫里森的处女作在地理空间中展现了南北两地的差异,心理空间诉说了黑人群体在白人文化盘剥下背离或坚守本族文化的两种态度,社会空间则关注黑人族群内部的优劣分化,力图阐释族群认同在社会空间中的重要意义。
佩科拉悲剧的酿成来源于内外两股邪恶力量:内部因素是白人强势文化对黑人的冲击;外部因素是黑人群体间冷漠的人际关系和恶意的社会交往。前者在心理空间中表现突出,后者体现在社会空间领域。长期受到压制和歧视的非人生活使黑人群体产生互相厌恶、落井下石的心理。白人将黑人狠狠地踩在脚下,黑人又将群体中最弱小的成员当作宣泄愤怒的对象,因为这些弱小成员的存在会唤起他们不愉快的过去,威胁到新近获得的安全感。当佩科拉被生父强奸并怀孕的事情被人知晓后,周边的黑人们议论她,言语中没有任何的怜悯和同情,“人们对这感到厌恶、可笑、惊讶、愤恨甚至兴奋”。“我们(指克劳迪娅和姐姐)想听人说,‘可怜的女孩’或‘可怜的孩子’之类的话,但这些话没有听到,只见摇头。我们想找双充满关怀的眼睛,却只见邪恶。”[4]120贴有种族代码的社会空间通过影响黑人群体的社会构建和自我认知,达到了使黑人自我憎恨和族群解体的双重功效,进一步强化了白人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内外交困的佩科拉“终日将自己柔弱的生命消磨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头随着只有她能听见的遥远的鼓声而晃动。”[4]133限制妇女在空间中的移动是维持她们隶属地位的关键,佩科拉走来走去的状态强化了女性在空间表征中的移动性,是对男性霸权压迫的反抗;而她耳中遥远的鼓声是黑人传统文化对她的召唤和抚慰,是对白人文化侵蚀的反击。佩科拉疯了,但亿万个像她一样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黑人个体必然会警醒,共同抵制和反抗充斥于社会文化空间中的种族歧视制度。
莫里森在批判种族歧视的同时,通过佩科拉在黑人群体中的可悲境地试图探讨重建黑人社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因为黑人社区能提供非常强的生命养分,能分担集体的忧愁,并给个体相互支撑的勇气。因此,族群内部的建构模式和运作机制是黑人群体要处理的首要问题,只有保证内部的团结一致才能维护好本族的文化根基和社会地位。
四、结语
作为地理生存空间、个体心理空间和社会政治空间的集合,莫里森对美国社会的思考与黑人族群未来发展的关切构成一个基调统一的空间体,它不仅是一种与时间并置的再现体,还是三种对立矛盾的容纳器,更是影响作家建构文本空间的表述机制。三维空间体一方面实现了空间哲学与文本内容的有效结合,把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走向贯穿起来,使小说的空间形式成为展现地域景观、人物心理和社会文化的手段,展现了南北两地、黑白族群以及优劣心理的二元对立结构;另一方面在地域空间位移、人物心理流动和社会文化渗透的动态变化中勾勒出一个清晰明了、多维交错的多维时空版图,全面动态地体现出作家从人物同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多种关系对黑人生存状态和未来出路的深刻思考,呈现出莫里森试图建构美国和谐平等理想社会的种种努力。
参 考 文 献
[1]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Uk: Blackwell,1991.
[3] 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秦林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4] Morrison T. The Bluest Eye[M].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70.
[5] White,Parham.The Psychology of Blacks:an African-American Perspective[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1984.
[6] 陆扬.社会空间的生产:析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J].甘肃社会科学,2008 (5):133-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