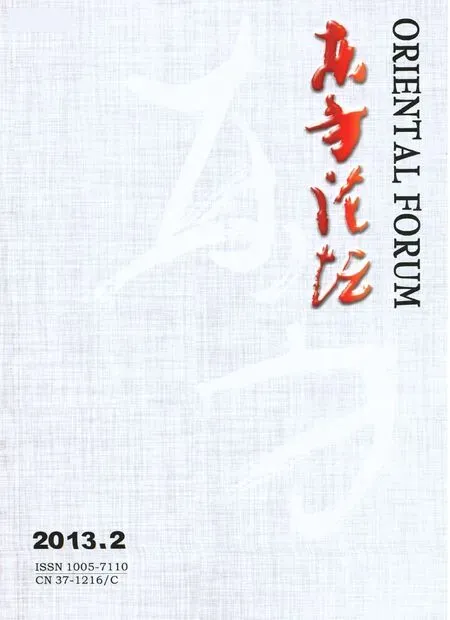话剧导演“第一人” ——张彭春早期话剧导演活动研究
陈元峰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张彭春(1892—1957)生于天津,南开学校创始人张伯苓胞弟。1908年夏,毕业于南开中学,18岁赴美留学,入美国克拉克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文学、欧美现代戏剧,获文学及教育学双硕士学位。1916年学成回国后,除在南开学校任教外,还担任南开新剧团①南开新剧团是二十世纪初北方最活跃、最持久的一个新剧团体。1909年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从欧美考察回国,即动手写了第一个剧本《用非所学》,在南开学校演出。他的理念是,演剧活动锻炼学生的口才,增长学生的交往能力,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在这一精神主导下,演剧活动成了南开学校的一个传统,1914年南开新剧团在多年演剧实践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的副团长和导演,积极投身于西方现代话剧的引介工作。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戏剧运动的先驱,张彭春系统学习了西方现代戏剧的编导演理论,带领南开新剧团从一开始即走向西方现实主义戏剧之路,影响十分广泛。他还培养了一大批戏剧人才,有被称为“中国话剧第一人”的曹禺,有著名电影导演鲁韧,有在剧坛和影坛赫赫有名的黄宗江等。张彭春,对中国早期话剧的现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堪称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
西方导演制的确立,为戏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推动力。导演按照导演艺术的特性来组织、领导剧目创作的全过程,使得创作过程成为可调控的有序的生产过程,避免了演剧的随意性,提高了创作效率。中国话剧诞生之初,文学史称之为“文明戏”,文明戏实行的是传统的明星制,因此没有导演,不需排练,主要靠演员的即兴表演招徕观众,致使舞台上面红耳赤者有之,手足无措者有之,期期艾艾者有之,挥汗如雨者有之,舞台效果难以保证。张彭春第一个把西方导演制引入中国,促使南开新剧团演剧高潮的到来,并为中国戏剧培养了大批的编导演人才。
1916年,张彭春自美国留学归国之后便开始了导演生涯。他的到来,使南开新剧团彻底抛弃了编剧与排演同步进行的所谓“新剧”模式,实行欧美现代戏剧流行的导演制。他正式执导的第一部有影响的戏剧《新村正》,被誉为“中国新剧最合西洋新剧原理的杰作”。[1]这比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导演”洪深首次为上海戏剧协社执导《少奶奶的扇子》早了六年。由于张彭春带来了崭新的现代西方戏剧理念和导演方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南开新剧活动最兴旺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张彭春先后把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原名《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苏俄戏剧《可怜的裴迦》、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和《娜拉》、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悭吝人》、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争强》(原名《斗争》)、俄国作家契诃夫的《求婚》等世界名剧,搬上南开戏剧舞台。另外,他还导演了丁西林的《压迫》、田汉的《获虎之夜》、陈大悲的《爱国贼》等国内名剧。
张彭春的导演使南开新剧团的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本来门庭冷落的现代话剧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压迫》、《获虎之夜》、《可怜的裴迦》“于该年(1927年)暑假期间作第一次公演,秋季开学后作第二次公演,两次观众,均形拥挤,并表示非常满意”;[2]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演出时名为《刚愎的医生》)和《娜拉》上演时,“连演两天,每次皆为满座,实地演出时,全场秩序甚佳,演员表演至绝妙处,博得全场掌声不少”;[3]《争强》的演出,著名导演黄佐临评论道,“这戏全篇大致,南开新剧团都弄得十分圆满。其中的意义,亦都能清清楚楚的传达到观众眼前,不稍暗昧”,演员“表演来,精神充足,畅而有力”;[4]《财狂》(原名为《悭吝人》)的演出,天津《益世报》出了专号,《大公报》出了特刊,誉之为“华北文艺界的盛事”。由于南开新剧团演出的成功,以至1934年南开中学新礼堂落成时,《大公报》称它为“中国话剧第一舞台”。
张彭春作为导演的成功,不是偶然的。纵观关于张彭春的回忆录和张彭春自己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张彭春已经掌握了当时欧美的现代导演方法和技巧,并能做到熟练运用。
第一,他确立了导演在话剧舞台艺术中的核心地位。1916年回国伊始,张彭春便运用在美国学到的西方现代导演方法执导了独幕话剧《醒》,该剧在试演之后,被校董严范荪、校长张伯苓评判为“情旨较高,理想稍深,虽写实述景,历历目前,可以改弊维新,发人深省,无如事涉遐高,则稍失之枯寂,似于今日社会心理不合”,[5]因而被取消了参加校庆公演的资格。从评价的字里行间,我们分明可以感觉到其现代话剧的特质:它完全采用“写实”的手法,把现实人生搬上舞台;它运用了西方话剧式的布景,且注意了布景对塑造人物、表现主题的作用;它之所以“稍失之枯寂”,是因为其纯用对话展现人物心理、刻画人物性格,不同于南开此前的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情节剧。
张彭春第一次的失败是大环境决定的。在当时的国内,别说纯粹意义上的西方戏剧理念,即使是导演也是不需要的。当时盛极一时的文明戏即是如此,它们实行的仍然是传统戏的明星制,主要靠个别演员的即兴表演招徕观众,并不想在舞台上创造如真似幻的现实效果,因此,导演对他们来说是“多余的”。南开新剧团在张彭春之前的早期演剧,虽然从整体上优于文明戏,但毕竟不能摆脱“过渡戏”的性质,这与当时人的思想观念和认识水平不无关系。即使是后来的南国社,也不知有导演这回事。“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导演,什么叫角色的创造,什么叫演技的基本训练。”[6](P127)南国社公演的剧目完全靠演员的现身说法,经常导致情绪失控与动作变形,是一种“野生的艺术”,难以形成整体的舞台效果。西方导演自打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和舞台幻觉、整体性、写实主义等美学观念联系在一起,他是明星制的天敌。这一些,对于深受传统影响的中国人来说,又怎么能够马上接受呢?其不合“今日社会心理”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时代的滚滚车轮毕竟不能阻挡,西风东渐,新思想新观念与日俱增。1918年的《新村正》演出时,张彭春的话剧理念和导演风格终于征服了观众。《国民公报》称《新村正》为“中国新剧中最合西洋新剧原理的杰作”,[1]甚至明确指出它与易卜生、萧伯纳的社会问题剧属于同一范畴。[7]这些评价固然得益于该剧内容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但更与它的导演、表演都力求合于“西洋新剧原理”分不开。从此,张彭春在南开新剧团的导演地位得以确立。
张彭春曾明确表示反对明星制,提倡导演与演员的团结协作。他说:“不止剧团的演员、职员,甚至工友都要做到好处。我们剧团里面没有‘明星’,各个演员都是主角。”[8]他强调话剧演员必须在导演的指导下进行刻苦的训练。“话剧在一般人的眼中以为是只要能说话就能上演。所以你演我也演。岂不知这末以来,实在糟蹋话剧的价值了。他们马虎地出演,对动作的姿势、语调的高低、布景的合适,及其它基本的演剧术都未能有相当的训练,所以话剧之失败并非偶然的。”[9]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张彭春坚持的是导演中心制。另外,张彭春十分重视话剧剧本的基础作用。在张彭春之前,南开新剧团基本是以边排演边编剧本为主;张彭春到来之后,剧团所演的每一个剧都做到了有本可依。他对演员们要求严格,演员的表演必须在导演的指导下按剧本进行,坚决杜绝演员的随意发挥。
张彭春作为中国第一位话剧导演的地位,得到了专家的确认。有着“南黄北焦”美誉的著名话剧导演黄佐临指出,张彭春是“第一位向国外学习戏剧,精通西洋戏剧专业知识,并且富有才华的导演”。[10]
第二,欧美多种导演风格的自觉实践。尽管张彭春成功地导演了多部中外名剧,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他记述自己导演理论和方法的文字却少之又少,我们仅能从当年南开新剧团演员的回忆和观剧者的感受中去寻找蛛丝马迹。
首先,他执法严格,近乎专制。导演时,他对每个演员的台词、音调、眼神、面部表情,甚至一些细微的动作,都不轻易放过,给以严格的指导。南开学生田鹏回忆当年排演《财狂》时说:
九先生事先有充分准备。对词,哪个字重要,哪个字念的轻,哪个词后面要停顿;走场子,走前后左右、快慢急徐,导演都记在自己的剧本上。……记得有一段戏,杨先生前腿弓后退绷,和楼上的少女调情。九先生说:“不许动!再说五遍。自己数着数!”……“几遍了?”杨先生答:“五遍了!”“不行!没戏!再说五遍!”杨先生只好再来五遍。[11](P296)
南开学生鹿笃桐当年也参加了该剧的排演,他回忆说:
剧中曹禺和严仁颖(海怪)的戏最多,他们的追、跑、打等场面中每一台步,每一方位,都要反复修改。尤其是对主角更是加倍严格。……张先生还亲自为我们几个较主要的角色化了装。连眉毛、眼尾纹和抬头纹都认真地勾画。对服装颜色、衣上的补丁也都仔细推敲设计。……在全剧中我的戏并不多。记得有一句台词“真的吗?”他不厌其烦地教了我多少次,直到说成“真……的……吗?!”语气和节拍都符合他的要求时,才满意地对我微笑地点点头。[12](P238)
南开学生、被誉为“电影皇帝”的金焰回忆道:
彭春老师排戏严格极了,我看过他排《压迫》、《可怜的裴迦》、《获虎之夜》,一进排演场,他什么都预先规定好了。无论是台词或是台步,甚至于台词的轻重音。这和我后来到上海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拍戏时可以即兴表演,演出时甚至也还允许自由发挥,完全是两回事。当时我想,看来张彭春是另有所师的。[13](P72)
导演的严格和专制是欧美导演制建立之初的普遍存在。西欧戏剧史之所以把主持萨克斯·梅宁根剧团的乔治公爵视为导演制的创立者,主要是因为他善于“把演员当作可随意使用的戏剧材料,加以熟练地运用”,而不是依靠演员个人的自由发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早年曾仔细观察了克隆涅克的导演过程,对他在排戏时的那种冷漠和严厉的作风印象深刻。他说:“我竟喜欢起克隆涅克的沉郁和无情来。我模仿他,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一个专制的导演了,而后来许多俄国导演又像我模仿克隆涅克那样来模仿我。结果就造成了整整一代专制的导演。”[14](P157)奥地利著名导演莱因哈特也是专制导演的代表。他把手下的演员当作导演的材料,“控制他们的每个动作和姿势,以及语调中的最细微变化。向他们集体地或个别地加上他个性的印记,直到他们被塑造成他自己概念中的角色”。[15]英国著名导演戈登·克雷说:“唯有导演才能赋予舞台艺术以生命。”导演才是戏剧演出的真正炼金术士,将演员视作是任其操纵的傀儡,甚或仅仅是一点点戏剧材料而已。阿皮亚也说过,导演是剧场的唯一创造者,要求演员在舞台上仅仅是导演的“超傀儡”,而导演则是这种超傀儡的操纵人。
应该说,导演的专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欧洲新的演剧方式出现的时候,由于没有熟练的演员,只好把一切都交给导演去支配,而导演就借助于装置、布景、道具,与新颖的导演手法,独自去创造。在中国话剧的发轫期,国内话剧从业者的情形于此相类,不要说学生剧团,即便是专业演剧人员的素质也值得怀疑。因此,张彭春顺应时代的要求,自觉地实践西方专制的导演风格,是明智的,对话剧的发展也是必须的。
当然,张彭春的“专制”是有限度的,很多时候他又表现出民主的一面。著名的电影导演鲁韧曾经有下面两段回忆:
张彭春排戏是很讲艺术民主的,……先要分析剧本、剧本的主题、角色的体现,让大家来讨论。他们有时争论得很激烈,经过争论,导演吸收大家的意见,或是大家接受了导演的意见。那是很浓的艺术追求的精神,是很难能可贵的。[16]
排练时,为推敲人物的台词和动作以及细节的处理,经常停下来反复争论。尽管九先生习惯地拍着大脑门,“噢噢”连声地思索之后,提出一个新方案,再排时常又发生了新的问题。像伉鼐如、张平群、万家宝、杨仲刚这些主要演员仍会要求重新研究,于是大家又面红耳赤地继续争论不休。我常躲在大礼堂后排的角落里看排戏,曾有一次看到伉鼐如、张平群和九先生激动地用手指着对方,互不服气地说:“谁错了,谁请大家到全聚德吃烤鸭!”大家立即起哄说:“对,那就今天晚上去!”当我默默地返回四斋时,回头望见排演场上仍在激动地争论不休。[17](P309)
张彭春的这种民主的导演作风,又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理念暗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演员的主动性,唤起他天然的倾向性和天赋,为了使他少受导演的强制、偏见和枯燥乏味的理性的影响而走向表现派的道路,必须反对在排练的一开始就把关于排练、剧中人物形象、舞台调度等等的现成决定都告诉演员,反对把剧本的案头分析搞得过于长久,反对将演员对角色的创造引导到纯理性的领域。他认为,对词不应在排练的一开始就进行,而应在演员产生了对角色的自我感觉之后才进行。民主是集思广益,是取长补短,是充分发挥创作集体智慧的必由之路。张彭春的专制是导演中心制的必然要求,张彭春的民主是尊重集体智慧的明智之举。
其次,“教演员在台上生活,而不是在台上做戏”。西方现代戏剧主要有两大对立的流派——体验派和表现派。体验派的代表导演是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它要求表演者不是描写角色形象,而是成为角色,活在角色之中。它所需要的不是模仿,而是与剧中人的体验吻合的体验的真实性。该派认为,演员能感动观众到什么程度,也正决定于他自己曾感动到什么程度。[18](P242)
张彭春显然认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演剧风格。①马明的《张彭春与中国现代话剧》记载,据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教授回忆: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三一年他(张彭春)两次访苏归来,以‘在苏俄看见的听到的跟想到的’为题,向南开师生演讲的时候,都曾提到观看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以及他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观感。正如重庆南开中学学生王铨的回忆:九先生“教演员在台上生活,而不是在台上作戏”。[19](P314)这一点,通过观剧者的反映也可以得到证实。
立厂在《记南开之〈争强〉》中记述:
第一场是在吴矿长客厅。万家宝饰安敦一,极像老人的声态,在全剧最为出色。其次张平群饰罗大为,那种激烈的样子,也很相宜。伉鼐如饰魏瑞德,活画出一个自私自利的市侩。吕仰平饰施康白,那种颟顸的样子,也都很受观众欢迎。……罗大为的妻是张英元女士所饰,装重病的样子,也很动人。[20]
著名作家萧乾在看了南开剧团的《财狂》演出后是这样评论的:
这里,我们不能遏止对万家宝先生表演才能的称许。许多人把演戏本事置诸口才、动作、神情上,但万君所显示的却不是任何局部的努力。他运用的是想象。他简直把整个自我投入了韩伯康的灵魂中。灯光一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悭吝附了体的人。他那缩肩抱肘的窘状,那抚腮抓手的彷徨,一声低浊的虚喘,一个尖锐的哼,一阵咯咯的骷髅的笑,这一切都来得那么和谐,谁还能剖析地观察局部呵。他的声音不再为pitch 所辖制。当他睁大眼睛说“拉咱们的马车”时,落在我们心中的却只是一种骄矜,一种鄙陋的情绪。在他初见木兰小姐,搜索枯肠地想说句情话,而为女人冷落时,他那种传达狼狈心情的繁复表演,在喜剧角色中,远了使我们想到贾波林(卓别林——著者),近了应是花果山上的郝振基,那么慷慨地把每条神经纤维都交托给所饰的角色。失败以后那段著名的“有贼呀”的独白,已为万君血肉活灵的表演,将那种悲喜交集的情绪都传染给我们整个感官了。[21]
从以上回忆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张彭春在导演时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样,强调演员体验生活。所谓“在舞台上,在角色的生活环境中,和角色完全一样正确地、合乎逻辑地、有顺序地、像活生生的人那样地去思想、希望、企求和动作”。[18](P243)演员演老人就要有老人的“声态”,演病人就要有病人的“样子”,把自我完全投入到角色的灵魂中,像是被角色“附了体”。这与中国的某些在舞台上插科打诨、舞蹈演说的“自我表现派”相比,其对西方话剧精髓——生活化的理解和把握要精准得多。
当然,再现生活的真实并不是追求自然主义,它要求既有世俗生活的逼真性,又有社会的概括性,做到社会真实、心理真实、剧场真实的完美结合。“活在角色之中”,并不是机械地模仿,而是与剧中人的体验吻合的体验的真实性。
为此,张彭春要求演员“带情绪上场”,以体现生活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完美结合。在《财狂》中,费升偷了韩伯康的装钱和股票的匣子,抱着匣子跑上场,韩伯康追上。张彭春规定,都必须带情绪跑上。“不能从上场门出来再跑,得在上场门里头先跑够。费升原地跑,数到十,韩伯康原地跑,数到三十,而且在后台两人不许见面,否则影响情绪。费升一定要又得意又害怕,韩伯康一定要急,丢了钱急得发疯:‘财,狂!’这两个跑,……但又有所不同!”[11](P296)张彭春已明确认识到,舞台真实来源于生活,但又区别于生活,它是对生活的提炼、概括和升华。
第三,现代舞台美术的自觉实践。舞台美术是除了表演人以外的各种造型因素的统称,包括化妆、服装、道具、灯光、音响、布景等。与中国戏曲不同,舞台美术是西方现代戏剧的重要组成要素。人们可以通过舞台美术表现戏剧发生的时间(季节)、地点(室内室外)、国度、时代、民族特点等,创造戏剧浓厚的生活氛围,突出戏剧的人物性格和主题;同时舞台美术还有利于导演的调度和演员的表演。
中国话剧的舞台美术,也像中国的话剧一样,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其中不少人默默无闻地为我国的舞美事业做出了贡献,张彭春就是其中的一位。1981年初,在中国舞台美术学会成立大会上,曹禺先生说:“没有舞台美术就没有戏剧。”正说明了舞台美术与戏剧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孪生的关系,也说明了像张彭春这样搞话剧重视舞台美术的远见卓识。
与中国早期话剧舞台美术的简单粗陋相比,①中国早期话剧,像《黑奴吁天录》,虽然采用了分幕制的形式,使用了写实的布景、灯光,但十分简陋,黑奴也未化妆,一切处理得十分简单。从业者显然并未真正意识到它们在戏剧整体中所具有的价值。张彭春之前的南开新剧团虽有舞美,但还不能自觉地做到服务于人物和主题,有时甚至直接上演没有布景的“天然剧”。张彭春的舞美要进步得多,现代得多。
首先是写实主义布景的自觉运用。舞台布景是舞台美术的核心与主导,从某种意义上讲,舞台布景在整个舞台美术中处于中心地位。张彭春归国之初导演剧目,就十分重视写实布景的运用。1916年演出的《醒》,周恩来就感叹地评述为“佳音佳景,两极其妙矣”。[22]1918年《新村正》的写实布景更是引起了观者的惊异。且看李德温关于《新村正》布景的文字:
继而振铃开幕,则客厅一所,几椅咸备。中设一榻,榻后横几,几一端置瓶,一端置石镜,而玉如意位其中。榻有琴几,别左右。南面上有额,曰“务本堂”,旁有联一副。……第二幕之布景,则为一荒村。树林阴翳,黄毛紫藟丛生于其间。败屋数间,皆毁瓦颓垣,楹柱皆不完。而竹篱乔木,俨然一野景也。天色蔚蓝,以竹为篷,糊以纸,涂以青,而以蓝色之电灯反映之,如真天然,而鲜丽之色盖有加焉。有古井一,井围为淡黄色,若经久剥蚀之。……村皆贫而无衣食者,老幼皆褴褛污秽,一若乞丐。……第三幕,即吴某家。室中不悬字画,右设几一、椅二,中置方桌一,上罩以采布。桌旁椅又各一,后有窗可以窥院内之花园,山石花木俨然在目,而园中风景之幽雅亦略见一斑焉。
全剧景色如出天然,且注重了贫富悬殊之对比,大大增强了演剧的现实效果和主题的深刻表达。恰如上文作者所言:“村民流离失所,饥苦枯肠,而求救于魏某之前,木叶萧萧,土屋黄黯,剧之人固声泪俱下,观者亦莫不饮泣。”[23]
在《财狂》演出时,张彭春和林徽因女士共同设计了布景:
布景是立体的、全台的。台右一座精致的楼阁,白石栏杆绕着斑痕的石墙,台左一座小亭,倾斜的亭阶伸到台旁。院中石桌石凳雅洁疏静,楼中花瓶装点秀美。这布景再衬上一个曲折的游廊,蔚蓝的天空,深远的树,这是一副好画面。[24]
这幅布景不但符号了写实的需要,而且为表演提供了切实的方便。萧乾观剧时即发现了这一点:“(那石阶)它划分了情绪的阶层。当木兰在阁上对韩可扬(韩伯康)表示不能嫁他时,失望的恋人垂丧着头走下台阶,晃在斑痕累累的大理石上的黑影和下降的脚步皆帮同象征了内在的怅惘心情。”[21]
为了布景的真实和服务于剧情,张彭春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财狂》的布景初设计时,院内门窗崭新,走廊朱红。演出的前一天,张彭春发觉,这样漂亮阔气的建筑,与一个吝啬鬼的性格很不相衬,于是他叫人们把门窗和走廊涂上了薄薄的一层乌黑。
舞台写实布景的运用而又能恰切地服务于剧情、服务于性格的刻画,张彭春可以说领时代之先。
张彭春在灯光的运用上也积极师法欧美。在《财狂》演出时,他弃用幕布而改用灯光来代替。“开幕时,他一敲锣(他有自己独特的敲法),灯光渐渐明亮,闭幕时,他再敲锣,灯渐渐暗淡。”[24]而在演出过程中,灯光的色调,明暗快慢,以及映影的错综、疏密,都经过细心的体会,周密的研究。
总之,张彭春作为深受欧美现代导演理论影响的中国早期导演人,其话剧导演实践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他不仅影响了京津一带的一代观剧者,而且为话剧事业培养了大量的剧作家、演员和导演,为中国话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理应还原他“中国现代话剧第一导演”的美誉。
[1] 高一涵.涵庐剧评 [N].国民公报,1919-01-28.
[2] 陆善忱.南开新剧团略史 [J].南开校友,1936,1 (3).
[3] 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一览 [Z].1929-10-17.
[4] 黄佐临.南开公演《争强》与原著之比较 [N].大公报 (5),1929-10-25,26,27.
[5] 严范荪,张伯苓.校闻·《醒》剧停演 [J].校风,1916,(42).
[6] 张庚.张庚文录:卷二 [A].中国话剧运动史 [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7] 宋春舫.中国新剧之商榷 [A].宋春舫论剧 [M].北京:中华书局,1923.
[8] 张彭春.关于演剧应该注意的几点——原则和精神 [J].南开校友,1936,1 (3) .
[9] 张彭春.苏俄戏剧的趋势 [J].人生与文学,1935,1 (3).
[10] 黄佐临.序二 [A].黄殿祺编.话剧在北方的奠基人之一:张彭春 [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
[11] 田鹏.跟随九先生、老伉先生排戏 [A].黄殿祺编.话剧在北方奠基人之一:张彭春 [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
[12] 鹿笃桐.深切怀念张彭春老师 [A].黄殿祺编.话剧在北方的奠基人之一:张彭春 [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
[13] 马明.张彭春与中国现代话剧 [A].夏家善,崔国良,李丽中编.南开话剧运动史料 (1909-1922) [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14]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卷一 [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8.
[15] 海兰·契诺伊.德国导演莱因哈特及其表现主义和印象风格 [J].杜定言译.戏剧艺术,1981,(2).
[16] 黄殿祺.曹禺的恩师张彭春 [J].中国戏剧,1991,(9).
[17] 鲁韧.回忆母校多彩的生活 [A].黄殿祺编.话剧在北方的奠基人之一:张彭春 [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
[18] 参见陈世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他的体系 [A].导演者:从梅宁根到巴尔巴 [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19] 王铨.抗战时期的南开话剧——纪念南开话剧诞生八十周年 [A].黄殿祺编.话剧在北方的奠基人之一:张彭春 [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
[20] 立厂.记南开之《争强》 [N].北洋画报 (3),1929-10-26.
[21] 萧乾.《财狂》之演出 [J].南开校友,1936,1 (3).
[22] 周恩来.特别纪事·民国五年冬季第九次毕业式记 [J].校风,1917,(特别增刊).
[23] 李德温.记国庆日本校新剧之布景 [J].校风,1918,(104).
[24] 巩思文.《财狂》改编本的新贡献 [J].南开校友,1936,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