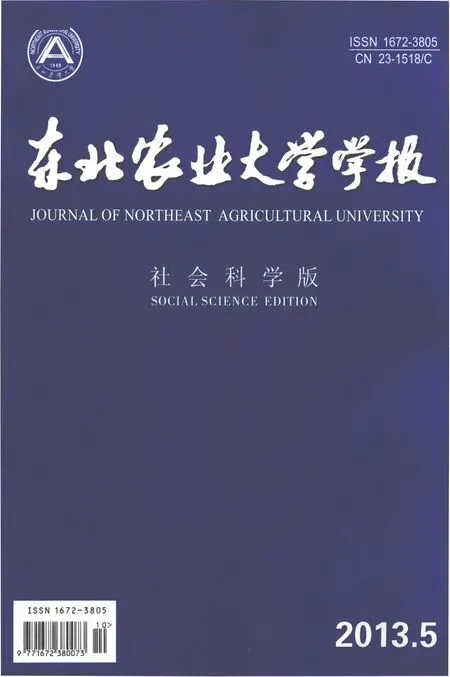论海登·怀特的理论贡献
王 霞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美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由于其凌厉激烈的反叛意识、解构意识与探究意识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在历史学界、哲学界以及文艺批评界引起的广泛争议至今不息。王岳川《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黄芸《真实·虚构·意义——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评析》等文涉及怀特理论创新性问题,但目前国内学界对于怀特的理论贡献还未给予足够关注。本文将从怀特对于历史诗学理论的体系化建构、去魅历史的反思批判精神及其对跨学科研究的实践三个方面,论述其理论贡献。
一、建构历史诗学理论的完整体系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构想并非空穴来风,如艾利克森所说:“任何新生代的价值观,都不是以发展成熟的形态从他们脑中跳出来的;它们早就在那儿,即便老一辈还不能清楚表达出来,它们已经存在了……年轻一代把上一代仍隐藏的想法宣扬出来,小孩子把父母忍住没说的话公然讲出来。”[1]考查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可以发现,怀特之前包括柯林武德、克罗齐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都曾提出历史的主观建构性,“诗学”“历史诗学”说法也非始自怀特。
以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为例,怀特对历史客观性的反思与批判、对历史主观性的强调等,与柯林武德一致。柯林武德认为,历史与自然科学虽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客观的物质、现象,历史研究不可能做到如此客观,因为历史同时蕴含客观发生过的事件和历史事件背后的主观思想。由此,柯林武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在他看来,传统“剪刀加浆糊”的粘贴史学,只是对历史事件进行死板的排列与组合及对史料的考订与堆积。历史并非单纯历史事件的过程罗列,不是对过去的机械照搬和模仿,而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2]。这种重演是在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框架中完成的带有主观性的建构活动,蕴含历史学家的想象力以及价值判断。柯林武德对历史与自然科学的区分,对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对历史学家主观性特别是想象力的强调,与怀特是相通的。怀特曾在《历史中的解释》《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等文,多次强调历史与科学的根本不同,积极倡导历史的文学性、想象力。
怀特常引述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弗洛伊德、皮亚杰等人的观点用以证明、支持自己的主张,并明确表达过巴特对其叙事理论研究具有引领作用。《元史学》的前言中,怀特曾坦言其历史诗学理论中关于情节编织、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的论述,分别受益于弗莱、史蒂芬·C.佩伯和卡尔·曼海姆。怀特根据弗莱《批评的剖析》中的线索提出四种情节化模式;根据佩伯《世界的构想》中分析构想的世界类型,提出历史解释的推理性论证所采用形式的四种范式;根据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提出四种基本意识形态立场。可以说,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吸收、继承了包括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艺学等诸多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
问题在于,既然怀特的理论观点具有很大的继承性,那么,他为何还能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和激烈批评?他的理论贡献又在何处?
笔者认为,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之所以备受关注与争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理论有力地应和了当时的学术语境。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到历史学领域,形成历史的“后现代”或“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史学解构了传统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语言的稳定性等概念,发掘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歧义性和相对性。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是一个由语言构成的文本。历史的文本性与语言性使历史编纂“文学化”,甚至“戏剧化”。历史与文学、客观与虚构之间原本森严的界限变得模糊,历史实在与真理成为一个日益远去的高贵梦想。希梅尔法布指出,后现代主义者否定的不是某个主题的这种或者那种真理,而是真理的概念本身[3]。
后现代史学的历史观、语言观、文本观,引起学界诸多批评。在此种学术语境下,怀特提出历史诗学理论,倡导历史的文学性、主观性、语言性,在历史学领域中应和后现代主义的诸多观念,解构历史学的科学神话与客观梦想,成为后现代史学对传统史学“入侵”的代表。尽管柯林武德、克罗齐等人也认识到历史与文学而非科学更近,认识到历史的主观建构性,但是在当时强调客观、科学史学的主流话语下,他们的观点就像一颗颗小石子,不足以击起学界的巨浪。
除应和时代语境、趁势而行,怀特引起学界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建构了历史诗学理论的体系化“大厦”。历史编纂中存在的诗性因素、历史的主观性、历史与文学的贯通性、历史学家语言的比喻修辞色彩,这些理论观点可见于柯林武德、克罗齐、利科、巴特等人的著述中。怀特受他们的影响与启发,在跨学科学术背景下,借鉴、继承其学术成果,为其历史诗学理论的提出奠定坚实基础。然而,怀特的理论不仅仅是前人学术成果的简单拼加,而是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进行全新构建。
历史编纂与历史解释的主观性、历史与文学的相似性等学术观点较为零散、琐碎,不足以构成一个全面的整体理论。怀特将前人的学术成果构建成一个体系化“大厦”,提出一整套关于历史文本、历史解释、历史叙事的具体分析策略与方法。正如王岳川指出的,怀特的理论贡献不在于他所强调的历史的诗性,不在于他肯定了历史编纂中虚构、想象、修辞等成分的作用,而在于他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提出历史话语的三种解释策略,即情节编织、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论证,也就是说,“怀特是以整个体系的完整性显示出自己的实力的”[4]。具体而言,情节编织包括四种类型的情节模式,即浪漫剧、喜剧、悲剧和讽刺剧,这四种情节模式为历史学家对事件进行解释提供了不同效果;形式论证包括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和语境论四种方式;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立场主要分为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历史话语的这三种解释策略之间存在某种亲和关系,三者综合代表历史学家的编纂风格。怀特认为,情节编织、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论证分别对应历史学家对故事进行解释的三种方式,即审美的、认识论的和道德的。此外,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体系性和完整性还体现在他对历史叙事语言的分析,对事件、年代记、编年史及严格意义的历史的区分以及对转义理论的论述。
二、“去魅”历史的反思批判精神
历史学家总是在追求客观性,并努力让其历史编纂看起来有理有据。为此,他们尽量掩盖其文本中的修辞性语言、情节编排、因果关系的连接等,使文本显得完全是客观事件的聚合,从而树立历史学作为一门客观、真实学科的权威,尽管这是以遮蔽历史中所蕴涵的诗性因素,否定不符合“标准答案”“权威答案”的解释、声音和视角为代价的。历史学家以全知全能的视角讲述过去时,读者会误认为那就是历史——历史通过史学家的口在说话——这就制造了一种“权威”,即“超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立场”“冷静客观、毫无主观偏见”的假象。这种客观性立场无疑有其弊端。它比明确的意识形态宣传更可怕,因为所谓的客观、真实、中立的立场和权威的面纱,更易掩藏其真正所指,误导读者。
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正是为了揭开、去除这种所谓的客观、真实、单一的历史神话,反思并解构这种虚假的客观性、权威性,通过发掘历史编纂中的诗性建构因素,倡导和张扬历史的文本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多元性和异质性。
从怀特对历史事实与历史事件的区分也可以看出,历史事实既包含客观性,也包含主观性。人们在确定哪些是历史事实、哪些不是历史事实时,已含有价值判断、阐释和建构。因而,客观性仅仅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如果只是将历史事实看作全然客观的而进行历史编纂和研究,无疑会忽略史学家进行历史编纂、历史再现、历史批评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史学家是如何实现客观性的,或者说,“文本是通过什么办法把表现性的东西掩饰为指涉性的东西的”[5]。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既然历史事实中含有种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因素和诸多表现性内容,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客观性的彻底消失?历史编纂、历史书写不可能客观?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尽管历史事实含有种种主观建构因素,“‘事实’是不稳定的,取决于修订和进一步解释,甚至由足够的证据而作为假象被排除”[6]。然而,历史学家在编纂过程中的种种主观性是建立在相对客观的历史事件基础上,并非凭空臆造,这就决定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阐释不可能是随意的。其次,尽管史学家不可能达到绝对客观,但可达到相对客观。历史学家自身所受的学科训练、必须遵循的学科规范,同行、公众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都决定历史学家不可能随意解释历史,从而保证历史编纂的相对客观性。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麦卡拉提出的可靠度问题,即尽管从严格意义上,历史学家并不曾亲身体验过去发生的事件,他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描述常常互相冲突、矛盾,但是,一般而言,具有大量不同证据所支持的、具有合理推论的历史描述通常比其他描述更具有可靠性[7]。
怀特对历史诗性的强调是为表明历史事实中存在建构因素,他并不反对历史客观性本身,就像他对历史事件、公认的道德评价标准的承认。从这个意义来说,怀特并不是批评家所说的语言决定论者,也不是一个允许随意解释历史、取消一切标准的相对主义者,他对历史的语言性、文本性、相对性的强调,并不等于他就主张让这些因素统治历史,将历史变成语言的游戏场,变成独立于道德、政治的纯粹学术推理,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解释历史。对怀特而言,历史的种种诗性特质与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二者分别是历史的两张面孔,不可偏废。
安克斯密特曾指出,怀特备受历史学家批评的原因在于他似乎不承认历史的客观真实性,然而,这些批评没有依据,也不明智[8]。因为对怀特而言,他指出历史编纂中的种种诗性建构因素,目的并不是彻底否认历史真实,也不是证明史学家不可能实现历史真实,而是以此表达对再现历史事实的真实性的担忧。也就是说,在作为历史真实的过去发生的事件与历史学家对真实事件的比喻再现之间,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关系,将二者等同的客观实证主义史学无疑陷入一种错误的幻觉。当然,历史再现中的比喻诗性因素不会阻碍历史真实的实现,因为过去并不是被动地等待历史学家的再现,也不是乏味枯燥的数据、文献的陈列,而是真实的事件与历史学家的诗性灵魂产生共鸣的产物。传统历史学家对历史客观性、科学性的过于强调,对历史诗性的贬低,以及对历史再现中文学风格、语言的排斥,使得历史学日益生硬,失去其特有的学科属性。怀特的贡献就在于提醒我们,所谓的绝对真实不过是个神话,真实本身与主观建构之间,历史事件与比喻再现之间,不是完全对等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再现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以敏锐的诗性方式将过去生动化,以多种比喻视角、风格、情节模式实现历史真实。这是怀特理论的独特价值,正如安克斯密特所言:“当普通的历史学家仅仅固守于一种比喻,怀特的比喻理论的确将常常扮演我们与历史真实之间的镜子的功能。”[8]
语言、文化意义的不确定性、差异性,史学家的个人偏见、信仰、兴趣、想象,都使传统的绝对客观性不再可能。但是,这并不等于彻底取消历史客观性。怀特对于历史事实的阐释与理解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在语言学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不能再固守于传统客观性,不能将历史事实理解为被史学家“发现”或“给定”,但是,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历史事实只是由史学家“创造”“发明”,而应将它理解为前者与后者的融合,既有发现、给定,也有创造、发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怀特的理论观点解构了传统的主观与客观、历史与虚构的二元对立,将看似矛盾的双方融合、统一,这种立场可能更为辩证和全面。
因此,怀特对传统史学观念中客观性的质疑与批评,不等于彻底取消客观性,而是说,这种客观性的单一立场排除了其他阐释的可能性,从而易致本质主义、普遍主义、极权主义。针对别人批评其在历史认识论立场上陷入怀疑主义的境地,怀特认为,他一直将怀疑主义作为任何一种科学世界观的必要组成部分,以及对教条主义、独断论的必要反对[9]。也就是说,怀特对传统史学的客观性、真实性等观念的质疑,是出于对更完善、客观、真实的历史认识论的追求,从而“去魅”传统历史阐释的单一性视角。
三、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从研究的方法论看,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为当今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倡导一种多元化、增殖性的研究,而非追求唯一的正确答案。同时,怀特还为跨学科研究树立范式,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怀特学生时代对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的广泛涉猎和知识积累奠定其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在怀特第一篇代表性论文《历史的负担》中,他不满历史介于科学与艺术中间的尴尬地位,不满当代历史学家对历史科学性的强调、对历史文学性的排斥,提出历史学家应该通过借鉴文学艺术的再现手法及叙事技巧,重新建立历史学的尊严。怀特认为,如果当代历史研究过于强调历史的科学性、客观性,排斥历史的文学性,那就等于让历史片面化;如果历史附属于科学的旗下,却被排除于一级科学门外,“仅作为科学的第三级形式”,那么这样的历史无疑是毫无尊严的。因此,怀特积极倡导历史的文学性,以文学特有的再现风格、再现策略为历史生成一张生动面孔。
如果说《历史的负担》只是初步显示怀特对历史文学性的强调,还不足以构成跨学科研究,那么,他的第一部著作《元史学》运用当代文学艺术、社会学、语言学、政治学等理论,分析19世纪欧洲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的著作,提出历史诗学理论,则充分彰显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及跨学科研究的强劲势头。
在《元史学》之后的《话语的转义》《形式的内容》等著作中,怀特将语言学、叙事学、解释学与历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不断完善历史诗学理论体系,打通历史与文学的坚固壁垒。在1976年发表的《当代文学理论中的荒诞主义时期》一文中,怀特进一步显示广阔的知识视野,以及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式探究意识。他分析了布朗肖、德里达、福柯、巴特等人的文学批评观念,指出在荒诞主义批评家的视角中,文学已降为书写,书写降为语言,语言最终成为符号的无尽游戏。他们为了对批评的正当性进行质疑与批评,攻击整个批评活动。由此,荒诞主义批评家使文本、文本性成为值得质疑的问题,将文本看作与作者无关的自足领域,改变了传统阅读与写作观念。此外,怀特还分析了萨特、加缪的批评观,以及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对文学批评、文本、写作的看法[10]。
在《实在再现中的叙事的价值》一文中,怀特认为,叙事的问题对于反思文化性质、人性等十分重要,叙事能赋予文化中的故事以可理解的意义。在《当代历史理论中的叙事问题》一文中,怀特进一步归纳总结西方历史学界、文艺批评界、哲学界对叙事的五种态度。怀特对叙事的性质、作用的阐述,显示了他对传统历史编纂学基本观念的反思与质疑。在《历史解释的政治学:规训与非崇高化》一文中,怀特指出历史编纂易受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影响。他认为,历史学家的政治立场是其解释的前提,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学术研究活动。
纵观怀特的学术发展道路,怀特将文学、叙事学、语言学等内容引入历史学,并打通历史与文学、哲学、政治学等学科间森严的壁垒,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这使其历史诗学理论具有极大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一方面使得对其历史诗学理论的探究呈现多元化、争议性,另一方面显示出怀特理论所蕴含的学术研究价值。
四、结语
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以其系统性、完整性在历史学领域中有力地呼应了后现代的学术语境,在坚守历史事件的客观性、人类基本道德判断标准的前提下,质疑并去魅了传统历史客观性、真实性观念,倡导一种多元主义的增殖性研究思路,打破历史与文学、哲学等学科的疆界,实现跨学科研究。这是怀特及其理论对当今学界不容忽视的贡献。由于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涉及历史、哲学、文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需要在多学科的交叉地带进行探究,因而对其理论贡献的分析与论述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其理论自身的盲点与局限性尚待研究。
[1]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M].刘北成,薛绚,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2]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新旧历史学[M].余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4]王岳川.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J].天津社会科学,1997(3).
[5]R.F.伯克霍福.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M].刑立军,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Hayden White.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995(2).
[7]C.B.麦卡拉.历史的逻辑:把后现代主义引入视域[M].张秀琴,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F.R.Ankersmit.Hayden White’s Appeal to the Historians[J].History and Theory,1998(2).
[9]Hayden White.The Public Relevance of Historical Studies:A Reply to Dirk Moses[J].History and Theory,2005(3).
[10]Hayden White.The Absurdist Moment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J].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