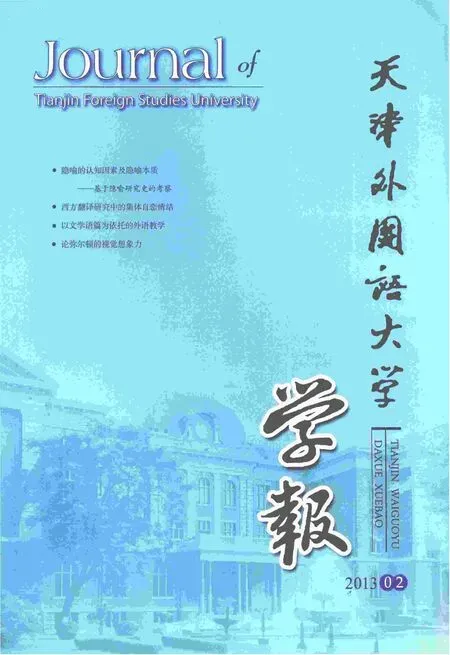论弥尔顿的视觉想象力—— 以《失乐园》为例
周玉军
(华南师范大学 外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一、引言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失乐园》是一部无可挑剔的杰作。萨缪尔 ·约翰逊就曾说过,阅读《失乐园》“是一种责任而非乐趣。我们读弥尔顿的目的是获得教益,读罢则厌烦困乏,转而去其他的地方寻求娱乐;我们要的不是大师,而是朋友”。这一态度的主要根源在于,约翰逊(Johnson,2009:107-108)认为弥尔顿的《失乐园》距离人的生活太过遥远,丝毫不表现具体的“人事与人伦”。作为一个喜欢热闹的城市生活,认为“谁要是厌倦了伦敦,肯定也就厌倦了生命”(Boswell,1992:756)的新古典主义者,约翰逊做出如此评价也许再正常不过了。大诗人艾略特的评价要惊人得多,甚至可以称为恶毒:弥尔顿“使英国语言受到了败坏!”具体而言,是因为他“任何一阶段的诗都没有突出地表现过视觉想象力”,根源则在于弥尔顿的眼疾。“弥尔顿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任何东西……读《失乐园》时,我发觉我感到最愉快的地方恰好是那些最不需要用眼睛看的地方。”(Eliot, 艾略特,1989 :139-145)非常明显,《失乐园》中没有那么多的关于“客观对应物”的描写,可以让艾略特去发现和欣赏。
杨周翰(1996:235)教授在《弥尔顿的悼亡诗》一文中也持类似的看法,认为弥尔顿的创作受视力缺陷的影响很大:“弥尔顿的天才表现在善于描写宏伟寥廓,不善于描写细节,这和他目力不佳有关。”但他的评价恰恰与艾略特相反对,称“弥尔顿的描写不具体,形象不鲜明……正是弥尔顿的长处,也是他意趣所在”(杨周翰,1983:94)。杨文并没有具体解释和阐明,为什么缺少细节描写反而成了长处,缺乏细节和“宏伟寥廓”决不是同义词。
那么,弥尔顿真的没有“视觉想象力”吗?缺少细节究竟代表着想象力的匮乏,还是属于弥尔顿的一种独特的“长处”?我们将以《失乐园》为例,从细节与想象力之间的关系、诗作题材的要求和体裁的传统等方面入手,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二、细节不等于想象力
麦考利的《弥尔顿》一文,很可能是杨周翰《弥尔顿的悼亡诗》文中若干观点的源头。在该文中,麦考利明确表示,弥尔顿的史诗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让读者产生的联想极度“邈远”,其制造的效果,不在于表达的内容,而在其暗示性;“不在于其直接表达的意思,而在与其相关的其他含义”;弥尔顿的诗篇,对人的心灵所造成的冲击是间接的,读者如果不用心主动与作者配合,将无法理解或欣赏他的诗作。弥尔顿不会画出一幅“完满”的图画,也不会为消极被动的听众演奏。他仅是简笔白描,空白处都留待读者去填充。也许正因如此,那些本来“平平常常的文辞”,便获得了“一种神秘的魔力”,就像是“咒语”,“一旦从口唇呼出,过去便回到现在,远方则来至目前。从没有过的美在瞬息间诞生,记忆的坟场中的所有逝者都将还魂重生”。显然,麦考利并不认为弥尔顿缺少想象力。相反,在他看来,从大处着笔,放弃一切不必要的点染,正是弥尔顿的诗艺所在,其作用在于让读者的思维保持活跃,并给他留出足够的想象空间。与那种“作者操办一切,意象场景描画得明明白白,想看不清楚都不成”,而读者“不需要花费任何力气”(Macaulay,1907:158)的文学作品相比,《失乐园》所表现出来的,显然是一种不同的、甚至可能更为高级的想象力,毕竟,一切文本所塑造的画面,最终都要在读者的头脑中获得实现。
较少细节描绘、充分利用“留白”和抽象的笔法以调动读者的想象并制造邈远、壮阔的意境,确实是《失乐园》——至少是其中某些篇章的一个特征,这并非意味着想象力的缺乏,当然,与诗人的视力缺陷更没有任何关系。至少,弥尔顿的眼疾并不构成描绘生动画面的障碍。
威廉·哈兹利特(Hazlitt,1967:628)曾说,弥尔顿即便描绘只在书中读到过的事物,也“有如目见:他的想象有自然之力;他行文如景、涉笔成画……我们难免会揣想,他描绘可见物体如此生动,是因为视力的丧失,反而使他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心灵之力”。哈兹利特从《失乐园》中引了两节诗文作为自己观点的例证:
跟在他后面的名叫临门,/他的庙宇座落在秀丽的大马士革,/亚罢拿和法珥法两条清澈肥沃的河滨。(弥尔顿,1984:25-26)
好像一只伊马乌斯山上生长的秃鹫,/在雪岭围绕着鞑靼人流浪的地方,/因为缺乏食饵而到放牧羊群的诸小山上去,吃饱了羊羔的肉之后,/飞向印度恒河或印度河的发源地;/途中降落在丝利刻奈的荒野,/那儿的中国人用风帆驾驶藤的轻车。(p.110)
细读以上两节诗文,我们可以看出,哈兹利特赞美弥尔顿的诗鲜明如画,并非基于诗中有充分的细节描绘,反而可能是因为诗行中飞快跳跃的名词,以及从伊马乌斯山到印度,再从印度到中国这种动辄跨越千里万里的地域转移,在哈兹利特这位读者心中造成了一种“紧张”,诗人用“空白”调动了他的想象。
但不是所有简约的描写都可以有这样的成绩。对读者的要求,是要积极调动想象力,配合作者去填充那些空白,不需要他用眼睛去看,但需要他用心去想;在作品方面,如麦考利所言,要求一种字与字间奇异的、有“魔力”的搭配,同时提供恰当的空间,让读者的创造性想象力能够有的放矢,如此一来,高度紧张的读者便会被“裹挟”着向前飞奔,甚至“顾不上停下来细细地品味某一行或某一节诗文”(Lewis,1966 :41)。
因此,艾略特说弥尔顿缺少细节则可(至少在《失乐园》的一部分章节中确是如此),说他没有想象力,无论是指哪一种想象力,都是荒谬透顶。艾略特在文章中曾引用济慈评价弥尔顿的话——“他之生即我之死”,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殊不知这恰是一个反证。在文学史上,济慈以感受力之细腻与想象之华美著称。《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
他(济慈)对于味觉的享乐就有极敏锐的感受力,并时常尝试着以特殊的刺激物来增强这种口腹之乐。一个朋友告诉我们,他有一次曾亲眼看见济慈在舌头上洒满辣椒粉,为的是能享受一番在这以后再喝一口红葡萄酒的鲜美感觉。……对于音乐,他有一对音乐家的耳朵;对于光和色彩的变化,他有一双画家的眼睛。(Brandes,勃兰兑斯,1997:168)
无疑,作为感受力如此细致的人,济慈的诗中充满了丰富的细节。但文学不同于生活,我们很难设想,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作家之间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济慈之排斥弥尔顿,正是因为两位诗人间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导致后来者很容易便会受困于前辈设定的规范,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弥尔顿的阴影太过庞大,连济慈都几乎要被笼罩其中了。或许,二人的想象力确实有所不同,但这不同只在表现的方式,而不是本质的差异。也许可以这样说,弥尔顿像手持圆规的天神,擅长从虚空中勾画恢弘的框架,而济慈所做的,则是让那框架之内嵌满闪亮的星星。如果这说法没错的话,那么可以肯定一点,济慈是几百年来弥尔顿最好的读者,如同繁星之于黑夜,白云之于天空。所以才要反抗,所以才要求得独立。一种较晚近的英国文学选本中有如下评价:弥尔顿对英语语言的各种可能性的探求与运用,除了济慈,数百年间无人堪与相比(McCormick,1963:249)。将二人并置,不能也不应解释为偶然的信手拈来。在本质上,他们是相投相契的,他们的诗作,他们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都体现出柯尔律治所谓的“想象的塑造之力”。
不妨再从《失乐园》中摘引几段以资说明。下面一节选自别西卜的讲话,他劝说众叛逆天使继续与上帝为敌,但不知该派谁去刺探人类的乐园最为合适:
但是,首先/得决定派谁去探寻这个新世界?/谁最能胜任?谁能试行漫步而走出/这黑暗无底的广漠深渊,通过/伸手可摸的浓暗,找到崎岖荒凉的路,/或者在广阔的太空飞行,越过大裂口,/振起不挠的双翼,到达那幸福的岛屿?(p.60-61)
下面一节描述撒旦来到地狱门口,为儿子死神所阻,父子尚未相认,几乎引发一场大战:
撒旦听了愈加气愤,/毫不惧怕地毅然站立在那里,/好像北极天空中燃烧的彗星,/纵火烧遍巨大的蛇星座的长空,/从他的怒发上抖落瘟疫和杀气。/那二魔都向对方的脑袋上瞄准,/准备给以致命的一击,不必再动手,/相对怒视的姿势,好像两朵乌云,/都满载着天上的炮弹,隆隆地/来到里海的上空;然后面对面/峙立一会儿,等到风的信号一下,/便在半空中做暗黑的交锋一般。(p.74-75)
再看这几行,撒旦得到混沌指引路线,直奔新创造的世界而来:
他说后,撒旦踌躇满志,/一时说不出话来,心里高兴,/他的苦海竟然有了边,重新振起精神,/恢复气力,升腾而上如一座火的金字塔,/飞入狂乱的混沌界,在四周都是/诸元素纷争冲突的夹缝中夺路而前。(p.87)
没有必要继续引下去了。会心的读者应该已经能够明白,弥尔顿的“意趣”究竟何在了。此处所谓会心,指的便是拥有擅长着色与填充的想象之力。那些喜欢漫画的孩子们,如果能够克服语言的障碍,读懂《失乐园》,一定会奉弥尔顿为最喜欢的作家,并把哈兹利特引为知己。“相对怒视的姿势,好像两朵乌云”,“如火的金字塔”一般升腾而起,不都是绝妙的漫画么?孩子们的想象力总是最丰富的,因此,麦考利在同篇文章中才会说:“无论谁想在一个已经启蒙、文化业已发展的社会中做一个大诗人,他得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孩子。”(Macaulay,1907:156)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华兹华斯才说:“儿童是成年人的父亲。”有的时候,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读者,也需要把自己变成孩子。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在成年之后依然保持了丰富的想象与感受力的话,面对弥尔顿,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崇拜他,要么像济慈一样,或者说像撒旦一样,反叛他。
三、体裁和题材的特殊性
张谷若在谈到《圣经》起首记述天地开创的部分(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虚空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时,曾有这样的评述:“这一节虽极简质,却把希伯来人想象中天地尚未开辟之前的景象,极形象化地传达了出来。直至近代,法人讲天文的作者,写到星际,无边无际,其邈远不可思议,尚能令人起一种awful之感,何况古代。希伯来人这种想象,更优于其他民族。例如,巴比伦神话,说,大神Marduk斩龙,分其体为二,一部为天,一部为地。中国神话则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试把这两种想象和希伯来人的想象比较,优劣自见。”(王佐良等,1983:203)
在几种创世说中,哪一种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哪种最缥缈玄奥,也同样是一目了然的。所以我们说,细节充分不一定就是好事,还要看作者所歌咏的是什么题材,以及他/她选用的表达方式属于哪一种文学体裁。没有疑问,《失乐园》境界、想象之恢弘阔大与主题崇高是有关的。可以将上面张谷若对 《圣经》的评价,与诗人在《失乐园》开篇处依照史诗传统向神灵祈求灵感的一段对照阅读:
特别请您,圣灵呀!您喜爱公正/和清洁的心胸,胜过所有的神殿。/请您教导我,因为您无所不知;/您从太初便存在,张开巨大的翅膀,/像鸽子一样孵伏那洪荒,使它怀孕,/愿您的光明照耀我心中的蒙昧,/提举而且撑持我的卑微;使我能够/适应这个伟大主题的崇高境界,/使我能够阐明永恒的天理,/向世人昭示天道的公正。(p.4)
威尔逊(Wilson,1983:197)在他的《弥尔顿传》中也曾引用这一节诗文,以说明弥尔顿在写作《失乐园》时,把自己提升到了和摩西比肩的高度,诗作的格调之所以如此“雄浑”,是因为“它是用神的语言写成的”,传达的是“神的旨意”。的确,诗人对自己作品的“伟大主题”和“崇高境界”是深有所感的。他将书写的是神的反叛、是天上的战场、是地狱里的惩罚,并通过这些描述“向世人昭示天道的公正”。也只有这样崇高的主题,才最适合发挥弥尔顿那高远无边的想象力。弥尔顿为什么一定要在这样一部史诗中寻求人事与常情呢?这即便不算苛求,也难免会让人觉得有些诧异。
《失乐园》开篇两章之所以追求恢宏的气势,专从阔大处落笔,除了为满足崇高主题的需要之外,可能还与这两章所集中描绘的场景地狱有关。麦卡卢姆(McCallum,1968:87)认为,《失乐园》中描写的地狱,不但指一个实际存在的地方,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心境”。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在描写地狱的时候,突出其虚缈抽象的特征,不是再自然不过了吗?钱钟书(1985:42)在《读拉奥孔》一文中,曾引《失乐园》一章63行“没有亮光,只是可以照见事物的黑暗”,来说明弥尔顿“有些形容状态的词句”,“无法画入物质的画”。正是这样,而且我们还可以说,如把地狱纯粹作为心理写照的话,一旦描写到能够“画入物质的画”的程度,反而会丧失应有的雄浑,减弱读者的恐惧感。退一步说,即便不将地狱作为心理状态,而只看作一个实际存在的场所,弥尔顿采用疏阔的笔法对其进行描述,也自有其道理。
此处同样需要做一点说明的还有撒旦形象的塑造。他那“忧虑的双眼”、“顽固的傲气”、“从火湖中站立起来的”“硕大身躯”,以及“永不屈服、永不退让的勇气”,曾使后来许多读者以为《失乐园》中的撒旦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一位反抗暴政的英雄;在我国权威性的英国文学选本中,甚至称他具有“一个受迫害的革命者的豪迈气概”,这未免离题太远了。作为虔诚的清教徒,弥尔顿是不可能选择撒旦来喻指革命者的,那将是对他自己的讽刺。他对撒旦的描写,只不过是遵循了荷马所开创的史诗传统,同时又是顺应自己诗作题材的一种选择。在传统的史诗中,通常英雄的敌手都被赋予一定崇高、悲壮的品质,以与核心的英雄彼此烘托。后世的文学家借鉴了这一手法,将英雄气质揉入反面人物的性格,塑造出一系列有深度的复杂形象,如马洛的浮士德和拜伦的曼弗雷德等。这就基本解释了为什么弥尔顿会运用雄浑的笔触,从大处点染,将撒旦塑造得气势非凡:“好像北极空中燃烧着的彗星,/纵火烧遍巨大的蛇星座的长空,/从他的怒发上抖落瘟疫和杀气。”这是何等的气概,即便称之为“极具魅力”(唐梅秀,2005:57),似乎也不为过。但英雄如撒旦者,也难免在神子手上落败,由此救世主的伟力更是不可想象了。
不单是叛逆的天使,诗中纯粹正面的英雄,也往往采用简笔虚写,以使他们在读者的想象中获得更大的光辉。以“神子”的第一次出场为例:“上帝从一目望尽过去、现在、未来的/高处望着他”;“神子的仪态,/看来最为光辉灿烂,无可比拟。”(p.95-97)何其 “空疏”!以简约的手法,间接或从侧面对英雄主人公进行虚写,文学史上绝非鲜见,在后世的神魔和侦探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显著,甚至在经典现代文学作品中,也可以很容易找到例证。且看盖茨比的出场:“他的笑容中带着理解——远不止是理解。这是那种罕有的推心置腹的笑容,你一辈子顶多能遇上四、五回。它先是面对着——或者似乎面对着——整个世界,刹那之后,便集中在你的身上,并表现出对你的不可抗拒的偏爱。它所表达的对你的理解,恰恰到你本人希望被理解的程度,信任你,不多不少,也刚好同于你对自己的信任;同时,它教你放心,此时对你的印象,正是你在最佳状态时希望给予别人的印象。”(Fitzgerald,1925:48)如此一位盖茨比,如此对他进行描写,都足称“了不起”了,其效果,要远远好过对人物的外貌和衣着进行浓墨重彩的描述。也许,这算是接受美学意义上的一种贱“近”而贵“远”吧。
四、场景的转变与细节的关系
前面谈到,弥尔顿在《失乐园》开篇章节中之所以采用“疏旷”的笔法,而不执著于做过多精细的描述,是与崇高的题材相适应的,并且符合塑造英雄形象的需要。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当史诗的线索离开天庭之战和地狱之火,转而进入伊甸园的人类世界,叙述的风格与口吻似乎逐渐发生了变化。宏阔的勾勒少了,细致的铺陈随处可见。仅以下面描述伊甸园景致的一段为例:
这里是如此气象万千的田园胜景:/森林中丰茂珍木沁出灵脂妙液,/芬芳四溢,有的结出金色鲜润的/果子悬在枝头,亮晶晶,真可爱。/海斯帕利亚的寓言,如果是真的,/只有在这里可以证实,美味无比。/森林之间有野地和平坡,/野地上有羊群在啃着嫩草,/还有棕榈的小山和滋润的浅谷,/花开漫山遍野,万紫千红,/花色齐全,中有无刺的蔷薇。/另一边,有蔽日的岩荫,/阴凉的岩洞,上覆繁茂的藤蔓,/结着紫色累累的葡萄,悄悄地爬着。(p.139)
看一下,闻一闻,这里有多少种色彩,多少种味道!而这样的段落俯拾皆是,举不胜举。弥尔顿笔下的细节突然变得丰富了。艾略特称弥尔顿因身有残疾,故不善于描写细节的说法,我们也只好将其推翻了。弥尔顿是擅长做细节描绘的,他只是在处理不同的题材时,相应地选择了最为恰当的表述方式而已。
类似地,对于撒旦这一形象的细节描述也多了起来。下面一段,描写撒旦潜入一条蛇的身躯后,试图诱惑夏娃:
开始时,他像偷儿想要接近她,但又怕/不方便,便从侧面,横着前进。/跟着又像个熟练的船夫,在河口/或峡口驶船,随着风向的转换/而改变舵的方位和风帆的方向。/他随机应变,为要惹夏娃注意,/便在她面前耍了一些玩艺儿,/用尾巴卷成许多波浪似的圆圈。(p.333)
读到这里,我们发现,随着描写的精细化,撒旦身上的英雄气概却消失了。王佐良(1997:175)教授也注意到撒旦形象有一个“转变过程”:“在前二章他确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但是后来他决定用诡计来报仇而且化成了一条毒蛇,他就变得猥琐了。”撒旦是否真的是革命者的化身,并且像王佐良教授所说的那样,至少在《失乐园》前两章中,在撒旦“不屈的斗志里也灌注着弥尔顿的革命精神”,这并非本文关注的问题。我们只想提请读者注意,随着场景的转变,为适应刻画不同人物形象的要求,弥尔顿可以自如地改变描述的笔法。正如麦卡卢姆(MacCallum,1968:86)教授所说,“地狱中的对话与天堂中的用辞大相径庭;堕落前亚当与夏娃的交谈和堕落之后有明显差异;对伊甸园的描述与对天堂和地狱的描写在方式上截然不同”。这证明《失乐园》中的细节多寡,与弥尔顿的眼疾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能成为评判他是否具有想象力的依据。细节的多与少,并非写作能力的标尺,而是因应场景变化和不同题材的需要所做出的选择,是不同文风的体现。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某些学者会说:“《失乐园》不只有一种风格,而是有几种。仅从最粗浅的层面上,便可看出,描写天堂时是一种笔法,描写地狱时又是一种笔法,写人类堕落前的乐园是一种笔法,堕落之后又是一种笔法。”(Rajan,1966:56)从大处落笔,只做宏观描写的手法,只是突出地表现在开头几章,尤以一、二章最为显著。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弥尔顿因失明的关系而“不善于描写细节”,甚至缺乏“视觉想象力”,这种错误看法的产生,大致有两种原因:或者是在评论中过分强调了《失乐园》最为人所传诵的开篇几章,或者是联系弥尔顿的眼疾,做出了先入为主的判断。
五、结语
最后再从《失乐园》中摘录一段,作为本文的结束。在这里,诗人仍然遵照史诗传统,在一章起首处向诗神祈祷:“因此,我迫切需要你,天上的光呀,/照耀我的内心,照亮我心中/一切的功能,在那儿移植眼睛,/把那儿所有的云雾都清除干净,/使我能把肉眼所看不到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并且叙述出来。”(p.94)创作《失乐园》时,弥尔顿的眼睛已经全盲,看不到东西了,但看不到不等于写不出,也不等于写不“清楚”,因为诗人的肉眼虽然丧失了功能,却依然具备想象之眸,敞开着心灵的窗口。
[1] Boswell, J.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M]. New York: Everyman’sLibrary, 1992.
[2] Brandes, G. M. C. 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Vol. IV)[A].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主流(第四分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3] Eliot, T. S. Collected Essays[A]. 艾略特诗学文集[C].王恩衷.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4] Fitzgerald, F. S.The Great Gatsby[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5.
[5] Hazlitt, W. On Shakespeare and Milton[A]. In D. Perkins(ed.)English Romantic Writers[C].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67. 620-633.
[6] Johnson, S.The Lives of the Poets: A Sele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7] Lewis, C. S. The Style of Secondary Epic[A]. In L. Martz(ed.)Milton: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C]. 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 Inc., 1966. 40-55.
[8] MacCallum, H. R.Studies of Major Works in English[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9] Macaulay, T. B.Critical & Historical Essays (Vol. I)[C].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07.
[10] McCormick, P. et al.Adventures in English Literature[C].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63.
[11] Milton, J. Paradise Lost[A]. 失乐园. 朱维之.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12] Rajan, B. The Language of Paradise Lost[A]. In L. Martz(ed.)Milton: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C]. 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 Inc., 1966. 56-60.
[13] Wilson, A. N.The Life of John Milt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4] 钱钟书. 七缀集[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5] 唐梅秀.布莱克对弥尔顿的误读[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6):57-61.
[16] 王佐良. 英国诗史[M]. 南京: 译林出版社,1997.
[17]王佐良等.英国文学名篇选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03.
[18] 杨周翰. 攻玉集[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19] 杨周翰.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