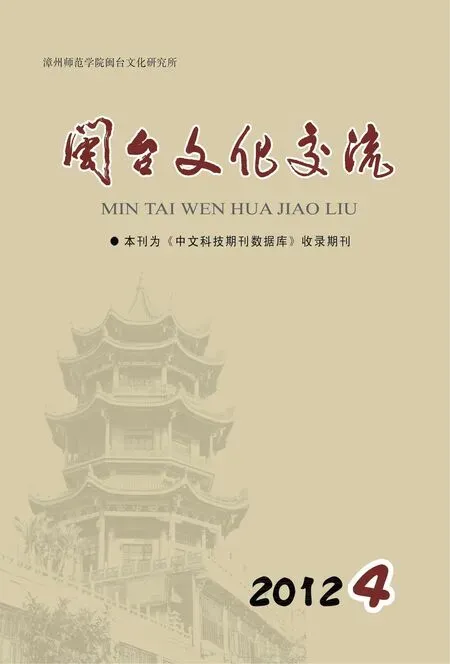试论陈淳思想中伦理范畴与天命的关系
吴文文
(作者系漳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一、朱熹、陈淳之前有关天与天命的认识简述
陈荣捷先生指出:“《北溪字义》以命为首,此是其特色处。《朱子语类》、《朱子全书》与 《性理精义》均未以 《命》字另为一门。陈淳之所以如此重视命者,盖以其寻觅源头处,穷到理而天理流行,以至于天命也。”[1]陈淳将儒家所倡导的 “孝、仁、义、礼、智、信”等伦理范畴直接上溯至天命,这些伦理价值观也因此有了不容置疑、不可悖逆的地位。和之前的宋代理学家相比较,这应该是陈淳思想中的一个特点。张加才认为:“注重 ‘命’实际上是陈淳早年 ‘根原论’追问的继续。”[2]在探讨陈淳著作中伦理范畴与天命的关系之前,先对中国古代有关 “天”、“天命”的认识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
汉字产生的初始阶段,在时间上要早于殷商时期。[3]因此我们可以根据 “天”的古汉字字形来推测殷商之前古人有关 “天”的观念。甲骨文 “天”字作”,王国维先生对此字进行解释时认为,古汉字 “天”的本义为人之颠顶:
后来,用本义为人之颠顶的 “天”字表示头顶之天、天神的概念,是由于这一抽象概念不易用图画的形式加以描绘,只能找一个同音字来记录。但同时,古人借这一字形来表示头顶之天也绝非偶然,我们由此可以窥知古人观念中人与天在空间方位上的关系:天是高高在上、俯视一切的;天以一种居高临下、永恒监督和时时审视一切的方式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之中。
殷商时期人们观念中的 “天”是什么样的?作为商王和商代贵族卜问的对象,起初在卜辞中被称作 “帝”的 “天”无疑是可以和占卜者沟通的具有人格意义的神。依董作宾先生的看法,殷代的这个 “天”掌管着命令下雨、降以饥馑、授以福佑、降以吉祥和降以灾祸五种权能。[5]
从老子和孔子的思想来看,春秋时期与殷周截然不同的 “天”的观念已经产生了。学者们通常认为,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是朴素的自然主义者。《道德经》中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道无亲”等表明,老子否认人格化 “天”的存在。至于 “罕言天道”的孔子,张岱年先生说:“孔子所谓天,可以说是由主宰之天到自然之天的过渡形态。”[6]章太炎认为孔子这一思想是受老子影响:“老子并不相信天帝鬼神和占验的话。孔子也受了老子的学说,所以不相信鬼神,只不敢打扫干净;老子就打扫干净。”[7]
“自然之天”所具有的诸如对过去的安排、对现在的限定、对当事个体将来的惩戒或激励这些特点,与人格神所具有的大多数功能类似,而其所缺乏的,恐怕是与人在语言或心灵上的沟通和交流。所以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从不以语言的形式命令或影响万事万物,而语言却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因此, “能说会道”也应该是人格神所应具备的一个显性标志。“天何言哉”表明,孔子所认为的“天”应该不是以一种类似于人格神的形式存在于宇宙的。而 “四时行焉”则反映,天是以一种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周而复始的大趋势,体现为一种季节变换的不可逆转性。这一不可逆转性逐渐演绎出后来的“逆天者亡”的认识和观念。“万物生焉”反映了在空间维度上,天是无处不在的,万物的生死兴衰无一不隶属于天的意志,无一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反之,天作为一种非人格形式而存在的意志,它的在场又体现在其对万事万物的限定。
《孟子》书中,有时讲到 “天”,有时讲到 “命”,有时讲到 “天命”,“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8]朱熹解释说:“以理言之谓之天,自人言之谓之命,其实则一而已。”[9]从孟子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尽其道”、“修身以俟之”等可知,孟子在敬畏天命的前提下,非常强调个体的主观修为。在政治思想上,其 “民贵君轻”等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又表明,相对于殷商时期,人格意义上的主宰万事万物的神性“天”在孟子这里显然是处于一种消解的趋势中,逐渐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主义色彩的“义理之天”。正如李存山先生指出的:
思孟学派的 “天”有时指 “主宰之天”(如 “尧荐舜于天”),有时指 “运命之天”(如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还有时似指 “自然之天”(如 “天油然作云,沛然作雨”),但作为道德的形上学依据的 “天”,主要是指 “义理之天”。此 “义理之天”当是从周代作为“德”之依归的 “天神”(即主宰之天)发展、转化而来。[10]
朱熹对传统儒家性善论未能在性与天道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联系是不满的。[11]他说:“孟子不曾推原源头,不曾说上面一截,只是说成之者性也。”(《朱子语类》卷四,黄义刚录)对于这一问题,宋代周敦颐即开始尝试在性与天道之间建立一个互通的渠道。
二、从周敦颐到陈淳:宋代以来伦理范畴与天命的对接
宋代周敦颐极其敏锐地认识到 《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所蕴含的天人相通的通道——“诚”。周敦颐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又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通书·诚上》)利用 “诚”这一中介,周敦颐将具有天命属性的 “乾元”和伦理层面的 “五常、百行”巧妙地打通了。程颐“性即理”的思想正是顺着他的老师周敦颐的这一路子而提出的。并且在这一基础上,程颐还提出了 “理即性”、“性外无物”的观点,将天命本体与人性合而为一了。朱熹认为世界的本体是 “理”或 “太极”,并且“把理更加实体化,用本体论进一步论证性即是理。”[12]陈来先生认为,朱熹秉受天理以为性的说法依据的思想资料主要是当时被视为孔子所作的 《易·系辞》中的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13]对此,朱熹说:“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这个理在天地间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来,方始名曰性。只是这理,在天则曰命,在人则曰性。”(《朱子语类》卷五,陈淳录)
在人性论与本体论的关系上,陈淳继承了周、程、朱等人有关宇宙本体与人性相统一的思想。例如,陈淳与程、朱等人一样,认为心之本体即理,为我之心性。心之本体包括仁义礼智,对应天理之元亨利贞:
盖通天地间惟一实然之理而已,为造化之枢纽,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为物之灵,极是体而全得之。总会于吾心即所谓性。虽会在吾心,为我之性,而与天固未尝间。此心之所谓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谓礼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谓义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谓智即天之贞。真实一致,非引而譬之也。故天道无外,此心之理亦无外;天道无限量,此心之理亦亦无限量;天道无一物之不体而万物无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无一物之不体而万物无一之非吾心。[14]
还可以从陈淳对 《中庸》一书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来看这一问题。陈淳说:“(《中庸》)盖真孔门传授心法,而尧舜以来相承之本旨者。”[15]在陈淳看来,《中庸》 乃儒学自尧舜以来一脉相承之心法,而朱熹、陈淳对 《中庸》开篇语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解读又表明, 《中庸》乃至整个儒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 “天命”这一基础之上。“其为书也,始原于天命之奥,而不出乎人心之近。”[16]这是陈淳对《中庸》所下的按语。而这一 “天命之奥、人心之近”之论,实源于朱熹的教诲。陈淳在回忆朱熹有关天命、无极的论述,较好地反映了朱熹关于如何面对天命的态度:
凡所讲道,一本乎实。尽性知命,不越乎人心日用之近。穷神知化,不出乎人伦事物之常。尝论天命之性、无极之真其所自来,虽极微妙而其实即人心之中所当为者而已。但推其本,则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为,故曰天命。虽万事万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实无形象之可指,故曰无极。非谓日用之间别有一物光辉流转,而其所以为此事,则惟在择善固执、中正仁义而已,又非别有一段根原之功在讲学应事之外者。是乃学问徹上徹下紧密之处也。其开端示人,大要类此。[17]
在陈淳对 《中庸》的理解看来, “天命”这一客体范畴因 “理一分殊”流布于万事万物。就致力于 “修道之谓教”的个体而言,这一天命的实现集中体现为通过对人心的教化而实现儒家修齐治平、下学而上达于天的主张。经过这一过程,天命“成为主体化或对象化了客体”[18]。从儒家士人个体的角度而言,“人心”通过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从而上达于天命这一过程,如张立文先生所说,“演变成客体化了的主体”[19]。
关于天命何以能与伦理层面的各个范畴相关,陈淳曾就 “孝”与 “天命”的关系展开了较为详细的论证。从 “孝”这一范畴切入进行论证,这也是他与周敦颐等理学家不同的一个特点。
在陈淳 《孝根原》(卷五)一文中,很大一部分篇幅为和其他儒家知识分子类似的道德说教,而重要的是,为了使这种说教能站得住脚、经得起追问,陈淳就 “孝”的根原这一问题展开了逻辑层面的论证。而逻辑论证的起点则是天命。陈淳认为,个体的出生,不是个体自身可以安排,也不是做父母的可以安排,而是出于天命。“父母之生尔为子而字育惟谨——壮尔体,强尔力”[20]。既然父母子女的血缘关系是由天安排,那么子女对父母的 “孝”也是出于天命。通过陈淳的努力,儒家伦理层面的重要范畴 “孝”得以和 “天”对接,从而使得这一伦理范畴镀上了一层金色,使之变得不容悖逆。
陈淳对 “孝”和 “天命”的对接甚为满意,因此又在 《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北溪大全集·卷五》)一文中加以拓展。在论证伦理范畴的君臣之 “义”、夫妇之“别”、兄弟之 “弟”、朋友之 “信”与 “天命”的关系时,其逻辑路径和有关 “孝”的论证大同小异,即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四种关系的产生和形成,皆是由 “天”安排所致:“夫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既皆天命所必然,非由外而来,则自此身有生以至没世,决无所逃于天地间,亦决不能一日而相离。”(《北溪大全集·卷五》)陈淳认为,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天命所安排好的各种伦理关系,作为社会的个体不可能孤立于这些伦理关系而存在:“天下岂有离君臣、离夫妇、离兄弟、离朋友而逃于天地之外而绝不与世接之人哉!”(同上)
上天不但安排好了这些伦理关系,而且为这些伦理关系制定了 “义、别、第、信”等伦理准则。个体身处天地间,则“当义、当别、当第、当友”,遵循之,则是 “奉天命而尽天职”(同上),反之则是“不循天命之正。”(同上)
为何陈淳将伦理和社会日常秩序层面的逻辑起点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指向 “天”或 “天地”之上?这一原因葛兆光先生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所谓 “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句话,似乎还有更普遍的意义,因为在中国人的思想里,这个天地所表现的宇宙秩序要比一个哲学的或政治的概念要宽广得多,当一个古代人面对世界的时候,这个 “秩序”也就是他的时间的和空间的框架,无论是他在处理自然问题还是在处理社会问题的时候,他都会不由自主地用这个框架来观照,在这个框架的背后隐隐约约支持它的就是人们头上的 “苍穹”和脚下的 “大地”。[21]
这个宇宙秩序正因为它系连了天体观察的感觉、神话想象的成果、哲学思维的理路甚至历史过程的推测,它就带有了无所不包的知识总背景的意味,从这里可以推衍出种种具体的东西。[22]
三、陈淳有关契合天理体验的描述
陈淳不但论证了道德伦理范畴与天命的关系,他还从主体角度描述了契合天理时个人的体验。这体现了陈淳对思辨之力与体验之功是同等重视的。陈淳说:
然则亦若何而为吾天理已到六分而上之验乎?曰:亦须是好善真如好好色之切,则善者真为吾里面实有底物矣。恶恶真如恶恶臭之酷,则恶者真为吾外面不容底物矣。是乃天理胜的人欲之验也。[23]
陈淳描述的是这一境界——对善恶的判断和选择不仅仅停留在理性层面,这种判断和自然而然的选择已经熟练化为一种情感反应。好好色、恶恶臭皆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自然的、不自觉的 “条件反射”,无须借助外力;而是非善恶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建立价值体系或道德标准之后做出的。所以,一般人在做出这些理性选择时需要借助外力,而当追寻善、远离恶已经完全融进了人的情感反应和本能判断,成为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性选择,这境界就正如陈淳所说:“是乃天理胜得人欲之验也。”
陈淳将这一状态形容为 “契乎天理自然流行之妙”、“此正与物为春、并育同乐之意,即尧舜之气象而夫子之志也。”[24]由此,陈淳又由 “天理”引出可以标记或作为天理表象的状态——乐。他说:“推此以往,随其所应,触处洞然冰释,小而洒扫进退三千之仪,大而军国兵民百万之务,何所而非此理,何所而非此乐哉!”[25]
陈淳说:“若曾点之言志,盖有见乎此,故不必外求而惟即吾身之所处,而行吾心之所乐——三子之事,亦莫非此理之所当为,但身未当其时,是则理在彼而不在此,在异日而不在今日,在吾身而不在日用之见定。”[26]
可见,陈淳强调 《论语·公西华侍坐》中曾点之境界之所以高于子路、冉有、公西华三子,在于他能体会此时、此地、此人之自然状态和理想境界。孔子的 “吾与点也”之说,是称赞曾点 “沐于沂”的这种人生境界,也即陈淳所说的 “与物为春、并育同乐之意”。[27]这正是 “孔颜之乐,所乐何事”的一个回答,也即契合天理之境界。然而,陈淳在这一问题上,却似乎与朱熹所强调的“道德修养严肃主义态度”相违背。
陈来先生说:
从程颢开始,理学中一派在强调“体贴天理”的同时,也强调心性修养中的 “自然”,反对著力把持,要求从勉强而行更上一层境界,特别提倡最高境界的洒落自得的性质。——然而,终朱子一生,他始终对 “洒落”不感兴趣,他在中年追寻未发的思考和所要达到的境界与李侗仍不同,而他晚年更对江西之学津津乐道于 “与点”、“自得”表示反感,反复强调道德修养的严肃主义态度,警惕浪漫主义之“乐”淡化了道德理性的境界。所以,他总是把延平的体验未发仅仅说成是读解义理的脱然贯通,甚至声称 “令胸中通透洒落”,“非延平先生本意”。[28]据陈淳在 《北溪大全集》中所述,他曾经把自己这一论述专门向朱熹请教,朱熹先生对此是深为赞许的。[29]解释这一矛盾,是否是朱熹为奖掖后进,采用以勉励为主的教育理念和方式的体现呢?
四、陈淳将伦理范畴与天命对接在当时的意义
随着商代的灭亡和周朝的建立, “天命”主宰一切的观念随之失去事实支撑,理性主义开始萌芽,君主贵族的德性成为兴亡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说西周以来理性主义的力量上升是对 “天命”主宰一切的一次否定,那么,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人所尝试的宇宙本体与人性的统一、陈淳的 “伦理范畴与天命的融合”乃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孔子、孟子虽然肯定天命及其对人世的影响,但不再追问或凸显天命本身是人格之神还是自然意义上的神灵。这种模糊、淡化其 “体”,强调其 “用”的哲学设计或选择,其实也正是殷周以来 “天命”与理性二者之间纠缠不休的延续和一种无奈的折中。或许陈淳等人认识到,纯粹理性的力量有时失之于微弱。而借助和依附潜藏于民间固有的对天命的虔诚信仰力量,理性才能为更大多数人认可和采纳,同时也可以给万事万物以一个普遍性的解释。陈鼓应先生认为孔子学说的一个弱点是缺乏形上学的思考。[30]朱熹、陈淳有关天命的论述,正是对儒学这一缺陷的补救。有什么力量能比信仰以及伴随信仰而来的情感更为强大?而这一情形,在具“淫祀”之风的闽南地区尤为突出,无论是对天帝之神、祖先神的虔诚,还是对自然万物之神的膜拜,这种 “淫祀”的实质是出于对众神真切的肯定和对神性空间存在的虚拟认知。而这一肯定和认知时时刻刻在场且渗透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这也是陈淳在朱熹理学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凸显天命在儒家理论体系中地位的深层次原因,而闽南地域影响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伦理范畴与天命的联盟的一个好处是,它可借助 “天理”中 “天命”的因素说服对人格之神虔诚信仰的民间信众,它亦可借助此 “天命”因素让士人阶层信服,无论他们信奉的是自然之天,还是人格之天,拟或是义理之天。并且,天理中天命的预设让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找到了一种可以在意识形态上驾驭社会各个阶层的方式,同时能在一定时期内较好的包容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理性主义的冲击。
此外,从不同接受者角度而言,天命这一概念具有极大的模糊性。葛兆光先生强调说,在研究宗教信仰问题时,要注意士人阶层的宗教世界与平民阶层的宗教世界的分别。[31]殷周以来,在士人阶层和思想家那里,他们对天命实质的认识有发展,有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天由盲目的膜拜的对象渐渐演化为 “义理之天”。但在大众层面以及相应的政权意识形态的宣扬层面,自从最高统治者把自己统治的合理合法性与天命相捆绑,这种人格意义上的天命之神的认识就作为一种显性存在一直延续着,秦皇汉武数次封禅就是这事实的体现。对于平民阶层而言,殷商以来天命始终是作为一种主宰一切的神而在场,可谓影响深远。这一情况在朱熹陈淳时期依然如此。虽然朱熹的理学体系对这一概念的内涵有明确的界定,但他所推出的天理之天,在普通民间信众这些接受者看来,却易被误读为天帝、天神所规定之理。其实这种误读无关紧要。如果一种意识形态能在人心教化中被广泛接受,不削弱其功用的误读其实也是一种殊途同归的方式。
[1][2]转引自张加才:《〈北溪字义〉与理学范畴体系的诠释和建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第 115~122页。
[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 年。
[4]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天》,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82页。
[5]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大陆杂志》第三卷第十二期,转引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第21页。
[6]张岱年:《中国哲学发微》,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1页。
[7]章太炎:《讲演录》,转引自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0页。
[8]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 年。
[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64页。
[10]李存山:《道家“主干地位”说献疑》,曹峰:《出土文献与儒道关系》,漓江出版社,2012年,第202页。
[11][16]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三联书店,2010 年,第227页。
[12][13]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三联书店,2010 年,第226页。
[14]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一·心体用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68册。
[15][16]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六·中庸发题》,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68册。
[17]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七·侍讲待制朱先生叙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68册。
[18][19]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20]陈淳:《孝根原》(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68册。
[21]葛兆光:《天崩地裂》,《葛兆光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0页。
[22]葛兆光:《天崩地裂》,《葛兆光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9页。
[23][24][25][26][17][28]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八·天理人欲分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68册。
[29]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三联书店,2010 年,第 65 页。
[30]陈鼓应:《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第191页,曹峰:《出土文献与儒道关系》,漓江出版社,2012年。
[31]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民间伦理》,《葛兆光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