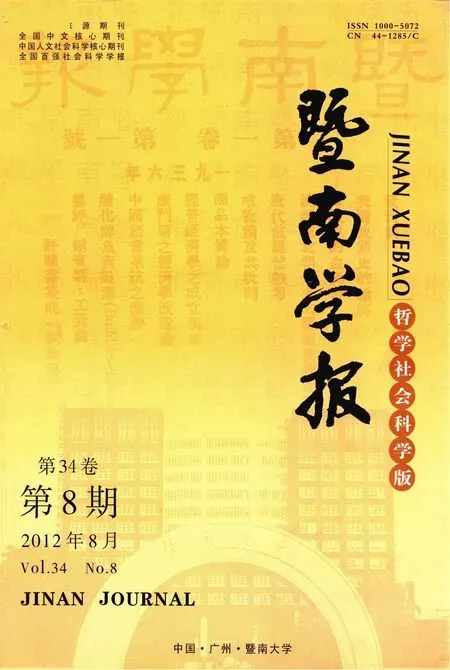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对比研究
汪东萍
(池州学院外语系,安徽池州 247000)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源于公元224年支谦撰写的《法句经序》,是关于译文语言风格的争论。由于文质之争距离我们比较遥远,一些学者常用意译、直译术语比附文质问题,如梁启超先生认为道安“极力为纯粹直译之主张。”[1]155罗新璋先生认为道安提倡的“完全是直译的做法”。[2]2马祖毅先生认为:“释道安也同意赵政的见解,主张直译。”[3]36苏晋仁先生认为“五失本第二项是文与质的问题,即直译与意译的问题”[4]32事实果真如此吗?文质问题是否等同于意译、直译问题?我们倡导回归历史,对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内涵和争论过程进行对比研究。
一、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和内涵
文、质原是我国文章学上的一对概念,指语言风格的文丽和质朴,移用到佛典汉译中,内涵变化不大,指译文语言风格的文丽和质朴。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源于公元224年支谦撰写的《法句经序》,具体内容如下:
法句经序
夫诸经为法言,法句者,犹法言也。近世葛氏传七百偈,偈义致深,译人出之,颇使其浑漫。唯佛难值,其文难闻。又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弗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5]
这段话记载了翻译《法句经》引起的文质争论,公元224年维祗难从天竺携带五百偈本的《法句经》来到武昌,由竺将炎传译,支谦笔受,进行翻译。竺将炎不谙汉语,传译时有的采用胡语,有的采用汉语音译,支谦认为这样的译文“过于质直”、“其辞不雅”,主张对译文进行文饰,语言文丽,属于文派。对此,维祗难引用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进行反驳,主张译文语言质朴,无须文饰,属于质派。在座其他人也引用老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和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附和质派,主张“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认为佛典汉译只要遵循案本旨意,译文无须文饰。文质之争的内涵是译文语言是否需要文饰,语言是质朴还是文丽的争论,文派认为翻译不仅要译出意思,而且应该进行文饰,主张译文语言文丽;质派认为佛典汉译只要译出佛祖意思即可,无须文饰,主张译文语言质朴,《法句经序》拉开了佛典汉译长达数个世纪文质之争的帷幕。
意译、直译之争源于公元前46年西塞罗(Cicero)撰写的《论最优秀的演说家》,西塞罗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也是西方翻译史上最早的翻译理论家。《论最优秀的演说家》有关意译和直译的内容如下:
De optimo genere oratorum(Excerpt)
…And I did not translate them as an interpreter,but as an orator,keeping the same ideas and the forms,or as one might say,the“figures”of thought,but in language which conforms to our usage.And in so doing,I did not hold it necessary to render word for word,but I preserved the general style and force of the language.For I did not think I ought to count them out to the reader like coins,but to pay them by weight,as it were.The result of my labour will be that our Romans will know what to demand from those who claim to be Atticists and to what rule of speech,as it were,they are to be held.[6]157
西塞罗说:“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译文保留原文的思想和形式……但却使用符合译入语表达习惯的语言。这样做时,我认为没有必要逐词翻译,而是保留原文语言总的风格和力量。因为我认为不应该像数钱币一样把原文词语一个一个地数给读者,而是应该把原文的重量如实地称给读者。”这段话成为西方翻译界的经典名言,特别是他提出的“解释员”式的翻译和“演说家”式的翻译,则成为直译、意译的滥斛,奠定了后世讨论翻译的方向。其中,直译(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源于“解释员”式的翻译,也就是逐词翻译,是译词的翻译方法;而意译(sense for sense translation)源于“演说家”式的翻译,是译意的翻译方法,直译、意译属于翻译方法,讨论怎样传达原文的问题。
这样看来,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意译、直译之争不仅出处不同,内涵也不同,我们接着对比文质之争与意译、直译之争的争论过程。
二、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意译、直译之争的争论过程
文质之争是贯穿我国佛典汉译的一条主线,佛典汉译初期安世高和支谶都属于“质”派人物,其译本给人总体印象是“辞质多胡音”,音译较多,译文朴拙,不加润饰,不合汉语习惯。质派有所不足的局面为文派的产生提供了契机,支谦和康僧会是三国时文派的代表人物,二人精通梵文和汉语,主张对译文加工润饰,所译佛典简略文丽。但由于文派过分追求译文的文采美巧,有时不免脱离佛典原义,造成“理滞于文”,遭至后人诟病。此后,佛典汉译又偏向质派,竺法护和赵政是质派代表。“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7]24相对佛典汉译初期的质派译本,竺法护的译本质量明显提高,其译文流畅,符合汉语习惯,质派翻译由朴拙走向质朴,克服了译文结构僵硬、义理晦涩等不足之处。赵政也认为:“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8]382主张译文应该像原文一样保持质朴的语言风格,因为质朴是经文本身的特点,何必改之?告诫译者如果不能传达原文意思就是其罪责。释道安则主张文质兼备,是文、质两派的兼容派,道安在《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中客观地评价了质派译本和文派译本的得失优劣,认为质派译本“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每至事首,辄多不便,诸反复相明,又不显灼也。考其所出,事事周密耳”;文派译本“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焕然易观也。而从约必有所遗,于天竺辞及腾,每大简焉。”[9]266道安认为最好的翻译就是把质派译本和文派译本合二为一,互相补充订正,以便读者可以择善而从,最后的结论是主张融合文、质两派的优点,提倡“合本”。不过,这一时期人们思想上还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认为“胡经尚质”,以为胡语佛经只有质朴一种语言风格。道安去世19年之后,从印度来到中国的鸠摩罗什明确指出:“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5]534说明梵文也非常重视文采,佛典原本也有文丽和质朴之分。这个问题直到二十多年后,道安的高徒释慧远在《大智论抄序》中才给出了正确答案:“于是静寻所由,以求其本,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10]390慧远的这篇序言进一步深化了文质问题,这是佛典汉译史上讨论文质问题时首次把原文当作参照标准,有了原文作为参照,以前争论得如火如荼的文质问题,一下子得到了解决。因为若用文丽的语言翻译质朴的原文,怀疑的人就很多;若用质朴的语言翻译文丽的原文,感兴趣的人则很少。既然“以文应质”和“以质应文”的结果都是错误的,那么正确的答案已经不言自明,那就是“以质应质、以文应文”,原文是什么语言风格,译文就应该保持什么样的语言风格。释僧祐也说:“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11]15认为文过和质甚都是翻译的弊端,同样有损经文的文体,主张译文“质文允正”。此时,人们开始从翻译思想上解决文质矛盾,寻求文质之争的出路。不过,具体到翻译实践,直到玄奘的“新译”才从根本上解决文质问题,使译文的语言风格与原文保持一致,原文质朴则译文质朴,原文文丽则译文文丽,从而在翻译中做到了“文质彬彬、文质相半”,玄奘“新译”是文质之争的圆满结果,从此“文质彬彬、文质相半”成为衡量佛典汉译译文好坏的重要标准。
意译、直译之争是贯穿西方古典译论的一条线索,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提出“解释员”式的翻译和“演说家”式的翻译,主张意译反对直译,拉开了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序幕。贺拉斯认为:“翻译必须坚持活译,摈弃直译,忠实原作的译者不会逐词死译。”[12]15昆体良说:“我所说的翻译,并不仅仅指意译,而且还指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12]20奥古斯丁主张《圣经》翻译要凭“上帝的感召”,哲罗姆提倡“文学翻译用意译,《圣经》翻译用直译”,被人们看成是意译、直译的折中派。到了中世纪,波伊提乌主张宁要“内容准确”的直译,不要“风格优雅”的意译,但丁提出“文学不可译论”思想。文艺复兴时期,尽管意译、直译之争一直在继续,明智的译者已经意识到单单注重意译或直译都失之偏颇,应该在意译和直译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直译派如德西德利乌·伊拉斯谟等人开始强调语言风格的重要性,其译文准确,风格优美,虽是直译,却结合了意译的优点。德国宗教改革领袖和翻译家马丁·路德认为只有意译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再现《圣经》的“精神实质”,提出了翻译的七条细则,列举了只有在七种具体情况下才可以改变原文,否则应该尊重原文,马丁·路德虽是主张意译的代表,但其意译已经打上兼顾原文的底色。英国翻译家兼诗人乔治·査普曼提出了译诗的原则:“我鄙视译者陷入逐词对译的泥坑,丧失本族语活的灵魂,用生硬的语言给原作者抹黑;同时我也憎恨不求简练,使用繁文缛语以表达原意。……凡有卓见而又持慎重态度的译者,都不应仿效原作的词数和词序,而应仿效其实质性成分和句子,认真掂量句子,用最适合译作语言的词汇、表达风格和形式表现和装点译文。”査普曼在谈论自己的翻译方法时说:“我的目标有三:内容清楚,忠于作者,以顺畅取悦于读者。”[13]130-131査普曼反对走意译或直译极端,主张用折中法进行翻译,其翻译以忠于原文内容为核心,兼顾了作者和读者,査普曼的意译、直译折中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被很多译者继承了下来。
到了近代,受文艺复兴余热的影响,翻译和创作卷入到风行一时的“古今之争”中,崇古派主张尊重原文,忠于作者,坚持译作顺从原作,采用直译,这种直译一旦过了头就变成拘泥原文的死译;厚今派提倡关注读者,重视译文,坚持原作顺从译作,采用意译,过了头就变成“美而不忠”的活译和创作。事实上,翻译本身是一项复杂的活动,意译、直译二分法过于简单,容易走向极端。随后人们认识到翻译既要忠实原文,尽量直译;又要兼顾译文,直译不下去就适当意译,在直译和意译之间寻求平衡点,运用折中法进行翻译,这样可以避免陷入死译和活译的泥潭。正如温特华斯·狄龙所言:“在翻译过程中,必须以透彻理解原意、忠实原作实质为总则,原作的语言一般总是上乘的,原作‘落’则译作‘落’,原作‘升’则译作‘升’,既不提倡死抠字句,也不得任意发挥,脱离或改变原作风格。遇到深奥难懂的意思必须细心理解,正确表达,使之流畅通达,不因难译而随意删节。但与增添相比,删节则有一定的优先权,因为增添是把原著没有的思想和语言强加给原作,因此更应避免。简言之,总的原则是,一不改,二不增,三不减,增减相比,宁减勿增。”[14]119-120温特华斯·狄龙的这一翻译原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尽可能直译,忠实原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直译不下去,可以保留一份可增可减的意译空间。翻译家兼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则把翻译分为三类:词译(metaphrase)、释译(paraphrase)和拟译(imitation),词译又叫逐词译,强调与原文逐词相对,这种翻译过于呆板,其实就是死译;拟译是基于原作意义上的一种活译,这种翻译脱离原文过于随意,在某种意义上,拟译是一种创作而不是翻译。德莱顿认为词译和拟译是翻译的两个极端,都应避免,主张折中,采取介于两者之间的释译。相对传统的意译、直译两分法,德莱顿的翻译三分法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其对意译、直译之争的贡献是:首先把走向极端的死译、活译从直译和意译中剥离出来,这样正确的翻译方法已经不言自明,只剩下介于意译和直译之间的释译,从而为意译、直译之争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以翻译原文意思为基点,既要尊重原文,掌握原作特征;又要考虑读者,认真选词,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进行释译。著名翻译家亚历山大·蒲伯也赞成德莱顿的观点,严厉批评词译和拟译,主张释译。此后,不仅词译大受抨击,拟译也不再纳入翻译的正轨,介于直译和意译之间的释译开始盛行。后来泰特勒提出著名的翻译三原则,包括:“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思想,译作风格应与原作一致,译作应象原作一样通顺。”20世纪进入“翻译时代”之后,翻译研究受到现代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的影响,翻译理论逐渐成熟,翻译分类从意译、直译简单的二分法到三分法、甚至更加多元的四分法,这些使偏执于一隅的意译、直译之争不再成为困扰译者的问题。意译、直译之争陪伴西方翻译从古代、中世纪、一直走到近代,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从喧嚣的前台退到了幕后。
三、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意译、直译之争的历史交集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意译、直译之争出处不同,内涵不同,争论的过程也大相径庭。文质之争渊源于我国古代的文章学,刻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是译文是否需要文饰,语言风格是文丽还是质朴的争论,是关于译文语言风格的争论。而意译、直译之争渊源于西方古典译论,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是译意还是译词的争论,是关于翻译方法的争论。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意译、直译之争原本并无关联,二者本无历史的交集。佛典汉译从东汉到宋朝,历时一千多年,翻译思想乃我国本土思想,关于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近代以前所有典籍中均未出现“意译、直译”这些从西方翻译中舶来的外来词汇。但是近代以来,受西方翻译思想的影响,梁启超先生开始用意译和直译等术语评价我国的佛典汉译,使得意译、直译与佛典汉译的文、质之间产生了关联,形成了历史的交集。梁先生把汉末译品看作是“未熟的直译”,把三国西晋支谦等的作品看成是“未熟的意译”,认为道安“极力为纯粹直译之主张”。梁先生首先对“未熟的直译”、“未熟的意译”进行了一番界定:“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其在启蒙时代,语义两未娴洽,依文转写而已。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的直译。稍进,则顺俗晓畅,以期弘通;而于原文是否吻合,不甚厝意。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的意译。”[1]155这一界定稍嫌含糊,与西方译界对“意译”、“直译”的界定有所出入,尽管“依文转写”勉强对应得上西方的直译(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literal translation),但“顺俗晓畅”只能说明译文符合译入语习惯、语言流畅,却并非一定是意译(sense for sense translation),因为梁先生那个时代西方的直译基本也能够做到“顺俗晓畅”。何况梁先生给出的完整定义是“则顺俗晓畅,以期弘通;而于原文是否吻合,不甚厝意。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的意译。”“未熟的意译”虽然语言流畅,却“不甚厝意”,与原意未必吻合。但西方的意译并无“未熟”、“成熟”之分,只要是意译都应该按意翻译,其核心就是要译出原文意思。由此看来,梁启超先生虽然借用了西方的意译、直译术语,却改变了术语本身的内涵,事实上是在用西方的意译、直译对佛典汉译的文、质进行“格义”。在此基础上,梁先生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汉末译品“大率皆未熟的直译也”,这一观点所引论据如下:
1.安世高“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出三藏记集》卷十,引道安《大十二门经序》)
2.“天竺音训诡塞,与汉殊异。先后传译,多致谬滥。唯高所出,为群译之首。安公(道安)以为若及面禀,不异见圣。”(《梁高僧传》卷一安清传)
3.支娄迦谶“安公校定古今精寻文体。云某某等经,似谶所出。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同上支谶传)
4.竺佛朔“汉灵时译《道行经》。译人时滞,虽有失旨;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5.支曜康巨“汉灵献间译经。并言直理旨,不加润饰。”(同上)
上述五条论据所谈均为文质问题,如安世高译本“贵本不饰”、“文通尚质”;支娄迦谶译本“审得本旨,了不加饰”;竺佛朔译本“弃文存质,深得经意”;支曜康巨译本则“言直理旨,不加润饰”,说的都是译文是否需要润饰,译文语言是文丽还是质朴的问题,对直译、意译并无涉及。梁启超先生尽管对“未熟的直译”、“未熟的意译”进行了一番界定,但据此推断“则初期译家,率偏于直译”,理由并不充分。梁先生接着写道:“然其中亦自有派别,世高、支谶两大家译本,今存藏中者不少。试细辨核,则高书实比谶书为易读。谶似纯粹直译,高则已略带意译色彩。故《梁传》又云:‘高所出经,辩而不华,质而不野。’道安《人本欲生经序》云:‘斯经似安世高译。义妙理婉;每览其文,欲罢不能’。窃尝考之:世高译业在南;其笔受者为临淮人严佛调。支谶译业在北,其笔受者为洛阳人孟福、张莲等。好文好质,隐表南北气分之殊。虽谓直译意译两派,自汉代已对峙焉可耳。”[1]145这里梁启超先生对比了安世高和支谶的译本,认为前者易读,“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认为译本的文质不仅与译主,而且与笔受者有很大关系,同时还与我国南北两地流行两种不同的文体风格有关,所谈内容均为语言风格的文质问题,与翻译方法之列的意译、直译并无关联。
梁启超先生还认为:“支谦、法护,当三国西晋间,译业宏富;所译亦最调畅易读。殆属于未熟的意译之一派。”理由如下:
1.《梁传》称:“谦辞旨文雅,曲得圣义。”
2.道安言:“护公所出,纲领必正;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
3.支敏度称:“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约而义显,可谓深入。”(《出三藏记集》卷八引合首楞严经记)
4.僧叡论支谦翻译的《思益经》:“恭明前译,颇丽其辞;仍迷其旨。是使宏标乖于谬文,至味淡于华艳。”(罗什译《思益梵天所问经》僧叡序)
5.僧肇论旧译《维摩诘经》:“支(谦)竺(法护)所出,理滞于文。”(罗什译《维摩诘经》僧肇书)
6.支敏度亦谓:“支恭明,法护,叔兰,先后所译三本(维摩),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诂,字乖趣同;或其文梵越,其理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出三藏记集》卷九引支敏度合维摩诘经序)
上述六条论据中,第1、3条评价了支谦译本“辞旨文雅”、“颇从文丽”,说明支谦是佛典汉译的文派代表,主张对译文进行文饰,语言文丽;第4条是说支谦译本“颇丽其辞,仍迷其旨”,第5条说明支、竺二人翻译的《维摩诘经》均“理滞于文”,这是因为二人的译本都受当时风气影响,采用老庄玄学“格义”佛典,译本存在意义不畅、扞格难通的弊端。第6条则从不同方面比较了支谦、竺法护、竺叔兰三位译者翻译的《维摩诘经》。尤其是第2条,虽引自《高僧传》之《晋长安竺昙摩罗刹(竺法护)附聶承远、聶道真》,但所引并不完整,原文为:“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7]24是说竺法护译本语言质朴,能够准确译出原文意思。人们对竺法护译本的总体评价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9]266这些说明竺法护的翻译“辞质胜文”,属于佛典汉译的质派,但并不能说明其翻译属于意译,或者是“未熟的意译”。事实上,上述六条论据与翻译方法并无关联,而且比较散乱,不能证明支谦、竺法护的翻译属于意译,更无论据证明其是“未熟的意译”。
梁启超先生认为道安“极力为纯粹直译之主张”,其依据有三:
1.“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斲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书》为质朴,而删令合今,则马、郑所深恨者也。”(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出三藏记集》卷九引)
2.“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十四卷本鞞婆沙序)
3.“(大法东流,其日未远,我之诸师,始秦受戒,又乏)译人,考校者少。先人所传,相承谓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或殊失旨,或粗举意。……意常恨之。(此土《尚书》及与《河》《洛》,其文朴质,无敢措手,明祗先王之法言而慎神命也。何至佛戒,圣贤所贵,而可改之以从方言乎?恐失四依不严之教也。与其巧便,宁守雅正。译胡为秦,东教之士犹或非之,原不刊削以从饰也。)……将来学者,实欲求先圣雅言者,宜详览焉。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比丘大戒序,《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引,括号中词句摘自原文,梁启超先生并无引用,添上去是为了更清楚地看清原文意思。)
梁启超先生所引这三条依据分别是道安三篇序言的部分段落,但这三篇序言的主题是讨论用质朴的语言,还是用文丽的语言翻译佛典的问题,上述所引段落至多只能说明道安主张质派翻译的思想,与属于翻译方法系列的直译、意译并无关联,梁启超先生所言道安主张的直译其实是指质派翻译。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有点问题,因为道安并不提倡纯粹的质派翻译,他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质派译本和文派译本各有优劣得失之处,质派译本“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每至事首,辄多不便,诸反复相明,又不显灼也。考其所出,事事周密耳”;文派译本“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焕然易观也。而从约必有所遗,于天竺辞及腾,每大简焉。”[9]265-266道安既不属于质派,也不属于文派,主张根据读者层次和不同文体选择质派或文派翻译,充分发挥质派、文派的优势,更好地融合两派的优点进行翻译,属于文质两派的兼容派。
由于意译、直译之争讨论按词翻译还是按意翻译的问题,属于翻译方法范畴,而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关注的却是译文语言的文丽或质朴,属于语言风格范畴。梁启超先生用意译、直译解释文质问题尽管可以方便后人理解,但毕竟隔靴搔痒,中间隔膜了一层,其实质是一种格义。因为“‘格义’是用原本中国的观念对比外来佛教的观念,让弟子们以熟悉的中国固有的概念去达到充分理解外来印度学说的一种方法。”[15]411这里梁启超先生采用原本外国的术语对比我国本土的佛典汉译思想,让后人以熟悉的西方翻译固有的意译、直译概念来解释距离我们比较遥远的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恰好把汤用彤先生给“格义”下的定义倒了个儿,属于反向格义,其实质还是一种格义。“五四”之后,由于佛典汉译的历史距离我们越来越远,而西方译论在我国译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此后一些学者开始步梁启超先生后尘,用意译、直译解释佛典汉译的文质问题。马祖毅先生认为:“释道安也同意赵政的见解,主张直译。”[3]36但赵政并没有什么直译的观点,其翻译见解体现在《鞞婆沙序》他对译者所说的一段话中:“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8]382这里赵政认为胡语佛经语言质朴,应该采用质朴的语言进行翻译,显然是佛典汉译的质派主张。罗新璋先生认为道安提倡的“完全是直译的做法”。[2]2与梁启超先生认为道安“极力为纯粹直译之主张”如出一辙,前文已经论述,这里不再累述。苏晋仁先生认为“五失本第二项是文与质的问题,即直译与意译的问题”[4]32如果说梁启超先生只是采用西方的意译、直译术语解释佛典汉译的文质问题,苏晋仁先生则已经在文与意译、质与直译之间划上了等号,把文质问题等同于意译、直译问题。至于为什么“文与质的问题”“即直译与意译的问题”?苏先生并未给出理由,只是说明“在骈骊风行的东晋,一般文人对于辞句的修饰,是相当重视的。所以译成汉文,便要注意辞句的整洁,也就是需要意译,才能适合中国人的口味。”[4]34辞句的修饰、整洁讨论译文如何进行文饰,属于语言风格范畴,明显是佛典汉译的文派,不知苏先生为何得出“意译”的结论?文中所举例子除了梁启超先生前面所引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鞞婆沙序》的例句,又增加了一些例子,如道安称赞竺朔佛翻译的《道行经》:“因本顺旨,转音如己,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也。”[16]263批评竺法护翻译的《光赞般若经》:“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17]266批评安世高翻译的《大十二门经》:“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18]254苏先生认为:“由这些例证可以看出道安是不赞成完全意译,同样也不赞成过于直译‘质胜文’的。”[4]34苏先生这里特意标明“直译”即“质胜文”,认为直译就是质派,然而这些例子所谈均是“了不加饰”、“事不加饰”、“贵本不饰”、“辞质胜文”、“文通尚质”的问题,主张译文语言无须润饰,提倡语言质朴,属于佛典汉译的质派。质派与翻译方法范畴的直译大相径庭,因为直译是指按词翻译,而质派则是指译文语言质朴、不加文饰,直译不等于是质派。
综上所述,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渊源于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对象是相差悬殊的天竺语与汉语的翻译,内涵是译文语言的文丽或质朴,需要解决译文是否需要文饰的问题,属于语言风格的争论;而意译、直译之争渊源于西方传统文化,研究对象为印欧语系内相差不大的语言间的转换,内涵是按意翻译还是按词翻译的问题,讨论如何传达原文的问题,属于翻译方法的争论。佛典汉译“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不同,内涵不同,争论过程也不同,这些不同说明不能用西方的意译和直译之争解释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文质问题不等于意译、直译问题,不能简单地在“文”和意译、“质”和直译之间划等号,因为意译不等于文派翻译,直译也不等于质派翻译,二者虽有关联,但侧重点截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比附于西方的意译和直译之争。
[1]Amos Flora Ross.Early Theories of Translation[M].New York:Octagon Books,1973.
[2]Cicero.“De optimo genere oratorum”[C]∥申雨平编.西方翻译理论精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Robinson Douglas.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M].Manchester:St.Jerome,1997a.
[4]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7]释道安.鞞婆沙序[C]∥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
[8]释道安.大十二门经序[C]∥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
[9]释道安.道行经序[C]∥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释道安.合放光光讚略解序[C]∥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释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C]∥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
[12]释慧皎.晋长安竺云摩罗剎(竺法护)附聶承远、聶道真[M]∥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汤一介整理.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4.
[13]释慧远.大智论抄序[C]∥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
[14]释僧祐.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M]∥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
[15]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C].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16]苏晋仁.道安法师在佛典翻译上的贡献[J].法音,1985,(4).
[17]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8]汤用彤.论格义——最早一种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方法[M]∥汤用彤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