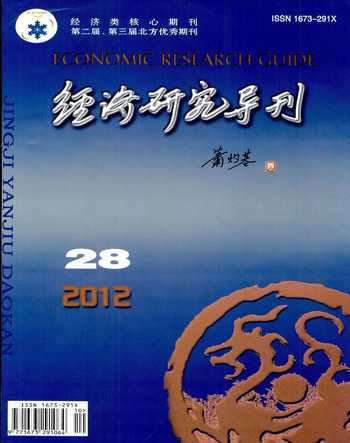制度经济学框架下重农抑商政策的变迁
秦语萌
摘 要: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为重要政策之一的重农抑商政策,其客观的影响对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来说是负面的。运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对重农抑商政策的产生及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深层次探究政策的内在机制。
关键词:重农抑商政策;制度供给;制度需求;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007—03
引言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要思想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制度演进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必须遵循节省制度创新成本的原则,从而尽可能提高经济绩效。但事实上,不同国家的制度演进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一个国家决定其独特发展道路路径的形成,不是某种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各个因素相互依赖相互强化共同演进的效果,这些因素是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相互影响与作用的结果。因此要研究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必须从历史线索分析入手,并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手段进行研究,才能对此有更深层的认识。本文拟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体制下工商政策的形成和演化进行分析,探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与各个因素的相互依赖关系。
一、对商业制度变迁的需求是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动因
1.上层决策者的预期利益
纵观两千多年的历史,君主专制下的一切具体制度、具体机构设置,其最初的动机都是为了实现政权稳定,其演变发展的直接动力也来源于此。而抑商政策就是这类政策的典型。统治者们通过抑商政策所想要实现的预期利益是不完全相同的,但其主旨总围绕维持社会的稳定以及君主权力的稳固。
首先,抑商政策对于有忧患意识的统治者来说,是加强专制、巩固统一的必备手段。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以秦制为蓝本,确立了抑制私营工商业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对富商大贾和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打击,贬低他们的社会地位。在经济上,进一步削弱商人力量,实行重税政策,严格执行盐铁的专卖政策,使得“田租口赋,盐铁治理,二十倍于古”。秦始皇之所以采取这样强硬的手段,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加强专制、巩固统一、防止商人篡权活动的政治目的。
其次,工商业的发展对于王权存在着很大威胁,在商业发展初期,商人往往更加注重自身财富的积累,而当商人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富商大贾开始出现后,商人就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政治方面。中国古代私营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的利润主要有:私营土地买卖、货币借贷、消费以及扩大再生产。其中最主要的流向是用于私营土地买卖和货币借贷,并由此形成了商人、地主和高利贷放贷者三位一体的商人地主阶层。轻商正是为了防止商业资本的壮大,从而威胁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政权稳定。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樨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篡组相樨也,谓之逆。”①商人资本日益强大,超过了社会经济容许的限度,商业资本为寻求出路,必然加大对土地的投入,兼并土地,从而破坏小农经济,威胁到地主阶层的利益基础。
2.利益集团的供给和维系
古代政治权力结构是“垂直型”结构,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维护了君主权力的绝对权威。受官商勾结影响,这一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商人凭着财富与官吏勾结共同盘剥普通民众,并把本来应属于自己所承担的义务也转嫁给了普通民众。这对统治政权产生极大的威胁。西汉农民起义时候,许多小商贩纷纷加入到起义军中。即所谓的“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头尉。烂羊头,关内侯”。
二、对商业制度变迁的供给是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保障
1.制度创新成本
制度创新成本包括规则设计和组织实施新制度的费用;清除旧制度的费用;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制度变迁造成的损失以及不确定性造成的随机成本。
早在商鞅变法中,就把抑商作为主要内容,颁布了一系列抑商法令。汉朝继续推行抑商政策,汉朝封建政权利用经济法规对商贾打击十分严重,从此成为了一个历朝历代相沿不变的传统政策。盐铁专卖法与均输平准法,不仅在汉代是“抑商”的有力工具,而且后世也多采用,成为中国封建制经济法的重要内容。越到后期,惩治“私盐”的条例越多,处罚也愈加苛酷。明清两代对茶叶的私营限制也很严,法律规定“凡贩私茶者同私盐治罪”①,“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因此这项政策的规则设计经历漫长的时间跨度,规则设计也非一朝一夕。
2.规范性行为准则
知识分子从古至今都主张抑商。就经济面而言,从生产和分配的观点倡导抑商。在生产上,认为工商是非生产的,管子所云;“公事竟于刻缕,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而由于工商者众,会减少农人数量,僵尸社会蒙受饥寒,此所贾谊说:“偿闻古人曰,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大残。”在分配上,工商经营与农业相比较会导致贫富不均,此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战国时代的李悝、商鞅和《管子》的作者,认为农业是人类衣食和国家富庶之源,又为战争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主张以农业为本,重农而抑商,重本而抑末,强本而弱末。
在教化面,《盐铁论》中的文学,认为末作的本质与行为,均有违教化:即“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工商将“教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自述其志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以重义还是重利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并且将义利关系的判断作为是否成人的标准:“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乎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孟子》开篇即讲“王亦日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认为自然生命是人的“小体”,精神生命是人的“大体”,物质利益只能满足人的“小体”需要,道德仁义才能满足人的“大体”需要。
三、中央政权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保障
1.诱致性制度变迁主体的缺失
诱致性制度变迁主体缺失是限制重农抑商政策变迁的另一主要原因。任何社会,倘若不建立一套保障创新的制度,制度创新活动就不会出现。张维迎曾经指出,任何一种企图削减利润的政策,不论出于什么理由,都会给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带来损害。同样,即使专制统治者是出于对于整个社会安全与稳定,都会对诱致性制度创新主体的积极性造成打击,从而对其创新活动造成损害。而在专制统治的封建社会,尤其是封建君主一人独大,一眼不慎很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中央集权政府正是通过对于制度创新主体的控制,包括诱致性制度变迁主体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主体,来实现对于抑商政策的维系与巩固。
从汉朝起,抑商政策就严重影响了商人的社会及经济地位。汉武帝的抑商制度包括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并加以各种形式的人身侮辱。“贾人毋得衣锦、绣、绮,毅、红、蜀,操兵,乘骑马” (班固,《汉书·高帝纪下》)。《史记·平准书》记载:“诸贾人未作贯贷买卖,屠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婚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络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招者以一算;商贾人招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人络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童。”《汉书·食货志下》记载:“杨可告络遍天下,中等以上大抵皆遇告,官府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也就是说,中产以上的商人之家大部分都破产了。可见汉朝封建政权利用经济法规对商贾打击之严重。
汉武帝时期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对于商人购买土地,商人子孙到官府做官有着严厉惩罚,谪发、迁徙商人到边远地区戍守,同时通过税收或者直接没收对商人进行经济上的剥削。而作为抑商政策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该主体首先要有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机,从这点来分析,商人无疑受到最大的利益驱动。而由于上述的政策对于商人行为和地位的限制,以至最有动机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商人)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封建专制统治权力的崇拜以及对于“家天下”思想的崇尚,使得对于君主权威的挑战与质疑显得大逆不道。正因为上述原因,最有可能成为制度变迁主体的商人只能长期忍受抑商政策的剥削而无力反抗。
封建统治者通过经济立法,使抑商政策贯彻封建社会的始终。并收到了预期效果,从根本上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禁榷制度就是把某些产销两旺、获利最丰的工商业收归官营,完全由国家垄断。这样一来,把工商业自由发展的道路彻底堵塞了。封建统治者对违反专卖法制的行为往往处以严酷的刑罚。这种专卖制度的垄断性和残酷性,对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主体产生的抑制作用不可言喻,商人虽然有利用法令漏洞牟利的动机,但严酷的法令往往使得他们望而却步,从而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其严重的束缚和破坏作用。当商品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被完全堵死,一点微弱的生机被彻底窒息时,刚刚出现的一点资本主义因素就再也没有增长壮大的可能了。
2.抑商政策供给与“诺斯悖论”
既然中央权力机关具有供给新制度安排的能力,为何不直接提供制度供给?事实上,制度或制度变迁的供给不但取决于制度供给者的能力,还取决于其意愿。后者是在中央权力机关的个体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确定的。同时,身为国家的统治集团和最高政治组织,在上述目标的框架下还要进一步要求降低交易成本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以换取政治支持。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冲突的。要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而建立高效的制度需要高昂的交易成本。该交易成本又主要由中央权力机关承担,因此,为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而提供新的制度安排这一行动所带来的成本会减少中央权力的利益。这样,中央权力在实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与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便构成所谓的“诺斯悖论”。在商业的发展渐渐威胁到统治者的权力,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后,政府不但不可能成为制度供给的主体,甚至会成为制度变迁的阻碍。
除上述原因之外,财政危机与政府掠夺也是抑商政策得以沿袭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都与政府的财政需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货币政策中的货币增发,还是工商政策中的重农抑商,都是为财政服务的。国家是一个具有“暴力潜能”的组织,它的存在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清朝不同阶段的商业政策就反映了上述理论。在康熙乾隆年间,清政府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恤商”、“扶商”政策,如整饬官吏、革除私税、改进度量衡等。到了晚清时期,中华民族遇到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加重与国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的冲击之下,晚清政府已近破产境地,为应付财政危机,其商业政策体现的不再是扶持,而是赤裸裸的掠夺。
晚清政府对商业加速掠夺的主要起因是财政危机。乾隆中期,清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约为7 100万两白银,但自乾隆后期起,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已呈明显下降趋势。至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已降至很低水平,财政危机形成。财政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总量的减少,如嘉庆三年(1798)户部的实际存银仅有1 918万余两;二是财政收入的失控,比如晚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大致在4.5%左右,但实际财政收入却基本不超过生产总值的2%。为缓解财政压力,晚清政府采取了发纸币、行大钱、广捐纳、对外举债等多种举措,与此同时,对社会各阶层的掠夺也随之加速。由于商人是财富的主要集中者,因而对商人的掠夺尤甚。政府加速掠夺的具体表现是各种赋税项目的大幅度增长。在清代前期,盐税收入只是600万两白银,到了光绪末期已经增至2 400万两;光绪十七年时,厘金的收入为1 631万两,到了宣统二年,已经达到4 318万两。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加之皇帝、官僚认为“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晋商被掠夺的命运自然难免。除盐税、厘金之外,晚清政府对晋商的掠夺又多了两种方式:一是捐输。据统计,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咸丰五年的八十年间,山西绅商四次共捐输830万两。二是强借。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垮台前夕,度支部所欠各票号的借款“已逾七百余万,归还尚无着落”。
不仅如此,对于抑商政策这样不仅关乎工商业者,也关乎广大人民的改革,不确定性因素众多,改革的潜在风险也十分大。这就使得统治者没有制度创新的动力,使得强制性制度变迁无法实行,而民间又缺乏诱致性制度变迁主体,从而使得诱致性制度变迁也无法进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抑商政策得以沿袭几千年而不止。
结论
当封建制这种崭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需要一个反复尝试,反复修改的过程。秦帝国的覆亡就是为此所交的第一笔学费。封建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都以达到各方利益调和为重要前提。重农抑商政策也是这一前提下的产物。
重商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无法像在欧洲那样得到蓬勃发展,进而颠覆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传统,并最终发展成为资本主义,除了上述的利益集团的博弈因素之外,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也起了决定作用,中国古代缺乏重商主义发展的土壤。一项政策的产生、发展和衰亡,不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喜好,也不是思想家们的凭空创造,而是一定历史环境和社会基础下的必然产物,在中国执行了近两千年的重农抑商政策亦不例外。对于这项政策的一切功过是非,应更客观、更全面地加以看待。
参考文献:
[1]国彦兵.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
[2]齐涛.中国经济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
[3]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姚遂.中国金融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5]魏华兴.论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社会基础[Z].
[6]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7]大明律:茶法条例[G]//王平平.浅议明代官营茶马互市衰亡的原因.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8]管子·立政[G]//侯家驹.中国经济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803.
[9]桓宽.盐铁论·力耕[G]//侯家驹.中国经济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803.
[10]郭蕴静.清代商业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11]清史稿[G]//刘宝宏,卢昌崇.晋商为什么衰落.财经问题研究,2008,(6).
[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