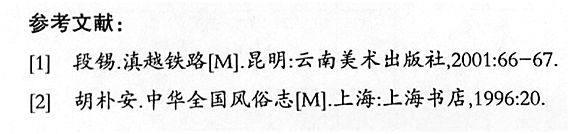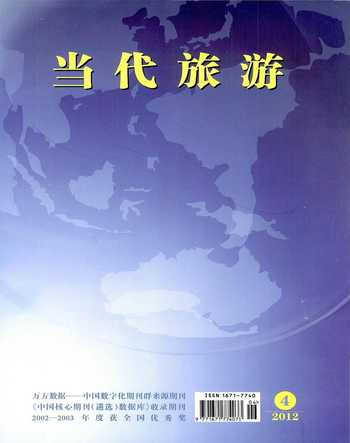铁轨上的开远
高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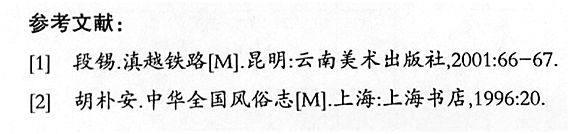
摘要:从云南昆明通往越南海防的滇越铁路通车已逾百年,是中国最早的国际铁路之一。这条铁路中的一个小小的二级站——开远——的命运,在相当意义上,折射了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影像:既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华掠夺的铁证,也是云南在被迫“开放”中,社会、文化、风俗处于“西风”冲击下急剧变化的缩影。
关键词:滇越铁路;开远车站;二重透视
2010年,是滇越铁路正式通车整整100年。这条迤逦于数千年来以“笮桥、马帮、栈道”著称的边远的云南的铁路,是当时世界上最险峻艰辛的铁路。有人与之同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并称为世界上的第三大工程奇迹。也有人将之列为世界三大高原铁路之冠。因为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海拔1400-2200米,长度仅为滇越铁路十分之一不到即78公里;秘鲁安第斯山中央铁路总长也不过329公里,其较高海拔地段全长只有144公里,大大短于滇越铁路。滇越铁路是中国至今仍在使用的米轨铁路,在世界上“准轨”已经通行的铁路大家庭中,具有一种苍老的历史韵味。
但是,如果从“文化全息律”的角度来审视,854公里长的滇越铁路,云南境内465公里的昆河(昆明到河口)路段,可以说折射了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影象。铁路连缀的滇中、滇南各重要城镇:从昆明、宜良、开远到河口,每一个连接点,都刻录了百年云南历史的苍桑变化。今天的开远市,作为昆河铁路的中间点。也有常被人们忽略却又不该被忽略的风痕云迹,却又总与这条铁路息息相关。
在长期的政治词汇中,近代百余年的历史总貌,我们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社会形态的总括。“半殖民地”,是指国家主权的不完整,即帝国主义列强间接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半封建”是指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西方工业文明以排闼直人之势对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造成轰击与改变,使中国自给自足、封闭隔绝的自然经济日渐解体,即中国封建的经济运作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世风民俗在“西风东渐”的冲击中半存半坍的状态。“半殖半封”是政治上的苦难深重与经济文化上的喜忧掺半的混合,是一杯主味苦涩而滋味复杂的鸡尾酒。
滇越铁路与曾作为二级站的开远的命运也是如此。
海外扩张与殖民地掠夺是资本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法帝国主义对殖民中国其用心是由来已久。19世纪40年代的“中法黄埔条约”,50年代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及中法“天津条约”,60年代的中法“北京条约”,尤其是80年代的中法战争与“中法新约”,迫使中国清政府保证法国日后在中国有修筑铁路的特权。铁路到哪里,势力范围就到哪里。法国要想同已经殖民印度的英国争夺对滇、桂的控制,在云南修筑铁路并使之与法国控制下的越南相连接,是其殖民逻辑与势力范围扩张欲的必然选择。1899年,法国迫使清王朝签定“越南条约”,确定铁道线路勘测与修筑滇越铁路。滇越铁路的修筑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云南成为法国势力范围渐成现实。1903年筑路动工的滇越铁路。1910年即正式通车,仅仅七年不到的时间便告修成。原因何在?正如法国人有一篇《滇越铁路》的文章所说:“云南铁路是长期目的的实现与法国政府坚决努力的成就,具有巨大的目前尚未大部分开采的自然资源的中国,对像欧洲的工业和商业来说,是无可比拟的敞开的销售场所和向最勤勉的人提供的巨大财源……云南这个巨大而沉睡的地区,需要铁路来使它振奋……”当时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认为:“根据我个人意见,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今后在远东地区争霸的生死问题。”法国人的经济与政治目的十分昭然。
滇越铁路的出现,对云南来说,当时绝非福音书。但开远,这座古老却又僻小的城镇。自此被裹挟进时代风雨的冲刷中。
滇越铁路昆河路段地形复杂,山高菁深,坡陡壑险,465公里的路段中,桥梁涵洞和隧道竟达3628个。172个隧道其总长逾20公里,最长的隧道长657米。加之气温高,瘴疠流行,毫无施工安全设施,工伤死亡频频。凌空施工的险绝,命悬一线的操作,比之滇南攀崖贴壁采燕窝的危险更胜一筹。有人统计,滇越铁路昆河段先后招募的外地与本地筑路民工约30万左右,而据当时亲临滇越铁路巡访的湖南候补道沈祖燕给朝廷的奏章所言:“此次滇越路工所毙人数,其死于瘴、于病、于饿毙、于虐待者,实不止以六七万计。”几乎是20%的路工死亡率。正如民谣所言,是“一颗道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其中,来自阿迷县(今开远)的民工,当有相当的数量。老一辈开远人中有这样的俗谚:出门三般死,背塃(采矿当砂丁)、铺轨(修筑滇越铁路)、打摆子(患虐疾)。这是半殖民地的云南,在帝国主义者压榨、掠夺下民生状况的小小侧写。在滇越铁路通车以后的一、二十年,开远一带还常常可见残疾佝缩、踽踽乞讨的乞丐,大多是当初筑路致残的外地路工,他们是开远路工命运的另一种显现。
然而,正如列宁所说的:本来想进这道门,结果却打开了另一道门。蒸汽机作为十九世纪“现代化”的最高标志,火车也挟带着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轰鸣沿着铁路震撼着昆河沿线,震撼着昔日的阿迷县。1909年5月1日,火车从滇越边境开到了开远,比火车到达省会昆明早了11个月。古老的毋掇县、阿迷州,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改名开远,寄寓着永历帝带“开拓远疆”之意。清代复置阿迷州。但在滇越铁路通车20余年后,又正式改称“开远县”,有“四面伸开,连接广远”之意。这个再次重称的地名中分明可以嗅得出火车与铁轨的味道。
开远,在《阿迷洲志》的记载中是:“以醇朴称”,“敦朴素。守俭约”,“服食不务文饰,盖习尚然也。”换一种语码表达就是:寒素贫困、生活简陋朴拙,是长期沿续的风习。在滇越铁路通车前,这种贫淡宁静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陈陈相因中,几乎是千百年一以贯之。铁路轨道犹如登天之梯,一下子打开了阿迷人的眼界,并以应接不暇之势突兀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东西。火车的速度、力度,使毗邻开远的个旧以“锡都”之名迅速蜚声世界,开远人于是清晰知道,身边竟伴着个物产之都。知道个旧大锡在铁路运力之下,出口量不断超过以往年出口6000吨的水准,1917年竟突破1.1万吨的空前限度。赞叹之余,有识之士也不免忧心忡忡:如此资源掠夺,国何以堪!在火车“机械能”的对比下,陡然感到祖祖辈辈数千年以来的人挑肩扛、牛驮马运的“筋肉能”是那样软弱,而火车带来的“洋”字号商品,又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眼界:洋铁、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碱(肥皂)、洋灰(水泥)、洋房(西式建筑)、安南面包(法式硬皮面包)、洋纱和洋布(机器纺织品)日渐充斥,显然洋装比之长袍马褂其精神气质又大有不同。生活事象的迥异,其实是文化理念的冲击,日用商品的替代,意味着自然经济的分解。
火车将僻塞的开远促向商品经济大潮。
由铁轨连缀的河口、开远、宜良、昆明等地,居然不同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以“斤”计量而用“公斤”(千克)计量,这正是云南当年“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带来的影响。西式医院在开远落
脚了,其建筑样式、诊病方式、医疗器械、药品形状、医生穿着、人员构成都与中医大相径庭。形状奇异的听诊器代替了切脉用的小垫枕,穿白大褂的医生不同于着长袍的郎中,精致的粒状、粉状“西药”与传统的生熟饮片的“煎汤”别是一番风景……如今早已被淡出人们记忆的数十年前的“开远医院”,这幢昔日的建筑还在无声地诉说着往日的“西风”随钢轨输来的巨大冲击。
滇越铁路的开通,使处于昆明与河口中间的开远迅速成为“边陲重镇”,其矿产、稻米、蔬果等物产也不断运往外地。至今人们熟知的开远甜蕌头、开远六果酒乃至开远土鸡米线等,早在数十年前凭恃着铁路带来的运输便利而广为人知。当然,一旦遇到粮食歉收,开远等地的粮食亦可利用铁道之便由越南运来,这种调节作用是马帮年代绝不可奢望的。
铁路不仅加速了物的流动,更加速了人的流动,从而拓开人们的眼界。一般说,路况与人一天的活动范围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与思维的活跃度:有径无路的时代,靠“体脚能”,人一天的活动半径在5里开外,所谓“适百里者宿春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马路时代,靠“畜马能”,人一天的活动范围在百里开外,所谓“健马疾行百里余,马困人乏待明朝”;铁路年代,靠“机械能”,高运能下相对低的票价,使人们一天的活动范围大幅变化。当时由开远乘火车经海防转道香港,可以在一周内完成,这在此前是匪夷所思的。因此,开远回民中有一大批赴麦加朝觐过的“哈只”,铁路交通的发展使各种阶层的人,都在相当的程度上扩开了眼界。近百年来,滇南铁路沿线各地的人“走出去”的比别的地方更多一些。历史原因是滇南临安府曾是“文献名邦”,科举考试年代,举人科考有“临半榜”之誉(中举的士人临安府占50%左右)。现实原因是20世纪以来,滇南人的“走出来”许多是端赖这条载着耻辱又掺和着现代文明原素的滇越铁路。所以,省会昆明的人,对红河州口音的熟悉程度往往超过省内其他地方,乃至昆明电视台的方言剧中总不免要有操滇南口音的角色。昆河铁路的另一端是河口,开远人说:“去河口的人们喜欢在开远稍事休息,带动得开远人也把去河口视作一件必须完成的事情,好象不去就算不得开远人。”这类心思产生的根基,就是滇越铁路赐予的便捷。
被称为“小火车”的窄轨滇越路,由于贯串开远,在历史上曾给这个除正线外仅设站线3股、站坪长600米的二级站带来过“荣耀”。
滇越铁路上有一台法国制造的载客胶轮内燃动车,在云南路险弯多、坡陡道艰、山高菁深的路轨条件下,时速仍可达75公里以上,称为“米其林”轨车,有“神行太保”之诩。著名作家肖乾先生这样描述过:“滇越铁路并不长。其实有一趟‘米其林特别快车,当天就可以到达,然而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坐得,那种便利与我无缘。”于是70多年前名倾一时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陈布雷的陪同下,由昆明乘坐贵族列车“米其林”沿昆河线到过开远观览,并摄影留念。随着“第一夫人”的照片示之社会,“开远车站”的名头传播弥远。宋美龄的行程不足道,但如果没有滇越铁路,则养尊处优的贵族们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亲莅僻远而名不见经传的开远小城的。滇越铁路提升了开远的地位,开远站是联接滇越铁路的重要枢纽。佚事不过是佚事,但消失的佚事透露出“开远”不消失的旧身影。
在云南历史上数得上的“为天下先”的重大事件中,1915年12月至1916年6月的“护国运动”算是一件。作为云南护国首义的前奏,即蔡锷将军秘密离开北京经滇越铁路返回昆明,在昆河路段上就历经过两次谋杀危机。
由于电影《知音》的渲染,蔡锷将军由北京经天津转日本再到香港绕道越南,最后由滇越铁路人河口往昆明的历程以及在当时的特等车站碧色寨遭遇暗杀者阻截之事,被演绎得活色生香,广为知晓。电影作为讲述故事,允许有铺排加工,只要未偏离基本史实便无可厚非。但是,在阿迷(开远),歹徒也谋划了一次暗杀的行动,却鲜为人知。
当时,阿迷县知事张一鲲、蒙自道尹周沆接袁世凯密令后,料想阿迷县作为昆河铁路的中点和二等车站(宜良、盘溪、芷村等都只是三等站),蔡锷将军会离站休憩,便可在阿迷洋酒楼设宴招待时伺机于酒食之中投毒,或者在下榻处徂击下手。于是踩点定位,周密布置。同时迅速调集蒙自、弥勒乃至丘北等地的乡兵乡勇连同阿迷县警备队700多人,准备配合行动,阻击对方援军。阿迷车站一时杀机四伏、阴霾重重。
1915年12月20日夜,都督唐继尧为保证蔡锷平安到昆明,将建水驻军一个营调至阿迷(开远)车站,严密警戒,凡是没有特颁证件者不得出入车站,对蔡锷专列的警卫工作,更是事先戒备森严。而身负大任的蔡锷就休憩于行李车箱内。21日傍晚,列车到阿迷车站。因当时火车夜晚并不行驶,蔡锷在车箱中歇息一夜,次日一早列车离开阿迷,当日到达昆明。谋害、暗杀的阴谋付之东流,但确然曾箭在弦上。12月25日,云南宣布“讨袁护国”(声讨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共和政体),全国响应。护国运动在中国、在云南的历史上留下了一笔绚丽的记载,而此前四天阿迷车站潜伏的惊险一幕,也使人们在纪念护国之役时难以忘怀。
开远,在平淡岁月中曾蕴藏着并不平淡的历史书笺。
抗日战争初期,海外援华的抗战物资进入中国的一条极其重要的通道就是滇越铁路,货运和客运量一时间陡增2倍到5倍。各种军备物资、内迁工厂设备、名流教授、莘莘学子以及各种援华人员纷纷涌入昆明等地。开远成为必由的站道。1937-1942年初,在开远设立工务总段,辖开远、宜良、昆明等工务段,开远的地位渐呈上升。由于战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40年9月成立“川滇滇越铁路线区司令部”。在开远、宜良、昆明等站都设车站司令部,使滇越铁路的运输调度权基本控制在铁路线区司令部的手中。抗战时期的开远,自有其辉煌。最终于1943年8月1日,中国方面断绝与亲日的法国维希政府的关系,接管滇越铁路,开远行使着自己辖段的中国路权。
自1909年至1959年,由于半个世纪滇越铁路促进下的累积功效,奠牢了开远“滇南重镇”的地位。
开远所辖乡镇,许多是原少数民族聚集地,这从其名称上可以瞥见一些端倪,如“米朵”、“阿得邑”、“则旧”、“宗舍”、“格勒冲”、“下米者”等,经济发达程度显然不高。但开远的铁道交通枢纽的地位,使得它在发展中有条件开拓工业发展的格局。新中国建立后,1953年,开远北面的小龙潭煤矿开建,面积达12.77平方公里,是云南省煤炭生产的重要基地,昆河铁路线通过矿区,正是铁路的便捷拉动了产业的拓展;1956年3月,作为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的156个规模以上项目工程之一的“开远发电厂”第一台4000千瓦机组运转。开远发电厂是云南第一座半自动化的火力发电厂,滇越铁路的影响使开远这座小城率先拥有装机容量2.2万千瓦的基础产业;嗣后,1958年“解放军化肥厂”在开远兴建,占地1.59平方公里,为云南省第一个中型氮肥厂,滇越铁路从厂区经过,表明了该企业与昆河铁路线息息相联的关系;同年,开远糖厂兴建。以后,机车修理、林业机械、水泥、造纸等产业先后兴起与发展,既是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功绩,也是老铁路牵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亚热带半干旱的季风气候使开远天气很热,这是自然的产物。一条百年高原铁路使开远成为有相当热辣度的重镇,这是社会要素的产物。开远处于红河、南盘江两大断层之间,但开远在昆河线上的历史与人文位势,不应当成为河口、碧色寨与昆明之间的断层。只要这条中国唯一的米轨铁路存在,开远的历史轨迹就存在;哪怕有一日米轨的滇越铁路沉寂了,开远的历史折光依然存在。滇越铁路苍桑百年之际,让我们共同注目铁轨上的开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