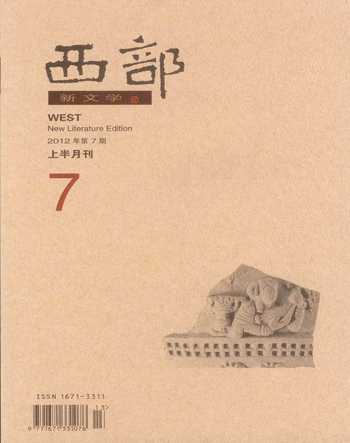敦煌黑暗书(外一篇)
白郎
如今,在莫高窟,放有王道士骨灰的道士塔仍静静地竖立在鸣沙山下,塔上敷着白色,呈不规则的喇嘛塔形制,有点像个长葫芦。使用这种塔来安葬一个道士,显得极为奇怪,不过这倒与王道士在莫高窟的“奋斗”生涯相匹配。这个冒着几丝诡异之气的道士塔,像一截浮在时间深处的标记物,里面充塞着一个时代的哀与恸。一首河西走廊一带叫《陇头歌辞》的古乐府诗唱道:“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也许这样的哀伤,才能表达中国人对敦煌藏经洞的凭吊。
藏经洞发现于大清向八国联军宣战的第二天
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甘肃敦煌县莫高窟,与往常一样,五十岁的王圆■道士从当地人称作下寺的太清宫沿宕河右岸步行四百米来到后来编号为第十六窟的石窟。该石窟是莫高窟千佛洞最大的背屏式石窟,面积达二百六十八平方米,窟主为晚唐敦煌(当时叫沙州)僧团首领吴和尚,所以当地人管这个石窟叫吴和尚窟。石窟甬道彩绘壁画上的一团红色映着身板弱小的王道士,明艳的夏日涌进来,几粒光斑在他宽大的褐色道袍上跳跃。见往昔积满流沙的甬道已被清除得差不多了,他的眼睛里挤出了一点欢愉的精光。在祥和的寂静中,他背着双手在空旷的石窟里踱步,不时盘算着手头维修壁画的银子,他的宽幅袖筒在流光中摆动,粗布布鞋面上粘了一层细沙。王道士哪里想得到,这天,在遥远的帝都,已于头一天向八国联军宣战的大清帝国乱作一团,义和团的长矛大刀正在天津以东拼死阻挡着两千洋人猛烈的炮火。而让他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天,一件文化史上石破天惊的大事在他手头发生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古代写本宝藏被发现。自然,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秘藏着五万多卷4世纪至10世纪古老写本的宝库的重要性,也断不会想到世界上由此会出现一门叫“敦煌学”的显学,众多一流智者为此而皓首穷经费尽毕生心力。略识几个大字的王道士只是历史棋局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和气、猥琐、周密、有责任心的小人物,一不小心撬动了历史的神秘机关。当他激动得像阿里巴巴一样举着烛火走进敦煌藏经洞的一瞬间,脸上却写满了失望,怦怦跳得像头小鹿的心脏很快平息下来,在洞内没有发现金银珠宝。
藏经洞是莫高窟第十七窟的俗称,位于莫高窟第十六窟甬道的北壁内,是附属于第十六窟的一个密室,未发现前,窟门上绘有壁画,十分隐蔽。这个秘密的小石窟边长三米,四面墙高二点五米,窟顶为覆斗形,最高处离地约三米,它当初是为纪念第十六窟窟主吴和尚而设立的影堂(即寺庙供奉尊长真实身像的纪念地),内有吴和尚塑像。藏经洞发现的古写本包括从公元359年到1002年间的各种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地志、民俗等方面的珍稀文献资料和图像,除大量的汉文外,还有为数可观的吐蕃文、回鹘文、突厥文、于阗文、叙利亚文、西夏文和少量的■卢文、梵文、粟特文等,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宝藏。
关于发现藏经洞的真实情形,至今仍罩着朦胧而幽暗的雾帐。据王道士写给慈禧太后的《催募经款草丹》(又称《王道士荐疏》,很可能是请人代笔写的),提到藏经洞的发现时称,在清理补修石窟过程中,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石窟的壁头上突然发出很大的响声,接着裂开一缝,他同雇工挖开裂缝,发现了一个密室,内藏古经数万卷。《王道士荐疏》估计写于1908年下半年以后,因为里面提到了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离开莫高窟的时间是1908年5月。这篇用丹笔催要经款的奏疏未及上呈的原因,应该是慈禧太后于这年的11月死了,王道士得到消息时,奏疏已写好。在1931年王道士死后百日,其徒弟赵玉明、徒孙方至福所作的墓志铭上,则说王道士为维修石窟四处苦口劝募、极力经营,用流水清除积压在甬道上厚厚的流沙,在此过程中,壁头上现出一个洞,里面仿佛有光,结果发现了密室。而据1941年前后在敦煌采风的著名画家谢稚柳撰写的《敦煌石室记》,当时王道士雇用了一个姓杨的书生抄写经文,杨书生在第十六窟的甬道上摆了一个案桌每日抄经,休息时他要吸旱烟,用芨芨草点火。他见座位后面的墙壁上有裂缝,便随手把燃剩的芨芨草插在裂缝中,习以为常。一天,燃剩的芨芨草很长,插入墙缝后深不可测,他用手击打墙壁,发现里面是空的,于是怀疑里面有异常,他向王道士作了汇报后,两人在夜半时分挖开墙壁,发现了藏经洞。谢稚柳所说的这名杨书生,其真名叫杨河清,系出身苦寒的敦煌人。1907年王道士亲口告诉斯坦因的情况则是,花大力气清理完甬道上的流沙后,他开始着手在洞窟里树立新的塑像,“在立塑像时,工匠们在甬道右侧的壁画上发现了一处裂痕,壁画下面不是岩体,而是一堵砖墙。打开砖墙,便发现了藏经洞及堆积在里面的藏经”。而1908年伯希和问及藏经洞的发现时,王道士信口开河地告诉他,是神灵在梦中向他揭示了密室的存在。
王道士献宝无门
王道士的法名是“法真”,“ 圆■”系其俗名。他是湖北麻城人,咸丰七年前后,由于连年蝗灾和旱灾引发的饥荒,被迫“逃之四方,历尽魔劫”。他在陕西流落了一段时间后,来到酒泉从伍,成为一名肃州巡防军的士卒,解甲后连回乡的路费都没获得。不久,他结束倒霉蛋般的红尘生涯,拜酒泉一个姓盛的道长为师做了道士。1898年,他云游至莫高窟,“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修建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那时的莫高窟,只在上寺里有几个诵习藏文佛经而不识汉文的喇嘛,王道长是出家人中唯一能读“天地上下、十方万灵”之类通俗道经及《西游记》的人,这一点让鸠占鹊巢的他很快便站稳了脚跟。
藏经洞被发现后,王道士一面小心翼翼地捂住秘密,一面谨慎地测试着洞中这一大堆老东西的价值。他先选了一些书法精良的卷子上呈给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择,希望能获得赏赐和嘉奖,没想到严大老爷只是象征性地选了两件卷子表示接受好意外,就再也不提此事了。接着,王道士把在藏经洞内他认为最值钱的那些小铜佛偷偷卖给了敦煌城里的绅士,并邀请了几个好奇的绅士,带他们去参观自己得到的一窟古代写本。这些人对这些古老的“破烂”完全没兴趣,只是告诫王道士说,这些经书如果四处流散是不吉祥的,还是封起来吧。王道士很是失望。过了段时间,他雇了毛驴,驮着两箱字迹较为漂亮的经卷,亲自送到酒泉城的道台兼兵备使廷栋那里。王道士以前在这里当过兵,知道廷栋大人雅好书法,所以不辞辛劳特来“投其所好”。没想到这位道台大人轻蔑地认为这些经卷的书法不如自己,因此仅是瞟了几眼经书,赏了王道士一杯茶,留了点东西打个哈哈答应把它转呈给省城兰州的藩台大人,就把王道士打发回去了。后来,尚未死心的王道士听说敦煌县令换成了进士出身的汪宗翰,再次把一些古经卷送到了他那里。学问很好的汪宗翰是个识货的人,他看过东西之后,断定是不寻常之物,马上向省里主管文教的甘肃学政叶昌炽写了份报告。叶昌炽是当时研究古文献的高手,接到报告吃惊不小,旋即向甘肃藩台建议把发现的所有古经卷运到省城兰州来保存,结果估算下来,得花几千两银子的运费,这笔经费一时无法落实。不久汪宗翰接到省里的命令,责成他先把藏经洞封存起来,让王道士暂时管理,等候处理。汪县令于1904年5月执行了这条命令,接下来由于其他原因他于1906年2月被调离敦煌,这前后,遭到撤职的叶昌炽返回了湖南老家。此后的两任敦煌县令都对藏经洞大不以为然,而王道士的肚子里也添了一腔怨气。他一直在为维修荒芜的莫高窟而孜孜不倦地努力着,全部心血都放到了这件事上,原指望官府能奖赏他对古代写本的发现,得些银子投入到维修工程中去,结果五年了一个子儿都没得到。把藏经洞简单地封存起来,显然不合他的心意,所以他表面上应承,暗地里却不断把古经卷拿到敦煌城里悄悄出售。
两个“洋玄奘”
1905年初,俄国人奥勃鲁切夫从文物贩子处听说敦煌发现了藏经洞,深秋时他为此赶到敦煌,用六包日用品换取了两大包流散出来的藏经洞古写本。
1907年3月,一个长着希腊式高鼻子的英国籍匈牙利犹太人来到了莫高窟,他是沉迷于丝绸之路考古发掘的斯坦因。他从一个叫扎希德伯克的土耳其商人处获知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大量古代写本的消息,于是带着懂英语的湖南师爷蒋孝琬从新疆赶来看个究竟。不巧,王道士和两个徒弟为募集维修石窟的经费外出化缘去了。斯坦因耐心地在壮丽得深不可测的莫高窟及敦煌各地转悠,直到5月21日才见到王道士。
王道士礼仪性地接待了这位异国的不速之客,并对其怀有戒心。在斯坦因眼中,王道士“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为了避免引起王道士的过度警惕,斯坦因声称自己主要是来考察石窟的,他和蒋师爷在空地上搭了个帐篷,准备慢慢和王道士磨。再三揣摩后,斯坦因让王道士带他参观了新近修复的一些石窟,说了不少恭维话,而实际上,斯坦因认为,“新做成的泥像,都跟真人差不多大小,依我看它们比起洞窟中其他的塑像要笨拙逊色许多。不过王道士为此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听了一堆赞扬后,王道士自豪地展示了这些年来他四处化缘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得非常仔细,全部募捐所得都用于修缮石窟,他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厘。接着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王道士发现的藏经洞上,他对官府的做法很是不满,尤其对未给予自己任何褒奖感到愤愤不平。
由于斯坦因只是略懂汉语,所以能说会道的蒋师爷在和王道士的交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蒋师爷费尽心机地提出想看看藏经洞的请求后,谨慎的王道士迟疑再三,只是让他们把放在自己住处的几本古经卷拿去翻看。结果其中一本的边页上竟题有玄奘的名字,表明这是当年玄奘翻译出来的汉文佛经,这让斯坦因在惊讶的兴奋中,决定利用王道士虔诚、无知而又很执著的性格。因为经过几天的接触,他已发现此人恰恰是玄奘的忠实信徒,还搞了些玄奘取经的新壁画。当蒋师爷把题有“玄奘”的佛经指给王道士看时,胸中本只有一小勺墨水的王道士愣住了,他先前从未细看过这些写本。蒋师爷声称这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在催促他向斯坦因展示密室里的藏经,而斯坦因则添油加醋地和王道士大谈“自己的保护神”玄奘,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是他在西域从事探险考古的行动指南,他对玄奘可谓滚瓜烂熟。最终,王道士确认眼前的这位洋人和自己一样都是唐僧的信徒,他来到这里是唐僧这位神僧的一种“神授”。在斯坦因承诺事成之后将捐一笔数目不菲的修缮石窟的功德钱后,王道士被“击溃”了,他允许把部分古写本取回“西天”。
那是很热的一天,外面空无一人,借着摇曳不定的烛光,激动得不能自持的斯坦因睁大眼睛向阴暗的密室走去,“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堆积的高度约有十英尺,后来测算的结果,总计约近五百立方英尺”。接着,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王道士分批把经卷拿到一旁吴和尚窟的耳房里让斯坦因细看,耳房有门,有纸糊的窗子,刚好可以避人耳目。其后数天,斯坦因一面竭尽所能地从卷帙浩繁的古写本中把最有价值的那些挑选出来,一面摆出漫不经心的模样,以免让王道士意识到他手中的这批东西是无价之宝。他暗自惊呼“我以前所有的发现无一能与此相提并论”,同时遗憾自己在文字学、语言学上功力的不足。最终,蒋师爷偷偷花了七个晚上把一捆捆选好的经卷运到马车上,总计二十四箱古写本和五箱绢画及麻布画珍品。王道士笑眯眯地拿到了十四块马蹄银(一说价值两百两白银,一说价值七百两白银)。在斯坦因走时,他再三叮嘱他离开中国国土前,对这批东西的出土地点必须守口如瓶。
大半年过后,在一阵暴烈的西风中,另一位“洋玄奘”来到了莫高窟,他是法国佬伯希和,一位集汉学、蒙古学、突厥学、伊朗学于一身的一流学者,通晓十余种语言和文字。伯希和在乌鲁木齐得到皇族载澜赠送的一卷敦煌古写本,卷末有“大唐贞元二年弟子法明沐浴焚香敬书”的题跋,他断定这是公元8世纪的古物。在了解了一些语焉不详的藏经洞发现的背景后,立即拍马赶到敦煌。伯希和在敦煌城里见到了王道士,他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将王道士“拿下”,并博得其好感。从斯坦因的手头尝到甜头后,王道士便对外国人有了好印象。见财神爷再次送来鸿运,他眯着一双小眼睛暗示出让古写本得花不少银子,派头十足的伯希和满口答应。1908年3月3日,王道士打开紧闭的铁锁,让伯希和进入了他后来称作“至圣所”的藏经洞,伯希和后来回忆说:“一种令人心醉的激动心情涌遍了全身,我面对的是远东历史上需要记录下来的中国最了不起的一次写本大发现……我简直被惊呆了。由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的时间长达八年,我曾认为洞中的经卷已大大减少。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各个方向都只有约二点五米,三侧均布满了一人多高、两层或三层厚的卷子的石龛中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此后的三个星期,借着一盏摇曳的烛光,伯希和蹲在狭小的空间里,每小时打开一百卷写本,以 “一种供语言学家使用的汽车速度”,把所有的精品都选了一遍,尤其是那些有纪年或题款的写本。眼力一流的伯希和精力耗尽仍容光焕发,每天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劳作之后带着一大堆文字宝藏激动不已地回到临时住地。最终,经过一阵漫长的讨价还价后,王道士以五百两银子的价格允许伯希和把挑选好的六千六百多件精华古写本及一些绘画作品带走。望着白花花的银子,他快乐地舒了一口气,沉浸在自己绚烂的千秋大梦里,意气风发地感到复兴石窟仙境的伟业已指日可待。在敦煌城,伯希和度过了三十岁生日,并收集到一些当初从藏经洞流散出去的小铜佛,整整有一褡裢。
中国被伯希和从靴子里抖出来的沙子击伤
1909年,北京六国饭店,伯希和举办了敦煌文物展览,中国内地学界才始知发现了大批珍稀的“敦煌遗书”。伯希和向学术名流们讲述了藏经洞的情况,并透露藏经洞还未全空,他没有取完,不然有伤他的品格。看完展览后著名学者罗振玉扼腕不已地用“可喜、可恨、可悲”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在他的再三呼吁下,官方把藏经洞的剩余古写本押运到北京,没想到押运过程中又历经了一场磨难,负责押运的官员大肆侵吞写本,运达北京图书馆的只有八千余件。视自己为掘宝人的王道士对政府给予的拨款极为不满,他私自藏下了许多古写本。1912年,这批写本中的六百多本被卖给了前来敦煌淘宝的日本人橘瑞超。斯坦因1914年第二次来敦煌时买走了另外的六百多本。1914年至1915年,俄国考古学家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不仅收集到一大批先前从藏经洞中流出的古写本,而且掠去众多石窟内的珍品文物。直到1919年,获知民间常有人向外国人兜售敦煌写本的消息,甘肃省政府下令敦煌地方官员查找流散的敦煌遗书,官员再次打开藏经洞,里面竟然还藏有九十四捆古写本。
1925年,在藏经洞发现二十五年之后,一个叫陈万里的学者才代表中国学界西行来到敦煌对莫高窟进行了三天的学术考察。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对这一艺术宝库进行正式考察。中国学界比蜗牛还缓慢的行动,令人想起鲁迅说过的一句话:“真正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假的国学家正在喝酒打牌。”
斯坦因把藏经洞的文物带到英国后,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几乎一夜之间,他达到了考古生涯的巅峰时刻,后被英国女王授予骑士勋章。而伯希和返回巴黎后,1909年12月,法国四千多各界名流在巴黎大学参加了为其举办的隆重报告会。他从西域带回去的文物,被收藏于巴黎国家博物馆和吉美博物馆,吉美博物馆至今还毕恭毕敬地陈列着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面放着伯希和当年探险返回后从靴子中抖出来的沙子。
1930年,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为《敦煌劫余录》一书所作的序中,概括了“敦煌学”的学科概念,他怀着无尽的悲怆感慨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茶花拉长了记忆之线
黑鸟在旭日上掠过,红花在白雪下绽放。这红花是茶花,这白雪是玉龙雪。当我用力拉动记忆之线,大片茶花便顺着丽江的某一根历史廊柱,覆盖了时间的镜面。
丽江茶花风雅叙事
在《茶花女》里,肺痨美人玛格丽特总是随身带着茶花,一个月里有二十五天带的是白茶花,另外五天带的是红茶花。这些花儿迷朦地飘着几丝哀艳的清香,现出纯真的幻灭之态。茶花传入欧洲的历史其实不长,据说是英国医生甘宁于1677年从中国引种过去的。西班牙OKA花园里有一株高十米的云南茶花,据说是1851年引种的。
唐代时,山茶花叫海石榴,李白就写过一首《咏邻女东窗海石榴》:“鲁女东窗下,海榴世所稀。珊瑚映绿水,未足比光辉……”那时候有个才子叫张籍,嗜花如命,见一个叫贵候的人养了一棵山茶,花大如盎,瑰姿婀娜,喜欢得不行,最后竟用爱妾将这棵山茶换到手。完成于1899年的珍品《南诏画卷》中,奇王之的圆形花坛中有两株高过屋檐开着大朵红色鲜花的山茶,表明那时大理一带已在庭院中种植茶花。
在与大理相邻的丽江,栽种茶花是传统雅道,这种热烈而单纯的花投合纳西人的脾性,所以广受欢迎。冬春之际,半空中堆满了玉龙白雪,雪影充塞万物,让人感到丽江仿佛是一座从白雪中长出来的小城。这时候茶花不断开放,花身遍浮烟霞之色,绢绸似的花瓣在虚空中曼舞,红花白雪间,天空像蓝色的大湖覆盖了纳西人的沃野和祖先的墓茔。丽江家养茶花主要有牡丹型和蔷薇型,牡丹型朵大、瓣阔、色艳,蔷薇型朵若芙蓉,娟秀清雅,名品如“雪狮”、“松子鳞”、“童子面”、“大玛瑙”、“恨天高”等。丽江的山野中,另有大量的野山茶,这种山茶是常绿灌木,带有光晕的心型叶片长着小锯齿,花只有拇指那么大,花心灿黄,卷开的花瓣如胭脂与凝脂的混合物,一派天然,美得无法无天。每年春节前后,乡民们用竹篮将野山茶背下山,摆在街头卖,随处都是,每天都可碰到众多买回一束野山茶的人。他们把这一新春尤物插进大瓷瓶的净水里,在素雅的吉祥中迎接春天的到来。我母亲最喜欢野山茶,年轻时候在农村做农妇,新春时节到山上砍柴,每次都会摘一大抱野茶花拴在沉重的柴禾上带回。后来住到城里,便每年都买。今年春节前,我回到丽江,到家的第二天,母亲专门去买了一大束野山茶回来。她推开门的一瞬间,我看见青枝上一堆红蕾突兀地伸进来,映着她的几丝白发。她慈祥地瞧着我时,想想自己漂泊异乡,陪她的时间很少,一种无言的痛便透入了骨髓。岁月静好,茶花依旧,生活在神秘地流逝,老母比去年又老了一点点哦。
家养茶花传入丽江的准确时间,已渺不可考。据《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七》,1639年农历二月初十,徐霞客在大研古城以南八公里处的木家院(即万德宫)辅导丽江土司木增的第四子木宿时,见到丽江最大的一棵茶花树:“转过一厅,左有巨楼,楼前茶树,盘荫数亩,高与楼齐。其本径尺者三四株丛起,四旁葳蕤,下覆甚密,不能中窥,其花尚未全舒,止数十朵,高缀丛叶中,虽大而不能近觑。且花少叶盛,未见灿烂之妙,若待月终,便成火树霞林,惜此间地寒,花较迟也。”侍侯徐霞客的小官吏告诉他,这棵茶花堪称“南中之冠”,树龄有六十多年,于是徐赞叹道:“余初疑为数百年物,而岂知气机发旺,其妙如此。”由万德宫遗存的明代汉白玉石碑可知,这一馆阁是土司木高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建造的。照徐霞客的描述,“六十多岁”的茶花应该长不了那么大,更大的可能是嘉靖三十五年前后栽种或移栽的,树龄至少应在八十年以上。巨木环绕的万德宫门前蹲着大石狮,在几十朵“其妙如此”的大茶花远映下,四公子木宿以隆重的纳西待客礼节——搭建遍铺松毛的松棚来接待徐霞客。吃着丽江的烤乳猪、牦牛舌,以寒士之身餐霞咽云遍游天下的徐公,当从松棚浓郁的净气和粉丽的茶花中,感受到纳西人的诚意。
清代时丽江茶花极多,尤以福国寺、文峰寺、指云寺、普济寺、玉峰寺几个喇嘛寺繁盛。据《丽江光绪府志·艺文志》,丽江十二景中的第六景便是“福国山茶”。 福国寺在藏语中叫“奥米南林”,晚明时开始种茶花,至晚清时已蔚然长成众多高古之树,有合围的,有合抱的,有丛生的,有一次开数千朵大花的。花开时节,青山绿水鹤梦烟寒,美丽的茶花在清寂的佛鼓声中高下相照烂漫若彤云。可惜的是,这些奇品后来尽数被毁。
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丽江茶花长得最好的是文峰寺。文峰寺是喇嘛教噶玛噶举派圣地之一,始建于1739年,藏语叫“桑纳迦卓林”。1949年时,寺内尚有五十多个喇嘛,分住于大殿后侧的二十四座僧院。在“三房一照壁”的纳西式僧院的堂屋里,酥油灯在静穆的佛像和彩绘唐卡前经久不息。每天黎明,喇嘛们都会在一阵空明而玄秘的法螺声中起床,上午十点左右,戴上高高的有毛边的曲型黄帽到大殿里集体念经。所有僧院里都种满了洁净的花木,正房前扎有一棚婉约的十里香,院子中央是一棵高大的茶花。生于1875年的丽江文人李白潭,在其《文峰寺记》中提到过这些茶花树。最妙的茶花,长在高玛亚法师的僧院里,这棵茶花树干粗壮,一人不能合抱,婆娑的树冠如巨大的碧玉顶出院落。法师每年都会用几大碗植物油涂抹树干,使树身保持光洁,增加肥力,预防病虫的危害。这棵资质绝伦的大茶花堪称神品,所嫁接的花叶共分三层,第一层高齐平房,开出的茶花为花大富艳的“九心十八瓣”, 每朵花都有几簇金黄的花蕊;第二层高齐楼房,所开茶花为鲜红中晕染粉红的大红宝石似的“红玛瑙”;第三层高出楼顶,所开茶花为桃红色的珍品“恨天高”(亦称“汉红菊瓣”), 每朵花的花瓣多达四十至四十五片,花身直径达九至十一厘米,花树的下端,还嫁接有一种叫“小白梅”的品种,惜乎光照不足未成气候。每年花开之时,身披猩红僧袍的高玛亚法师坐在明媚的繁花下读着经书,恍同神仙中人。
数年过后,在激进的大跃进号角声中,丽江第二中学搬到文峰寺,近五百名师生“攻占”了这一古老的庙宇,我父亲稍后亦成为了该 “团伙”的一分子。虽有一些喇嘛留守,每月十五还可在在大殿念经拜佛,但庙产大多被改造为教室或宿舍,庙宇周围被自力更生的学生辟为田地,种满了瓜菜洋芋。1961年10月31日,汪宁生教授到文峰寺考察时,寺内尚有六个喇嘛,不久,这几个喇嘛也被迫离开了。1970年二中迁出后,文峰寺几近毁灭,仅剩下一院残破的殿堂和一院僧房,那些阆苑仙葩似的茶花,早被毁坏得干干净净。
一个茶花僧的性情
两年前,北方最著名的一棵茶花树枯死了。它是崂山太清宫三官殿前有600年树龄的“绛雪”,人们再也看不到那满树芳艳的红花犹如落了一层绛红色的雪。附近原有一株高及屋檐的白牡丹,也早已不复存在。当年,蒲松龄曾在“绛雪”旁边的房子里住过一段,终日与牡丹、山茶相对,构思出《聊斋志异》中的名段《香玉》。故事写一黄姓书生在太清宫附近读书,白牡丹感其深情化作白衣女香玉与之相恋,后白牡丹被人掘走枯死,香玉亦失踪,书生终日在花穴前恸哭。山茶花所化的红衣女绛雪见其对好友香玉如此情深,便悉心照料并与之常常悼怀香玉。花神被黄生的精诚感动,使香玉复生与之相见。多年过去,黄生死后变成牡丹花下的一株赤芽,不幸被小道士砍掉,白牡丹和红山茶花于是相继殉情而死。在故事的末尾,蒲松龄感慨道:“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这句话让我不禁想起照料丽江玉峰寺万朵山茶四十余年的茶花僧那督来。
2006年2月6日,碧空下,大片隐遁的蓝光朝着玉峰寺周围的森林落下去,空阔的松风在沉吟,仿佛怀着一阵古琴的玄音刮过我的骨头。寺庙不远处,有两个清幽的小湖,像一双森林的明眸,湖水一碧到底,倒影着松林的绿裳,阳光清澈地打在上面,高洁的水体泛出梦幻的碎光。我和家人游完了这两个湖,来到森林中央的玉峰寺,大殿内两个喇嘛正在虔心念经,一边念一边敲了几下身边的法鼓,其中一个是来自四川得荣县白松乡的纳西人,但一句纳西话都不会说了。他告诉我老家除了少数老人之外都不会讲纳西话了。大殿背后不远处是茶花院,以前来过多次了,我还未踏入院子便猜想,那督老人十有八九会在院子里。四十多年了,除非有事外出,不然他是一定会日夜守护在茶花院里的。走进一看,老人果然默坐在屋檐下,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树冠已一片灿红的大茶花树。老人未穿僧袍,头戴1950年代时髦一时的伊万诺夫式鸭舌帽,身穿蓝布中山装,脚上套着黑色呢面棉鞋,看上去比两年前衰弱了许多。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向他问好时,发现老人的耳朵已聋了,靠拢耳朵大声说话,他才能略微听得到。老人告诉我,前不久生了一场病,现在尚在恢复之中,不要紧的。他露出孩童般的微笑,眼眸中饱含着单纯的深邃和慈祥的澄明。而一旁的这棵茶花王,倒愈发地玲珑丰茂了。
茶花王, 是目前中国名头最响的一棵茶花。每年开花二十余批,每批千余朵,持续一百余天,故俗称“万朵山茶”。据和在瑞先生考证,这棵茶花始种于明末,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一个叫隆品的喇嘛将它从福国寺移栽到玉峰寺今天的位置。实际上这是两棵不同品种的茶花树合生而成的“合欢树”, 日久天长合二为一。经历代寺僧精心培育,树身奇异地呈现出蟠根苍润的画屏状,纷繁的枝条遒劲如龙,被匠心独运地编为一个大花房,冠幅达五十六平方米,花墙高三米多,两侧花墙长约三米,中间花盖面积近二十平方米。纷繁的枝头花开两种,一种是花有碗口大的“照殿红”,九丛蕊,并蒂而开,艳若玫瑰。另一种是单朵开放的“红花油茶”,花身略小,红似羊血。这两年,气候转暖,花比以前开得早,所以我们来的时候第一批茶花已经吐露绝代芳华,若是以前,这个时间花儿尚都是骨朵。走进花棚,见数十朵莹洁的红花挂在翠叶间,热烈而真淳,站在其间能仰天聆听到某种清凉的天意。叶腋里挺着大批丰满的花蕾,估计要不了多久,整棵树就将开成“红霞万朵百重衣”的花幄。
1994年,我在一篇短文中提到过那督老人,那年他七十六岁,转眼间,时光的恶之花已把他推向八十八岁。老人是附近的纳西人,自幼随做喇嘛的叔父出家。1961年后,喇嘛纷纷离寺还俗,他亦被迫离寺回到自己的村庄。文革开始后,破四旧风潮涌起,玉峰寺遭到严重破坏,“万朵山茶”也遭受损害。为了保护这棵珍宝级茶花,那督独自搬来砖头石块,将花树团团围住,然后日夜守护在一旁,饿了便以野果野菜山泉充饥。山下村民被他的坚贞打动,常偷偷送点干粮给他。此后的漫长岁月,那督一直厮守着这棵茶花,日日与之相伴,为其修枝、施肥、浇水,焚香默坐,静习佛典,成为一名为一棵树而活着的茶花僧。近年来,到玉峰寺看茶花王的人越来越多,只要见到有生人靠近茶花,那督老人都会善意地提醒不要去碰花朵,而对试图用手去触摸花朵的人,老人则会生气地加以呵斥。情到深处,可以通神,老人的一腔血脉早已融入这棵树中,他日羽化而去,精魄亦必将灌注于花树之中。民国时期,云南名士周钟岳深为玉龙大雪山浮在半空中天造地设的白雪震撼,认为山下当诞生有特立独行之士。他说对了,那督老人正是一位真正的特立独行之士。他那么大岁数了,身体又不好,却常年守护着一棵茶花。
茶花院的柱头,题有一幅对联:“花性即佛性乎?有机有缘有果;禅机乃天机也,无形无意无言。” 显然是有心人为那督老人而作的。这幅对联让我想起胡兰成有本书叫《禅是一枝花》,这五个字,倒和那督老人的一生很吻合。告别的时候,老人双手合十走到我跟前,深切地用纳西话缓慢地说:“不要牵挂我,不用担心,我很好,你们要珍爱自己,好好地活着。”他的话令我无限伤感,泪水已噙满了我的眼底,再不走就会滚滚落下。我低头离去的瞬间,老人那颗悲悯的菩提心,像一朵寂静的大茶花,刻骨铭心地映在我的灵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