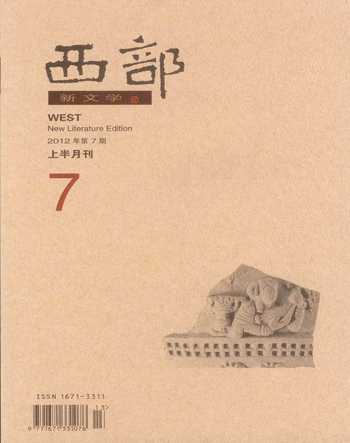是谁拨动了萨塔尔琴弦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走进新和
初春
该是诗歌发芽的时节。
2012年3月,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前往阿克苏地区新和县。
飞越天山山脉时,我从飞机的舷窗看到被白雪覆盖的连绵起伏的山脉,从未有过的一种震撼在心中油然而生。在群山间一块巨大的平川上,我依稀看到几片淡绿色的冰湖和弯弯曲曲的冰河,尽管我没有去过那里,但敢断定那就是巴音布鲁克草原和天鹅湖……
飞机冲破寒雾,渐渐降低了飞行高度,并最终降落在库车机场。我们踏上了这片龟兹故地,开始了在新和县的几日采风。
这是一个怎样的季节,让你在三月的原野看不出任何春天的动意,从天山山脉的各个谷口奔向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条条河流仍被封冻在河床里,分片散布的胡杨林依旧在冬眠的梦里打盹,可细细听来,它们又似乎是一群拥挤在巴扎的维吾尔人,又或是扎堆儿讲述他们的爷爷们曾经讲述的那些没有文字的传说,或眯缝着眼睛,斜望渐渐温暖的阳光,或选择了周五集体做晌礼,有的还暗自估摸自己是否虔诚……一个古老得让人无法揣摸的季节,一片水系纵横的神秘地方,由于水多而被维吾尔先民命名为托克苏的天堂。此时此刻,我只能透过即将更替的季节尘埃,看到一个个传说中几度夕阳残血的古老村落,古老村落里沸腾的生活,它们无序而又合情合理地分布在并不太大的新和县周边。
新和县塔什艾日克乡有个叫加依的古老村落,无论是过去或者现在,它都是个很有名的地方,似乎所有的传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圣人古墓旁的清真寺院子里,一根高高的旗杆上五星红旗微微飘动;八十多岁的老支书只记得他父亲那个时代有关都塔尔琴师的故事;还有现在的年轻艺人,他们已经懂得把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商标一样贴在亲手制作的乐器上,然后销往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噶尔等地,日出日落地数着家乡的每一天,把最浓最香的茶敬给老人们。于是所有的故事都从老人们开始。
没有文化的智者往往都是爷爷,这是加依村老少爷们儿给我留下的印象。说起加依村,无论那些纯爷们儿是否有文化,多数都能告诉你一个有关加依村的传说。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当一个青年人把这段传说讲完时,他也就成了下一代的爷爷了。这是一个长着雪白胡须的古老村落,几乎每个家庭都有那么一位白胡子老人。
很久以前,有五位维吾尔先知仰问真主,说:“万能的主啊,请告诉我们,哪里才是我们的葬身之所?”主回答说:“什么地方的水土能让你们的手杖发芽成林,那里便是你们的安息地。”一日,五位先知因路途疲惫,将手杖插在地上就酣然入睡了。次日清晨,他们醒来发现有四位的手杖已变成林木,其中三棵胡杨、一棵柳树,另有一位夜里不知去向。那四位先知甚为惊讶,齐声说这就是我们的“加依”。从此这里就被称为加依村了,意为家园或地方。
新和的大多数乡村都是以什么托格拉克(胡杨),或什么艾日克(水渠)命名的,可见这里水与树、自然与人的微妙关系。从加依村的许多白胡子老人的回忆中不难看出,三百多年前的先辈协合依拉力、协合比拉力兄弟挖渠引水,从此开始演绎加依村的历史。有历史的地方必然有人,有人的地方必然有琴,有琴的地方民歌、音乐就像春水一样维系着维吾尔人的生命。于是,一部部维吾尔人的历史就这样由歌舞和传说写成了。
在我看来,加依村就像一把萨塔尔琴,它的音色浑厚而绵长,穿透于历史和现实,它会告诉你不曾知晓的故事,因此想读懂维吾尔人的心酸史,首先得读懂萨塔尔。
萨塔尔是在演奏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中不可缺少的主奏乐器,它那浑厚而极具穿透力的音色会拉开一部浩瀚的历史大戏之序幕,还有缠绵于爱恨情仇的人生哲学。
诚然,爱是人生永恒的主题。历史的纠结也永远灭杀不了维吾尔人的爱,他们热爱自己,从贫困中解读自我;他们热爱大地,从大地的脉搏里感知温暖;他们热爱祖国,在辽阔的原野里守护着自信。他们更热爱生活,加依村的维吾尔民间乐器大王艾依提·依明和他现在的老婆,依旧用萨塔尔琴歌颂着爱和生活。
慈父早故的艾依提·依明说他从爷爷那里学会了制做乐器。那年头,一把好琴也不过卖个二三十元。七十年代的艾依提·伊明吃不饱肚子,后又被小队长以误工为借口扭断右臂,在无奈中他带着亲手制做的都塔尔琴游走四方,靠卖琴或琴艺为生。
在维吾尔人的传统中,艺人一向受人尊重,因此在外漂泊的岁月里,除了思乡之外,更多的体验就是自由与快乐,他的几度婚姻多少蕴含着维吾尔女性对音乐与歌舞的炽爱。
后来,艾依提·依明去了轮台。估计他能行走天下,与父亲是个鞋匠也有些关系。他在轮台替别人看护鱼塘,心烦意乱之时,他就拿起都塔尔纵情弹唱,先是俘虏了他现在的老丈人,之后,掠走了他女儿的魂魄,靠的就是都塔尔和木卡姆,那是一份久远的记忆,一份凄美的乡村爱情。
维吾尔女人多数都会成为音乐的人质,她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远嫁到陌生的土地,投入陌生人的怀抱,在音乐的幻想中品味人生的甘苦。艾依提·依明靠一把都塔尔点燃了多少姑娘心中的爱。
在加依村拜访的那几日,多数琴师和乐器制做师傅每每谈起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妻子都会自豪地说,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少钱或有多少文化,完全是因为对歌舞的痴爱,让她们选择了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对艺术的执着,使得加依村从全县最贫困的乡村,后来变为了一个有一百零一户民间乐器制做家庭的脱贫村,许多村民盖起了十分宽敞的房子。
几乎每个乐器专业户都有一到两间乐器陈列室。一间是成品房,里面大多陈列着都塔尔、弹拨尔、萨塔尔、热瓦甫、羊皮鼓和手鼓之类的乐器以及套装乐器艺术品。那些乐器装饰十分精美,特别是都塔尔、弹拨尔、萨塔尔、热瓦甫更是精美绝伦。听艾依提·伊明说,光是一把都塔尔上就得粘贴成百上千片装饰物。另一间是半成品,制做乐器则另有空间。
院落里总有一些牛羊或鸡鸭,它们早已习惯了那些经常光顾的陌生人怯生生的脚步,流露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斜眼瞅了瞅我们。春天来了,它们也早有准备,毛驴的冲动最为明显,或许它们是从主人那里学会了用歌声表达情感。在我的记忆里,很早就有南疆的维吾尔人经常骑驴行走天下的印象,热瓦甫是他们随身必带的伴侣。如今,那都是陈年旧事,加依村的维吾尔青年再也不用只身驴行天下。横亘在天地之间的天山山脉再也挡不住他们的歌声,他们只需坐在家里,那精妙的手艺和能够穿透心灵的歌声,自然会引来美貌女子落脚,引来无数游客驻足,就像蝴蝶无法抗拒鲜花的芬芳。然而,在维吾尔人的许多传说和想象中,散发芳香的鲜花永远都是女子,而男子则毫无疑问都是求爱的鸟儿。
高远的天空没有立柱支撑,
涛涛的江河之上没有桥梁,
这世界间万物可为我做证,
一生一世我只为你而痴狂。
……
这是维吾尔民歌中的一段歌词,立柱和桥梁与人的情感本无关系,但在民歌中却有着许多看似无关的类比。多少世纪以来,维吾尔人就是这样,在爱的选择中永远追求着一种坚贞。
加依村的老人们所能回忆起来的乐器宗师斯马义阿凡提,估计也应该是从他父辈或祖先那里学会了手艺和歌唱。建立在音乐和歌舞之上的爱让艾合提江·吾斯曼与情人星夜私奔;艾依提·依明和他年轻的老婆也曾在池塘边定下终身。然而最关键的是,在我看来,他们懂得为谁歌唱……
如果说弹奏都塔尔琴能够表达一份个人情感,那么萨塔尔琴的旋律里则回荡着历史的沧桑,相比个人情感,我更陶冶于岁月的涛声之中。
通古孜巴希的风
南疆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里的每座沙丘、每一棵胡杨、每一个古老村落,甚至每一棵小草或一朵开在红柳枝头上和荆棘上的野花,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方言,只是我们听不懂而已,然而我们却能从中感知千百年的岁月风沙。
位于新和县塔木托格拉克乡西南十公里的通古孜巴希古城,地处新和与沙雅两县交界的荒漠中,是当年龟兹军屯驻地,也是周边八座城堡之中心,故称“九城之首”。“通古孜巴希”在维吾尔语中的另外一个含义则是“野猪头”,或许那里曾经是野猪经常出没的地方。
之前我只是听说过托克苏(新和)有个叫通古孜巴希的地方。我从一些文章里看到音译的“通古孜巴希”被写成“通古孜巴什”,有的写成了“通古孜巴西”,我只是认为这样的音译不够精准,觉得把“什”或“西”改写成“希”更雅一些,更贴近些。历史上曾有许多西域地名或人名,可能是因为当时方言或读音的原因,多少有些偏差,不太准确,不少音译与现在仍在延用的名称不太接近,但那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了。古代地名或人名也是一种文物,我只是从个人的角度,认为写成“通古孜巴希”更合适一些。
从一公里之外,便可看到一座厚重的古城全景式的画面。三月之初的风还略带寒意,从北边硬生生地刮来,但已奈何不了渐渐消融的冻土。当我们带着初次涉足的喜悦走进古城时,古城的残垣断壁似乎已列队等候多时,宽有四米的土城墙虽已没有当年的雄伟之气,但它依旧像一位古稀老人,它坦露胸膛,破碎的袷袢在风中“啪啪”作响。老人吟诗一首:
若问苍天天亦老,
大漠孤烟风还啸。
岁月已去人不见,
唯我策马仰天笑。
桀骜不驯的大漠狂风驰骋在南疆大地,它侵蚀了多少历史的沧桑,抹平了多少远古的印迹,或许维吾尔乐器萨塔尔琴悠远哀长的音色就是模仿了风的原始音调。如今,古城内遍布的红柳,就像塔木托格拉克乡巴扎上拥挤的人群,不同的是巴扎上的人们涌动在现代生活的节奏里,把朴素而平淡的生活追求,实实在在地投入到巴扎的热闹与沸腾之中,而那些古城里有着庞大根系的红柳,仿佛古代曾身披铠甲的士卒,毅然守候在岁月的深远之处,任它千年风沙侵袭。它们一个个早已化作岁月的千年老翁,就像大画家哈孜·艾买提的宏幅巨作《木卡姆》里跪坐在画面正中的那位演奏萨塔尔琴的白胡子老人。
站在古城墙上,远望无边无际的原野,一片片古老村落向远处延伸出去,喋喋不休的麻雀们不时成群地飞过我们身边,然后消失在被风带起的灰尘之中。它们或许是去参加某个村落里正在举行的麦西莱甫。
都说家乡是戈壁
他们哪知是天堂
我们家乡的少女
不是白糖是冰糖
……
一段甜美的新和赛乃姆从远处传来,那清脆悠扬的萨塔尔琴不知被谁弹唱。是啊,这是一片美丽的家园,它辽阔无垠,是印象在荒漠与绿洲之上的天堂。
带着一份眷恋,我们从通古孜巴希回到了县城,去了新和县塔什艾日克乡,观看了民间艺人们的歌舞表演。乐手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也有一些是他们的徒弟。
我去过的地方很多,见过的所有艺人都那么朴实善良,痴迷于音乐歌舞。据乡里的领导介绍,自从国家开始启动非遗项目以来,这里凡被评为各级传承人的艺人们,每月多少能得到数百元的生活补贴。这些艺人大多没有文化,他们的本领都在口头上,能演唱很多祖辈世代口传下来的民歌,别看他们都上了年纪,记忆力却出奇的好。我曾遇见过一位牧民歌手,他能唱很多很多我从没有听过的民歌,所有的歌词都是靠记忆演唱,从不漏词或错唱。他说他能唱二百多首民歌,我问他有多少只羊,他说一百六十七只,可问起他的年龄时,他却不怎么知道,我问他因何如此,他说,年龄不会被人偷走。
塔什艾日克乡的几位白胡子、花胡子和没胡子的艺人大凡也是这样。萨塔尔琴师握弓的右手优美地左右摆动起来;弹拨尔手右手食指上的钢丝拨片飞快地在琴弦上弹奏;都它尔琴师激情似火;鼓手们则更是狂野地打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鼓点。于是白胡子老人们终于坐不住了,他们甩开苍劲有力的步子,震臂狂舞。之后就是几位中年舞者和美丽女子跳入舞蹈的海洋里。他们从不开口讨要报酬,只要上面有人组织,他们便兴高采烈地参加。那位八十多岁的白胡子光头老翁便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位。他现在还能跳一组完整的顶碗舞,舞姿飘逸不减当年,就像通古孜巴希的烈风。
我还会来
没有火的燃烧哪会有煮沸的铁锅,
这颗炽热的心哪能让恋人受折磨。
我说我并不爱,她朝我嘴唇走来,
我说我不理睬,她向我眼里飞来。
美丽的新和,美丽的托克苏,我初次向你走来,走进你的怀抱,又匆匆离开,我的心在沸腾,也无法拒绝你的爱。不必说你蔚蓝的天空,不必说辽阔的原野,不必说你悠久的历史文化,不必说你夏日里飘香的瓜果,也不必说你丰饶的水土,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现代化的美丽小县城、新兴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和令人惊叹的新农村建设,这一切无不让人感动和眷恋。怪不得这里的琴声是那么的动听,歌声是那么的柔美,因为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勤劳智慧、勇敢而善良,他们的胸怀又是那么的博大,能包容天地。实际上那位维吾尔老艺人的一曲并不地道的京剧已经告诉了我们,他们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他们是世代保护美丽家园、维护国家统一的维吾尔先民之后代,他们续写着这里的历史,他们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几天的采风活动中,我看到一张张灿烂的笑容绽开在乡村的庭院里、马路边或田间地头,激动时都想弹那么一曲赛乃姆,唱一段让人荡气回肠的木卡姆,再跳那么一段激情似火的顶碗舞……
这就是新和,初见一回便让你梦绕魂牵的托克苏:
你的话语如此动听,
就像春天里燕子在歌唱。
你的容貌冰清玉洁,
就像戈壁当空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