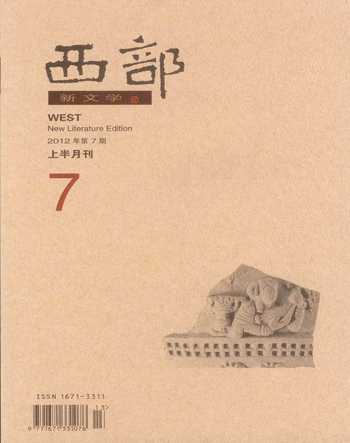托马斯的零零星星
1
与托马斯·温茨洛瓦的第一次相见,是在1996年首都国际机场,当时他五十九岁,我三十七岁。看到我手中的“Yale Tomas”字牌,身材高大但略微驼背的他径直走来,片刻的迟疑之后,我们还是西方礼节式地拥抱了一下。返程的车上,交流并不欢畅,大多为简短问答,只是当交谈的语言在不经意间由英语转为俄语之后,才有些滔滔不绝,但话题始终只有两个:北京和布罗茨基。前者是他此次旅游的主要对象,后者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唯一对象。
在以布罗茨基为题写作论文时,我先后给布罗茨基的多位友人和研究者去信,请教相关问题或寻求相关资料,最早给予回复的就是托马斯,他还同时寄来The Third Wave: Russian Literature in Emigration(《第三浪潮:俄国流亡文学》)一书,可谓雪中送炭。当时尚无互联网,中美间的通信来回一次就需一个月,可我们的书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居然往来了五六次,直到他出现在首都机场的出港口。
我们一起看北京的名胜。他手里始终捏着一张折成手掌大小的纸片,不时在上面记着什么,蝇头小字一会儿便黑压压地爬满一面,再有内容要记,他便将纸翻折过来,如此这般,那张纸便很快成了一幅语言六面画。在故宫和颐和园,他或俯身在膝盖上写,或趴在石墩上写,或干脆把纸贴在墙壁上站着写。“记录灵感?”看他写得入迷,我不禁问了一句。“也许。”他一边回答,一边下意识地将纸揣进口袋,神情似乎有点神秘,甚或羞怯。
当时的北京公交车太挤,出租车太贵,我于是建议托马斯骑自行车游览北京,他欣然应允。我借来一辆旧车,让他在院子里试骑,他迈上车,两手紧握车把,长长的双腿一直支撑着地面,等他慢镜头地把两脚放上脚蹬,竟如杂技演员般原地定车,纹丝不动,片刻之后,自行车又慢镜头地倒了下来,好在他及时松手,才避免与车一同栽倒。他小声嘀咕一句:“以前骑过的。”我宽慰他道:“中外自行车的结构和操作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于是,我们改骑三轮车。我当时拥有一辆小型轿式脚踏三轮车,是接送孩子用的。托马斯坐进狭窄的车斗,两边似乎没有任何多余空间。我们由劲松出发前往并不遥远的天坛,托马斯两手紧握车帮,背挺得笔直,兴奋得满脸是笑,周围的路人和骑车人见之,脸上纷纷露出更多的笑,像围观一只稀奇的外国猴子一般跟随我们前行。托马斯并无丝毫不适和不快,还不时腾出一只手来,向周围的观众挥手致意。
在长城,我们选择一个“景点”拍了一张合影。托马斯不爱照相,这是他北京之行中为数不多的留影之一。十年后的2002年,我在翻阅画册《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戈宝权》(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时惊讶地看到,托马斯的父亲阿纳塔斯·温茨洛瓦(Antanas Veclova, 1906—1971)1954年访华时与戈宝权先生在八达岭合影。他们选择的位置几乎与我们选定的不谋而合。我将那张旧照扫描后寄给托马斯,他称这是“历史的重叠”。
托马斯父亲的中国之行历时一月,收获甚丰,回国后出版了《中国行》(1955)一书。作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立陶宛诗人,作为当时立陶宛的教育部长和作协主席,他为在立陶宛宣传中国文学和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甚至在中苏关系恶化时期、苏联人都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避之唯恐不及之时,他仍发表了一篇关于鲁迅的长文。我们不难揣测,托马斯对于中国的强烈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源自他父亲的中国情结。
托马斯在《金藏羚羊奖受奖词》中回忆起他当年的中国之行:“大约四十年之后,1996年,我自己也首次造访中国,追寻我这几位先辈的足迹,我到了北京和上海,杭州和苏州,桂林和拉萨,还有其他许多地方。我后来把我的中国印象写在一部旅行笔记和一组由五首诗构成的组诗中。我在北京见到了高莽,他还清楚地记得我父亲。我还结识了刘文飞博士,甚至与他成了朋友,他精通俄国文学,是普希金、曼德尔施塔姆和布罗茨基的中译者,我俩的合作已持续多年,我将这一合作视为命运赐予的礼物。”见他将我俩的相识上升到“命运赐予的礼物”的高度,我诚惶诚恐,深感不妥,连忙去信建议他删去此句,没成想他却立即回信,严厉地提醒我作为译者不能删改他的文字。
托马斯在北京最想见的两个人,就是他父亲当年“感觉亲近”的两位俄国文学学者戈宝权和高莽先生。戈宝权先生当时病重,在南京住院,托马斯无法前去见他。戈宝权先生曾陪同托马斯的父亲访问中国,后又亲往立陶宛,受到托马斯的父亲的接待。据说,戈宝权曾为阿纳塔斯·温茨洛瓦的书作序,在如今维尔纽斯的阿塔纳斯·温茨洛瓦博物馆中,还保存着一部戈宝权访问立陶宛的记录影片。高莽先生当年是阿纳塔斯·温茨洛瓦作为其中成员之一的苏联作家学者代表团的翻译。我带托马斯去见高莽先生。两人见面,拘谨之中似乎也含有几分温情和激动。托马斯谈起父亲对高莽先生的记忆,谈起高莽先生曾为他父亲画像,高莽先生闻之,便又拿起画笔勾勒起他故友后人的轮廓来。
托马斯也像他父亲当年一样,走了中国的许多地方,甚至还到过西藏。托马斯的中国之行也很有意义,他写出一些诗文,更保存了一份情感。十几年过后,在耶鲁的一次圣诞聚会上,面对他的学生和友人,他又津津有味地回忆起他在中国的见闻,尤其是他的西藏之行。听众们似乎不如托马斯那般陶醉,看得出来,他们早已不是第一次听闻他的这些奇遇了。
托马斯中国之行于我而言的收获之一,便是托马斯为我的《诗歌漂流瓶——布罗茨基与俄语诗歌传统》(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所作的序言。他在序言的结尾将布罗茨基与中国联系起来,同时也给了我的处女作以很大的鼓励:
我感到高兴的是,布罗茨基的创作在中国也已为人所知了。我曾有幸与这位诗人交往多年,因此,我知道,他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怀有非常强烈的兴趣,这在他的诗作、首先是在《明代书信》中,就有清晰的体现。布罗茨基知道他的诗歌导师阿赫玛托娃所翻译过的屈原,知道并高度评价过杜甫和李白。在他生命的晚年,他曾想访问中国,但一场重病妨碍了他的成行。
刘文飞博士作为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一位俄国文化严谨、内行的研究者,出色地完成了这部对布罗茨基与俄国传统、首先是与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之诗歌的关系进行考察的著作。我相信,他的这本书将会赢得许多心怀感激的读者。
2
托马斯·温茨洛瓦1937年9月11日生于立陶宛克莱佩达市,先后就读于维尔纽斯大学和塔尔图大学,1977年因政治异见被迫流亡,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1980年起落脚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1985年在该系获博士学位,不久成为耶鲁终身教授,一直工作至今。
托马斯十六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维尔纽斯大学,是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生。可三年后的1956年,他却被校方勒令休学,因为他对当时苏联入侵匈牙利表示了抗议。布罗茨基曾写道:“当时,与匈牙利革命一同升起的种种希望被苏联坦克的履带碾碎,这些坦克镇压了起义。匈牙利起义之命运对于托马斯·温茨洛瓦(以及我本人)这一代、亦即1956年一代而言,其意义恰似十二月党人的失败之于普希金的同时代人,或西班牙共和国的灭亡之于温·休·奥登以及其1930年代的同辈们。它不仅塑造了这一代人的世界观,而且还导致了许多人的个人末世论。”“另一方面,这一代人却成了文学的意外收获,因为他们在开始生活时较少幻想,匈牙利悲剧成了他们的试金石。托马斯·温茨洛瓦在十九岁时便爱上了文学,文学于他而言成为存在的主要现实,稍后,又成为他的职业。”
托马斯的父亲阿塔纳斯·温茨洛瓦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还位居立陶宛共和国部长之高位。但托马斯并未因此而得益,因为据布罗茨基说:“儿子为父亲的选择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尤其在他的中小学时期。托马斯·温茨洛瓦的同学有相当一部分均认为他的父亲在将祖国出卖给外国势力,因此对这个男孩采取了相应的态度。阿塔纳斯·温茨洛瓦是立陶宛人民诗人、斯大林奖获得者,可是其名声无济于事,反而使儿子的处境更为复杂。此类情况要么会使一个人终生受伤,变成一个畸形生物,要么使他变得坚强。托马斯·温茨洛瓦就变得坚强了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母系亲戚的贵族血统和艺术影响。”托马斯似乎也从不因其高干子弟、名人之后的身份而得意,因为他公开选择了与其父服务的体制和文学决裂:1970年代,其诗集《语言的标记》的出版,被视为他与立陶宛官方文学、乃至整个苏联官方文学的分道扬镳;与此同时,他参与创建了立陶宛赫尔辛基人权观察小组,成为一位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家。
作为诗人的托马斯出名很早,像当年的许多地下诗人一样,甚至在其诗作、诗集公开发表之前即已是一位名诗人。他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长期生活,认识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曾把两位大诗人的作品译成立陶宛语。通过阿赫玛托娃,他又与布罗茨基等阿赫玛托娃的“孩子们”密切交往,被视为继承“白银时代”传统的“彼得堡诗派”的成员之一。
托马斯的英文版诗集《冬日的交谈》(Winter Dialogue)面世时,布罗茨基为之作序,序言题为《诗歌是抗拒现实的一种方式》(Poetry as a Form of Resistance to Reality),这是其中的几段:
人们只需匆匆浏览一下托马斯·温茨洛瓦的诗,便可发现一些在同类出版物中日渐稀少的成分,首先是格律和韵脚,即赋予诗歌表述以形式的东西。温茨洛瓦是一位具有高度形式感的诗人,因此,那些吃着低卡路里自由诗食品成长起来的现代读者,或许会将他与传统之消极面联系在一起。但是,形式感和传统性并非一回事。一位诗人之所以显得传统(就“传统”一词的消极意义而言,但并非仅就这一意义而言),其原因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只要读一读温茨洛瓦的数行诗便足以明白,他是一位地道的二十世纪诗人。
立陶宛语、波兰语和俄语都是托马斯·温茨洛瓦的母语。此外,他还出色地掌握了英语和拉丁语,法语、德语、希腊语和意大利语对他而言亦非外语。由于立陶宛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原因而同时拥有三种母语,这可以用来解释这位诗人的宗谱以及他所继承的遗产之规模。温茨洛瓦是三种文学的儿子,而且是一位心怀感恩之心的儿子。
当然,他首先是一位立陶宛诗人,但他却是一位汲取了两大邻国一切最佳养分的诗人。而俄国最好的东西就是语言和文学,其中也包括其诗歌。我觉得波兰恐怕亦如此。整体而言,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能配得上其语言和文学。不过,温茨洛瓦却并非波兰诗歌和俄国诗歌之影响的结果,更确切地说,他是两者相互融合的产物。
每位大诗人都拥有一片独特的内心风景,他意识中的声音或曰无意识中的声音,就冲着这片风景发出。对于米沃什而言,这便是立陶宛的湖泊和华沙的废墟;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而言,这便是长有稠李树的莫斯科庭院;对于奥登而言,这便是工业化的英格兰中部;对于曼德尔施塔姆而言,则是因圣彼得堡建筑而想象出的希腊、罗马、埃及式回廊和圆柱。温茨洛瓦也有这样一片风景。他是一位生长于波罗的海岸边的北方诗人,他的风景就是波罗的海的冬季景色,一片以潮湿、多云的色调为主的单色风景,高空的光亮被压缩成了黑暗。读着他的诗,我们能在这片风景中发现我们自己。
西方人在生活中喜欢以名字相称,但学术著作中却大多只标明姓氏,托马斯的“T. Venclova”之署名也常引起误解,因为在多种斯拉夫语言中,以va结尾的姓氏会被理解为女性。托马斯的名字曾被汉译为“温克洛娃”,我将此事转告托马斯,他颇为坦然,并说在欧美已有过此类遭遇。记得叶廷芳先生也有过相似体验,一次在石家庄开会,一位主持会议的出版社女领导在介绍来宾时高声念道:“叶廷芳女士。”叶廷芳先生只好站起身来,在大家的掌声中,介绍者和被介绍者一时都有些脸红。
我与托马斯商量如何将其姓名更准确地译成汉语,“温克洛瓦”,“文茨洛瓦”,“温茨洛瓦”,他认真听着其姓名在汉语里的不同发音甚至不同含义,最后选中了后者。后者的发音近似其姓氏的俄语发音,与英文发音差异较大,但我猜想,托马斯是想让自己姓名的汉语发音更接近立陶宛语。
此次邀请托马斯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邀请方需他提供护照扫描件,托马斯当时在格陵兰岛旅行,他夫人在家操办,先是寄来一份美国护照,第二天又心急火燎地寄来一份立陶宛护照,要我们一定按照立陶宛护照上的信息为他购票,并说这是托马斯的意思,千万不能搞混。我明白托马斯的意思,具有双重国籍的他,此次拿定主意要以一名立陶宛诗人、而非一位美国教授的身份出现在中国。
3
1977年3月,托马斯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在《伯克利之春》(Spring in Berkely)一文中,他深情地回忆起初到美国、初到伯克利的见闻和感受,回忆了他与米沃什的交往,正是后者邀他去伯克利任教的:
那时,我已经几乎只读禁书,自然地,自己的文字也多少游离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结果可想而知:我的作品被禁止发表,我与当局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一直留意立陶宛、尤其是维尔纽斯动向的米沃什,发现了我的困境。他甚至翻译了我的一首诗,并将其发表在著名的侨民杂志《文化》上。当我的祖国的情况最终让人忍无可忍,也正是他邀请我去他所在的那所美国大学教书。刚开始,苏联当局不打算放行。米沃什给我打了电话,还写了一封信:有理由相信,当西方表现出对异己分子的兴趣,这就给了他们帕斯捷尔纳克所言的“安全证书”(尽管不完全可靠,通常只抵得住一阵子)。
尽管此前我只见过米沃什的照片而非他本人,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当他沿着花园的铺砖小径走向我。他六十五岁高龄,却显得十分年轻:颀长而健壮,风趣而儒雅,略高于常人,浓眉之下是一双严峻的眼睛,好在严厉的目光终有迷人的微笑来补偿。那天以前,我只见过一位年近七旬却跟米沃什一样不显老的人,即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顺便说一句,他们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相似,不仅在外表,更在行为方式。
伯克利的山丘与维尔纽斯的山丘很相像,尽管从伯克利的山丘上可以望见极好的海景,而立陶宛的首都是个内陆城市。米沃什的房屋建在一座高高的斜坡之上,下面就是大学校园,要欣赏学校全景,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我越来越习惯到米沃什家去,甚至还会在他家的小阁楼里过夜。就是在这阁楼里,米沃什曾为我诵读他的诗作《魔山》(“我记不清布德伯格死于何时,不是两年就是三年以前。/陈也如此。不是去年就是前年/……十月酷热,七月流火,二月枝繁叶茂。/此处蜂鸟的婚战不预言春天。/唯有忠实的枫树,年年落下它的叶子。/没有理由,自古如此。”)
我仍然常与米沃什碰面,先在相似的情境,后又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有时在美国,有时在波兰,或者甚至在维尔纽斯。即使现在,我也不时感觉到他就在我的眼前。单缘此故我便足以宣布,我的生活是幸福的。而这幸福生活的源头就是伯克利,是那座望得见大桥与千帆的山间别墅,是那幢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房屋,它最吻合米沃什的这句话:它“次序井然,其内部的存在将永远存在”。
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托马斯写道,布罗茨基是“让米沃什真正感到亲近的唯一俄语诗人”,反过来,布罗茨基也曾说:“米沃什是我认识的最有造诣的人。”米沃什、布罗茨基和温茨洛瓦,这三位分别来自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的诗人,似乎构成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东欧、乃至整个世界诗歌中一辆醒目的“三驾马车”。前两位诗人分别于1980、1987年获得诺贝尔奖,人们普遍认为,托马斯·温茨洛瓦作为布罗茨基所言的俄、波、立“三种文学之子”,作为波罗的海地区文学的代表,也有可能获诺贝尔奖。我曾与托马斯谈及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并不太“谦虚”:“我入围很多次了。”一副胸有成竹、甚至志在必得的架势。
1990年,托马斯在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接受布罗茨基研究者、英国基尔大学教授瓦连金娜·波鲁希娜的采访,集中表达了他对布罗茨基及其诗歌的认识,他在访谈中说了这么几段话:
我认为我们两人很少共同之处,如果不考虑一些趣味方面的吻合;在诗歌中的确有我们两人都着迷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有我们两人都排斥的东西。或许可以说,在布罗茨基那里能学到的东西,就是清醒、尊严、对词本身的尊重以及这样一种意识,即必须为词支付现金,也就是全部的生平,全部的生活。还有这样一种理解,即诗是与前人的交谈,以前人的参与为前提。不过,一切真正的诗歌,无论用哪种语言写成,都会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尽管我这一代人主要是从布罗茨基那里再度学到这一切的。布罗茨基巨人般的语言和文化视野,他的句法和思想,能够超越诗节的限制,使人们对其诗歌的阅读成为一种灵魂的锻炼:这种阅读能扩大人的灵魂容量,大约就像跑步或划船能够增强人的肺活量那样。
布罗茨基的诗学是阿克梅派诗人语义诗学的继续和发展,或者说是“超发展”。
如今布罗茨基具有一种中立的“无光泽”调性,它与无比充盈的语义和句法相互结合,与复杂的节奏相互结合,他的素材也十分多样。天下皆冷漠的感觉有所增强;这种感觉始终存在,却从未表现得如此清晰,比如《鹰的秋鸣》一诗。这种感觉腐蚀着布罗茨基的诗歌和他的作者个性,就像酸腐蚀金属;但奇怪的是,无论是他的诗歌还是他的个性,却都未被摧毁,依然保持完整,这大约是上帝本人的意愿。
于是,这篇访谈也就被编者加上了《语义诗学的发展》这样一个标题。
作为诗人的托马斯,显得过于理性。他曾在塔尔图大学师从著名符号学家洛特曼,之后长期从事符号学、尤其是符号诗学的研究。初到伯克利,他开设的课程就是符号诗学,他还与同样任教于伯克利的波兰裔逻辑学大师塔斯基多有切磋。无论生活中还是课堂上,他都是一副标准的教授派头,没有诗人常有的热情洋溢,或多愁善感。布罗茨基的好友之一、美国达特默斯学院教授列夫·洛谢夫去世当晚,托马斯给我发来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
Dear Wenfei,
As you may already know, Lev Loseff has died. What a pity!
Tomas
(亲爱的文飞:
你或许已经得知,列夫·洛谢夫去世了。太可惜了!
托马斯)
即便在传递噩耗时,托马斯也是节制和理性的。
托马斯的正式身份是美国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诗人不是他严格意义上的“职业”。耶鲁斯拉夫系是美国最早设立的斯拉夫学研究专业之一,由“美国比较文学之父”勒内·韦勒克教授于1946年创建。该系现有五名教授,托马斯为其中之一。这位学者诗人在写诗的同时,也有许多学术论文和著作面世,除《冬日的交谈》(1997)和《交叉路口》(2003)等诗集外,他在耶鲁还写作了文集《希望的形式》(1999)、《布罗茨基论集》( 2005)和《维尔纽斯人物志》(2006),目前他正在写作专著《维尔纽斯文化史》和《约瑟夫·布罗茨基的生活和艺术》。
耶鲁斯拉夫系坐落在校园核心区的研究生楼里,教职工们的办公室占据了研究生楼一侧的两层,窗外的狭小庭院里铺满青藤,室内的走廊低矮而又弯曲,房间很小,光线也暗,哥特式小窗上还装有铸铁窗栅,这一切都使得斯拉夫系看上去像是一座修道院。这里的教师在耶鲁深厚的学术传统上添砖加瓦,这里的学子也在美丽的校园里生生不息,就像赭红色的仿古建筑和石壁上的常春藤所构成的对比和呼应,既传统又灵动,既古朴又青春。
去年,我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在耶鲁斯拉夫系访学一年,托马斯是我的“合作导师”。我到系里报到时,请系秘书Dorothy给托马斯打电话通报我的抵达,谁知他几秒钟后便出现在我面前,原来,他的办公室就在系办公室的隔壁。我们相互拥抱,然后坐进他的办公室。十平米左右的小屋,低矮阴暗,两排书架依墙而立,两个皮沙发分列在一个古老的椭圆形木桌的两边,黑色铸铁窗栅上挂着绿色的青藤。寒暄之后,我说这里很像牛津大学,他说:“是的,耶鲁是牛津的翻版。”沉默片刻,他又说道:“别尔别罗娃在这里工作过。”他提到的别尔别罗娃(1901—1993)是一位俄国侨民作家,她似乎与我和托马斯的研究都关联不大。谈话就这样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但托马斯显然是兴奋甚至激动的。在耶鲁一年间,我不止一次目睹托马斯在兴奋和激动时的寡言,或曰话语的不连贯性和思维的跳跃性。
在耶鲁斯拉夫系的开学典礼上,就在师生们在一间巨大的橡木大厅里相互举杯致意、窃窃私语的时候,托马斯突然用一把叉子使劲敲打香槟酒瓶,换来一片寂静,然后郑重把我介绍给全系师生,说了大堆的好话,最后的结尾一字一顿:“刘文飞教授是普希金、曼德尔施塔姆和布罗茨基的中译者。”托马斯显然想用我的这一“身份”来打动他的同事,我却感觉到,这可能才是我在他心目中最有价值的“身份”。
托马斯在耶鲁斯拉夫系的处境似乎也有些尴尬:首先,他毕竟主要是一位诗人而非学者,虽然美国的当代诗歌大多退缩进了大学校园,但教授的职业还是会要求更多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其次,他所属的立陶宛文学和文化并不属于斯拉夫学的研究范畴;再次,与米沃什和布罗茨基等流亡诗人迅速融入美国主流文学的取向不同,托马斯似乎始终有意对英语和美国文化保持着某种距离感;最后,由于年事已高,托马斯目前每年只在耶鲁工作半年,他们因此卖掉了耶鲁的居所,在耶鲁工作期间则租住公寓,托马斯夫人塔尼娅在谈及他们夫妇的生活状况时说:“我们是耶鲁的吉普赛人。”
4
托马斯在北京时,提出要给夫人买一块中国的玉石。我们一起去友谊商店,他相中了一块绿色翡翠项坠。他向售货员提出一大堆问题,我当翻译。友谊商店的女售货员看来见多识广,发现我们说的是俄语,便小声地对我说:“让他换一块吧,这块贵,不值。”不知那位售货员对俄国人有好感,还是认为俄国人没钱,总之是满怀善意的。但我在耶鲁一直没见塔尼娅戴那块项坠。
在耶鲁过新年时,塔尼娅曾告诉我,她年轻时,托马斯和布罗茨基曾同时追求她,她后来选择了托马斯。塔尼娅非常想来中国,可是此次,她却因为膝伤而无法前来,她在给我的信中对此懊恼不已。
在耶鲁过中秋,托马斯夫妇应邀来我的居所做客。塔尼娅快人快语,东长西短,托马斯却沉默寡言,若有所思。只是在不顾塔尼娅的一再劝阻喝下几杯酒后,他才又不紧不慢地聊起往事,引得陪他前来的几位研究生竖起了耳朵。临行时,托马斯悄悄走到我身边,塞给我一个小铁盒,小声说了一句:“中秋节快乐!”那神情似乎在背着他夫人和其他人。这是一盒香港产的月饼,盒中只有一块月饼,铁皮盒上绘有一位仕女,像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上的装扮。
为迎接托马斯访华,我在高兴兄的协助和督促下为《世界文学》编译一组稿件,组成“托马斯·温茨洛瓦小辑”。这是托马斯·温茨洛瓦第三次出现在《世界文学》上。
1998年第四期《世界文学》上,刊发了我翻译的托马斯的一篇论文,题目是《茨维塔耶娃的〈山之诗〉、〈终结之诗〉与〈旧约〉、〈新约〉》。托马斯在文中将茨维塔耶娃的两部长诗与《新约》和《旧约》进行对比,深入分析了茨维塔耶娃长诗中的宗教和文化内涵。
2004年第三期《世界文学》上,我将托马斯·温茨洛瓦和叶夫盖尼·莱茵、列夫·洛谢夫的诗各选几首译出,以《“布罗茨基诗群”三诗人诗选》为总题刊出。其中有托马斯写于1995年的《多年之后在迦太基》一诗,此诗是献给布罗茨基的,这是该诗的最后一节:
仅此而已。爬满那扇窗户的
是坚硬的常春藤,
闪亮的树枝在严寒中抽打玻璃,
晚霞渐渐地隐身,
让那声作为徒劳之后记的叹息
不要再属于我们,
让它属于底片的白影和诗中的黑暗,
让它属于诸神。
托马斯1996年来华时,应邀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做了一场关于布罗茨基的学术讲座。此次来京,我和高兴兄计划邀他再访外文所,我们可以递上新出的《世界文学》,那上面有他的作品小辑,我们还可以听他朗诵自己的诗歌。他可能会选择用立陶宛语。
5
在不久前举行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新闻发布会”上,立陶宛驻华大使丽娜·安塔纳维切涅女士说:“托马斯·温茨洛瓦是当今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作为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金藏羚羊奖”得主,托马斯·温茨洛瓦将于近期访华。立陶宛驻华使馆参赞尤拉特·拉莫什凯女士发来电子邮件,与我商量如何接待托马斯访华,我请她为托马斯预定酒店,而我负责去机场接站。这一次,在川流不息的出港人流中,我一定能老远就看见托马斯略微驼背的身影,较之于十五年前,他的驼背会更为显眼了。
2011年7月6日于北京
栏目责编:舒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