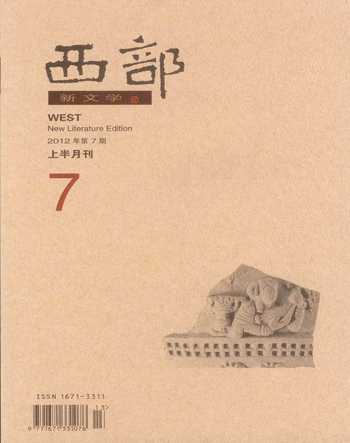缅怀的时代:憧憬,还是幻象?
陈维果
庄严的墓碑就在眼前,
它遮住了人类
归途之入口。
星辰在我们头顶沉默,
坟墓在我们脚下无声。
——歌德:《石匠的小屋》(郭凤彩译)
缅怀与记忆是人类的普遍性精神活动。在人类的精神中缅怀与记忆标定了我们情感的历史性拯救:缅怀,是对逝去的历史的一份尊重与温情,藉此获得现实生存的合理性。过去是用来缅怀的。缅怀也是一种祈祷与招魂,为拥有的灵魂祈祷,藉此去拯救我们自己的灵魂。记忆是个人与群体的历史任务,将人类个体或种群的已发生行为从注定要被遗忘的虚空中拯救出来,使之继续存在。记忆也创造了这个存在,复活了这个存在,人类的片断历史延伸了,易朽的人与事在永恒的自然中找到了位置。任何存在过的事物消失时,我们总要诘问消失的意义,因为任何一种消失都是我们完整性的一份丧失,而缅怀与记忆就是一种补偿的努力,甚至是加倍补偿的企图。
每一个亡灵,总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回来的。“清明时节雨纷纷”,每当这个用来缅怀的节日到来的时候,我们都在恍惚间重复梦忆,拾起片片记忆的碎片。如果说个人是历史的人质,在对逝去的伟人招魂时,我们何尝不是对一个更宏大的范畴(如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思考,并指向一个现实的维度:维护与建设。
一
为什么缅怀?拯救的努力。
在屈原、海子等诗人那里,死亡不仅仅是人类旅程的终点,不仅仅是把我们渡到忘川之舟,在他们那里这是永恒的拥有,更是神性智慧莅临的必然目标。于是,把生命归还死亡,实现了生与死的意义交换。生与死是所有诗人们的文学主线:生是定义,死是想象。生命是可以定义的现实,如用诗歌命名世界,为了把这一现实以“实证主义”的价值来体现,就需对死亡展开持续的幻想。宗教的公理就在于因来世与天堂的想象获得在世的意义,用死亡来管理现实。国家也一样,通过对人世俗生命的暴力管理和对人精神生命的思想管理,来实现政权与权力。不可及的政治理想如同宗教对来世生命的幻想。国家政治是在对现世本身的想象与来世生命的想象性中成长起来的。幻想的深度决定了现实意义的深度。如此,让·波德里亚说:“真实的死亡事件属于想象的范畴。”
清明节的缅怀,就是一个“想象的范畴”。人们在仪式和节日的庇护下与他们的死人共同生活,我们以忧郁与哀情的形式与我们的死人交换意义。
如苏格拉底所言,哲学是死亡的练习。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与哲学家们孜孜不倦地对死亡的命题进行神秘的打量和眷恋,以哲学和文学的名义,借亡灵的启示,向人类发出求援的呼吁:是拯救的时候了!
为什么每一代诗人们都在叫嚷拯救?迷失是每一个时代永恒的文化主题,精神的迷失已是基督诞生以来人类的一种精神存在,背负与遗忘是人的自然禀性。工业革命以来,文化的迷失被逐渐强化为一种时代特征,丧失与疲乏是人的时代属性。
当然,让我们迷失伟大传统,也与人们所处的接受、学习传统的谬误形态有关,我们对传统的学习多是基于“解读”模式的接受,我们对于传统的谬误状态是:不相信自己的心智能与古人同步感受;不相信古人是在为我们代言,古人的语言就是我们的语言;不相信自己的文字常识、语言常识、写作常识和阅读理解常识;不相信自己直接观察到的古代经典中的白纸黑字与直接观察到的山河大地之间必然存在的启示。结果我们在开始解释传统与经典之前就已经选择了怀疑、猜测、争议、批判。
更深层次的是,现代性割断了我们历史的连续性,我们传统的断裂已经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了,这不是任何人选择的结果,也不会因任何行动而改变,而标志了现代与二十世纪的分野。记忆的丧失是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忘却甚至发生在被视为经典与传统的继承人身上,也降临在见证者与当事人身上。与背负、遗忘、丧失和疲乏斗争的拯救,就是招魂并缅怀。
到哪儿去了,那种幻象的微光?
现在在哪儿,那种荣耀和梦想?
华兹华斯询问人类的童年,对人类与神性临近感消失的缅怀与招魂,打量了我们的拯救意向。但,我们能否救出我们的缅怀?从渺茫的空间黑箱中,从虚度的时间之河中,捞获光荣的片段。
招魂,即寻找伟大灵魂的回家之路。正如哈代所言,呼唤与被呼唤相呼应,如此,伟大的灵魂有了回家的路。每一个伟大的灵魂都在等待呼唤,每一个现实的生命都在渴望佑护。在这里,生与死契合在一起,不分彼此,生的勇气与死的意义等同了。但一个更为痛苦的招魂,不是生对死的指引,而是生对生的渴望,死者对生者的超度。屈原的《招魂》为我们“自招其魂”提供了一个原型:“目极千里兮,伤心悲。魂兮归来,哀江南。”当今,我们身体在一边,灵魂在另一边,魂兮归来,更多的是我们现实中的人对魂物一体的渴望、精神皈依的渴望。这已成了中国古典文学伤春传统的滥觞。魂不附体的现代人,没有了回家的路,因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更广的意义上,是因为尼采的“上帝死了”。
缅怀,也是为了救援自己的心灵。我们内心深处久已的冷漠、荒芜、封闭、空白、黑暗,要用过去的光荣来获得照亮与开启。“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灿烂的往事,光荣的古典,升腾、缭绕在我们面前。从时间之河打捞起来的光荣片断,抚摸着我们,从历史中重新获得立身为人的荣光与温情。
“解释历史就是描述在伟大时代表现出来的人类的激情、天才和活生生的力量。”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如是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历史学”的起点,就是以缅怀形式书写、描述在伟大时代表现出来的人类的激情、天才和活生生的力量的历史。缅怀是拯救自己的心灵,那么,历史就是自己合理性的存在证明,就是自己的心灵拯救形式。一切历史都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缅怀正是这个思想意识的基础和重要表现形态。对过去的缅怀比对未来的洞察,对人们的吸引力大得多,正是未来把人们的心灵送回到过去,直至最初的原始、最遥远的古代。
清明的意义,有关心灵的拯救,有关历史的述说,而这个述说是指向当代、指向传统的维护与建设,载体就是缅怀。就大众而言,是对自己的家族、先辈的缅怀,对群体而言,是关乎民族、国家的历史态度。但,在温情与敬意的背后,都是对自己现实存在的唤救、求援。
二
如何缅怀?颤栗性的敬畏与信仰。
清明的祭祀,无疑是最显性的缅怀。中国自秦汉以降形成了视死如生的观念,即认为去世的人只是离开了人间,却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着,坟墓就是他们的居所,他们离不开子孙亲友的供养,在此前提下他们才能庇佑人间的亲人,给亲人带来福祉。要与死者做近距离对话,就要整修维护其居所,就要去扫墓并祭祖。趁此机会,祈求庇佑,经过一个冬天的冰霜风雪后,祈求给新一年带来希望。
坟墓,仅是逝者的物理居所吗?是躯体的存放地吗?它更是一个象征,一个灵魂居地的象征,一个精神场所。当人一旦死亡,他与他的群体就失去了物理联系与循环,他就要被删除,于是,被放逐于墓地,这个场地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地。找不到这样的场所意味着什么?如果墓地不存在了,那是因为现代城市与农村在整体上承担着墓地的功能:人类生活的现代城乡是死亡之域。功能不能区分,是因为被社会平均化了。如同世界上没有学校了,是因为教育的每一个环节都被全社会的所有生活浸透,独立的学校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清明的扫墓,就是一年一度的功能整理,整理生命与死亡的关系,死亡被收敛为死后的生存,生命被放大为预备死亡。
缅怀,是一种传导,借此,我们获得了与我们过去的对话与凝视。但现代人的祭祀,置自我拯救与表现于第一位,借古人索取自己的东西,没有自己的灵魂安慰,没有信仰基础上的缅怀,渲染与极度的表现,把历史用来撒娇,泛情与媚俗。现今公祭盛行的清明,更像是一个表演场,行政首长们好像是巫师,获得了通灵的技能,祭文如咒语。他们要什么样的清明?一是大众面前表现的“孝”评,二是神灵庇护的“顺”道。
丧失了原气的招魂,是一种掠夺与篡改,更像是劫持,有如过度开发资源造成的生态破坏。
爱默生曾奉劝每一位读者:“不做自己,而做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不做一个灵魂,而做一名基督徒;不做一名博物学家,而做一名笛卡尔主义者;不做诗人,而做一名莎士比亚崇拜者。”人类伟大的激情,是以每一个人的亲历与实践而获得传布的。回到原点,吸取雨露,以身体之,以生验之。以个人创造性的心灵体验与伟大的传统对接,“顺应内心的召唤,你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天才”。
其实,在历史的世界里,我们的生命是活生生地相互交织在一些的,我们的所有感觉与理性,都是历史方向的部分。如果说历史是“运动”,人的个体、群体、民族、国家就是“运动对象”,即运动质点。没有运动质点,就没有“历史”这个运动状态的描述。那么,我们努力缅怀的过去经典,是生息、传递于我们个体的呼吸中、我们群体的生活中、我们民族的符号中、我们国家的制度中,而不是一些独立形式的表现,也不是一些凝固存在的过去。缅怀传统,需要我们将其内在于自我心灵、民族灵魂、国家建设,信仰并虔敬于日常、平常、经常的事务与生活中,我们要的是历史现象与我们的日常现象、生命本身之间的象征及意义交换,不需刻意,不要骇世,如一蔬一饭、一呼一吸、一生一世。
缅怀,是要从历史中“把世界中的实在、爱、意义、精神价值等等转换为抽象概念的逻辑结构和形而上学本质的类似物,并把这种转换视为精神的最大幸福;将逻辑思维及其颤栗性的敬畏关系与诸事物的根据充分连结起来”。(西梅尔:《论个体与社会的诸形式》
颤栗性的敬畏关系是人与自然,更是人类的宗教信仰。我们如何拯救出我们的缅怀,虔敬我们的历史,建设我们的信仰情愫?没有信仰情愫的缅怀,不会实现两个方向的充分连结:水平方向,“向后”的过去与“向前”的未来;垂直方向,脚下的亡灵与头顶上的神灵。问题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缅怀都是水平方向的,缺失垂直方向的连结。没有敬畏意识,没有信仰维度,如何丰满我们的缅怀?
一切关联的事物都是相互想象的冲突与和解,灵魂是肉体的想象。肉体的劳动属性是马克思定义的“我生产,故我在”;灵魂的想象属性有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生命的内涵在于:人的灵魂的唯心主义与人的肉体的唯物主义不断进行的意义交换。
三
一个国家如何记忆?历史肌理的建构。
缅怀,就是保护记忆。记忆是一种个人属性,一群人共同的记忆,就是一种意识,进而拥有了“国家记忆”、“民族记忆”之说。记忆是人的一种最深层次的身份认可。借清明节气泛起的认祖与民族文化、国家意识之热情,亦如此。
“国家是处于停顿状态的历史,历史是运动状态的国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战后,一个德国中学数学教师,斯宾格勒,“躲进小楼成一统”写了一部思想巨著《西方的没落》。他用动力学来解释国家与历史,他的意思是,国家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相对静止时,才能被观测描述,历史是一个过程,处在这个过程中的是国家的变化与运动。对历史过程中国家的观测描述,其实就是对国家记忆的一份记录。
国家记忆,这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个问题不单单是理论,也不仅仅是以历史文本格式的记录、写作、出版,而已放在了一个物质层面上了,如建中国“圣城”、“中华伟人堂”、“中华文化标志城”、“重建园明圆”之风愈来愈烈。
重炼一个想象的历史肌理,定义一个政治文化符号,以丰富中国的文化形象,这是我们当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任何一个城市、乡镇的建设中,设计师们最迫切的就是寻找当地的历史线索,哪怕是蛛丝马迹,也被放大并物化为一个凝固的纪念,甚至可以用想象来代替求证,撰传历史记录与传说,也要塑造这个历史肌理。于是,一座座“古人”雕塑、一排排仿古建筑屹立城乡,在这种场景中,使人油然而生一种无知的黑暗感与幽默感:这是历史的忧伤岁月,还是忧伤的人类对历史的怀想与纪念?这不是历史的具象,它们娇情、媚俗、乔装,这是以文化的名义意淫历史。
与其如此,不如以废墟、残垣断壁,甚至空白的消失地作为一种气氛、一个空间,来沉思时间的流逝,来激发内在的想象。用反思代替静态的重建,将个人的时间置于历史的时间之中,做一个时间的享受者,延续状态的享受者,从感性上享受时间的肌质,享受纳博科夫“说吧,记忆”的恬静。
记忆,不仅仅是空间的位移,空间仅是我们外在经验的形式,时间才是我们内在经验的形成,外在经验与内在经验没有意义交换,就不是历史的记忆。
恩格斯讲过:现在谁也做不出来希腊的青铜雕像。因为做的人没有希腊时候的人的精神了。你可以拥有更好的技术、更多的物质资源,但是整个历史变了,你思想的丰度,被压缩了,你思想的纯度,被污染了。你做出来的青铜雕像,根本是魂不附体的。
魂不附体的复制存在,不如忽略一个物质的世界,而去丰富一个想象的精神世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思想去抽象灿烂的文化精神,而不要仅用我们的视觉去具象一个幻象中的文化复兴。在没有了传统灵魂的当代去制造传统,这有如一个萎缩时代的血脉扩张。
缺失,我们可以忧郁地回望;丢失,我们不可垂死地挣扎。
捍卫我们的国家记忆,需要我们的理性建设,抽象出历史中形而上的逻辑与秩序,在此基础上,培育我们“建构的想象力”。以想象力获得国家记忆的感知力与创造力,对生动而复杂的历史生活世界进行建构,更是对人类生命的深度发现,对我们过去与未来美好生活世界与美好人性生活的创造性解释。丰富我们的想象力必须是全面的思想与艺术创造,既要能想象我们记忆中光明美好的生活,又要能想象国家记忆中黑暗苦难的生活。国家的黑暗岁月也是国家记忆中的宝贵财富。一个国家的记忆不仅仅要追忆一个消失的伊甸园、一个温馨的回声,也要追忆牺牲与苦难之地,追忆留在历史长河中的呻吟与哀号。过去的失败与胜利、耻辱与荣光,具有一样的感召能力。因为,这个往昔事件的集体属性,不可分割,不可选择。
捍卫我们的记忆,需要从遗忘中拯救、打捞,记忆是与历史的交换,这与我们的步调有关。昆德拉叹息道:“徐缓的程度和记忆的强度成直接正比;速度的程度和忘记的强度成正比。”快与遗忘使人失去自我,对于当下的时代,“你是旋转,我是迷失”,只在慢与记忆中的人才能回视存在,为存在去蔽,敞亮存在的本真状态。我们丧失了缓慢的优雅,也必然丧失深刻的记忆。如果要建构我们的历史肌理,需审视我们的现代性诱惑。现代性不断给我们带来剧变,并把越来越多的精神焦虑,植入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危机与困惑浸渍文学、艺术、思想。
那么,捍卫记忆,需要我们从今天眩目的快速变化中,从概念丛生的不断呈现中,明晓自己的灿烂方向,重新创造一些越来越紧密的核心,为此,浓缩、省略、简洁、坚定、单纯自己的理念与思想。
四
伟大的灵魂何在?爱与美的不朽。
狄更斯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更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旧的神祗纷纷离场了,新的上帝还没有到来。
“留给我们的珍宝(遗产)没有任何遗言。”法国诗人勒内·夏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面对战争打乱了已有世界理性的秩序与思考,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但,勒内·夏尔这句话还没有简单到就仅是针对战争改变了理性的启蒙节奏的感叹,如我们的“五四”双重变奏猜想。就此,汉娜·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进行了解读:
当诗人说留给我们的珍宝没有遗言的时候,他暗示的就是这笔失落财富的无名状态。遗言,告诉继承人什么是合法地属于他的,把过去的财富遗赠给未来一代。而没有遗言,或回到这个隐喻的所指,即没有传统,在时间长河中就没有什么人为的连续性,对人来说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有世界的永恒流转和生命的生物循环。因为恰恰是传统选择了、命名了、传递了、保存了、指示了珍宝是什么和有什么价值。因此,这个珍宝不是由于历史遭际和现实困难而丧失的,而是由于失去了预见它的出现或实在性的传统而丧失的。因为没有传统,就意味着没有一个把它遗赠给未来的遗言。
没有灵魂的传统,是没有什么实质性东西的存在,是一个幽灵、是一个幻影,没有可以依附的载体、没有核心的承担、悬浮于时代的飘荡,当然就没有可以传达的遗言。如浮士德的命题:你可以不朽,但要交出灵魂,成为幽灵。
存在两个传统,一个是灵魂的传统,一个是幽灵的传统。
在基督神学那里,灵魂的本性是人格不朽的论证,正是这种不朽定义了伟大的特质。李白、茨维塔耶娃们对人性的追求、对黑暗的抗争、对自由的歌颂、对自然的关怀、对苦难的痛切、对腐朽的批判形成了他们不朽的人格,铸就了诗歌的伟大传统。这类传统的灵魂永恒存在,并附着于一个又一个时代,在多次轮回中寓居于每代诗人身上。一方面,在诗人的坚持下,文学传统的灵魂获得了复活;另一方面,在文学传统的坚持中,诗人在现实挣扎中得以净化。不朽,是因为持续的复活与净化。这是文学的不朽,也是人类精神的不朽。
还有一些诗人,在人类事务的共同世界中离弃哲学经验、人文关怀,热忱于政治思想传统,他们把自己缪斯的灵魂交给了魔鬼,他们以现实的服从、政治名声的索取来替换和消解人格的不朽,呈现的是幽灵般的飘浮。“郭沫若现象”如是,一切以政治为标准,这是政治变异的传统。思想与行动的对立:剥离了现实关怀的思想与剥夺了人文关怀的行动,共生并存。“没有任何赞美希特勒的诗歌留存到了他本人死后,因为没有一位颂歌诗人真的拥有悦耳的嗓音。”(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汉娜·阿伦特如此批评前东德的诗人、剧作家、名导演布莱希特。在她看来,一个诗人最大的惩罚不是死亡,而是他的天赋的丧失,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用最美妙的嗓音赞美暴政的知识分子或文人不会因为这一罪过,而受到丧失才能的惩罚。
在当下比政治变异更危险、更应该值得警惕的是另一类幽灵:文化的飘移。当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期,其中充满着各种权力的压迫和偏见,人性世界也高度变异。一是文化虚无的传统,从十九世纪末到上世纪初,在文学界、思想界始终涌动着强烈的信仰虚无情绪——“世纪末情绪”,一个无片刻宁静的环境,但无处不在地寻求刺激,没有思想,只有感觉,精神幽灵般地飘浮。正是在这个幽灵传统的影响下,当代作家们缺乏对文学的敬畏和奉献精神,“玩文学”、“码字儿”等游戏文学、娱乐文学的现象普遍存在,在他们的眼里,心灵与感性都是“超验”的东西,内在于观念上的东西都是虚无,而对抗思想上虚无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求新、求异,是强烈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是绝对的自我中心和对他人的高度冷漠。文学已经沦为政治交易、肉体欲望、商业文化的奴仆。二是文化迷失的传统,在工业革命、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丧失了自身独特的精神内涵特质,缺乏严正的批判力和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严重丧失了价值判断力和思想把握力,没有表现出正义的精神和人文的力量,没有对时代的黑暗和人性的丑恶进行犀利的揭露和鞭挞,也少见对弱者的关爱和同情,文学醉心于个体生命体验、追求文本形式,对现实人生的终极关怀表现无力,主体精神与价值理性的困惑 , 自喃自语于肥皂剧般的个人生活经验,喋喋不休于花前月下的瞬间感觉,即便有所谓“思想”的作品,只是在一个缺少纵深感的平面上“分享艰难”,没有精神维度的现实挣扎,思考仅此为止。
面对信心的丧失和热爱的匮乏,我们如何重燃激情,恢复人文的影响力?对人文的信心,就是对人类精神的信心,文学比哲学在恢复信心中更具有影响力,许多哲学家在人类出现信仰危机时将希望寄予文学。如海德格尔到后期就根本不讲哲学了,就讲荷尔德林的诗,在他看来诗的本质是“从最高的意义上看是历史的,因为它预示了历史的时代,但作为历史的本质,它是唯一的本质性本质”。于是通过思与诗的交谈,聆听彼此的心声,唤出一个又一个神灵。如此,“充满才德的人类,诗意地栖息于这片大地” 。
歌德通过“浮士德”进行的思考,是任何伟大的哲学家都不能相提并论的。别尔嘉耶夫也认为,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托尔斯泰、司汤达、马塞尔·普鲁斯特等人在理解人的本质方面,比经院哲学家和学者(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贡献更大。
伟大的灵魂借文学在两方面拯救我们的心灵。一是重建爱的维护、影响、感召,重建以人文和爱为中心的价值观;二是对美的坚持,以美的方式,依靠内在的精神鼓舞、感染与支援我们的心灵,对美的本质的坚持应该是文学的根本。
是爱与美的唤起,使信心、信仰回到我们的身躯,我们才拥有伟大的灵魂,拥有了灵魂的维度、灵魂的深度、灵魂的视角,从而光辉人类。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爱与美的唤起与传接,何尝不是先人们的遗愿?渴望获得年轻而颤栗的心灵崇拜。有两位伟大的诗人,洞察了他们逝去后自己灵魂的寄托,寻找爱与美的承接,不约而同写下了相同的诗句。一个是爱尔兰的叶芝,1893年创作的《当你老了》,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献给女友的情诗,也是对后来崇拜者的憧憬: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另一个是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1919年创作的《致一百年以后的你》,更是深切、深情地呼唤:
你拒绝了所有情人中的天姿国色——
只为伊人那骸骨些许。
五
缅怀还是憧憬?复兴的幻象。
如爱尔兰诗人希尼所说:“诗歌的目的是激发更多的诗歌。”一个伟大传统的缅怀是为了激发与憧憬未来的伟大传统。
伟大的传统存在于缅怀、憧憬、再缅怀、再憧憬的时间循环往复中,也存在于成其伟大的光辉时刻和寓居安身的平凡岁月空间里。
博尔赫斯在《论惠特曼》中写到:一直存在着两个惠特曼,一个是由一生枯燥乏味的日子构成的凡俗肉躯,另一个则是由诗歌的天国般的宇宙所提炼出的伟大象征。同样的道理,存在两个历史世界:一个是平凡、空白的时间流逝,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占了大部分时间,另一个是人类的光辉岁月,这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有很短的、非连续的片断。
伟大的传统既存在于人类历史中激动人心的时代,也存在于平缓恬静的岁月;伟大的灵魂,存在于光辉与安详两面之中。一个伟大的传统激励了我们坚定的光辉,也保护着我们平实的安详。伟大的灵魂附着于我们平凡的凡俗肉躯,这也是生命的部分。
但是,我们的记忆与缅怀指向传统与历史中的光辉岁月与伟大象征,我们的记忆力不是把纯粹偶然的某一件事记住和把纯粹偶然的另一件事忘掉的一种机制,我们的记忆是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它会由心智、识别、意义来整理和判断舍弃。
任何的伟大都将毁灭、没落。存在于历史长河的,也将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生存不是永恒的,只有死亡是永恒的。传统的伟大走远了,又有新生的伟大走近了,不是为了我们的现代与当代,而是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以及更遥不可及的未来的缅怀。当然,新生的伟大只存在于历史中很短的片断,这个片断绝不是当代,而是我们可期的一个未来,这是憧憬,也是我们对未来的缅怀。两个方向的缅怀,获得了我们的历史存在与意义。
所有向后的缅怀,都是为了向前的憧憬。憧憬,也许是幻象,在当下的缅怀中,我们为什么会诞生“复兴”的幻象?
当下我们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就一定会带来我们文化的复兴?有平庸的广度,就不可能有光荣的深度。经典不是现代制造,我们仍然可以反复吟诵屈原的“后皇嘉树,橘徕服兮”而获得现代中国人的心灵救援。灵魂的东西不是在现代制造,而是在过去启明,在已消逝了的时间长河里。一切伟大的文化都不是诞生于“繁荣时代”,能让我们人类感动并救援心灵的伟大作品无不是“黑暗时期”的产物。换一个角度说,对“文化复兴”呼唤越强烈,这个时代的精神越匮乏。平庸的昌盛,催生了“复兴”的幻象。
如汉娜·阿伦特所说,文化是“启明”,启明是大众在最黑暗时代最强烈的渴望,也是用生命去期待与捍卫的东西。它并不一定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在政治灾难或道德解体中退守到孤独状态,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用生命和艺术与这个时代抗衡并烛照着后来者。启明,孕育于黑暗又照亮黑暗;黑暗不仅是混乱和饥饿、不义和绝望,更是“公众性的光把一切都变得昏暗了”。
文化是“启明”,文化也是“没落”。每一个文化都要经历内在的和外在的完成,直至终结,如同人类要经历孩提、青年、壮年和老年时期一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说:“西方文化最初是一个年轻而颤栗的心灵,满怀着疑惧之情,呈现在罗马式和哥特式风格的初生时期。”“最后,在文明的昏暗的破晓时刻,心灵之火熄灭了。萎缩的力量再一次努力地做着半成功的创造,由此产生了古典主义,这是所有垂死的文化所共有的现象。再后来,心灵还有一次思考,那便是在浪漫主义中,忧郁地回望着它的童年;到了最后,它也疲倦了,厌烦了,冷漠了,失去了生存的欲望,于是,正如帝国时代的罗马那样,它盼望能走出那漫长的白昼,而坠落到了原始神秘主义的黑暗之中,回到母胎里,回到坟墓里。”回到坟墓中的黑暗与回到母胎中的孕育,具有等质性,同向同构。任何伟大的孕育都是在黑暗中!
其实,文化的繁荣与没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昌盛的繁荣中获得的是平庸的广度,在黑暗的没落中获得了光荣的深度。
对伟大传统的回望,是历史中一切思想启蒙运动的方法,这种思想启蒙运动将成为一切文化复兴、民族复兴的先决条件,而作为一种先决条件,这种思想启蒙运动本质上就是以伟大传统的缅怀、继承来回归每一个普通人的与生俱来并普遍保持了的认识方式和思想方式的运动,维护普通人的尊严、正义、公平、幸福等概念构成的生存意识,就是回归每一个普通人的直接经验、观察和常知常识的运动,就是使我们的学者们的思想学术方式重新回到事实本身,进而把事实和真相作为自己的全部追求的运动。
真正伟大传统的影响在你还未曾在意的时候就悄悄在你心底里埋下了种子,只有当你的修行或年轮到了一定的程度和年头,才会看清自己与传统的关系。传统不是僵死的,它是流动的,也有其恒定的状态。有些传统一直发生着作用,比如杜甫的诗歌,一直是中国诗歌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参照坐标;陶渊明的精神气质,也是后世诗人学习的一个高标。就是“五四”以来的新诗也没能与中国古典诗歌断裂,它们是我们的血脉传统,即使你不是一个诗人也会受到它们的影响。波兰诗人米沃什把诗歌视为人类重大转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因此,不是我们见证诗歌,而是诗歌见证我们。同样的道理,不是我们见证了传统的伟大,而是传统的光荣见证了我们,照亮了我们。
所有的缅怀与记忆,都出于我们的渴望,得到伟大传统的见证与照亮的渴望,并且加入其中。我们自己选择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选择了从神性中回归人性,没有神性的规定,没有上帝的圣明,人自己为自己立法,人在行动中以自我选择创造自己的价值。我想说,没有信仰的维度,没有超验的灵感,没有对无限的敬畏、虔诚,仅有“复兴”的幻象是不够的,仅有一年一度的“清明”时间节点也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