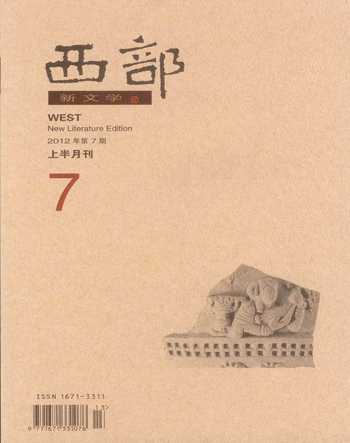皇帝的双枪
艾多斯·阿曼泰
1
2007年的秋天,很不寻常。我终于向暗恋多年的女孩子表白了。那年我高三。
说实话,我并不渴望,甚至绝不相信我和她能在一起。我想要的只是“成与不成”的一份判决。
表白时,我紧张地凝视着她。然而从那紧咬的嘴唇中只艰难吐出来了“我不知道”——这四个字。
于是,我崩溃了……
忧郁时,我总喜欢趁午休时间,晃在学校空荡荡的走廊,站在某个很黑暗的角落,出神。
那一天,我像往常一般地在楼道游荡。突然,一个尖锐的东西,顶向我后脑勺。
我本能地一颤。
低沉却带着某种难以察觉的童稚声腔。
“不许动。”那个声音说道。
我没有动。我感到他的身躯渐渐靠了过来,在我耳边。他粗重地喘着气。
“总算找到你了,呵呵。”他冷笑道。
“我?”我很惊奇。
“不要害怕,我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我机械地回答着,呆在那里。
“我想让你答应个事情。”
“什么事?”
“我想找你单挑。”
“为什么打架?”
“不是打架。”
“那干什么?”
他把嘴唇贴在我的耳边,深深吸了口气,缓缓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
“单——挑——青——春——的——活——力!”(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找我单挑广播体操)
我惶恐地转过头,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他双手高举着两个三角板,好似握着双枪的侠客。他跳蹿着,还为自己配音:“哒哒哒,嗒嗒嗒嗒嗒。”
什么嘛……原来刚抵着我的后脑勺的不过是个三角板。
而那个小孩不过是个疯子。
2
我急于想知道她的答案。虽然之前我早已默默爱了她好多年。
我给她不停地发着讨好的、示爱的短信。她不回复。
烦恼愤懑时,我又歇斯底里地拿出手机发送这样的短信:“我知道你当然不会喜欢我这样的傻缺。我是个傻缺,最恶心最愚蠢的人了。”
我并不一定真是傻缺。当时真正以“缺”而闻名的则恐怕非“李团长”莫属了。
李团长就是那手提三角板找我单挑的孩子,他似乎是个神经病。
李团长每次在上课间操时,总拿着两个三角板,跳跃在国旗杆旁的沙坑旁边。
“哒哒,哒哒哒。”他自我陶醉地配着各种音效。
那时,一部叫做《亮剑》的电视剧正在热播。没有人知道这孩子的真名,于是我们便称他李团长。
往来的初高中同学都被他所吸引,停下来,看他表演。
女生多是忍俊不禁地“扑哧”一笑,接着走自己的路。而男孩们则更有兴趣停下来奚落嘲讽他一番。
我本不是爱嘲讽的人,但在那个时候,或许因为特殊的心境……
我嘲讽得最欢。
只有李团长,完全视众人如无物。
“哒哒,哒哒哒。”
……
3
之后,那个女孩子在楼道里见到我都不和我打招呼,只是很冷漠地与我擦身而过。
面对学业和爱情的双重压力,我闷闷不乐。我变得不喜欢和周围人交流说话了,只闷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有一天,我正在班里写作业,同学对我说:“有女孩叫你。”我百无聊赖地踱出教室,惊讶地发现是那个女孩子。她让我伸出手来。她将一片红叶放进了我手中,温柔而又不失俏皮地说道:“给你,红叶。这可不是普通的红叶啊。我刚在操场上找了好久,就这片叶子最红最完整。”我刚想说什么,那颤抖的手已经把叶子塞进了我的掌心,然后娇羞着跑走了。
我握着那片红叶乐了两天,没写作业。
可一切并不如想象的好。当我和她在楼道里碰面时,她依然是装作不认识我。
这种态度的反复,我又经历了好几次。
一时仿佛在饮着清晨花瓣上的露珠,一时又似乎被蒙在了黑暗里。
每日,我梦游般逛荡在课间的操场。
可就在某天,我又和李团长相遇了。
他静静地呆在那里,看到我,突然扑上来,把我使劲一推。
我一个踉跄,差点儿摔到。
愤怒的我,正准备恶语相加。
他长长地舒了口气:“好悬,刚才那颗子弹差点儿打到你,你知道吗?”
我刚想说:“去你大爷的,根本没什么子弹!”却忽然愣住了,看着他的脸:“你是——你是用你的身躯帮我挡住子弹了吗?”
他默默地点了点自己的头。
4
我想,在生命中,还会遇到很多朋友,但和团长这种奇怪的友情却很难再遇到。
每日,似乎像和团长有个约定。看着他满头大汗地在校园里跑,举着它的“三角板双枪”。
我居然很羡慕他,他的生活好简单。他想为我挡住子弹就能挡住,而我因为自己的不成熟,伤害着喜爱的人。
我最早爱上她时,和她不在同一个初中。
倘若我的学校放学早,我就会躲在她中学门口的角落。我品尝着在涌出校门的众多人群中,一眼望到我的所爱这种甜蜜的感觉。
在下雪的日子里,我一动不动地站几个小时,只为看我所爱的女孩七八秒钟。她骑着橙色的自行车,“刷”地在我面前驶过,从出现到消失,不过一瞬。
但每次能有这七八秒,我就会感到很满足。
那七八秒的满足,却也让我感到自己有些低贱。
我曾是内向、不善言辞、认生、默默无闻的人,没有多少朋友。
爱上她后,我告诉自己:你连当着众人说话的胆量都没有,谁家的姑娘会爱上你这么窝囊的男人啊?
所以我开始努力去改变自己。
我竞选学生会副主席,竟是为了让那女孩知道我是出色的,她就会爱上我了。
我成功了,但在成功的刹那,发现这一切毫无意义。
之后愁闷的我,便只好用写诗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5
爱她时,还是有很多温馨的时刻的。
当时我在文科班,我周围坐了一大圈女孩子。她们一眼就知道我爱上某个姑娘了,但不知我爱上了隔壁班的谁。她们就一个一个试。她们每说一个名字:“莫不是她?”我都会带着某些虚假的骄傲回应道:“当然不是她,她那么丑。”
当从她们的嘴中终于吐出那个女孩子的姓名时,我羞得满脸通红。
现在想来,这着实没什么,但我却始终深深地记得这个瞬间。
我甚至为这个瞬间骄傲。
那个女孩子的班级门口是打热水的水池。我把周围所有女孩的水壶都包了。每天我都帮她们打水,而且一次只打四分之一左右的量,就是为了能在打水时多望她两眼。
那时,大考小考很平常。她在重点班里,学习压力特别大。周围学生们拿到试卷,都认真改题……只有我爱的女孩子,她捂着试卷,撅着小嘴。
这也并不是什么令人感动的瞬间。
但……它的美好之处在于,我能看见我的心上人撅着嘴,似乎要掉金豆豆。
我回到教室,把水壶还给我周围的女孩子。我总是笑得合不拢嘴。她们问我发生什么了,我就把看到的那一幕讲出来了,但她们却体会不到有什么美好可言。
我也是笨嘴拙舌,解释不清。看到她们一副有些迷糊的样子,我觉得发自心底的喜爱。当我望着我的心上人时,我就觉得:你看她撅嘴要哭的样子多美好啊。周围人,全世界的人都比不上她。我为她感到骄傲和自豪。
女孩子大约是不能够领会男孩子到这个程度和层次的爱的,只是笑着说我好变态。
6
爱情初始之时,我想做一个李团长一样的傻子。
但越到后来,我却越觉得自己是李团长的知己。
李团长总让我想到《皇帝的新装》里的国王。
他就像国王,穿着所谓的“新装”,全城的人都发现他是赤裸的,嘲笑他。
但他还是那么一本正经,不为所动。
我总觉得他之所以那么做,是一种孤独。他热烈渴望着能够被人所关注。
这让我想起自己初中的时候。
初中时,我的成绩并不很好。当时我在实验班,压力特别大。在班中成绩倒数期间,又正好陷入暗恋,总之十分纠结。
那时,我有过一段以自我侮辱为乐的时光,算来和李团长正是差不多的年纪。
我在她学校门口等她时,碰到了一位老朋友,他现在是那所学校的全年级第一。
他看见我后,对和自己顺路回家的朋友随口说道:“我有一位特别重要的朋友来找我了,你先回吧。”我四处张望,竟没想到他那“重要的朋友”就是我。
自贬成性的患难之时,这一句话,帮了我很多。
我想李团长,欠缺的也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
在这个被压力扭曲的时代,大笑着说对方是赤裸的,已经不再管用了。
皇帝不信。
全部的人一起大喊:你是赤裸的。他还是不信的。
但如果你能把自己多余的一件衣服,套在他的身上……
7
自从喜欢上她,我就在不停地写诗……
有一次,我对周围的朋友说了我目前的情况。他特别认真地对我说,其实我缺的就是一次总攻。他说下次那个女孩再有些任性的时候,你应该一把抓住她的手。反正,需要让她明白你强烈的感情,让她感受到你的爱情是认真而强烈的。女孩子们有时需要的就是这个,需要一个表态。
我只是很怯懦地笑了笑:“呵呵,我说,我还是写好诗歌吧。也许她不跟我,是因为我的诗歌还不够好。”
那个男孩子气的说了句:“竖子不可教也。”然后愤愤而去。
其实我并非怯懦,也不缺少所谓的握手的勇气。
我只是奇怪地觉得诗歌已经变成了我的语言。
最后,如果没有通过诗歌得到这场爱情,似乎会是很怪的事。
8
某日。
上学时,走到楼道口,李团长突然把一把“枪”交在了我的手里。
他说:“嗨!跟我一起,我们去打日本鬼子。
我跟随着他。
有一个女孩出现在门口时,我察觉到他目光忽然闪了一道很怪的光,身体颤了一下。
他冲到那个女孩旁边,拿着三角板,在那女孩身边跳来跳去的。
而那女孩只是厌恶地把他推开了。
他一次次上去招惹那个女孩。
直到最后,一切答案都揭晓了。
他总守在那楼梯口,等待着那个紧皱眉头的女孩出现,他会冲上去,最认真地表演着,跳着大叫着,给那个女孩最温柔的一枪。
那个女孩就是李团长心上的姑娘。
不知当年知道李团长的朋友们,还记不记得他?
就算记得,恐怕也只是把他当做一个玩笑罢了。
是啊,我们的笑声嘲笑着团长,嘲笑着我们没有穿衣服的国王,却不知道这位国王为什么赤裸。
他甚至只是为了能够听到自己的心上人嘲笑自己,而赤裸地站着。
这个世界上没有伟大的爱情。
最伟大的爱情,就是最——可怜的。
9
后来,我离开北京闯荡,无非是以为她不爱我了。
就在我离去前的几天,我约她一起去圆明园。当时,我们正好赶上了圆明园快日落的时刻。
其实我并未经历什么。我只是经历了一个女孩子理所应当的任性而已,但我依然是无法释怀地压抑着。
当时我说起自己要离开北京闯荡,做一个诗人,写出全世界最美好的诗给她。
望着圆明园里伤感的日落,我说到了生命,也说到死亡。
她板着脸,皱着眉头——这是她在我脑海中形成的最经典的形象。
她气愤地说道:“你能不能不那么幼稚啊!”
忽然,她的表情如同崩溃般地转向了悲伤。
泪水从她那双眼眸中涌出。她一边哭一边说:“你怎么能那么幼稚。”
我不知道自己说的话到底哪里幼稚了。
所以我想或许她也是爱我的。
在那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原来我不是傻缺。
但无论是爱情,还是这个醒悟……
都显得太晚。
青春是一段发生在很早的故事。
但她发生后,一切就都太晚了。
10
我写诗,所以有些人管我叫诗人。
有很多朋友带着各种问题来问我。因为他们觉得我身为诗人是最懂生活的。
我不是,我也不懂。
刚毕业,就听说李团长忽然变得和正常人一样了。他不仅正常,甚至彬彬有礼,闪耀着迷人风度,找到了女朋友。
这让我不禁茫然若失。
他放下了三角板,就是正常人。
而我呢?
我对于诗歌本身并无兴趣,只是以为写一首好诗,我喜欢的姑娘便会愿意和我永远在一起了。
诗歌就是我的枪,我的三角板。
我不仅没有放下,反而走到了文学的道路上。
李团长以为拿着三角板,向自己喜欢的女人开枪,就会被爱上。
而我以为写首好诗,就会被女人爱。
我们都一样愚蠢。
我为得到爱情而写诗。
而我现在开始要做的工作,就如同“如何玩好三角板”般荒谬。
离开了我心爱的女孩,没有追求的对象了,我却依然刻苦地钻研着如何写好情诗。
我无法放下自己的双枪。
青春的结果竟如此荒谬。
11
有多少人,费尽心机通过各种方式要证明自己是成功的人。
到头来才明白:自己只是自己。
自己不是傻缺也不是英雄。
只不过是个孩子。有时候爱,有时被爱。
相信自己不是相信自己是个成功的人。
而是相信自己,是自己。
可一切又哪里来的那么简单呢?
不要嘲笑那些迷失在金钱中的人。他们不过是以为当了学生会副主席就能被女孩爱的傻孩子。
在这个可怜的世界里,我们谁都不要嘲笑奚落谁。
其实我们都是李团长。我们都无法爱到我们依恋的人,只能紧紧握住某些我们自认为重要、但终究难免是可怜的东西。
送那个女孩上地铁的路上,我思索这场爱情中我得到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她到底是爱我的,还是不爱我?是愿意和我在一起,还是不?在离别的刹那,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却因为失去它固有的意义而显得格外美好。
若干年后当我回忆爱情时:没有一个说愿意的女孩子,也没有一个远离我的倩影……
我只记得一位可爱的姑娘,将一片红叶放进了我手中,温柔而又不失俏皮地说道:“给你,红叶。这可不是普通的红叶啊。我刚在操场上找了好久,就这片叶子最红最完整。”
有时结果并不是一个态度。
它更该是一个画面。
正在我愣神之际,地铁开来了。我心爱的女孩就要坐着地铁离开了。
我也即将踏上所谓的“文学之梦”的旅程。
我一直死死盯着她在地铁上的身影。那个身影和众多陌生的影子挤在一起。 “刷”地一声,地铁开走了。只有我的影子,孤独地映在玻璃防护门上。
看着玻璃防护门上自己有些失落的情形,我着实不知自己准备从事的文学之路是不是对的。
文字不过是爱她而产生的副产品……
但我却又不由得这样问自己:
“就算如此……又有什么能比从青年起就握着的这把假枪更珍贵呢?又有什么能比它更真实呢?”
它比爱情本身更忠实地伴过了我们的青春。它已经成为了一场寄托。
感情如云烟般泛去,剩下的难免是寄托。
我忽然想:尘世若大海,人不过是叶扁舟于其之上。
连这本身都恐怕更是场寄托而不是感情,又何处寻来的得失成败?
如果您能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送走我的她,在地铁站,对着空空的玻璃防护门。
忽然我有种空洞而略显空明的温暖,某种难以诉说的感觉。
于是,我伸出食指和拇指,摆出一把枪的形状,冲着玻璃上自己的形影,歇斯底里喊着:“哒哒哒,哒哒哒。”
然后我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
是的,就在这一刻,也不知为何。
我竟前所未有地热爱起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