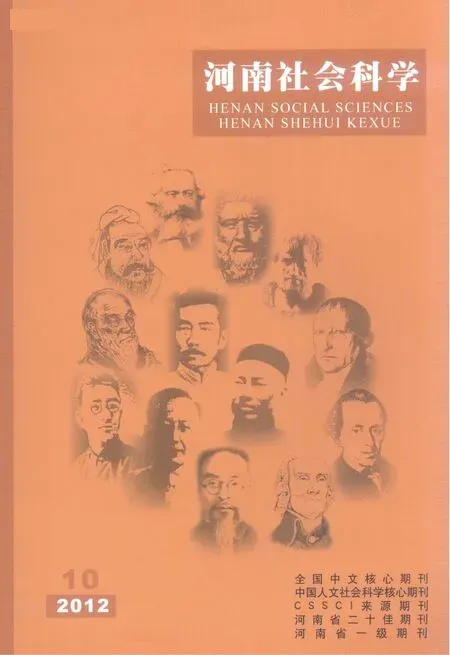反腐败神话与廉洁转型
——基于香港案例的研究
袁柏顺
(湖南大学 廉政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2)
反腐败神话与廉洁转型
——基于香港案例的研究
袁柏顺
(湖南大学 廉政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2)
作为一个实现了由腐败到廉洁的转变,且长期维持较高廉洁程度的成功样本,香港反腐败的经验是廉政研究当中长盛不衰的话题。虽然香港惩处、预防、教育三管齐下的反腐败战略已经众所周知,但其中教育战略的重要性往往受到严重的低估。墨宁认为,教育战略能够在廉洁均衡状态当中帮助维持一个已经较低的腐败率,而在腐败均衡中以及发生均衡转换的情况下却功效不大,因为当腐败比比皆是之时,腐败活动并不大会因大张旗鼓的道德教育而受到影响。与波普一样,她认为,虽然教育战略很可能也是必要的战略,但教育战略最好努力为惩处和预防的战略服务。本文则认为,在由腐败到廉洁的均衡转换当中,惩处和预防虽然是整个反腐败战略的基础,但却有着先天的不足,它们未必能够实现降低腐败收益及收益预期,影响均衡当中博弈者的理性选择;相形之下,社会神话的构建与运用,可以赋予教育战略以更为巨大的力量。反腐败社会神话一方面可以激发民众痛恨腐败的情感,重塑廉洁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鼓舞民众支持和参与反腐败行动,帮助实现由腐败到廉洁的关键性转换。
一、理性选择、社会神话与廉洁转型
普遍而严重的腐败,以及低度腐败或较高程度的廉洁,往往被视为纳什均衡,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身处均衡之中的任何一个博弈者,都无法独自改变其所处的均衡状态。对于一切反腐败事业而言,最大的挑战,无疑是找到合适的战略,以打破腐败均衡并实现从腐败均衡到廉洁均衡的转变,或者说完成廉洁转型。论者往往认为,“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战略,其目标在于降低腐败行为的收益,增加腐败行为的成本,从而影响特定社会当中各行为者的理性选择。如通过惩罚腐败犯罪,使腐败成为一种高风险而低回报的行为;使易受腐败诱惑的政府部门及人员减少腐败的机会;通过给政治领导人和公务员以适当之薪水,降低腐败的诱惑[1]。一个廉洁而独立的反腐败机构则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有论者进而提出,不仅要改变腐败收益,而且必须改变收益预期[2]。通过建立反腐败机构,推行反腐败改革,一方面对腐败行为进行惩处,另一方面通过制度设计预防腐败,减少腐败行为发生的机会,从而达到或改变腐败行为的收益,或改变对于收益的预期,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循此路径的反腐败改革达到一定程度,“足够廉洁”的政治就会产生向更为廉洁的政治的冲动(势头)[2],从而必然实现两种均衡的最终转换。而独立反腐败机构的建立,被认为是腐败收益及腐败收益预期改变的信号,是腐败均衡向廉洁均衡转变的开始。
然而,惩治与预防并举的战略并不能有效地改变腐败收益及其预期,从而影响博弈者理性地选择廉洁交易行为。经验研究表明,反腐败政策决定本身要么对于腐败“没有什么作用”,要么发生作用的过程“缓慢得令人痛苦”[3]。旨在惩处的执法(纪)资源的有限性、腐败预防效果的滞后性,尤其是腐败民俗的存在,使得惩治与预防未必能够改变腐败收益与收益预期。而时间并不站在反腐败力量一边,腐败民俗相较反腐败力量更为强大。在普遍腐败的情境下基于理性选择的惩治与预防战略,未必能够实现均衡的转换,更可能在经过腐败民俗与反腐败改革之间一定时期的拉锯战之后,最终重回腐败均衡之中。短期内实现关键性转折因此十分必要。而关键性转折的实现,有赖于社会动员。反腐败神话的构建与运用,可以改变腐败民俗,动员民众支持和参与反腐败工作。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阿罗(Kenneth Arrow)、唐斯(Anthony Downs)、奥尔森(Mancur Olson)的推动,理性选择理论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西方学者热衷于运用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政治与社会现象,其中包括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对于腐败问题的研究中,理性选择理论亦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分析工具之一。由此衍生的腐败机会、成本、收益模式,已经被广泛运用。
但是,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并非毫无缺陷。正如诺思(Douglass Ceil North)所指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那些在生活中同样常见的、并非出于自身利益算计的人类行为,如隐姓埋名的无偿献血等利他行为、要冒重大牺牲而无明显可能利益的非理性选择行为等[4]。格林(Donald P.Green)等学者更是认为,“理性选择模式在经验上应用成功的事例屈指可数”[5]。
廉政研究者同乐于引用其著作的贝克尔与其他理性选择学派的经典作家们一样,在将理性选择理论运用于犯罪研究时亦同样不乏审慎。他承认理性人对于不同活动带来的损害或利益的认识经常存在分歧,如对某些人来说,任何竞争的劳动市场决定的工资率都是可以接受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低于某一最低限量的工资率则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对于某些人来说,只要愿意支付市场价格,赌博、卖淫、堕胎都可以自由地进行,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赌博无异于罪恶,堕胎等同于谋杀。贝克尔的研究所建基的理论预设却并“不考虑这些分歧”[6]。但事实上,这些分歧恰好是至关重要的。犯罪行为如果涉及道德与价值,则并非单纯利益计算可以衡量。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廉政研究当中任何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工具与方法本身的缺陷不可忽视。正因如此,需要其他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
反腐败改革同样是一场斗争,一场“革命”。身处腐败均衡之中的博弈者即便接收到反腐败的信号,亦很可能只会暂停或更为隐蔽地从事腐败行为,难以做到真正的改弦更张。至于挺身而出支持和参与反腐败改革,这对于博弈者个人来说则根本不是理性选择的行为。
腐败民俗(Folklore of Corruption)的存在使得理性选择的天平更容易偏向腐败均衡的维持,而不是廉洁转型。腐败民俗是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一个社会内部广为流传的关于腐败的看法和与此相伴而生的情感[7]。在论及香港反腐败的相关论著中,墨宁对这一概念的看法更侧重于强调其后所体现的对腐败的信念,而Lee则更强调作为价值与习俗的腐败。腐败民俗的概念虽未为缪尔达尔所展开论述,对它的理解不同的学者也各有侧重,但腐败民俗的客观存在、腐败民俗的存在不利于腐败控制却被认为是肯定无疑和基本一致的。如果腐败是无关道德的行为,“如果腐败变得理所当然,愤恨就会变成对于有机会通过不光彩手段营私之徒的羡慕”。义愤不生,举报腐败行为就缺乏相应的意愿。此外,腐败的传言或者民俗还会使人们对腐败行为的普遍性,尤其是高级官员中腐败盛行产生一种“夸大的印象”,而不论它是否属实。如果某些众所周知的腐败分子能够逍遥法外,那么这一事实反过来又会使人们关于腐败的看法得到证实和强化。而相信腐败十分普遍的观念常常会使人们放弃对腐败行为的抵制,甚至主动参与腐败的交易行为之中,而这种主动参与显然成为人们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对于由普遍腐败状况实现廉洁转型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这场革命性的变革不仅需要政府意志、相关反腐败立法及相关机构的制度化运转,如执法机构的强力行动,司法机构的配合,同样需要唤起民众,从而使这场变革扩展成为社会运动。而“从来没有一次显著地改变事件进程的群众运动,其参加的个人不是为某种信仰所鼓舞的”。信仰“也许是关于今世和来世的神话,而附有在尘世和天堂求取更大幸福的一种希望,或者也许是被解释为正义要求的一种反对不平等的愤怒感”[8]。反腐败改革的决定性进展,需要反腐败社会神话的鼓舞。就这一关键性变革的产生而言,索列尔的神话理论有着更强的解释力。由索列尔开创的神话理论不乏传承者。包括民主在内的神话被承认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力量,所以它不能是纯粹的神话”[9]。
诚然,索列尔“较少关注神话的细节”[10],但是他的神话理论已经足够清晰地呈现出几个要点。就其理论预设而言,社会神话不是诉诸理性主义的功利算计,而是诉诸奋起一搏的勇士精神、英雄心态,能够充分调动和激起受众的情感[11],凝聚和表达出一个群体的信念。就其内容而言,它是信念、情感、价值的混合体。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神话所具有的特别功用。神话“不是对事物的描述,而是行动意志的表达”。运用神话不是对事物进行被动描述,而旨在唤起行动的意愿,引导人们为一场战斗做准备;而神话一旦被群众接受,将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一旦群众被打动,就可能描绘出一幅构成一种社会神话的画面”。而如果群众“没有接受神话,人们就可以无休止地谈论造反,而不会引发任何革命运动”。在索列尔看来,社会神话的具体内容本身并不重要,即使神话所描述的“图景是完全虚幻的,只要这种虚构图景以一种完美的方式体现出”,“所有期望”并具有确定性,那它“就是一种伟大力量的源泉”[12]。“即便知道它是一种神话,我们也能像现代物理学家一样行事”,理性地利用神话所产生的力量[12]。
二、香港廉洁转型中的反腐败神话
香港的廉洁转型在短短数年之内即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而那种被认为更难改变的腐败民俗,几乎在20年之间,或者说一代人之内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反腐败教育战略对社会神话的构建和运用。
一方面,在廉政公署成立初期,虽然其资源优先配置执行处,全力于反腐败执法调查,但其执法活动往往会处于被动状态,根本无暇主动进行腐败案件调查。如果不考虑道德、价值与情感,腐败交易行为往往授受相悦,具备隐蔽性特征。腐败惩处不仅需要高超的调查技巧,更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配备更多的执法力量,由于反腐败机构与资源投放本身不可能无限扩张,相对于普遍腐败均衡状态中腐败行为数目之巨,单纯依靠执法活动使腐败行为收益降低,从而改变博弈者的收益预期,即使不是不可完成的使命,至少可以认为是极其困难的。腐败预防工作的开展在初期因为经验和资源的因素影响有限,而且其成效发挥具有滞后性,因此对降低腐败收益与期望亦助益无多。另一方面,廉政公署成立及初期执法活动给予民众的信心与鼓舞则可能出现停滞乃至衰退,贪污举报数量在经历了廉政公署成立初期的急剧上升之后,并没有显著增加。大量匿名投诉的存在,使廉署认识到部分市民对贪污罪行仍未敢正面揭发,需要有更多的鼓励,他们才会积极地挺身而出,署名举报贪污,以支持廉政公署的工作。腐败民俗的强大可能使反腐败取得的成果不保,刚刚开始的向廉洁均衡的转变可能停滞。
与此相对照,香港社会的腐败民俗却有着更为普遍而深远的影响力。
1971年夏天,香港中文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对拥有60万人口的香港九龙塘区所做的一项关于社会与经济生活质量的调查中发现,只有29.2%的受调查者认为腐败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事实上,根据当时香港法律的规定属于违法犯罪行为的腐败是普遍而严重的。这一矛盾现象的发生,个中原因正如Lee所指出的,上述“中国人中有其自身的腐败民俗——即某些被法律界定为腐败的行为被人们认为是正常的生活方式”[12]。
当廉署在1974年初开始工作时,匿名的举报,是所有贪污举报的2/3,但在1975年底已减至约半数。显然,此时发挥作用的并非社区教育,而是独立反腐败机构的成立与致力惩处所带来的信心发挥效用所致。1975年初社区关系处方才正式工作。当时该处还只有28名职员,且其中部分还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3月才成立社区关系处的中央工作单位,1975年7月31日才在九龙城美东成立第一家地区分处。受到财政紧缩的影响,是年社区关系处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原计划开设的8个分处只开设了3个,廉政公署的宣传及社会教育计划也都不能平均发展。社会教育组的首位职员到1975年11月底才被委任。但廉政公署的宣传与社会教育一经启动,其成效之巨,即远远超过预期。社区关系处的成功实践,既达到了支持反贪工作的目标,也改变了民众的价值观念。
从一开始,香港当局及其反腐败机构即认定没有大众的参与,反腐败就难以取得成功。而一般普罗大众,尤其是存在腐败民俗的基层群众,更是动员、教育、改变的重点。社区关系处成立以后,社会神话即得以构建。一组时长各约为半小时的13集电视剧,被廉署认为“特别值得一提”,该剧既各有主题,而又相互连贯,共同以贪污及有关问题为主题,描写本港的市民生活及一般态度,可以说比较集中而系统地勾勒出反腐败神话的全景。这部剧集首先塑造了廉政公署无处不在的威慑和维护正义的中流砥柱形象,激发了民众痛恨腐败的情感,塑造了廉洁的价值,勾勒了一幅廉政公署与市民合作反腐,使香港变得美好的理想图景。
这部剧集曾首先于1976年2月至5月间在香港当时三个播放中文电视节目的电视台之一丽的电视中文台播出。因反响热烈,在电视台的要求下,这部电视剧接着于5月至8月间在佳艺电视台播映,12月份又在丽的电视重播。13集电视剧加上廉署制作的同样主题的5分钟宣传片,借助于当时电视机的普及与免费中文电视节目的提供,以及同样反映相关内容的平面广告与无线广播,加速了市民对这一神话的认同。在社区关系处成立并成功地开展其最具影响的工作(制作并投放电视剧和相关广告、短剧)之后,市民“似乎将公署当做‘冤情大使’”,不管是腐败案件还是其他并非腐败的一些举报,一体向廉政公署涌来。1976年的实名举报率出现了最大升幅,紧接着实名举报超越了匿名举报,实现了此长彼消的转变。这种转变后来虽有微小变化,但基本呈持续改进的态势。
电视剧并非唯一的宣传渠道。社区关系处全面运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各种传播媒介,采用新闻公报、电台及电视广告短片、海报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在随后的工作中,社区关系处的教育工作并非仅仅局限于通过媒体,它们更走向学校与社区,全面扎根于香港社会之中。反腐败神话亦随着社区关系处工作的开展,借由反腐败执法的印证与强化日益深入人心。
三、结论
香港的经验表明,廉洁转型可能以某种突变的方式而不是渐进方式发生。而这其中,反腐败神话的构建与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这一突变的发生。它一方面帮助实现了价值观的转变,减少贪污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也动员民众挺身而出,积极支持和参与反腐败工作,从而成为继独立反腐败机构成立之后的第二节助推器,在廉洁转型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事实上,构建和运用反腐败神话从而实现廉洁转型,在新加坡亦有着类似的情况。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主管皇家香港警察队检举贪污组的总警司罗彼得在考察新加坡的反腐败经验后总结说,新加坡反腐败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是新加坡大部分人口“经由政府鼓吹而了解,国家的前途不容有贪污行为存在”,从而产生一种热心、一种责任感和对国家的忠诚。这与新加坡成为共和国之前民众的态度“大相径庭”。至于新加坡所谓的高薪养廉等旨在影响人们的理性选择的举措,不是在廉洁转型之前或过程之中,而在实现廉洁转型之后。
反腐败神话也改变了反腐败宣传教育战略的地位。在香港三管齐下的反腐败战略当中,教育战略并非单纯地传递信号,扮演旨在降低腐败收益及相关预期的惩治与预防工作的一个配角。在廉洁转型过程当中,促使社会价值转变和腐败民俗改变,以及鼓舞民众挺身而出参与反腐败,承担着更为根本的使命,其中,教育战略才是真正的主角。腐败均衡或廉洁均衡的维持,诚然是身处其中的博弈者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由腐败均衡向廉洁均衡的转变,则更有赖于社会神话所宣传的价值与所鼓舞的民众行动。在廉洁转型的反腐败改革进程中,诚然需要发挥反腐败执行与腐败预防的功用,但重视教育战略更有其独特价值,尽管社会神话的构建与运用远非这一战略的全部。对于大国来说,腐败民俗更加强大,确立廉洁价值和动员民众支持与参与反腐败工作的任务更加艰巨,腐败均衡更难改变。反腐败社会神话的构建与运用,或许能够为由腐败均衡到廉洁均衡的关键性转折提供新的思路。
[1]Jon St Quah.Curbing corruption in Asia:A comparative Study of Six Countries[M].Categories:Ea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3.
[2]Melanie,Manion.Corruption by design:Building clean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3]D.Treisman.Thecausesofcorruption:across-national study[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0,(3):399—457.
[4][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5][美]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重译本)[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8][美]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9][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11][法]乔治·索雷尔.论暴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2]Rance P.L.Lee.The Folklore of Corruption in Hong Kong[J].Asian Survey,1981,(3):355—368.
2012-07-13
袁柏顺(1970— ),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