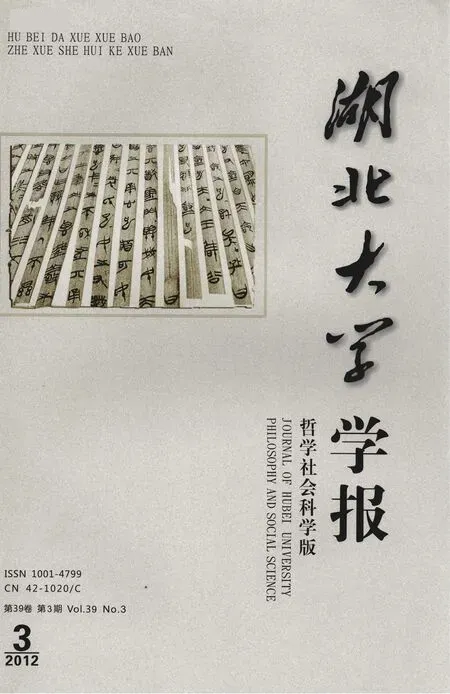新文化史视域下教育活动史研究的“三个转向”
黄宝权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新文化史视域下教育活动史研究的“三个转向”
黄宝权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新文化史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史学形态,它的兴起拓宽了历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使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推动了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的发展。教育史学作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一门交叉学科,与历史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应该也需要从历史学中汲取营养,获得自身新的发展。近些年来在教育史学界悄然兴起的教育活动史研究可以从新文化史当中获取一些新的启示。新文化史视域下的教育活动史研究需要实现“三个转向”:研究视角应从上层转向民众,将人重新放回到历史当中;研究重心应从宏大转向微观,注重具体描写;历史撰述应从分析转向叙事,注重平实生动。
新文化史;教育活动史;研究转向
新文化史又称为“社会文化史”,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史学形态,它的兴起拓宽了历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使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推动了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的发展。亨特指出:“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经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罗伯特·夏特尔则把新文化史概括为“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的转向”,其内涵是指在绘画或音乐的文化史之外还有一种身体、时间或图像的文化史,其发展方向是在文化里囊括了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许多新的研究主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教授认为:“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不是一种简单的新的时尚,而是对较早的研究范式所做出的明显的反映”[2]199。
“新文化史学最新的一点是它将许多新主题包括在‘文化’系统之内,这些主题或内容包括政治、衣服、日常语言等等。他们强调的是对文化的‘建构’或‘创造’,即一个又一个历史学家创造着新的词汇,如‘印刷文化’、‘视觉文化’、‘企业文化’等等,这样与特定的场合、技术或社会群体相联系的一系列文化规则或预期得到确认”[3]143~150,“文化”的观念深入日常生活,重视某些微观历史事件的文化含义,是新文化史的突出特征。新文化史学的产生是一场“国际化的集体运动”[4]7,其代表人物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就地理和社会方面而言,今天文化史研究的呼声更加广泛和多样化。这种愈益强烈的呼声是与文化研究名义下跨学科课程的兴起息息相关的”[2]190。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新文化史逐渐摆脱了过去史学研究中僵化、枯燥的现象,涌现出来的众多的西方新文化史著作,向人们展示的是一种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推陈出新、具有创新精神的史学面貌,日益受到史学界的推崇。
一、研究视角应从上层转向民众,将人重新放回到历史当中
在长期的历史研究历程中,人们关注的往往是精英人物和上层社会,对人物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帝王将相、伟人、成功者,或者是参与大事件的历史人物。新史学强调历史中结构的价值,在以长时段为代表的结构史学中,个人几乎被淹没在静态的结构性力量中,因而丧失了活力。在一些学者看来,只有结构性的因素,如经济变动周期、政治制度等才是历史中的重要力量。即使社会关注人,但也是以群体、而不是以个人的面貌出现,仍然是抽象的人。而在新文化史学著作中,“人”首先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人[5]。所以,新文化史学视野中的“人”非常广泛。某个人之所以被选择记录和研究,不是因为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他很重要,而是因为他自身就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新文化史继承了新史学反对精英史观的观点和做法,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下层民众集体或个人之上。因此,以往所不被重视的对象,包括妇女、儿童、群众、磨坊主、文学家,甚至乞丐、妓女等各色人等,都可能成为新文化史学著作中的主角和研究对象。着力新文化史学的历史学家大多认为,个人(甚至普通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他们至少有某种自由的边缘,至少在日常生活和就长时段而言影响历史的趋势。某些个人的行为也可能会代表着一个时代或社会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大众的行为特征,因此,那些“微不足道”的微观世界和小人物的生活构成了新文化史研究的核心内容。
受新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影响,教育史学界近年来也出现了“视野下移”的学术实践,开始出现了研究民间和基层教育活动的倾向。以往教育史研究曾出现了研究中心“高位化”的情况,具体表现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上层精英人物的教育思想与国家层面教育制度变迁,论述精英人物教育思想的研究很多,而涉及社会底层人物的教育的具体问题与情境的研究极少;教育制度研究“重视的是国家教育机构的形成及其演变,重心放在了描述制度的内容及因袭过程”[6]2,缺乏对决策的生成过程、在基层的实施情况及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所以,有学者认为,教育史研究应当将研究的视线逐步向下移动和对外扩散,实现教育史研究从精英向民众、从高层向基层、从中心向边缘、从经典向世俗的过渡。通过转向研究历史当中的日常教育问题,来真正展示生动鲜活的教育史学科特色[7]。这表明,教育活动史研究要借鉴新文化史以人为中心的做法,要做到凸显“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特别是普通民众在教育活动和过程中的形象,因为教育活动是以“人”为中心的活动,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为此,应将教育活动史研究的触角转向基层的、民间的、日常的和微观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彰显人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教育活动状况,使教育活动史研究既丰富完整,又具体生动,这样才能还原鲜活真实的教育历史活动场景。
二、研究重心应从宏大转向微观,注重具体描写
新文化史所从事的是具体的个案考察,特别是关注人民日常、细小的生活细节。正因为如此,许多史学家将之称为“微观史学”、“新微观史学”或“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学”是指“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8]29的研究方法。他们希望通过描述细微的事件和平常的人物来重构历史,让人们体会历史的脉搏,看到一般人的历史活动[9]121。微观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重新发现那些被忽视的小人物、小事件和小问题,通过逼真的描述展现这些人物的生活世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借以弥补社会史中笼统研究方法的不足。可谓以小见大,见微知著[10]。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微观史学感兴趣的是历史上那些具体的、易于观察的、个别的人或事物,要对微观的个体的所有具体情况进行考察。但是,微观史学家并不是主张仅仅局限于对某个微观现象的孤立研究,而是主张尽可能地通过研究微观现象同时看到或折射出其他方面的现象。这不是简单地用微观的共同体(如社区、家庭、个人)来代替宏观的共同体(如国家、民族等),而是要改变研究的原则。即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概括的。如研究个人,既要研究其一切方面,又要探讨个人的变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因此,微观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只是很小的对象,它既可以研究一个或几个人,也可以研究单位,一个村庄,甚至一个城市和地区。而从研究方法上看,如何从限定的对象、缩小的范围中收集证据、鉴别史料,可以说是微观史学在方法论上所必须致力解决的问题[11]17~18。
我国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注重对重大历史事件和著名历史人物的研究,注重于从宏观的角度着手,而缺乏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如对我国古代书院的研究,人们更多的是去考察书院的起源、功能、学规、学田以及著名教育家的讲学活动和场所,而很少有人去关心和研究书院师生的日常生活状况和教学活动情况;对我国家庭教育的研究,人们往往关注于家庭教育的效果和影响,而很少关注家庭教育是如何进行和开展的;对教育政策的研究,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它的内容和作用,而很少有人去关注它是如何出台、又是如何运转的,等等。总之,以往的教育史研究,注重的是对教育历史的总体研究,而缺乏对教育活动和过程的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教育活动史研究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研究缺憾。新文化史中的微观史学取向,对研究教育活动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因为教育活动史主要研究的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如何开展活动的历史,涉及的范围非常之广泛和琐碎,它的研究重点应当着眼于人的微观的、具体的和日常教育活动,重点研究学校教师和学生日常活动,包括教师教学实况展示、教师生活状况、学生学习生活、校长治校活动等日常的微观的教育情节;探究历史上的家庭家族教育活动,包括家庭启蒙活动、家庭品行教育、家法惩戒等家庭教育的一般场景;探究历史上社会教化活动,如乡规民约教育活动、宗教礼仪教育活动、民风民俗传承活动等[12]。可以说,教育活动史研究包括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教育活动。唯有用微观史学的方法去着手研究教育活动的历史,才能展现教育活动史鲜活丰满的情景,再现真实的教育活动场景。
三、历史撰述应从分析转向叙事,注重平实生动
新文化史学可以说是对旧的“新史学”的继承和发扬。这种旧的“新史学”通常指的是计量史学。计量史学信奉“科学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文化是某种超结构。为此,职业历史学家对他们研究历史的方式和范围所产生的结果不是很满意。因为用计量方法研究的宏观经济史或宏观社会史在某些学者看来太枯燥,甚至是非人格化的。因此,对历史的社会学或社会历史学的批评呼唤历史回归。可以说,新文化史正是为解决与日常经验失去联系的社会史这个问题而创造的[13]202。劳伦斯·斯通指出1970年代初新史学所依据的假设已经被基本否定,而一种企图建立“科学历史”的白日梦也随之破灭。他断言,历史能成为科学的这个观点是个“神话”,即历史将成为严格的、科学的、令人陶醉的乐观主义业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将来历史撰述由分析回到叙事。因为历史研究中强调了人类的具体经验,叙事史的回归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雅克·勒高夫解释说:“各类文化出于什么原因和通过什么方式相互接触?这是一种必须加以叙述的历史。叙述就是解释。对所述各类历史问题,若不首先加以分析,就不能编出好的叙述史”,“一个叙述、一个历史的叙述,不是一个单纯文字的叙述……也是而且尤其是一个科学的叙述”[14]127。所以,在对如何编纂和表述历史上,出现了由历史学的科学性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并逐渐形成了历史分析和历史叙事两大主要撰述风格和流派。
“新史学”在将历史研究带入一个更理性化、更深刻化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自身的缺陷:“新史学”在批判传统叙事史学的局限时,逐渐走向极端化和绝对化,结果在“新史学”不断追求历史的“整体性”和“宏大历史叙事”时,多少忽略了“小历史”中所包含的独特性、过程性和“具体历史叙事”;在强调长时段、结构、功能、规律的同时,多少排斥了构成史学作品本质特征的编年、叙事、事件、人物;在强调经济史、社会史、环境史、生态史的同时,政治史、文化史、心态史、人物传记等则相对被削弱了。总之,“随着对静态的结构的研究的加强,动态的运动的分析被忽视了。栩栩如生的人物、有声有色的事件被经济增长、人口曲线、社会结构变化、生态环境变迁、价格图表等所取代了。即使有人出现,也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群体”[15]209。通过对现代历史叙述所出现问题的反思,一些历史学家认识到,历史学不完全像其它社会科学那样,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性学科,它同样需要运用想象和直觉。再者,非历史专业读者不再阅读历史著作使历史学产生一种生存危机,这种危机的消除要求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对个人及事件的关注结合起来,从而重新赢得读者群[16]。正是“新史学”所暴露出来的局限及对此进行的反思,直接促成了西方史学中“叙事史的复兴或回归”。
教育史学作为与历史学有密切关系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历史编纂上应该从新文化史学中吸取一定的营养,倡导“叙事”编纂,使教育史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受西方新文化史学的影响,近年来在教育史学界,也出现了“叙事史的回归”,主张用“教育叙事”的方式去表达和书写历史。而教育活动史研究由于它所涉及的教育活动内容的广泛性和教育活动情境的微观化,有必要从西方新文化史学中吸取经验,采用“叙事”的方式去进行教育活动史研究,从历史分析所主张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史学转向主张以重新回到历史演变的“场景”为主要特征的“叙事史学”之中,即实现从历史“问题”到历史“场景”的转向。新的叙事史在一定程度上将传统历史叙述和现代历史叙述融合起来,不仅关注社会问题也关注个人和事件,把人放在历史叙述的中心,把对整体与问题的研究和叙事结合起来,利用新史学的各种功能构建用于叙事的总体社会背景,以问题的解决为逻辑推进过程,寻求对历史的总体解释。
在教育史面临新形势下生存和发展危机的情况下,为了寻找教育史发展的新的出路,应打破以往的教育史研究晦涩难懂、诘屈聱牙的传统撰述做法,让教育史研究走下“圣坛”,走向民众,成为普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读物,使史学成为平民和大众的史学,这样,教育史学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正像王笛在他的著作中所提到的那样:新著不同于以往研究成果之处,便是从现代化理论分析方法回归到“叙事”(narrative)的方法,试图通过叙述和描写引导读者进入“事件”内部,让他们“身临其境”来对“事件”进行观察,“力图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得简单易懂,力图以比较明了、直接、清楚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理论和术语,其目的是使不仅本领域的专家,而且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大众读者都能读懂、而且喜欢看下去”[17]4。他的观点代表了当今新文化史学和主流历史学界对于新文化史学的一致看法和潮流。“叙事史的转向或回归”越来越受到史学界人们的推崇,并对相关学科产生了深刻影响。
所以,教育活动史的撰述有必要吸收西方叙事史学的优良传统和经验,生动地撰述教育历史,再现教育历史的鲜活场景,使教育历史变成可触摸的、可接近的、可普及于民众的历史。当然,历史撰述包括教育活动史研究,要将分析和叙事的撰述范型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叙事与分析并举,达到史学研究的理想境界。那么,历史研究的理想境界应该是什么呢?章开沅先生曾这样指出: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探索历史的“原生态”。一是要充分运用原生态的史料,注意史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也要重视解释,追求研究对象的原生态,“历史研究的本身首先是求真求实,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原生态,就是其本来面貌,就是他们的本来面相”[18]。这对研究教育活动史是颇有启示的。所以,所谓“理想的叙事”,就是能够真正接近乃至恢复历史原生态的叙事,是有助于构建历史原生态场景的叙事。无论是小历史还是大历史,首先要看是否能够反映历史原貌的真历史;无论是叙述还是分析,首先要看是否有助于直探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真实内在联系;无论是“清明上河图”式的白描还是急风骤雨式的历史大写意,关键要看其是否透出了历史的原色[19]。
因此,教育史研究也应该倡导“叙事史”的回归,教育活动史研究既要追求教育活动历史的“原生态”,写出教育活动历史的原貌和原色,又要做到形式之美。教育活动史撰述要力求做到以叙事为主,结合分析,真正写出人民大众和学者都喜爱和乐于接受的教育活动史,从而开拓教育史研究的新的领域和美好明天!
[1]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J].河北学刊,2004,(6).
[2]Burke·Peter.Varieties of Cultrual History[M].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7.
[3]杨豫,李霞,舒小昀.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J].史学理论研究,2000,(1).
[4]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姚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李霞,杨豫.走向开放的综合——新文化史学探析[J].国外社会科学,2001,(5).
[6]李弘祺.中国教育史英文著作评介[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
[7]周洪宇.对教育史学若干基本问题的看法[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1).
[8]Giovanni levi.‘On Microhistory’.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M].Edited by Peter Bueke.University Park.PA:The Pennsyl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
[9]王晴佳,古伟赢.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10]丰华琴.对西方新文化史的阐释——历史研究中的多维视角[J].历史教学,2010,(16).
[11]于书娟.微观史学与我国的教育史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2007,(12).
[12]周洪宇,申国昌.教育活动史:视野下移的学术实践[J].教育研究,2010,(10).
[13]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赵世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4]雅克·勒高夫.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J].刘立文,译.史学理论研究,1995,(2).
[15]鲍绍霖,等.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6]陈新.论西方现代历史叙述范式的形成与嬗变[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
[17]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8]章开沅.商会档案的原生态与商会史研究的发展[J].学术月刊,2006,(6).
[19]马敏.追寻已逝的街头记忆——评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J].历史研究,2007,(5).
G40-09
A
1001-4799(2012)03-0102-04
2011-10-08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AA090143
黄宝权(1978-),男,河南周口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
雷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