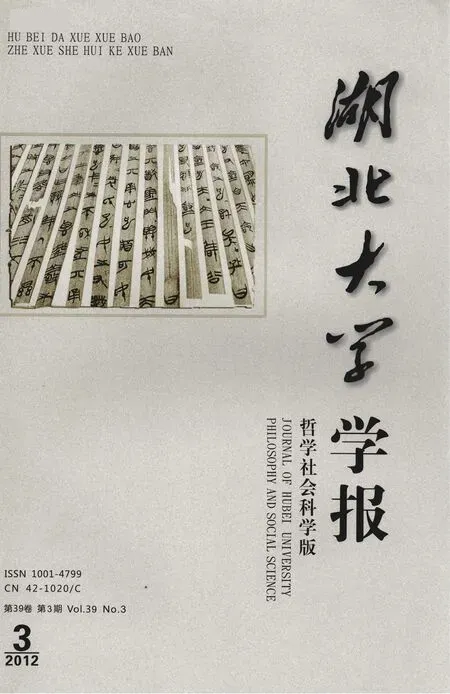论非国家行为体的健康权保障义务
邓海娟
(三峡大学法学院,湖北宜昌443002)
论非国家行为体的健康权保障义务
邓海娟
(三峡大学法学院,湖北宜昌443002)
非国家行为体在健康权的实现上理应承担义务,该义务的承担应以基本权的客观价值秩序和第三者效力理论为基础,且应以国际法、宪法、普通法和司法判例上的法律为依据。国家始终是保障健康权的基础和首要的主体,其义务中包括对非国家行为体履行健康权义务的监管。国家是实现人权义务的基本主体,国家负有对非国家行为体履行健康权义务的监管之责。
健康权;非国家行为体;义务
非国家行为体是指区别于根据宪法和法律设立的政府机构的实体和个人,包括国家之下的社会主体和国家之上的国际组织、区域性组织、跨国组织等,是对社会权保障中国家责任之外“社会”因素的强调。这与国际政治学中采用的非国家行为体指向有所区别,后者一般是指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区别于主权国家的具有独立性、从事跨国性权力竞争的作为世界政治行为体的实体。健康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即人人享有各种对于最高可能达到的健康标准所必需的设施、物品、服务和条件的权利[1]。在健康权的实现上,非国家行为体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并承担着责任。但国家始终是保障健康权的基础和首要的义务主体,其义务中包括对非国家行为体履行健康权保障义务的监管。
一、非国家行为体承担健康权保障义务的法理基础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宪法对自由权的保护大都禁止国家机关以作为方式侵犯,自由权的国家保护义务也仅以国家制定刑法、诉讼法等法律的形式履行。社会权则不同,一些国家的宪法规定“国家”和“社会”同时作为该类权利的义务主体,说明宪法从文本上明确了社会的社会基本权保障义务主体地位。
德国法上,基本权利具有两重属性,一是作为主观权利,二是作为客观价值规范。基本权利作为一种主观权利,是“个人得以主张”的意义上的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规范,是国家机关或国家一切权力运作必须遵守的一种规则。这些规则并不是个人向国家主张意义上的,因此称为客观的规则或“客观的法”。主观权利与客观规范的联系在于: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主观权利就其权利内容要求义务人遵守,权利义务对义务人而言是一种客观规范,在消极的意义上,义务人不得侵犯,在积极的意义上,义务人必须加以保障。
主观权利与客观规范的区别在于:主观权利是在个人意义上使用的,既是一种先国家和前宪法的权利,也是一种消极权利;客观规范是对社会而言的,它是社会共同体通过立法确认的规范和价值,社会中的个体和统治者有义务遵守并保证这些规范和价值的实现。正如狄骥所指出的,国家通过立法职能表述客观法或者法律规则,国家制定要求全体公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遵守的法律,该法律是客观精神的表达。客观法要求社会全体成员(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承担义务[2]。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规范属性与第三者效力理论密切相关。作为客观价值秩序,基本权为所有国家机关设置了保障义务,包括司法机关。因为司法机关的权力职责是审判普通案件,处理私人诉讼,因此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要求法院在处理私人纠纷的过程中有义务尊重基本权利。由此,基本权利的效力就由传统意义上对抗国家延伸到私人领域,体现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中,即基本权利的第三者效力理论。德国学者尼伯代(Hans Carl Nipperdey)是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他认为基本权利不是用来对抗国家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最高规范”,应该对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具有约束力。因此,在人民彼此间的私法关系上,基本权利应当具有直接的效力。如果基本权利的条文不能直接在私人间被适用,则宪法基本权利条文将沦为绝对的宣示性质。尼伯代的主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否定了基本权利仅仅针对国家,仅仅以国家为义务主体的传统模式。后来在德国取得通说地位的是不同于尼伯代的间接适用论,其代表人杜拉希(Gunter Durig)认为基本权利只能通过民事立法或者法官对于民法概括条款的解释而对民事案件发生效力[3]。但无论基本权利在私法上的效力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基本权利可以对国家以外的主体产生约束力已经成为德国公法学界的共识。这就使传统的“基本权利——国家义务”模式被修正,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开始了多元化。
与第三者效力理论相似,在美国存在“州政府行为理论”,英国存在“水平效力”理论,加拿大存在“政府行为”理论。尽管该理论在不同国家的理论基础和具体形态有所不同,但也显示出类似的主张,即承认宪法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在规范的延伸意义上亦内在地蕴涵了同时排除私人之间侵权行为的规范内涵,换言之,即基本权利可以对国家以外的主体产生约束力。非国家行为体在健康权实现中承担的义务正是以基本权的客观价值秩序和第三者效力为理论基础,作为基本权利的健康权,其客观价值秩序的属性,使得不仅国家有保护义务,各种社会组织,包括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社区等都有义务实现健康权。
对于作为社会权的健康权而言,其保障具有很强的积极属性,国家保护义务反映在法解释学上即要求国家制定大量的社会法,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因素则需要根据法律承担高于自由权的义务。总之,非国家行为体承担健康权义务是国家和社会协力实现健康权保障的问题,体现的是国家义务与社会责任的合理契合。
二、非国家行为体承担健康权保障义务的法律依据
1.国际人权公约
国际人权条约为非国家行为体清楚地设定了角色,如《世界人权宣言》在其序言中强调:“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其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序言中规定:“考虑到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负有义务促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普通尊重和遵行,认识到个人对其他个人和对他所属的社会负有义务,应为促进和遵行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而努力,兹同意下述各条。”同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健康权的第14号一般性意见第42条规定:“尽管只有缔约国家是一方当事人,因此最终是国家为遵循它而负责,社会所有成员——个人、包括卫生专业人员,家庭,当地社区,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国内社会组织和私人企业部门,都有责任实现健康权。”
2.宪法
许多国家的宪法规定国家和社会同时作为健康权的义务主体。如秘鲁宪法(1993)第11条规定:“每个人享有健康、家庭和社区获得保护的权利,每个人有义务贡献于它们的发展和保护。”卢旺达宪法(2003)第41条规定:“所有的公民有健康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有义务动员公民行动以促进良好的健康并支持这些行动的实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宪法(1990)第49条规定:“(1)所有人有卫生保健的权利和保护它的义务;(2)根据国家卫生制度,国家有义务促进公共卫生以实现公民身体和心理的良好状态及与他们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相平衡;(3)允许遵守法律的私人医疗活动。”巴拉圭宪法(1992)第57条规定:“每个老年人有获得家庭、社会和国家充分保护的权利。国家机构将通过为老年人提供社会服务、满足其食品、健康、住房、文化和娱乐以促进老年人的幸福。”阿曼宪法(1996)第12条规定:“国家关注公共卫生及预防和治疗疾病、流行病的方法。国家致力于为每个公民提供卫生保健并鼓励在其间监管下建立私人医院、综合诊所和医疗机构。国家还致力于环境保护,预防和控制污染。”[4]在我国,宪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3.普通法
普通法也对非国家行为体实现健康权的责任做出了规定。如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第4331条规定:“国会特宣布:联邦政府将于各州、地方政府以及有关公共和私团体合作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手段和措施,包括财政和技术上的援助,发展和增进一般福利,创造和保持人类与自然得以共处与和谐中生存的各种条件,满足当代国民及其子孙后代对于经济、社会及其他方面的要求。……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参与对环境的改善与保护。”日本《环境基本法》第3条规定:“把环境作为得天独厚的资源维持在正常的水平上,是人类健康的文化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第4条规定:“应当本着下述宗旨实施环境保护,即在可能的限度内,减少因社会经济活动及其他活动而对环境的负荷及其他与环境因素有关的影响,在一切人公平分担的基础上,自主而积极地去实施保护环境的措施……”同时第8条规定:“企(事)业者有责任根据基本理念,在进行其企业活动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处理伴随此种(事)业活动而产生的烟尘、污水、废弃物以及防止其他公害,并且要妥善保护自然环境……”除此之外,第9条规定了国民的职责:“国民应当根据基本理念,努力降低伴随其日常生活对环境的负荷,以便防止环境污染。除前款规定的职责外,国民还应当报据基本理念,有责任在自身努力保护环境的同时,协助国家或者地方公共团体实施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措施。”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1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水环境,并有权对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4.司法判例
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一些案件显示出非国家行为体的义务获得的重视。如印度一些矿厂和石棉厂的工人因石棉的伤害易于患肺癌和其他疾病而提起诉讼。最高法院认为宪法第21条、38条、39(e)条、41条、43条和48-A条等条款,都是为了使工人的生命有意义并以保障人的尊严为目的。无论是联邦或州政府,还是公共的或私有的企业,都有义务采取行动为工人提供相关保护措施,保障工人在职时及退休后的健康与活力[5]。还有一个关于医生是否有权拒绝为病人提供治疗的案件,法院认为,生命权意味着每一个医生,包括非为国家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有为保护生命而延伸其医疗服务的职业责任[6]。
三、健康权保障下国家义务与非国家行为体义务的关系
1.国家义务是健康权保障的基础
(1)国家是实现人权义务的基本主体。国家是实现人权义务的基本主体可以从人权思想中得以追溯,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社会契约论,成为人权及宪政史上的重要法律思想。他认为:在自然的社会状态下,人们享有一系列普遍的、永恒的自然权利,即生存、自由、平等、追求幸福,获得财产和人身、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如果自由被强力所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以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同时自然状态下存在各种弊端,人类需要以平等的资格订立契约,从自然状态下摆脱出来,建立国家,以确保每个结合者的权利得以国家保障。人民把权利转让给国家,形成国家权力,并凭借这种国家权力使自己的权利获得保障。因此,国家形成后的首要职责应当是保护人民的权利[7]。如果说卢梭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我们仍然可以在唯物主义人权思想中找到渊源。按马克思的理论,先有社会,后产生国家,是国家“吞噬”了社会主体的权利和权力,国家有义务还权于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应当对人民负责,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自由”是人类首要的基本人权[8]。国家是最基本的和首要的主体,这点在国际法和各国宪法中也得以确认。在国际人权法中,各种国家人权文书中有明确的规定,人权保障的义务主体是主权国家,各种人权公约中的几乎绝大多数条文都作了如下类似规定:“本公约缔结国各国承担……”,“ 本公约缔结各国承认……”。国际上的各种人权行动宣言对此亦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在宪法中,美国宪法序言规定:“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第三款规定:“下列基本权利拘束立法、行政及司法而为直接有效之权利。”我国宪法第33条女第3款确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等等,都阐明了国家保障人权的首要职责。
(2)旨在保障平等的社会权更需要国家承担基本职责。社会权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两大变化:一是随着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而使得社会化程度得到高度发展;二是贫困和失业以及贫富分化等资本主义弊病开始给社会投下巨大的阴影。消极自由的国家观因此遭到了空前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对国家由消极不作为的要求逐渐转化为积极作为的要求,即通过国家积极的介入和干预来保障国民社会与经济生活,以此来保障国民普遍过上最低限度的生活,使国民能够实现广泛的自由和平等。这种平等与自由权保障的机会平等不同,是要求对社会中的弱者进行特殊的照顾,进而所有人都达到自由平等的目的,是一种实质的平等。这种平等依靠自发的市场竞争不可能实现,因为在市场机制下,适用的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强调的是效率而不是公平。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私人企业、个人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社会权的保障责任,但必须与国家或者政府义务相结合,且主要责任者必然是国家。对于健康权而言,国家积极给付的义务是其权利的主要内容,因此,健康权通常被视为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对应的社会权的一部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第2款还规定了缔约国为实现该权利而应当采取的步骤,如减少死胎率和婴儿死亡率,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方面等。不仅强调了与权利对应的积极义务,且特别明晰了这种义务的主体是国家。
(3)健康的公共品属性强调了国家作为主要提供者的地位。社会所生产的产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私人产品,一类是公共产品。在理论上,率先对公共产品做出严格定义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在2004年修订出版的第17版《经济学》(Economics)中,把公共产品定义为:“将该商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分享。”从中可以推知公共产品的两个重要性质: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指的是在公共产品既定的效用下,增加一个消费者不会使该商品的供给者所承担的成本有所变化,而增加消费者后也不会使原有的消费者所获得的效用降低,消费者之间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存在竞争。非排他性指的是既有消费者无法排除其他消费者对该产品的享用,也无法将那些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这可能是因为技术上无法实现或者是因为将付出较高的成本,非排他性意味着公共产品有较大的外部效应。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市场不能成为其有效的提供主体,因为公共产品的社会边际收益要大于个人边际收益,而消费者是根据自己的边际收益来决定自己所付的价格,而不会按照整个社会所得到的利益来定价,并且无法排除那些搭便车的人,理性的经济人不会生产这样的产品,这必然导致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公共产品的实际消费者是全部的理性人,必须由可以按照社会的收益对全部消费者进行强制收费的机构来提供。在现代社会,最具有这种强制力量的是政府,政府是一个国家最高的权威,可以运用强制手段通过税收使得公共产品的成本被分摊到纳税公民身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的主要任务即“提供那些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社会成本,从而不能通过市场有效供给的物品或劳务”。严格符合萨缪尔森公共产品定义的产品很少,最典型的是国防,有些产品部分满足公共产品的定义,即或满足竞争性和排他性其中的一个,或某一部分满足定义,这样的产品称为准公共产品。卫生设施、服务及商品的消费因为仅具有非排他性,而不具有非竞争性,因此属于准公共品。准公共品由于只是部分具有公共品的性质,政府可以只承担部分的成本。但由于健康问题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政府应在其供给中起基础性作用。除了以财政作为保障健康权的有力后盾之外,还应承担起监督责任,保障公民公平地获取各种健康条件。所以,健康权无论是作为一种基本权利,一种社会权,还是作为一种准公共品,其实现都是以国家作为首要的、基本的义务主体。除此之外的主体义务是补充的、第二位的。
2.国家负有对非国家行为体履行健康权义务的监管之责
由于非国家体也承担健康权义务,他们因此被期望通过对保护、促进和实现健康权给予充分的注意以遵守健康和人权标准。无论是在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内,如倡导或提供服务,还是在他们的内部工作程序和行政管理之中。因此,为确保这一点,国家就有必要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有关行为进行监督。如玻利维亚的政府曾面临在严重的财政困难下为一重要的城市提供饮用水的困境,政府为此向国际机构要求经济援助,获得了有条件的贷款,即这项服务必须私有化。一个跨国公司在公开招标中取得这个项目,但很快地,该公司把供水的价格提高到当地数量众多的穷人无法承受的地步。之后公众上街示威,迫使政府最终收回了所有权[9]。该事例反映出政府监管的缺位和为此造成的消极后果。事实上,在健康领域,私人提供已经在全球卫生市场上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包括一些高收入国家,但这些国家与私立提供者的合作往往是与管制紧密结合的。这种管制包括能力、质量、价格、服务水平和应有权利等方面。相反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私立医疗提供者很多时候未受到管制或管制不当,使人们很容易受到不安全的医疗行为的影响。现在,为使健康权保障获得显著进展,在任何国家背景下,如何选择最佳管制机制都成为了一个焦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曾要求卢森堡提供使用公共资金提供服务的私有部门如何被监管的信息,儿童权利委员会也指出私有化的服务会影响到儿童权利,国家和私人部门因此产生法定义务。它特别强调:“私人部门提供服务并不影响国家在其管辖范围内确保儿童权利公约中所有权利的充分实现……,这要求监督,为此应存在一个持续的监督机制或程序以确保提供服务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尊重公约。”私有提供者由于以追逐利润最大为目标,与健康的公益性有所冲突,因此在国家监管上往往得到更多的强调。但受监督的主体并不限于此,非政府组织和从业人员也应包括在内,信用缺失,腐败、不遵守职业规范等问题都会造成对公民健康权的损害。
总之,在健康权的实现上,由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发挥作用的模式已日渐清晰。探讨非国家行为体的义务因此成为十分必要的问题,正如B.特贝斯(B.Toebes)所指出的,对国家之外的实体承担人权责任进行研究是健康权发展的前景之一,也是挑战之一[10]。
[1]岳远雷.论公民健康权的国家基本责任[J].中国医学伦理,2007,(6).
[2]莱昂·狄骥.宪法学教程[M].王文利,等,译.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3]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Eleanor D.Kinney,Brian Alexander Clark.Provision for Health Care in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d[J].Cor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04.
[5]曲相霖.外国宪法事例中的健康权研究[J].求是学刊,2009,(4).
[6]郑贤君.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兼论社会权的国家基本保护义务[J].浙江学刊,2009,(1).
[7]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刘霞.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及其现实意义[J].党政论坛,2005,(5).
[9]Adam Mcbeth.Privatising human rigts:What happen to the state's human right duties when services are privatized?[J].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4,(5).
[10]B·托贝斯.健康权[M]//A·艾德.C·克洛斯.A·罗萨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教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D922.1
A
1001-4799(2012)03-0091-05
2011-05-1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研究项目:11YJC82001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2011jyty098
邓海娟(1974-),女,湖南武冈人,三峡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
朱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