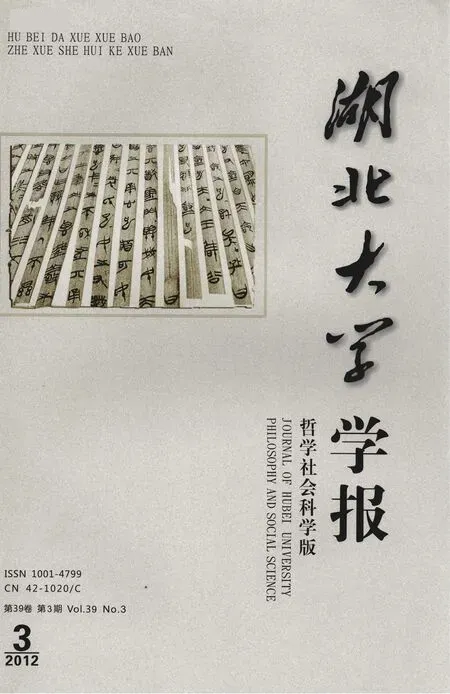张之洞道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与洋务事功
万国崔,何晓明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张之洞道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与洋务事功
万国崔,何晓明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张之洞是晚清儒家道统复兴阶段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仁礼兼重的道观、“中体西用”的功用观构成其道统思想。其“中体西用”功用观秉承龚、魏、曾诸公“经世致用”的精髓,以其首创的现代意义而居现代儒家道统论开基立业之功,并以此成为“返本开新”说之滥觞。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到现代儒家“中体西用”的转变,而推动此进程的决定性物质力量是洋务事功。督晋期间与李提摩太的交往,启动了张之洞对“洋务”的接触、认识,而后在广东、湖北的成功洋务实践,更直接促成了其功用观的转变,并进而实现了其儒家道统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定立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基调,从而使其道统思想在晚清道统复兴阶段起到了理论枢纽的作用。
张之洞;现代儒家;道统思想;仁礼兼重;“中体西用”;洋务事功
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洋务事功之践履者、“中体西用”思想之开创者,近世学人之研究成果丰硕,亦大有探析其卫道精神、经世实学者,而从现代儒家道统论者的角度研究者却不多。张之洞作为晚清体用派的代表人物且被界定为现代新儒家道统论之早期接续者一说,《返本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1]一书中已有详论。其后,有吉林大学石文玉之博士论文《儒学道统与晚清社会制度变革——张之洞〈劝学篇〉研究》[2]、任晓兰之专著《张之洞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3]对此亦略有论述。石文玉认为张之洞作《劝学篇》意在捍卫儒学道统,以应对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对儒学道统数千年根基的动摇。任晓兰亦是肯定张之洞对儒家道统论之续接,认为其经世致用思想即是对儒家道统的固守。兹借前述学人之光芒继续前行,对于作为现代新儒家道统论早期接续者之主要代表人物的张之洞,以现代新儒家道统论时期之“唐韩”定论,对其道统思想从理论架构的角度予以分疏析理,并予历史定位,且进一步探析其道统思想的发展与洋务事功的密切关系。
一、道统思想:仁礼兼顾与“中体西用”
嘉道以降,国是日非。吏治腐败,贿赂公行,局面难以收拾。官吏士民,狼艰狈蹶。财政困窘,经济极为凋敝。且军备废弛,暮气沉重,不堪任用。此期土地兼并严重,贫富不均日甚,以致社会危机四伏。朝野上下呈现出一番“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4]87的衰世景象,而康乾之时“百宝万货,人功精英”、“府于京师”之盛况不再。正如时人所言:“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5]9且士人专以考据词章、八股帖括为业,学风务虚,琐碎、空洞。值此晚清衰世,儒家之道不明已久矣,为了挞伐异端,收拾人心,此期儒家学者如龚、魏、曾、张等奋起,而拾坠先圣所创传之儒家道统,犹如“唐韩”开宋明儒道统论之端绪一样。晚清疆臣张之洞承龚、魏、曾之后,以复兴儒家道统为己任,切实践履,而成其仁、礼兼重之宽泛道观,并首创颇具现代意义的功用观——“中体西用”说。
无论时代如何更新,先秦原始儒家道统论,宋明儒学道统论抑或现代新儒家道统论,其所以阐发其道统义理的形式载体,即儒家道统论之理论架构,可从道统观和功用观两方面来看。道统观包括道观和统观二者,道观即道统论者对道的解悟、自认。统观则为对道之垂统,即关于其所崇尚、宗主的先贤人物系列的论说。道统观是统绪之所在,是就其承续义而言的。功用观亦可谓之为外王说,是儒家道统论为响应时代需求,解决时代问题而遥承周、孔、孟、荀之道的精髓,吸纳或生发时代新内容所形成的理论构想,即道统论者对道统之新时代之社会功用的理论建构和设计,这是从其发展义来论的。道观、统观、功用观三者三维地传播、承续,整体地构建着儒家道统。这里从道观、功用观两方面来论述张之洞的道统思想。
自孔子始儒家道统论就有明确的道观,孔子有内仁外礼复合型道观,孟子以仁义为道,荀子则以礼义为道。迄唐韩尊承孔孟仁义之道,经二程发展,以天理为道,朱子集其大成,创理学道统论,陈亮、叶适径承周孔,以外王事功为道,陆、王承二程余绪,成其心学道统论。曾国藩、张之洞二公感于时势,效法“唐韩”,“文以载道”,竟现代新儒家道统论开局之功。然其所承之道不像前圣诸贤那样,以狭义道观成其论,而是仁、礼二者兼顾的。
承自曾国藩仁、礼并重道观,张之洞所承儒家之道亦是仁、礼兼顾,其对于道统的接续已不止于孔孟、程朱、陆王、事功等一派一系之论,而是提出宽泛义的道观。他指出:“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6]9707兹道是“五帝三王”所开创,“孔、孟、程、朱”所阐发、传承,“汉、唐及明”以及“我朝”所“躬行实践”的,即“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6]9715。其所承续的是宽泛意义上的儒家之道。“政教相维”乃其宗旨,即道的功用。立足“政教”,则可“治身心、治天下”。此道载于六经,“经学贵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6]9725。“大义”即道,以约见博,“守约通博”。然“沧海横流,外侮荐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浸微浸灭,虽无嬴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矣”[6]9725。这些议论体现出张之洞强烈的忧道、续道意识。
功用观是儒家道统论之一重要理论部分,它与作为本体的道形成体用关系,是道施之于万物、人生、社会、政治所成的功用,“道,体乎物之中以生天下之用者也”[7]1。“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8]25。文以载道,道以致用。孔子“为政以德”,孟子以仁政、王道为其功用观,荀子崇尚王霸杂用。晚清之际,内外交困,国事日非,异族环踞。张之洞深怀“亡国”、“亡天下”之忧危,认为“国家”不保,则“圣教”难继。且“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6]9797,儒家之道固然重要,然“要其终也,归于有用”[6]10076。遂倾心于儒家道统之复兴,先后以经世致用、“中体西用”构建其功用观。
张之洞秉承龚、魏、曾经世致用之精髓,以“中体西用”成其功用观。“中体西用”说与被称为传统外王说之终结的曾国藩“经济之学”存在着某种本质上的关联与承接。在《劝学篇》中,张之洞指出:“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6]9707道统与政统紧密相维相系,功用观的精心构建以保国祚之不辍,而唯有政统延绵方能光大道统。“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6]9725。迫于时势,张之洞将引进西学作为其所传接、坚守之道的功用,即突破传统外王说之藩篱。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之洞以其“中体西用”说,勇当疗治时弊的“医国手”。兹说所涉“西用”于提出之时只是限指坚船利炮之器、百工之术,但其中蕴含有科学精神,至张之洞系统阐释之际,已关涉益智而去迷昧、游学外国(“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广立学堂,储为时用”、“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之西方学制、译西书、阅西报、“变科举”、“养民在教,教农工商”、设“兵学”、设“矿学”以及修“铁路”等等,虽看似仅于教育、经济体制为主,然已由器用进入学、制之域。科学精神的培养和教育、经济体制的草创,为国人由单一的道德主体向认知主体、政治主体的转出和自觉兼立扫除了障碍,从而为引进西方科学、民主之内在根据准备了思想和制度的前提。可以说,张之洞道统思想之功用观即是以“中体西用”为准则来引进西学,其旨即在以西学之强助襄晚清朝政,再以皇权之盛保儒家之道不坠于中华。此举乃是其仁礼兼重的道观之立足于学、政之现实功用,这相对于曾国藩道统思想之传统“经世致用”式功用观或外王说来讲,颇具现代意义的“中体西用”足可称为现代新儒家道统论的新外王说。儒家道统论体系与“中体西用”说皆各归属于中国传统体用范畴之一义。而相对于现代新儒家道统论者的“返本开新”新外王说而言,“中体西用”居现代儒家道统论的开基立业之功。
二、洋务事功助推道统思想转型
张之洞道统思想的“中体西用”功用观以其初具的现代意义掀开了儒家道统论现代时期的序幕。然其道统思想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或猝然临之,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以至于转化的过程。在此功用观的转化进程中,对洋务事功的了解和效仿起到决定性作用,即推动此进程前进的物质力量就是洋务事功。换言之,张之洞所开创的“中体西用”功用观对于其兴办一系列洋务实业的指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督晋期间与李提摩太的交往,启动了张之洞对“洋务”的接触、认识,而后在广东、湖北的成功洋务实践,更直接促成了其道统论功用观从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到现代儒家的“中体西用”的转变。
作为晚清道统复兴阶段传统儒学饱学之士的张之洞,其早期道统思想与曾国藩“内圣外王之业”、仁、礼并重之道观、“经世致用”之传统功用观并无二致。成书于光绪元年的《书目答问》是张之洞早期在四川学政任上所撰写,是一部旨在指引学子读书、治学门径目录书学举要之专著,其早期“经世致用”之功用观在此体现犹为明显。在《略例》中,张之洞提出“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6]9797的读书、治学原则,并进一步论证之,“书,犹谷也:种获春榆,炊之成饭,佐以庶馐,食之而饱,肌肤充悦,筋骸强固,此谷之效也。若终岁勤动,仆仆田间,劳劳爨下,并不一尝其味,莳谷何为?近人往往以读书、明理判为两事,通经致用视为迂谈,浅者为科举,博洽者著述取名耳。于已无与也,于世无与也,亦犹之获而弗食、食而弗肥也。”[6]9797因此,“苟有其本,以为一切学术沛然,谁能御之?要其终也,归于有用”[6]10076。文以载道,功用至上。此为何等功用?“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6]9793。兹修、齐、治、平式的“经世致用”仍未超出传统儒家道统论功用观之藩篱。
督晋期间,张之洞所行政之作为皆不出当时清流派官员之行则,俨然一派传统儒家修、齐、治、平之风范,实乃传统儒家道统论“经世致用”功用观之践履者。张之洞以治国、理官、养民为国之三务,其见略并未超出儒家传统功用观“德政”、“仁政”的范畴。他认为:“国之元气,在户口蕃息,田野垦辟,政事有纪纲,经赋无侵盗,而聚敛吝音不与焉。民之元气在官,吏无苛扰,四民无游惰,而末富奸利不与焉。官之元气在官项无亏累,上司无诛求,贤否不颠倒,功过有黑白,而滥恩曲法不与焉”[14]101。他提出,循此行则而治晋,“大抵晋省要务二十事:……务本以养民。……养廉以课吏。……去蠹以理财。……辅农以兴利。……重士以善俗。……固圉以图强。”并说明“凡此皆儒术经常之规,绝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14]102。张之洞认为治理疆土无外乎“责垦荒”、“省差徭”、“除累粮”、“储仓谷”、“裁摊捐”、“杜吏奸”、“救盐法”、“开地利”、“练主兵”、“遏盗萌”等等“儒术经常之规”,舍此而无它。而此等“清官累、厉廉洁、苏民困、核蠹弊、除吏奸等事,皆中法,非西法也”[6]10141。
清流人士一般对于所涉洋务一切,诸如各国外交、军工企业、近代学校等,无论黑白都予抨击,而作为清流派领袖的早期张之洞却并非如此。籍此态度,督晋两年有余(光绪七年底至十年三月),随着张之洞对“洋务”认识的提高,其道统思想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促成张之洞道统思想之功用观从传统“经世致用”向“中体西用”飞跃,首先是得益于他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交往。李提摩太传播西学的方式有类于利玛窦,即是以西学向中国高层士人群体渗透。他向张之洞及在晋各官绅推介并演示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诸如地理、天文、医药以及声光化电等科学理论,这无疑深化了张之洞对于洋务以及“西技”、“西艺”的认识。其中李提摩太常常提到一个理念,即“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15]28,这让深谙儒家义利之辩的张之洞犹如醍醐灌顶,幡然有悟。
经历李提摩太之西学熏染之后,张之洞对于“洋务”则大有愿闻其详之意和畅抒己见之愿,甚至是切实作为之欲。在致清流名士张佩伦的书札中,他曾谈及,“鄙人僻在一隅,大事都不闻知。《防海新论》交议未及,大约止沿海及本省耳。如蒙朝命,洋务亦许与闻,下采刍荛,则当抒其管蠡,不致后时发议,徒为不切题之文章也。”(光绪八年)[6]10142,然而,从张之洞任晋抚之前的一些折、片里,可以体会初其对于“洋务”态度的变化。在其1880年的奏折里,张之洞将对“塞外”、“泰西”夷务之习练和仿效尚置于次要位置。“得其人则皆胜算也,不得其人则尽空文也”[14]42,这就是说,只要朝廷广纳“奇杰之才,不拘文武”,则可解决边患争端。此“才”只是传统意义之“边才”,他认为“边才”之培养“非本天生,皆由习练。疆圉孔棘之秋,正磨练人才之具。我朝平准、回,平金川,平川、楚教匪,平粤、捻,每办一次军务,即出一次人才”,这亦正是传统“边才”的历练之法。“足食足兵,量能授任,南船北马,用所长,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光绪六年)[14]42,认为夷之长技可为我用,然并未予以足够重视。虽此期张之洞已颇为关注西人海战之术,“宜发《防海新论》,令各营讲习。近年西人著有《防海新论》一书,……分发诸将领,细心讲求,触类引伸,必有实效”[14]51。然其御敌战略之重心仍停留于传统战法,他在上折中总结道,“综而论之,欲御洋人断以讲陆战、扼内河、截后路三者为要义,伏祈圣明裁度施行。”(光绪六年)[14]51张之洞初任晋抚前后,其对于“洋务”的认识和态度的变化已清晰可见。
在李提摩太向张之洞展示其诸如磁石吸铁、氧气助燃以及“别西墨炼钢法”等西洋技、艺之后,李提摩太遂成为张之洞在晋初办洋务实业的顾问。进而,1883年(光绪九年),张之洞在晋“悉心筹议,即于东门内新买金姓房屋,设立洋务局”[12]2399。首先,他在各省延访“涉于洋务”、“习知西事”之才,“举凡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汽诸端,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各省局、厂、学堂,人才辈出,搜长者当不乏人,已咨请选择,资送来晋”(光绪十年)[12]2399。并且,“先就晋中通晓洋务之人,及现已购来各种洋务之书,研求试办,详立课程,广求益友。如有试造新式各器,不得吝惜工料……所有新出关涉洋务各书,随时向津沪购买,……令其在上海购买外洋新式织机、农器数种前来,以为嚆矢”[12]2399。开设洋务局正是张之洞一生洋务事业之“开端”。同时,他开始关注西方各国之“政令”、“学术”等等。“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周知各国特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为根抵,以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为入门”[12]2400(光绪十年)。此时的张之洞已深刻地意识到,“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12]2400(光绪十年)。此语之出仅为“洋务亦许与闻”之后的两年,然其对于“洋务”紧迫性的认识已上升至理论的层面。这种高度是以其对于西方各国之“政令”、“学术”的查知,以其治晋期间依据李提摩太之“西化”主张中兴办实业的具体方案和措施而试办洋务实业为积淀的。作为幕僚的辜鸿铭对此期张之洞思想之转向有如下评述:
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长,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长也。……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13]166
“为国则舍理而言势”可对应于张之洞所言“西学为外学,……西学应世事”[6]9764,而“为人则舍势而言理”一语则可以其“中学为内学,……中学治身心”[6]9764释之。张之洞“中体西用”之功用观的思想光辉隐约闪烁其中。
此后,在中国兴办洋务事业以为用的想法遂占据了张之洞功用观的主导地位。而贯彻实施李提摩太兴办实业的具体方案和措施又促成了张之洞现代功用观的初成。张之洞督晋两年有余,期间初办铁业、修通山西榆次什铁镇至直隶获鹿县土门口计约三百八十余里的公路、“悉择防勇之精壮者挑补,仿直隶章程作为练军”[14]146,即试办山西练军。在晋初办洋务的尝试使得张之洞兴办洋务事功的政治生涯从此发端,而更为重要的是,指导其在后来两广、湖广总督任上成就兴办民族工业、编练新军等洋务实业的主导思想即“中体西用”之雏形正是在此期形成,张之洞道统思想籍此完成了其儒家道统论之功用观从传统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向现代“中体西用”的转化。
三、历史定位:枢纽与滥觞
洋务事功成就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功用观,从而使其道统思想在以曾、张为代表的晚清道统复兴阶段,乃至整个现代新儒家道统论发展时期皆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张之洞道统思想是将晚清道统复兴阶段之所以归属于现代新儒家道统论发展时期的主要因素,其道统思想实现了儒家道统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现代转型的枢纽即是其道统论之功用观从传统“经世致用”到现代“中体西用”的转化。张之洞道统思想以其秉承龚、魏、曾诸公“经世致用”之精髓所创建的、颇具现代意义的“中体西用”功用观,实现了儒家道统论在晚清道统复兴阶段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使得以曾、张为代表的晚清儒家道统复兴阶段道统论思想位居现代新儒家道统论发展时期之列。可以说,张之洞道统思想在以曾、张为代表的晚清道统复兴阶段起到了理论枢纽的作用。
兹所言道统复兴是指清道咸以降,宋明以来的儒家道统之不继、不振已久矣,西风东渐,人心不古,大有天下危亡之势,承继、复明先秦、宋明之儒家道统正当其时。道统复兴阶段涵盖自嘉道以迄清末这一时期,此期国运衰败,世风日下,士气不作,曾国藩、张之洞等儒臣率先而起,犹“唐韩”然,而秉复兴儒家道统之帜,力倡文以载道,道以致用。
曾国藩在其著、文、书札中表现出强烈的儒家道统接续意识。道咸之际,太平军兴,毁儒弃道,“金陵文物之邦,沦为豺豕窟宅。三纲九法,扫地尽矣”[9]1579。他们截取“耶稣之说”、“《新约》之书”而成其上帝教。对此,曾国藩疾首蹙额,“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他疾呼:“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9]1579。当其奉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之时,他郑重申明,“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9]1579。可见,曾国藩以捍卫儒家道统相号召,以孔孟人伦、礼义名教之担当者自任。
曾国藩以仁、礼为其所接续儒家之道,俨然直承孔子内仁外礼的复合型道观。“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礼并称。盖圣王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9]1615。他强调,“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10]39,内圣、外王不可偏废,守此仁、礼之道,其功用方有可为。唯以身践行其道,成其功用,方不负《大学》之旨。“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白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10]39为此,在前贤对孔孟之学以义理、考据、词章三科相概括的基础上,曾国藩增经济一科阐发之。“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此四者缺一不可”[9]4867。程朱理学以言义理性命见长,而忽于考据、词章,于经世致用之学犹略。曾国藩承其道,明其体,而畅其用,专设一“经济之学”以概之,足见其对儒家之道功用观建设的苦心孤诣。曾国藩功用观体现着传统外王特色,于政主张德治、爱民、廉政,于军则强调恩威兼施。可以说,曾国藩道统论之功用观是儒家道统论传统外王说之终结。“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10]22。其所行之道,仁义也,施之于身、于政,则有所成。曾国藩将其内仁外礼之道身体行之,于带兵、为政皆有所得。他认为,“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11]133。对于百姓,当以仁心爱之,“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此心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10]369。他注重社会教化,将求以德化人。“为人上者,专重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7]681。在对于太平军起因的分析中,足可见其对民间疾苦的体察,“推本寻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非一朝一夕之故矣!”[10]77
曾国藩接续传统儒家道统,以仁礼并重的道观开现代儒家道统论多元、宽泛道观之端绪,其“经济之学”以及德政、仁政之说实为传统儒家道统论功用观收官之论。然其论仅止于此,则晚清道统复兴阶段尚不足居现代儒家道统发展时期之列,此阶段道统思想亦难负儒家道统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之继往开来的枢纽理论之盛名。张之洞以其颇具现代意义的“中体西用”说为功用观,立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之基调,以为“返本开新”说之滥觞。可以说,传统儒家道统论向现代儒家道统论的转型由曾国藩启其端,而竟其功者则是张之洞。
张之洞之“中体西用”说具有联结儒家道统论传统与现代的枢纽作用,可从两方面予以阐释。从体用说与儒家道统论体系之关系看,所谓体用之义,在此借用相关学者的论述:“体与用,不仅有本体与现象的含义,还有本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意蕴,作为通常用语,又有主与辅、本与末的意思。”[16]395由此可知其义有三:一曰本体与现象,或本质与现象。如:“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礼·序》),“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庄子·知北游》)“凡有貌相声色者皆物也。”(《庄子·达生》);二曰本体与功用,或实体与功用。如:“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荀子·富国》)“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三曰主与辅、本与末。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论语·子张》)“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具体而言,本体与现象,二者绝非相离或对立的二物,而是统一的、一体的,所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程氏易传·序》)。以及对于“中体西用”之“体用两橛”、“体用不二”的责难正是其义。这迥异于西方哲学之本体与现象对立的两个世界之说法。对此一义,可用源与流、根与枝为喻;本体与功用说则是论述道与其于百姓日用间、天地万物中所生发之功用的关系,即“道,体乎物之中以生天下之用者也”[7]1。从儒家之道与其功用的关系看,宋儒道统论者有言,“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8]25。“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即是指“圣人之道”的社会、政治功用。对此,王夫之强调“体用相函”,“无车何乘?无器何贮?故曰体以致用;不贮非器,不乘非车,故曰用以备体”[7]198。儒家道统论体系之道观与功用观或外王说即是“体以致用、用以备体”的关系;主与辅、本与末之说则更着意于次序、轻重,如“洒扫、应对、进退”只属农圃医卜之类的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但无本,“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不可因末失本,犹如“绘事后素”之喻。“中体西用”的提法就是“从‘主’与‘辅’、‘本’与‘末’这种约定俗成的日常用法上发挥”[16]396。可以看出,“中体西用”与儒家道统论皆各为中国传统体用范畴之一义。
作为儒家道统论的功用观,“经世致用”、“中体西用”、“返本开新”三者存在着必然联系。有学者说,“一定意义上说,‘中体西用’是‘通经致用’的发展和结果”[17]91。“经世致用”是传统功用观,即传统外王说之要义。迄张之洞们则深知学习西方之势趋必然,道之功用必然涵盖着对西学的引进。现代新儒家道统论诸公虽然已在道的本体构建、体系完善方面吸纳西学之优长,但只是以康德、维也纳学派等逻辑、架构来重建现代道统论,儒家道统论其“本”尚在。“开新”则围绕着如何整套地引进科学、民主所作设计,这与体用派“体用两橛”之弊已不可同日而语,然作为同样以引进西学为其功用之圭臬两种学说,“返本开新”无疑是对“中体西用”的承接与发展。所以说,“中体西用”是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说的滥觞,是连接儒家道统论新、旧外王说的过渡、枢纽理论。
[1]何晓明.返本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石文玉.儒学道统与晚清社会制度变革——张之洞《劝学篇》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8.
[3]任晓兰.张之洞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5]张穆.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M]//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
[6]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7]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M].李鸿章,校勘.宁波,等,校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1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5.
[11]蔡锷.曾胡治兵语录[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
[12]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四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3] 辜鸿铭.清流传[M].语桥,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14]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一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5]孙铁.影响近现代中国的50位外国人[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
[16]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7]张昭军.传统的张力——儒学思想与近代文化变革[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K249
A
1001-4799(2012)03-0106-06
2012-03-05
万国崔(1971-),男,湖南辰溪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何晓明(1951-),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研究。
邓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