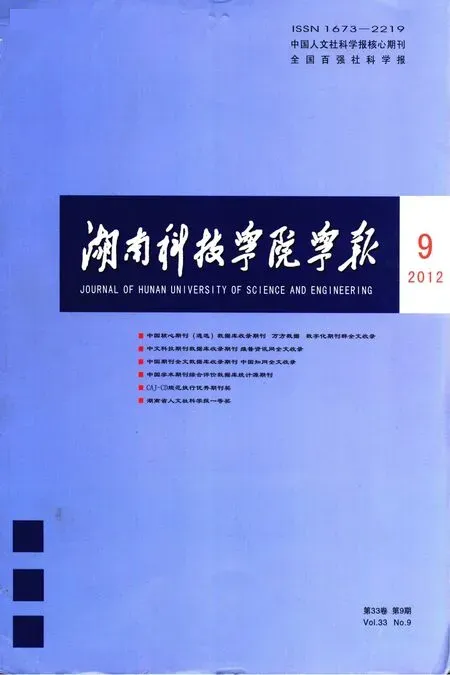从反垄断法宗旨看行政性垄断主体之规定
比干尧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从反垄断法宗旨看行政性垄断主体之规定
比干尧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行政性垄断是中国反垄断法制定时的焦点问题,也是公认的难以解决的反垄断难题,虽然我国《反垄断法》明文规定了行政性垄断,但是在实践中,基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原因,以行政长官个人意志来进行实质上的行政性垄断的情况时常有之,但是反垄断法却无法进行规制。应该从反垄断法的宗旨出发,严厉打击利用公权力来实现私人意志的行为,并对行政性垄断的内涵予以厘清。
行政垄断;行政机关;行政性垄断主体
行政性垄断,顾名思义是与行政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垄断行为,虽然我国反垄断法并没有使用行政性垄断这一说法, 而是使用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表述,当然也没有就什么是行政性垄断作出相关的定义,可是学界对行政性垄断的定义大多相似:所谓行政性垄断,就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一种违法行为。[1]323行政性垄断是指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2]315出于表述的方便,本文将对行政性垄断行为与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对行政主体和行政机关与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职能的组织做同一理解。
对于行政性垄断的研究,首先应当明确的是行政性垄断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行政性垄断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主观和客观三要件。其中主体要件指地方政府和中央、地方政府部门,主观要件指行政权力的滥用,客观要件指对竞争的实质限制[3],有学者则认为,行政性垄断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四要件。其中主观要件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垄断及其后果所持的主观心态,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况,只是在司法实践中,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不管是有意实施还是无意实施的,抑或是误解法律实施的,都应视为有明显的主观过错。[4]48而较为普遍的观点就是行政性垄断的构成要素应该包括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三方面。可是到底行政主体包括哪些主体,大多语焉不详而仅仅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阐述。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政性垄断的主体就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
因此笔者个人认为,所谓行政性垄断的定义学界各种说法殊途同归,其本质就在于行政权力不恰当地介入了市场经济行为而导致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故可以定义为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这一定义是比较简洁的,也是与我国反垄断法相吻合的。所以对于行政性垄断的构成要件,三要件说与四要件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关键在于理论中如何去定位行政性垄断的主体要件中的行政主体的概念是否真的能够涵盖行政性垄断的实施者。
一 对现行反垄断法规定的行政性垄断实施主体的质疑
行政主体,作为一个行政法学中的重要概念,是很多国家法律中有着明文规定的,比如法国行政法中的行政主体就是指具有行政权能,并能负担由行政职权所引起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它包括国家,大区,省,市镇,公务法人。在德国也有相类似的表述,含义基本相同。在我国,行政主体即是拥有行政职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的能够独立承受实施的行政行为所引起的法律效果的组织。这一定义在行政法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也不存在很多的争议,但是我国反垄断法上对于行政性垄断的实施主体限定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实际上也就是限定了实施行政性垄断的行为主体只能是行政主体,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这一点的合理性值得怀疑。
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主体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其中应当明确的是行政机关是不包括中央行政机关的,因为中央行政机关的行为属于国家行为,是应该被豁免于反垄断法之规制的,这一点没有疑问。问题在于,反垄断法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主体规定得过窄,将行政性垄断的适格主体限定为了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也就是将主体限定在了公法人或者准公法人的范围,而排除了自然人作为行政性垄断的主体的情况,导致有很多行为虽然是借助于行政权力排除限制了竞争,却会产生由于主体不适格往往不能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的情况。比如说我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这是一种滥用行政权力强制交易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之中,这种利用行政权力强制交易的行为比比皆是,如办理身份证必须到指定的照相馆照相取像,办理工商营业等级必须到指定的印刷点复制打印等等,这些行为往往是以行政机关单位的推荐或者直接的命令式的形态出现的,通常人们也会认为这就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的意志或者行政行为,而我们往往忽略了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这种推荐或者命令行为其实并不是行政机关作为一个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行为,而是单位内部某个领导人的纯个人意志而导致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往往是出于领导者个人为自身利益或者为与自己有某种关系的经营者或单位谋利而做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个人意志既非履行职权的行为,也不是经过单位内部正常程序而确定下来的行为。根据大陆法系有关行政行为的界定,个人行为要被视为是行政行为,就必须具备有权代表单位、是履行职权的行为、外观上必须能把个人行为与单位联系起来这几个要素,所以上文所述的这种领导人的纯个人行为不能视为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但是在实践之中,这种单位领导人的纯个人行为,却以整个单位滥用行政权力而做出的行为的面目出现,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反垄断法是否可以对这种领导人的个人行为进行规制呢?
首先,根据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从法条中我们很明显就可以发现,反垄断法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适用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从法定主义的角度来看,行政垄断的适用主体则上面所述的这种单位领导者的纯个人行为并不能适用反垄断法,而此种行为却是实实在在地利用了某种在行政体系里的个人行政权威或者潜在的个人的行政性质的权力所实施的反竞争行为,具体地说就是在目前中国的行政体制内,领导者个人的意志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威慑力,使得单位及其组成人员不得不按照或者也乐于按照其意志实施各种具体的职权行为,这就形成了一个法律上的空缺或者死角,使得这种实质上利用了行政权力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得不到反垄断法的规制,而被这种行为所侵害了合法利益的相关经营者又找不到其他有效的救济途径,实践中有关对此种行为的救济充其量也就是由行政主体的上级部门或者管辖部门对其作出批评并责令改正,但是鉴于我国行政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真正能够实现有效救济的经营者往往是凤毛麟角,更勿论对有关经营者由于此种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的赔偿。
二 反垄断法宗旨对行政性垄断主体之要求
各国反垄断法都有不同的立法宗旨和目的,即使在同一国家,也会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对反垄断法产生不同的认识,比如欧盟的反垄断法立法宗旨就是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美国,其反托拉斯法的立法宗旨也是在追求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福利、提高社会民主化程度三个目标。我国的反垄断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表现了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就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多元化目标。这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重点是我们应当从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出发,来探求立法中什么样的适用主体是更契合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的,这样才能更符合反垄断法的原意,也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反垄断法的精神。
从我国的反垄断法立法宗旨来看,反垄断法是为了追求一个公平的市场秩序,是为了能够增加消费者的福利,是为了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那么在现今中国行政垄断大行其道、地方保护主义日渐猖獗的时候,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大宪章”理应对行政性垄断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种清醒的认识就是:在当今中国行政体制之下,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根本就不能局限于某个行政主体的单位行为了,而是单位行为和个人行为夹杂发生,甚至个人行为掩盖单位行为,或者说是个人意志凌驾于单位意志之上的行为,而且领导者个人行为的危害往往更为严重,因为这种个人行为通常因为里面包含了不正当的利益牵连而使得这种行政性垄断行为的实施力度与强度更为彻底,对市场秩序的侵害也更加严重。
从保护竞争秩序的角度看。这种个人行为与行政主体所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是有所差异的,行政主体所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通常是明示的,或者是以公开文件的形式进行,往往还动用了各种行政力量来进行辅助。比如地区封锁行为中,地方政府往往会采取红头文件进行命令式的管理,采取突击检查、查封、没收、罚款等方式对销售当地政府所限制的外地商品的经营者进行处罚,这种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是很显而易见的,往往也是最容易认定的,因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只要是行政主体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或者更为极端地说,只要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都无法做到完全隐秘,因为一个行政行为的实施必须以对相对人的公开为前提。而领导者的个人行为则可以完全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所谓“潜规则”面目出现,无需公开的文件,也无需动用什么国家力量就可以达成,这其实是在中国官本位思想指导下的一种行政权力异化的表现,但是只要是这种行为侵害了竞争秩序,就理应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
从保护经营者的角度看。虽然我国反垄断法第一条有关立法宗旨的条文中没有出现对经营者的保护的字样,这主要是因为立法机关为了突出对消费者的保护的考虑,担心经营者和消费者发生利益冲突时候面对法律条文的无从选择,但这并不是说我国的反垄断法就不含有保护合法经营者的宗旨,实际上从反垄断法出现开始,对合法经营者的保护就是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之一,我国也不例外。领导者个人的行为破坏竞争秩序对合法经营者的利益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最直接的就是这种行为让受到特权保护的经营者取得了不合理的垄断地位,而这种垄断地位并不是通过合法经营、通过提升效率、改善服务获得;其次,这种不合理的垄断减弱了经营者进行创新、改善服务、提高质量的热情,使得竞争畸形化,以领导的指示作为竞争目标;再次,这种个人行为会衍生出其他如腐败、受贿等问题,也从另一个方面减少了合法经营者的利润或者说增加了他们的经营成本。既然领导者的此种个人行为确实损害了合法经营者的利益,那么也就应该被反垄断法所禁止。
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看。正是因为行政性垄断最终侵害的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体来说就是消费者的合理选择权,而领导者排除限制竞争的个人行为也是能够达到和行政主体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同样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个人行为的危害性更大于行政主体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因为行政主体的限制排除竞争行为具有公开性,在程序上也有一定的要求,故而受到行政主体保护的经营者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的质量也会受到一定的要求;而领导者个人行为导致的特权经营的经营者因为没有受到正常的公开性监督,其产品或者服务质量常常令人堪忧。故而反垄断法规制此种领导者的个人行为也是在终极意义上保障消费者权利的有力措施。
从促进经济有序健康发展的角度看。由于领导者所为的排除限制竞争的个人行为已经不单单是关乎其本身利益的事情,而是由于其个人行为而使得本来应当是行政主体所为的行政行为发生了质的变化,那就是以个人行为代替了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而且这种个人行为具有强烈的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使得某些关系经营者具有了不恰当、不合理的垄断地位,进而造成了妨碍市场秩序的结构状态,或者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反竞争行为。众所周知,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行政性垄断行为,无论是强迫交易行为,还是地区封锁行为,都具有严重的反竞争效果,更为关键的是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性垄断行为会严重地妨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对比来看,领导者人个人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实践中会发现这种个人行为造成的危害并不比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性垄断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其对竞争秩序造成的损害还大于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性垄断行为,那么反垄断法对此种个人行为的规制就是应该且必须的。
从保护社会经济民主的角度看。反垄断法对此种领导者的个人行为的规制更是防止特权经营者的经济独裁的有力武器,能够对有着不正当利益联系的经营者和领导产生必要的制约,有利于净化竞争环境,保障一个有助于民主政治和民主社会制度的环境。
三 行政性垄断主体之具体规定
笔者认为,在我国现在的政治体制之下,要实现对行政性垄断的有效规制,就必须严厉地打击这种利用公权力来实现私人意志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已经不光是为自己或者关系人谋取私利了,而是切实地破坏了竞争秩序和公平的竞争环境,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利益,也侵害了消费者的合理选择权。故我国反垄断法中所规定的对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适用主体是狭隘的,是不能够涵盖所有利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的,对于实施利用行政主体排除限制竞争的主体的理解,必须站在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野来界定。至于有的学者认为,领导者的个人行为违法或者违纪自然有其他的法律法规或者内部纪律来约束,而无需反垄断法来予以规制,笔者认为这是说不通的。因为正如上文所述,某个领导的个人行为特别是在不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往往得不到其他法律的有效规制,由此受到损害的经营者更是不能得到切实的赔偿。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已经成为常态而导致对竞争秩序的严重破坏,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使得特权经营极为嚣张,民众有苦难言,也极大地损害了我国行政机关单位的威信与权威,降低了行政主体的严肃性和公信力。
所以,我国反垄断法在对行政性垄断的实施主体的界定上必须予以一定的修正,笔者认为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可以作更为具体的规定,即以:行政主体和以行政主体中有能力影响行政主体作出决定的个人为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适用主体为宜。进一步而言,甚至正如盛杰民先生所述,只以是否形成限制排除竞争来作为行政性垄断的唯一标准。[5]也就是说只要有了排除限制竞争的后果或者效果的行政行为,就应当认定为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而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而无论此种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是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亦或是能够实际影响到行政主体意志的个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制止与公权力相关的行政性垄断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经营者的经济性垄断。
[1]种明钊.竞争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王先林.竞争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王保树.论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4):21.
[4]郑鹏程.行政垄断的法律控制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盛杰民.规制行政性限制竞争是中国《反垄断法》的必然使命[J].工商行政管理,2002,(9):9.
(责任编校:张京华)
D922.1
A
1673-2219(2012)09-0129-03
2012-08-18
比干尧(1988-),男,湖南常德人,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