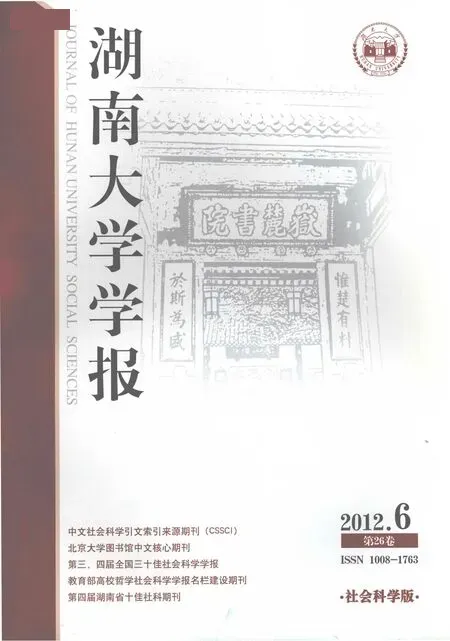我国合同司法解除的类型化探究*
陈 坚
(湖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一 引 言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合同解除都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合同解除亦占据重要的地位。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具备合同解除条件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的一种行为。[1]当事人依据《合同法》第93、94、96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向对方行使合同解除权时,如发生争议,可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解除,法院可依据上述规定作出是否解除合同的判决,此乃解除合同的一般情形。而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并未成就或者尚未出现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但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双方的合同目的事实上已无法实现,合同继续履行对一方甚或双方当事人已毫无助益,当事人直接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抑或当事人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已经成就或者出现了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但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不依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的程序向对方行使合同解除权,而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合同解除;也有的合同解除权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对方恢复原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赔偿损失,而没有诉请解除合同,如此等等,法院是否受理此类案件,受理后是否判决合同解除,当事人该如何行使解除权,实践中存在很大争议。由于《合同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加之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之间互相冲突,增大了法院的处理难度,也导致各地法院对此做法不一。据统计,湖南省郴州市两级法院近五年来共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两万九千余件,其中涉及到合同解除的案件九千余件,而当事人依据《合同法》第93、94、96条的规定诉请法院解除合同的仅为一千件左右,还有将近90%案件的当事人未按《合同法》第93、94条所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条件或者未按《合同法》第96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的程序,即直接诉请法院解除合同。上述诸多法院解除合同的情形,笔者在此称之为合同的司法解除。解除合同究竟是合同当事人的权利还是裁判者的权力,《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是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合同法》第96条规定的是解除权人向对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法定程序。就规范分析而言,《合同法》第94条是一种授权性规范,其本身并非裁判规范;《合同法》第96条虽表述为“应当”,但并不能解释为强制性规范,本质上仍属于任意性规范。而且,就合同解除的目的而言,上述条款亦非行为规范,当事人不一定需要根据这些规定的内容对合同进行解除。故而,《合同法》第94、96条本身并不能直接约束法官。因此,在《合同法》的这些规范中,法官具有解除合同的权力。在公法层面,法院作为争议解决的审判机关,在司法程序中不仅需要遵循“不告不理”原则,同时更需要体现“有告必理”的要求。而司法解除合同,恰好顺应了这一需求。与此同时,合同司法解除也得到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确认,如《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①《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②《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根据《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9条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9条发包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承包人无法施工,且在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相应义务,承包人请求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予支持:(一)未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二)提供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三)不履行合同约定的协助义务的。中均对《合同法》中所规定的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之外的合同解除情形予以了确认。
二 合同司法解除的界定
合同解除作为合同消灭的特有原因,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之后,因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溯及或不溯及地消灭,未履行的部分不必继续履行,已履行的部分依具体情形进行清算的制度。[2]一般而言,当事人应当依据《合同法》第93、94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与96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程序向对方行使合同解除权,对方如有异议,可诉请法院确认解除的效力,法院则依据上述规定作出是否解除合同的判决。而合同司法解除是指当事人未按《合同法》第93、94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或者未按《合同法》第96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程序直接诉请法院解除合同,以及当事人虽未向法院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但因合同内容具有违法性或者因客观原因当事人的合同目的事实上已无法实现时,法院判决合同解除的情形。作为区别于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的一种特殊合同解除形式,合同司法解除具有以下基本特征:首先,在解除原因和条件上,合同司法解除主要是指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之外的合同解除情形,不以《合同法》第93、94条所规定的一般合同解除条件以及《合同法》第164至167条、第219条所规定的特别合同解除条件为限定,对当事人在上述合同解除情形以外提出的解除合同诉求,甚或当事人未向法院提出解除合同的诉求,但基于合同内容具有违法性或者因客观原因合同的履行事实上已无法给当事人双方带来利益甚或损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利益,合同解除已成为当事人的一种违约救济手段时,此时应由法院对合同是否解除依法予以裁断。其次,在解除程序上,正因为合同司法解除的主要功能在于对当事人未按《合同法》第93、94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或者未按《合同法》第96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程序行使解除权的救济,在此情形下,合同应否予以解除只能由法院作出评判;对于合同内容具有违法性或者因客观原因合同的履行事实上已无法给当事人双方带来利益甚或损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利益时,即使当事人未向法院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法院仍得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决合同解除。合同司法解除是以法院司法裁判程序作为必经程序,由法院依法就应否解除合同以及合同解除的后果处理作出裁判。最后,在合同解除的争议解决上,在司法实务中,即便对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而言,仅仅依据解除权人的合同解除通知,往往难以使合同真正得以解除,对方当事人大多会对合同解除提出异议之诉,故而绝大部分合同解除争议仍需诉诸人民法院,由法院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除非当事人能就合同解除与否以及合同解除的后果处理达成和解,合同司法解除均须由法院依法裁判。由于在法治社会解决争议的诸多方式中,相比其他任何纠纷解决方式而言,司法裁判具有终局性,由法院对合同解除的争议最终作出裁判,既解决了合同应否解除的争议,又可以对合同解除的后果一并作出处理,确保当事人之间的纷争得到彻底解决,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益,使得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解除实现各自最大的的利益。
三 合同司法解除的类型化
合同解除是结束合同的一种手段,也是当事人对不愿或者不能履行的合同寻求解脱的一种手段,法律过于严格限制合同解除,也并不必然地符合当事人的合同目的或者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确保在合同司法解除中有效实现当事人合同自由与法官司法权的平衡,我国《合同法》应当考虑设置解除合同的一般条款,同时对需要解除合同以及不能解除合同的情形进行类型化区分。一般条款也可以称为概括条款或者一般规定,是指在解除合同的情形规定不足时所需要采用的概念,一般条款主要是克服成文法的不足,用以扩展法官与行为人的权利自由。类型化是指合同解除制度一般条款之外就具体的合同解除情形作出规定。就合同解除的一般条款而言,不同国家因为合同解除的价值取向不同而有所差别。在禁止或者严格限制合同解除的国家,一般对解除合同的情形进行严格规定,并不赞同对解除合同的条件规定一般条款。如我国《合同法》并没有对合同解除的情形规定一般条款,而仅在第94条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进行了列举。而允许或者鼓励合同解除的国家,对合同解除的情形则规定一般条款。如《法国民法典》第1184条第1款规定:“双务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其债务时,应视为有解除条件的约定。”这就是解除合同的一般条款。[3]由此可见,解除合同的一般条款在立法中确然存在。当然,无论是鼓励解除合同还是禁止解除合同的立法,二者区分界限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合同作为社会财富创造的手段之一,如果过多地宣告合同解除,并不一定符合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尤其在许多情况下,因一方违约而具备合同解除条件,但对无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并不是必然有利的。如一方迟延交货,而另一方愿意接受,不愿退货。又如一方交付的产品虽有瑕疵,而另一方不想退货,仅希望通过修补后加以利用,前述两种情况就没有必要解除合同。[4]所以,法国尽管规定了解除合同的一般条款,但就解除合同的条件而言,并不是一方当事人想解除就必然得以解除,解除合同仍然需要通过司法途径。这就避免了在实践中一方随意解除合同的情形出现。设置解除合同的一般条款,相对于不予设置解除合同的一般条款而言,对当事人利益保护更为有利。故而我国应当设置解除合同的一般条款,赋予合同当事人解除合同的自由选择权,使得合同当事人特别是守约方依法取得更为充分的救济的权利。在规定了一般条款之后,有必要对合同司法解除的情形进行类型化规定。
在下列情形下,法院一般应当予以解除合同:
第一,尽管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合同解除的诉求,但由于合同本身具有违法性,且违法的程度还不足以导致合同无效,如果允许该类合同履行,就会对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此时法院应依职权判决解除合同。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当认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4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作无效认定,而那些内容与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相抵触的合同不得认定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第14条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强制性规定”限缩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作无效认定。根据民法强行性规范的内涵不同,可以将强行性规范区分为指导性强行性规范、禁止性强行性规范以及效力性强行性规范。[5]指导性强行性规范是赋予私权保障与规范权利行使的规范,违反此类规范只会发生当事人因违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禁止性强行性规范,又称管理性强行性规范,该种规范一般不对规范的效力产生影响或者进行评价,旨在禁止某种行为的发生,在该种规范中,如果行为人不从事某种行为,有可能承担非民法上的责任;效力性强行性规范是指对行为模式的效果进行评价的规范,是为了实现私法的价值而进行的效力评价,其作用和功能在于对法律行为的效力进行规定,即直接赋予法律行为有效、无效或者效力待定的后果。效力性强行性规范的目的在于:一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如表见代理的规定;二是为了对某种类型的行为进行强制,如物权法中有关物权的设定与移转行为的规定;三是为了侧重对某种利益的保护,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与其年龄、智力不相符的行为无效;四是为了避免产生严重的不公平的后果或者为了满足社会的要求而对私法自治进行限制的规范。[5]合同内容即使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但如果没有违反效力性强行性规定的,仍然作有效认定。随着《合同法司法解释(一)》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的施行,一些虽然具有违法性,但违法的程度还不足以认定无效的合同将逐渐增多。此类合同虽不作无效认定,但可以通过合同解除途径消解其危害性。
2.一方行使不安抗辩权,而另一方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恢复履行能力并提供适当担保的,不安抗辩权人诉请解除合同的,法院应当判决解除合同。所谓不安抗辩权是指在双务合同中一方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约定须先为给付,在对方当事人有难为作出对价给付之虞时,得以拒绝先为给付的权利。对此,《法国民法典》第1613条规定:“如买卖成立后,买受人陷于破产或处于无清偿能力致使出卖人有丧失价金之虞时,即使出卖人曾同意延期支付,出卖人也不负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但买受人提出到期给付的保证者,不在此限。”《德国民法典》第321条规定:“因双务契约而负担债务并应向他方先为给付者,如他方的财产于订约后明显减少,有难为对价给付之虞时,在他方未为对价给付或提出担保之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该条实际上扩大了不安抗辩权制度的适用范围。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如《奥地利民法典》第105条、《瑞士联邦债法》第3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496条均对不安抗辩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68、69条的规定,在不安抗辩权的情形中,当事人一方可以通过中止履行的手段获得自力救济,在对方当事人仍然不提供适当担保情况下,中止履行方可以解除合同。这是因为一方行使不安抗辩权后,对方没有恢复履行能力,双方的合同也没有履行,为了保护不安抗辩权人的利益,同时增进社会财富,此时解除合同,对双方以及社会财富的增进都有裨益。
3.合同守约一方尚未履行合同,但由于违约一方给付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此时法院应该判决合同解除。因为合同违约一方给付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对守约一方没有意义,如果不判决合同解除,守约一方徒增货物保管的风险,这对社会财富也是一种浪费,所以应当判决合同解除。对此,《合同法》第148条规定,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
4.一方因预期违约,合同应当得以解除。预期违约又称先期违约,是指在义务履行期到来之前,债务人就已声明将不履行契约义务或其行为或客观情况已经表明他将于义务履行期到来时不可能履行义务的违约行为。我国合同法对预期违约的规定体现在《合同法》第l08条的规定中,即在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提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不过,这里需要结合《合同法》第94条第2项的关于“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认定规定。如果拒绝履行的债务是次要债务或附随债务,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则不能依此解除合同。
5.一方迟延履行并经催告后仍未履行,合同应予解除。这主要发生在非定期履行债务的行为中。所谓非定期履行债务的行为,是指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对债权人的利益并无根本影响,债务人的迟延履行不会立即导致债权人合同目的落空。[6]在《合同法》第94条第3、4项的规定下,解除迟延履行的债务合同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其一,须当事人一方已经迟延履行债务。这里的“迟延履行”是指债务人能够履行而不履行债务的情形。其二,须守约方催告债务人于合理期限内履行。在债务人迟延履行时,法律并不立即赋予对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以避免此前双方为履行合同而作出的准备工作浪费。同时法律赋予守约方催告权,在合理的期限内催告违约方及时履约。[7]其三,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即债务人在债权人所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然未予履行。其四,债务人没有正当事由。债务人未履行其债务应具有违法性。如果债务人能证明其不履行债务有合理理由或者法律规定的特别权利如留置权或者抗辩权,则不发生履行迟延。一般而言,迟延履行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应区分合同的性质,考虑时间对合同的重要性及迟延履行方的过错程度。迟延履行也在《合同法》分则的相关规定中得以体现。如《合同法》第232条规定,不定期租赁中出租人在通知的合理期限后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第248条也有类似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6.一方迟延履行债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这种行为主要是指定期债务履行的行为。“所谓定期债务履行的行为是指根据合同性质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不在特定时日或期间履行,即不能达到合同目的的履行行为。在该种合同中,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相对方无须催告,即有权解除合同。”对此,2002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债务法现代化法》第286条第2项的规定就确定了此种情形。如果合同未约定履行期限或约定不明,而且又无法从法律的规定、债务的性质或其他情事中确定履行期限的双方可以随时行使各自权利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如果当事人虽然在合同中约定履行期限,但该期限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债务人履行迟延将会给债权人造成较大的损失或者影响债权人的订约目的,则可以根据一方的迟延而允许另一方解除合同。
7.一方当事人履行了合同的非主要债务,在履行期限届满后没有或者拒绝履行主要债务,抑或全部债务迟延履行,因为债务的一体性,可能致使对方合同目的落空,此时应判决合同解除。即使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了次要债务,但由于其仅仅履行了次要债务,仍将影响对方合同目的实现,债权人可据此解除合同;如果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则应适用非定期债务迟延履行的解除规定,债权人不能立即解除合同,应向债务人发出催告,要求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履行。如甲为庆祝其母60大寿,向乙蛋糕店定制蛋糕一份,约定于寿宴开始时交付。该履行期限即属特别重要,届时乙未能履行,甲得不经催告而径行解除合同。[8]
8.一方履行合同需要对方予以配合,但在双方约定的期限或者在合理期限内,对方不予配合,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下去,此时应当判决合同解除。如根据《合同法》第259条的规定,承揽工作需要定作人协助的,定作人有协助的义务。定作人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承揽工作不能完成的,承揽人可以催告定作人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并可以顺延履行期限;定作人逾期不履行的,承揽人可以解除合同。
9.因一方的原因致使合同履行不能时,法院应当判决合同解除。履行不能,又称给付不能,是指作为债权之客体的给付不可能的状态,即债务人在客观上已经完全丧失了履行能力。[8]以特定物为标的的合同,该特定物已经毁损灭失;以种类物为标的的合同中,该种类物全部毁损灭失。如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签订后,因合同约定的工程项目已被政府有关部门取消,鉴于合同约定的标的已不存在,合同目的自然无法实现。司法实务中,根据产生的原因不同,合同履行不能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因债务人的原因致使履行不能,如订立演出合同后该演员因病声带受损不能出演、债务人丧失劳动能力致使不能提供原定劳务;二是因债权人的原因致使履行合同不能,如债权人意外死亡且无权利义务承继者或者债权人下落不明、债务人请求给付而无人受领;三是因第三方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当履行不能的情形出现,法院应当判决合同解除。[9]
10.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一方诉请解除,另一方不同意解除,且提出合理的抗辩理由,但合同如继续履行,则有违诚信原则或公序良俗原则。如甲乙签订租赁房屋合同,一方在出租房内开设麻将馆,严重影响了居民的休息,也给小区的治安带来隐患。但因双方在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有“承租方有权经营一切事务”的内容,此时,出租方提出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尽管承租方具有合理的抗辩事由,但为了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并从公序良俗原则出发,应当判决合同解除。[10]我国《合同法》第233条对此也有类似规定,根据该条的规定,租赁物不符合承租人安全或者健康的一般要求,即使承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存在质量问题,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11.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虽不成就,一方诉请解除,另一方不同意解除,但双方已完全丧失合作基础,合同继续履行事实上已不可能。如王某与他妻子的弟弟李某签订合伙合同,但由于王某有外遇,导致李某的姐姐自杀,李某报复王某的行为致王某轻伤。此时,王某要求解除合伙合同。本案中,尽管合同解除的事由并不存在,但合同已经失去合作的基础,继续履行已经无望,尽管李某不同意解除合同,此时也应该判决合同解除。
12.合同解除条件虽不成就,一方诉请解除,另一方不同意解除,但双方已完全丧失合作基础,继续履行已无法实现双方的合同目的。《合同法》对此在第166条规定继续性合同可以解除全部合同也可以解除部分内容。如丁某与李某系某煤炭公司职工,见倒卖煤炭可以获得高额利润,于是二人从公司辞职出来,并签订合伙协议,商定共同出资承包该公司煤炭的包销工作。但因该煤炭公司出现爆炸事故,被相关部门查封。此时,尽管解除合同的情形没有出现,但二人从事合伙经营的基础已经丧失,合同继续履行也无法实现双方的合同目的。应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官应该判决合同解除。我国《合同法》在231条对租赁合同的规定中同样亦有类似规定。
13.双方已完全丧失合作基础,继续履行可能危及一方或双方利益并可能引发不稳定事端。此种情况,尽管合同的解除情形虽不成就,但双方已经完全丧失合作基础,继续履行已经没有必要,此时应该判决合同解除。如李某是某市百货公司的总经理,与蒋某签订合同,预备整体出卖该百货公司给蒋某。但该百货公司在改制的过程中,数百名职工对李某出卖百货公司的行为意见很大,集体到市委、政府门前上访静坐,甚至冲击政府机关。如果该合同继续得以履行,将引发不稳定的事端。此时蒋某要求解除合同,尽管本案并不完全具备合同解除的条件,但为了增进社会利益,维护一方稳定,应该判决合同解除。[11]
在下列情形下,法院一般不应判决解除合同:
1.一方诉请解除合同,但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解除条件并未成就,或者一方要求解除合同,但尚不具备《合同法》所规定的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为贯彻合同严守原则,保持合同的稳定,维护市场诚信,此时尽管一方诉请解除合同,法院不应判决合同解除。
2.合同解除条件成就,一方诉请解除,另一方不同意解除并提出抗辩,且抗辩理由成立。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与购房户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开发公司应于房屋交付后三个月内为购房户办理好房屋产权证,逾期不能办理的,对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相关责任。因开发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无法办理好房屋产权证,甲购房户即诉请法院解除合同,并由开发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开发公司则辩称其已积极履行了办证义务,房屋产权证之所以办不下来,主要是因为该项目部分业主未尽到必要的协助义务,未能按有关规定提交完备的办证资料,致使该项目整栋产权证无法办好,从而影响了各购房户分户房产证的办理。本案双方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虽已成就,但鉴于开发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且提出了合理的抗辩理由,开发公司未按约履行合同事出有因,如此时判决解除合同,则于开发公司而言有失公平合理,宜判决不予解除合同。
3.合同解除条件成就,一方诉请解除,另一方不同意解除,且合同解除后,将会导致对方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即使一方存在违约行为,但因解除合同将会对另一方造成重大损失,此时则不应判决合同解除。如甲服装加工厂与乙服装销售公司签订服装加工协议,合同签订后,乙将布匹交给了甲,甲即着手加工事宜。但由于乙未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支付预付款,而且经甲催告后也未在宽限期内支付。此时,乙诉请解除合同。本案如果解除合同,将会导致甲的加工费得不到保障。同时,由于布匹已经加工,甲返还原物将成问题。所以,如果此时判决合同解除,不利于维护合同另一方的利益。
4.合同解除条件并未成就,一方恶意违约,以牟取更大的不法利益,双方利益严重失衡,此时不应该判决合同解除。即一方恶意违约,是为了取得基于合同之外的利益,此时如果判决合同解除,恶意违约方将会获取非法利益,违反了法律的诚信原则。如王某与李某签订门面转让协议,但还没有办理好转让登记手续,当王某得知该房即将被拆迁,可以获得高额补偿,为了驱赶李某,采取吵闹、谩骂等严重影响李某继续经营的手段试图使李某放弃购买该门面。此种情况下,王某基于恶意违约要求解除合同,以牟取更大的不法利益,严重损害对方利益,为维护市场诚信,制裁王某的违约行为,弘扬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所以不应判决合同解除。
[1]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4]张新宝.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J].法学研究,2001,(4):42-54.
[5]许中缘.民法强行性规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6]江平.合同法精解[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7]李国光.合同法解释与适用(上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8]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9]王淑华.征收权与财产权平衡视角下的公益性征收认定[J].齐鲁学刊,2011,(5):107-111.
[10]王欢.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探析[J].湖南社会科学,2011,(4):72-74.
[11]郭翔峰.合同约束力的判断标准—— 以“法内”“法外”之间的允诺为分析对象[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5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