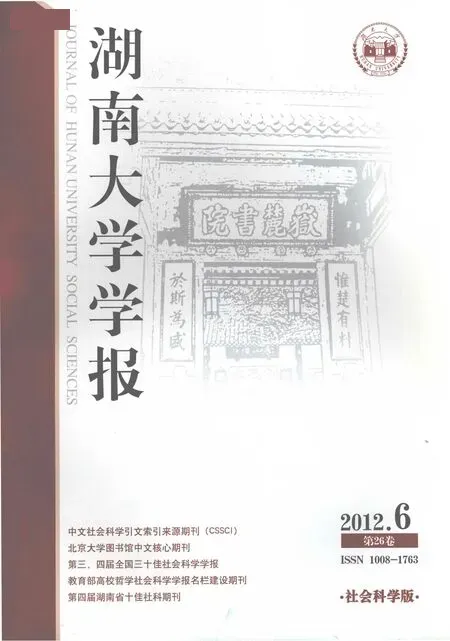儒门论学三题*
张文初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 相对于对“思”的关注,儒门重“学”
儒门重“学”。《词源》释“学”,含义有四:1)仿效、学习;2)学校;3)学问、学说、学派;4)诉说。就思想史的关注而言,“学”的古汉语涵义主要是两个方面:作为“活动”形态的“学习”和作为“成果”形态的“学术”。儒门对二者都极为重视。儒门的重视可通过与对“思”的关注的比较看出。
首先,“学”作为话语为儒者乐道。从《论语》首章首句的“学而时习之”,到荀子的“劝学”,《中庸》的“博学”、扬雄的“好学”、[1](P1201)《后汉书》乐羊子之妻的“积学”[1](P1202)、虞溥的“亲 学”[1](P1203)、颜 之 推 的 “勤 学 ”[1](P1204)、刘 勰 的 “学 而 鉴道”[1](P1203)、张载的“学 所 以 为 人”[1](P1206)、二 程 的 “学 贵 乎成”[1](P1207)、朱熹的“学为无疑”[1](P1212)、陆九渊的“学之无穷”[1](P1211)、方苞的的“学以济用”[1](P1215)、李颙的“学贵博不贵杂”[1](P1215)、康有为的“学者,效也”[1](P1217),关于“学”的论说盈千累万;相对而言,“思”的讨论则少很多。其二,在儒学视野中,“学”的内涵丰富、功能极多、地位极高。在语言学上,学指学习、仿效,或学问、学派。在思想层面上,学有知识论的含义,有伦理学的含义,有准宗教的含义,也有实践生存论的含义。知识论上,学指阅读、了解、探索诸种心智活动及其所获得的成果。《白虎通义》言“学”时说:“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故学以治性,虑以变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虽然“治性”、“变情”、“成器”、“知道”已超出知识论的范围,但“觉悟所不知”首先应该是知识论的或包含知识论的阐释。伦理学上,学指个人品德的修养。张载“学所以为人”,扬雄“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1](P1201),虞溥“学亦有质,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内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P1203),把“学”的伦理学内涵作了清晰的揭示。“学”的准宗教含义是中国传统赋予“学”的最高境界和最高功能,指的是“学”具有终极性的安身立命的作用,它意味着人能因之而获得最终的归宿、获得最大的幸福。刘勰说:“至道无言,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以光身也。”[1](P1203)陆九渊言:“道广大,学之无穷。”[1](P1211)“得道”是中国古人心目中最高的人生境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圣人之言对此作了明确揭示。“学”即是“得道”,可见“学”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类似于西方人的进入天国。此外,学对于像颜元、康有为这样的学者,还是人生实践能力的获得与落实。康有为说:“学者,效也。有所不知,效人之所知;有所不能,效人之所能。”[1](P1217)相比之下,“思”没有这样多的含义、功能,没有这样高的地位。思一般就是指思考、思虑。孟子所谓“心之官则思”,即此含义。虽然也有个别学者如程颐,说过“思曰睿,睿作圣。才思便睿,以至作圣,亦是一个思”[1](P1209)这样一类高扬“思”的意义的话,但此类情形极少。而且,这样的高扬实际上并不是在“思”与“学”的区别性上谈的,它强调的是“思”与“学”的内在同一,其内在实质仍是在扬“学”。
其三,在“学”与“思”的相关性上,儒门的主导性思路是“以学统思”、“纳思于学”。所谓“以学统思”是把“思”看做内属于“学”的一个要素、一种功能,“思”不具有整体上与“学”相对的意义。思是为了学,促进学、服务于学。学是目标、目的;思是途径、手段。思从属于学,受制于学。张载说:“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谓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1](P1206)这里讲的“思”与“诵书”、“通贯得大原”一样,都从属于“学”。“思”和“诵书”是具体的“学”的手段,“通贯得大原”是“学”的最终状态。程颐说:“思虑有得,中心悦豫。沛然有裕者,实得也。思虑有得,心气劳耗者,实未得也,强揣度耳。尝有人言‘比因学道,思虑心虚’。曰:人之血气,固有虚实,疾病之来,圣贤所不免,然未闻自古圣贤因学而致心疾者。”[1](P1207)程颐此论在于区别“思虑有得”,和“思虑心虚”两种学习状态。从他的论述可看出,无论哪种“思虑”,都是指学习过程中的具体的思考活动,“思”都从属于“学”。不过,也应该指出,因为思可以从属于学,有助于学,中国古代因此有对于思的重视,《孟子·告子》“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也”,即是对于“思”之重要性的充分肯定。宋明理学亦多有同类论述,前引程颐的话就是证明。但不管思之地位有多高,因为是纳“思”于“学”,相对于“学”,“思”的地位仍然偏低。
其四,在思与学相对的意义上,儒门对于学和思的取舍有两种立场:重学轻思和以学制思。思和学作为活动形态有两个层面的区别:第一,一般语言学上所指的“学习”和“思考”的不同;第二,理论上所注重的“接受前人知识”和“独创自家新说”的差异。关于第二方面的区别可看王夫之的论述:“学则不恃己之聪明,而一惟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徇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1](P115)王论精警而且也应该说符合古代思想家们关于学、思第二种区别的主导性看法。王论有强烈的价值学意味,从纯知识论的层面还原,可以认为其包含了下列内涵:“学”是接受既有的知识,“思”是生发出新的思想;“学”是效法古人,“思”是个体独创;“学”关注的是过去,“思”重视的是当下和未来。在第一种区别的层面上,中国古代取重学轻思的立场。《论语·卫灵公》“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荀子·劝学篇》“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即是此立场的言说。葛洪是道教徒,但下列论述可同时看做是儒门观念的表达:“知徒思之无益,遂振策于圣徒,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进德修业,温故知新。”[1](P1202)在第二种区别的层面上,儒门强调以学制思,扬学弃思。虽然如王夫之一类的论说是学、思并扬的,但大面积的中国传统有明显的扬学弃思的倾向。王阳明说“只存着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之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1](P1174),郑玉批评朱熹陆九渊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1](P1336)陈确责斥“舍其所已明,而日求其所未明”[1](1337)的明末学风等等,都含有扬学弃思的倾向。“以学制思”、“扬学弃思”是就学和思的对立情形而言的。不能说在儒门观念中二者总是对立,前论“纳思于学”已明其有同一,但有对立也是无疑的。孔子就已注意到二者的对立。“诗三百思无邪”的名言潜在地表明“思”有“邪”的现象。针对着邪恶之思,儒门要用“学”将其制止、排除、消灭。“扬学弃思”即此之谓。虽然从现代学理上看,可以认为儒门所谓的“邪思”当指特殊的思之“内容”,与思之“机制”有别,但在当时,二者不分,“现代学理”所谓的思之“机制”(如个体性独创)在儒门那里也属“邪思”,也被制止。
“重学轻思”和“以学制思”两种倾向在儒门的一些论述中常常并存杂糅。《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名言就可如是解读。“学而不思则罔”的“思”是一般语言学上的“思”,指思考、体会;“学”则是指低层次的阅读、听讲之类的接受活动。《论语正义》将之等同于《荀子·劝学篇》所谓“入耳出口”的“小人之学”[2](P31)。相对于“低层次的学”,孔子重视思的作用。但是孔子和儒家的“学”还有远比“低层次接受”更为深广丰富的一面。深广内涵的“学”被儒门称之为“大学”。孔子所谓“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学而时习之”、“吾十有五而至于学”等名言所指的“学”即都是“大学”。相对于“大学”,语言学上所说的“思考”、“体会”的“思”只是手段。传统的“重学轻思”就发生在这一层面上。儒门把语言学上的“学”作理论上的提升,构建为“大学”,进而给予价值论上的推崇;而当深入考察“思”的认识论内涵,进而发现其内在秘密和力量时,对“思”则选择了与对“学”相反的态度:不是推崇,而是制裁、排斥。“思而不学则殆”就隐含了排斥。殆者,危险。何以危险?朱熹说是“不习其事,危而不安”[3](P57)。李泽厚说殆者在于康德意义上的“知性而无感性”的“空”[4](P64)。不能说“思之殆”中完全没有朱、李所说的内涵,但孔子的主要意思应该不在这里。前面提到的孔子在同一篇章中说的“思无邪”可与“思之殆”对读。“思之殆”即源于“思之邪”。何谓“邪”?朱熹、郑浩、李泽厚等都释为“虚假”、“不诚”[3](P50),但古注多以“不正”释之。所谓“不正”,按《论语正义》即是《传》所谓“盈其欲而不愆其止”的“盈而不止”,《史记·屈贾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的“淫”和“乱”[2](P21)。质而言之,邪,就是不符合传统的礼乐、礼仪、礼义。“思而不学则殆”说的就是:背离传统礼义礼仪先贤古训的独立思考会把人引向危险之路。如王夫之所说,思的本质含义是“不徇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这里的“不徇”、“任吾”可以有“非对立性新探”和“对立性新探”两种情况。即使王本人选择的是“非对立性新探”,但思之本质包含有“对立性新探”。而从“思之殆”和“思无邪”的观念看,孔子是明显忽视或排斥“对立性新探”的。这就意味着至少在一定意义上,孔子有对于思之本质的拒绝。《中庸》用“博学、慎思、明辨、笃行”来系统地解释“学”就是在演绎孔子的思想。“学”可以“博”、可以放开、可以极致性地发展,思则要“慎”,要有限制、有禁区,不能背离古训而自创新论。宋儒对《中庸》之“学”极力推崇,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世学术文化的发展。对王夫之所说的“不徇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所内含的颠覆性思之本质的放弃,因之成了古代中国乃至今日社会大面积流传的信念。陈寅恪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之所以仍是国人可望不可即的目标,究其根源是传统在作祟。
二 “学”与“传承”的同一:历史的演绎
“学”在历史发生论层面的品格是“传承”。因为重学,儒门因此特重传承。传承的主导面是接受、继承、保存、积累。孔子梦 回 三 代,“好 古 敏 求 ”[2](P146),“祖 述 尧 舜,宪 章 文武”[3](P37),“述而不作,信而好古”[2](P134),奠定了后世儒家的传承风范。宋明理学高扬“横渠四句”,把“为去圣继绝学”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等同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本体性追求。“臣闻学莫急于致知,致知莫大于读书,书之当读者莫出于圣人之经,经之当先者莫要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篇”[1](P1336):说此话的虽是明代的陈邦瞻,但表达的是自宋而始的儒者传承圣学的真切心愿。后世如清代的考据学传承圣学的激情更是有增无减。“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训诂不明。……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经诂,况圣贤之道乎?”[1](P1352)这是主张训诂的呼声。“训诂流而为经解,一变而入于子部儒家,再变而入于俗儒语录,三变而入于庸师讲章,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1](P1352)这是批判训诂风潮的声音。不管是赞还是批,两者却是共同地说明了清代考据学对儒学经典的崇尚。恽敬对这种传承之风的过于强劲给出了准确的批评:“彼诸儒博士者,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1](P1353)
中国自汉代以后,儒学成为正统,孔子成为圣人:“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1](P1309)随后一千多年儒门的学术争鸣就主要发生在“谁是真正的儒学继承者”这一问题上。宋儒批评汉学“说字无字外之句,说句无句外之意,说意无意外之味。故说经弥亲,去经弥远。”[1](P1319)明儒责备宋代的儒学为假儒学、假道学:“至于有宋,学者庶几近古。而程、朱又立为《大学》之教,一旦出《戴记》,而尊之《论孟》之上,于是知行遂分。而五百年来,学士大夫复相与揣摩格致之说,终日捕风捉影,尚口黜躬,浮文失实,是何异敝晋之清宫,痴禅之空悸乎?”[1](P1337)清代的考据学,则既反宋学的心性之求,也反顾炎武、刘宗周等为代表的儒门经世之学,一味沉迷于词章的考证之中。到近代,清代考据经学则又受到具有强烈救亡意识的近世儒者的猛烈批判。儒学的历史表明:相互的争论可以非常激烈,观点可以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各方都志在传承圣学;相互的批评只在于对方的传承不到位,不准确。
儒学自身的发展正是依据思想家们的期待,按照传承的范式走过来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以生、住、异、灭四阶段轮回的佛理解说世界历史上所有学术思潮的演变;说生是启蒙期,住是全盛期,异是蜕分期;灭是衰落期,“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1](P1367)梁论既抹杀民族的差异,也显然与中国古代的历史不符。中国自汉代形成的以儒家为主体的学术文化,一直到五四前夕就一直处于“生”、“住”两阶段之中,完全没有所谓“异”和“灭”的更替。现代新儒家的“儒学三期说”,李泽厚的“儒学四期说”均可以为证。中国儒学,无论是汉代的外王论,还是宋明的心性论,或者清代的考据学,其总体风貌都可以用梁氏所谓“住”相来描述:“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1](P1367-8)。儒学的基本观念、基本理论、基本信念始终没有变化,所变者只是某些局部、某些细节性的内容。
“传承”除了保存、继承外,也还有“发展”。“发展”既意味着前代的东西向后代“延展”、“伸展”,使其在新的时代新的文化土壤中依旧保有其生命力;也意味着“生发”出新的要素、成分、细节,使传统的知识、观念、思想、理论更为完备、宏大、精深。章太炎“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名言描述的就是“生发”的具体方式。不过,要看到的是:传承之所以是“传承”,就因为它是以继承、保存、“延展”、“伸展”为主,其“生发”的一面相对弱势,稚嫩,不成为主导性功能。就具体内容来说,传承的“生发”偏注于细节、局部,它重视的是对既有基本观念、知识、原则的继承、维护、修补。“传承”不追求整体性、根本性的变化、创造、革新。“传承”的“生发”不在于“颠覆”既有,而在于巩固它。因为是以继承、积累为目的,儒门强调的常常是对圣学的虔诚信守,其最信守者甚至因之而反对怀疑、反对质询、反对责难、反对提出自我的见解,“扬学弃思”的倾向在此种情形中表现得特别清晰。汉代著名儒生鲁丕就说:“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1](P1317)“不得相让”,就是不得有所质疑和责难。“非从己出”,“精思不劳”,就是循规蹈矩,亦步亦趋,把传承建立在蒙昧主义的基础上。这是以“保存”完全吞没“生发”的传承。
当然更多的传承论不是这样。在很多论者那里,传承包含了“生发”,包含了变革、创新。《周易》“日新之谓盛德”,《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王羲之“适我无非新”,王安石“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都是在强调“创新”的重要。相对于言“新”,中国传统文化言“变”、言“革”,更是常谈,“变”、“革”与“新”同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凡物变之渐,不惟月变,日变,而时亦有变,但人不觉尔”[1](P66),“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1](P57),此类言说,如恒河沙数。虽然这类谈新谈变的说法包含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历史、人生、人性各个方面的看法,并不完全是从学术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的,但其中无疑也包含了对学术的解读。了解“变革”、“创新”在“传承”中的地位,了解其与传承的关系,了解其是否整体性地否定传承,要先明了中国人的“二分论”天人观。古代中国思想家普遍认为,包括天、人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有两个层面,一是本根,二是事象。前者是单一的,不变的,起决定作用的;后者是多样的、变化的,被支配的。中国古人所说的本与体,本与末、体与用、常与无常,常与权,道与器,道与术、一与多、理与欲、性与情等等,都是在揭示这二者的区别,或者说都包含对这二者区别的揭示。华夏本源和事象的区分,类似于西方的实在和表象、本质和现象的区别。不同的是,在西方,两者的区别主要是从认识论上说的;而且由于强调区别,两者有分裂成两个世界的态势;另外,对何谓实在、本质的解读则因重视个体的思考而完全不同。在中国,区别主要是从人生人性及社会政治的适用性上说的;由于关注实用,两者的区别不成分化之势。儒家一方面区分本末、体用,另一方面总是极力主张“即体即用”,二者同一,甚至连佛学也受其影响。[5](P235)因此,两者即是有别也仍可用李泽厚所说的“一个世界”视之。另外,由于大一统政教形态的建立,在独尊儒术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本根”固化成儒家的纲常伦理;加之,道统常转化成政统,或以正统代之,因之,“本根”不再如西方的“本质”一样因个体性、时代性的思考而不同。儒门传承范式所包含的继承和创新就建立在“本根”与“事象”的两个层面上。“继承”指的是“本”、“常”、“道”、“理”这些被视为“本根”的东西,而创新则只限于“用”、“权”、“器”、“欲”这些事象方面。以道、本、常、理的恒定不变为重,故崇尚的是继承。“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1](P55)
这是庄子的论述,但与下列大儒的心声一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之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1](P57)“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1](P55)儒门重视新、变、革,其前提就是大本、常理不变。儒者知道,所谓“本”、“常”是和“用”、“权”结合在一起的,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另一方而存在。因此,一方面,在理论上,只要本、常不变,体、权就可以尽力变化,“不变”就可以允许“万变”;而另一方面,在实践操作上,“体”、“权”等变化,总会牢记着是为了“本”、“常”的不变,总会以自身之变来保证本、常之不变,来成就本、常之不变。“常者,道之纪也。道不以权,弗能济矣。是故权者,反常者也。事变矣,事异矣,而一本于常,犹胶柱而鼓瑟也。”[1](P63)“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虽随时变易,乃常道也。”[1](P64)
三 “学”与“传承”的同一:逻辑结构与历史渊源
学与传承的同一源于两者自身的逻辑结构和历史渊源。
朱舜水释“学”时说:“人之所以必资于学者何?盖前人之学也已成,所以著之即为教;后人之学也,未成而求成,因以循古圣先贤之道而为之,斯为学。”[1](P1217)“循古圣先贤之道”即是“传承”,也即是“学”。朱熹释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时说:“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3](P37)以排斥“邪思”为内涵的“扬学弃思”的机制直接地表现了学与传承二者的同一。“扬学”的“学”有两义:一指传统的观念、思想、信条;二指对传统观念、思想、信条的接受。传统的观念在孔子是三代之治的礼乐,被祖述的“尧舜”、被宪章的“文武”;在先秦之后,则主要是孔孟之教,《四书》《五经》所内含的观念;到宋之后,则加上了程朱理学等儒门新派。王符《潜夫论》在阐释董仲舒、景君明、倪宽、匡衡的成就时说:“夫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夫此四子者,耳目聪明,忠信廉勇,未必无俦也。而及其成名立绩,德音令闻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托于先圣之经典,结心于夫子之遗训也。”[1](P1202)张履祥说:“学必以圣贤为师,今人以为迂,予以为特未之思也。使圣贤之道而在于此身之外,迂之可也。孰非人子,孰非人臣,孰非人弟与人友。思为人子,则求所以事其亲;思为人臣,则求所以事其君;思为人弟与人友,则求所以事其兄与施其友,不然尚可谓人子人臣人弟人友乎?”[1](P1215)张伯行说:“自邹鲁而后,天下言道德学问之所出者,曰濂洛关闽。然集群圣之大成者惟孔子,而集诸儒之大成者惟朱子。士生千载之下,欲明圣人之道于千载之上,苟穷之不得其术,探之不得其源,守之不得其宗,而欲自命为学,是非不谬于圣人,盖亦难矣。”[1](P1216)这些论述或明学之本义,或责悖圣之迂,或揭圣学源流,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扬学”即是“传承”,“传承”即是“扬学”,二者完全同一。
在“重学轻思”的层面上,“学”与“传承”的关系加进了一些复杂的因素。“重学“的“学”除了包含“扬学”之“学”的两种含义之外,还增添了多种内涵。比如,它也包括颜元、康有为观念中那种“实践人生能力的获得与落实”,包含刘勰、陆九渊那种意义上的修身养性得道通神。但可以注意的是,其一,不管“学”的内涵如何扩展,儒门“扬学而弃邪思”的一面始终没有放弃。“扬学弃思”之所以允许“学”的内涵扩展,而转化成“重学轻思”,其原因在于这一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顺着“学”的方向进行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学的伦理化。“学”超越纯知识论的范围成为伦理性的诉求,是学之得以高扬、得以传承的重要原因。中国自先秦之后,特别是自宋之后,儒学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学的伦理诉求性的加强。程朱吸收道释的成分,提升儒学的地位,其目的就是要用儒门之理制裁现实的人欲。伴随“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意志的高涨,传承作为机制和作为对儒学正统实际继承的行为也就更其重要。其二,扩展的“学”尽管可以同被传承的正统之学有别,但在规模和地位上从来没有能够与正统之学抗衡。激进者,如李贽可以放言“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以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1](P1213)颜元可以提出“书本上所穷之理,十之七分舛谬不实”[1](P1214);郑板桥可以说“《五经》、《廿一史》、《藏》十二部,句句都读,便是呆子”。[1](P1215),但李贽的非孔之声完全不能撼动传统的学术天穹。颜元郑板桥之责读书并不意味着否定圣贤学统,颜元说“以多读为学,圣人之学所以亡也”[1](P1214),郑板桥说自己于《四书》、《五经》“未尝时刻而稍忘”,[1](P1215)可见他们否定的只是那种死读书的治学方法,并不是被传承的圣学本身和对圣贤学统的传承。其三,实践人生能力的获得也好,修生养性得道通神也好,历史上扩展的“学”在精神实质上也并不与“传承”对立。康有为的“学”所重之“效”,其中当然有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分,但他是把他的“学”同尊孔连在一起的。
儒门“学与传承的同一”,作为具体的历史规定,其形成与“学”的一般逻辑机制有关。学,无论是古人的理解还是今人的理解,作为活动,在一般意义上,指的总是对既有知识的接受;作为成果,指的是前人已经形成的知识。接受既有的知识当然需要有一般语言学意义上的思,学与思有一定的同一性;但在发生认识论上,学与学问不同于思和思想。思是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揭示;思想是由思考者形成的领悟、观念、理论。学识学问作为知识,不是由学习者本人第一次提出来的;学识本质上不来自于学习者,不来自于学,只是由学习者所接受。在学习者学习之前,学问学识作为知识就已经存在。思想是由思考者形成的。在思考者思考之前,思想并没出现。思想来自于思。学识既是他人已经形成的概念化的知识,学习面对的就是概念本身、语词本身,或者说已经语词化、概念化的事实。思面对的是未曾知识化的现象、事实。所谓未曾知识化,也就是未曾概念化,即人们未曾对之进行概念性的言说。海德格尔论“解释”时说,“解释向来奠基在先行视见(Vorhabe)之中”,“被领会的东西保持在先有中,并且‘先见地’(vorsichtig,通常作谨慎地)被瞄准了,它通过解释上升为概念”。[6](P175-176)海德 格尔此处所 说的 从“领会的先有”到形成“概念化解释”的过程可以说就是思想产生的过程。就具体情形来说,思想当然可以在阅读前人著述的过程中发生。但这里的前人的概念化著作不是思想的源泉,它只是一种触发性媒介。阅读要能导致思想的发生一定是思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了某种非概念化的东西;是这种非概念化的感受性的东西导致了思想的发生。当然,这里说的非概念化是从思想的源发性上说的,它同思想本身要依赖概念不是一回事。
思与学的同一也可从思想向学问的转化上看出。当思考者提出的思想获得他人认可,被他人接受时,思想就成了学问。《论语》的内容作为孔子经由自己的思考所形成的知识,是思想;但相对于后世的学习者,它则主要是以学识、学问的形态存在。但此种同一不能逆反。思想可以直接转化成学问,学问则不能直接转化成思想。如果学问可以转化成思想,则意味着思想可以来自于学问,可以来自于学,这是荒谬的。思想不能来自于学,只能来自于思。这样说,不等于否定思对于学的依赖性。陆世仪说:“思处皆缘于学,不学则无思。”[1](P1214)陆之“缘”如果理解成“源”,就错了;但仅仅从揭示思对于学的依赖性上看,则是对的。学对于思的形成具有必须性,任何思想的形成都不能完全离开学问,人不能以零知识的状态进入思考,人们对于世界的发现总是步步深入的,只有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在既有知识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新的发现:此类道理应该是人所共知。“学问”可以学习。思想则在本质上不能“学习”。现代汉语中常有的“学习某某某思想”的说法,不包含对学和思的本质认定,只是日常语言的随机性应用。无论是接受某人的观念,还是学习某人的思考方法,既与“学”搭配,实际上指的都是学问性的知识,不是真正的思想。真正的思想不是“已经对象化”的知识,而是思考者自生的知识。日常性说法模糊真正的义理,其危害在于导致思想的萎缩。不过,要指出,“学习某某某思想”的说法中往往也内含了一种有意义的揭示:它区别了作为对象的“原创性思想”和“非原创性学术”。在日常说法中并非任何人的知识都可以被后学者作为思想来学习。只有那些具有原创性的知识才是后学者当做思想来学习的对象。一般的学术在日常语言中是不会作为思想学习的。比如,人们可以说学习王夫之的思想,但很少有人会说学习乾嘉学派的思想,因为后者只是考据性的学问。
学的历史发生论品格是传承,与之对应,思的历史发生论品格可以说是“扬弃”。学和思的区别,学问和思想的区别,内在地包含了传承和扬弃的区别。“学”既是指对前人已经形成的知识的接受,本质上就是传承。儒门既然重学,扬学,不管他们对于学的一般内在机制是否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是否有清醒的意识,只要他们选择了学,而且选择了与“思”相对相异的“学”,儒门就必然选择“传承”。[8]
儒门重学、重传承与中国之“学”的“出身”有关。上古社会的历史表明,在中国,学出于官。学者对此已有共识。章学诚《校雠通义》论官—法—书—学的源流:“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有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故私门无著述文字。”[7](P29),龚自珍《治学》说:“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戒语者,谓之师儒。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7](P29)钱穆:“古者治教未分,官师合一,学术本诸王官,民间未有著述。”[7](P29)中国古代甚至有某某学派源自某种官职的说法。《汉书·艺文志》就说学之九流源自古代的九种官职。现代学者如胡适虽力斥《艺文志》之说为谬误,但并不否定学出于官的历史。学出于官从另一重要层面说明了儒门和中国历史重学、扬学的原因。中国自古就是国家本位、管理本位、官本位的社会。这种本位机制既存在于现实的社会机构设置之中,也存在于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既然学出于官,官之本位自然意味着学之本位。官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全面管治,自然导致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学得以被崇尚。学出于官意味着在中国学与官本质上同一。官源于群体性的需要,学自然也是诉诸于群体的意志。官意味着上对下的治理,学自然也如此,只不过这种治理是改用教化的方式实施。官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同一,学因此也以排斥异端为特征。官决定学,学秉承官的本质、意志,学的立场、视点、视域、视界皆与官同一。虽然具体的观念可以随官之不同而有差异,视界可以有伸缩,在狭隘的官者那里,连清风也不能歌咏;在开明的官者那里,说几句犯上之语也无妨,但如同孙悟空始终在如来佛的手心里一样,学始终是官之意志的体现。虽然针对作为人类历史个体的官员,学可以具有引领、规范、惩罚、制裁的作用,但学从来不会自异于整体性的官之外,不会在与官相对的立场上展开思考,反思官的本质、局限。学不会在超越官之意志的自然、宇宙、人性的层面上构建可以制约、规范官的现实运演的强大力量,以保障官仅仅只是作为管理国家的历史手段的实践合目的性与有限性。[9]官学的此种同一保证和强化了学的崇高地位,因之也促成了传承机制的形成和实施。除此之外,官学的同一还与“传承”有直接的相关性:传承本质上也是官的地位、官的本质、官的意志的传承。传承之所以特别为中国文化所重视,所坚持,这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1]中国思想宝库编委会.中国思想宝库[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2][清]刘宝楠.论语正义[A].诸子集成(第一册)[C].北京:中华书局,1954.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7]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8]朱汉民.先秦儒家性理观念溯源[J].齐鲁学刊,2011,(5):5-8.
[9]唐明燕.先秦儒家教化哲学及其影响[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0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