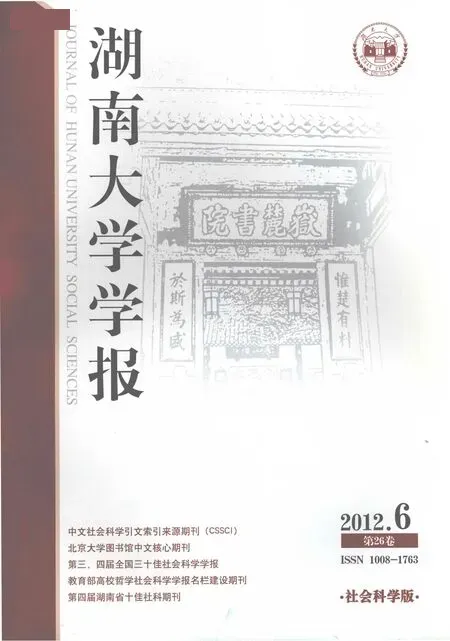美国极权主义心理解析————以《裸者与死者》为例*
陈 娜,季水河
(1.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4; 2.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一 引 言
战争催生权力的集中。二战结束后,美国并没有停下扩张的脚步,把极权主义推向古巴、朝鲜、越南等国,远离本土点燃战火。“战争在战略上是政治的延续”[1](P189)。有批评家认为,尽管美国一再声称它的对外扩张战争是为了维护人权、推行自由,但在实质上,二战后的美国对外扩张战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诉诸民族主义情绪的右派为缓解国内阶级矛盾造成的内部紧张局势而采取的有益措施,即美国的对外扩张战争有利于“国家的健康”[2](P249-250)。美国的对外战争到底是有利于“国家的健康”,还是国家极权主义膨胀在外交政策上的体现呢?二战后,美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家政府引导舆论,权力经营模式发生转变等,给人们认识政治权力的实质带来了困难。新精神分析派的出现为人们从心理层面解剖权力、战争和人性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契机。早在1940年,马克斯·霍克海默在 《独裁国家》(又译《极权主义国家》)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美国这个民主自由国家背后隐藏着极权主义暗流,而法西斯主义就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极限形式。诺曼·梅勒在他创作的二战小说《裸者与死者》(1948年)中表示出同样的看法。战争是罪恶的,它是美国实现极权主义的重要途径之一。小说描写了极权主义支配下的美国军队,它和法西斯主义具有同样的心理基础“权威主义性格”,不仅体现在个体性格特征上,而且存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
二 “权威主义性格”:极权主义的心理基础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或社会活动的手段,权力总是和实施或承受它的主体和客体互相影响、互相生成的。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将人对权力的欲望如“权力欲”、“权力意志”归为构成助长人与人之间敌对和冲突的反社会心理动机之一,用霍布斯的话说 :“我把永无休止谋求权力的欲望,至死方休,视为一切人类的普遍倾向。”[3](P86)在他们的影响下,权力是基本欲望,贪图权力是人类基本天赋这一观念被广泛接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一步将对权力的追逐导致的侵略和暴力倾向内化为人类的本能和人的天性,从而得出结论:战争就是被压抑的侵略性的发泄结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希特勒的成功似乎证明了弗洛伊德的结论。二战的爆发催生了以强制性和绝对性为代表的法西斯独裁主义或极权主义,德国纳粹分子通过狂热宣传、鼓吹,煽动大众绝对服从。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极权主义”指专制或寡头政体,侧重权力的“广延性、综合性以及强度”[2](P19)。希特勒领导下的法西斯独裁主义是它在20世纪最典型的代表。然而,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极权主义不是法西斯德国的专有产品。精神分析学家威尔海姆·赖希认为,作为极权主义最高阶段的法西斯主义,它不是某个人、某个民族、某个政治集团的仪式形态和行动,而是“普通人的性格结构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这种性格结构既不限于某些种族或民族,也不限于某些政党,而是普遍的和国际的。从人的性格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我们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正是现代人的机械主义的神秘的性格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党,而不是相反”[4](P第三修订增补序言3)。这里的“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心理学层面的概念,指人的一种“基本情感态度”,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威尔海姆·赖希极大拓宽了人们在文化或心理层面对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的认识,为20世纪40年代新精神分析派在美国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新精神分析学说代表人物弗洛姆对威尔海姆·赖希的“现代人的机械主义的神秘的性格”进行分析、凝练,进一步提出“权威主义性格”(或译“极权主义性格”),解释了极权主义的心理基础和运行机制。作为人性结构的一部分,“权威主义性格”受生存本能驱动,宣扬“优于他人”和“臣服强者”的信念,在性格上表现为施虐-受虐冲动。根据“权威主义性格”理论,在施虐-受虐共生关系中,施虐者对受虐者实施统治,给予荣誉和利益,而受虐者通过依附前者消解主体,把自己融入施虐方的权力荣誉中,代价是失去自由和独立,从而达到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目的。“权威主义性格”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存在的心理共同点及其对集体性格的影响,施虐-受虐冲动解释了战争条件下命令-服从关系的运行机制,为阐释战争作品《裸者与死者》中极权主义对性格、心理的影响开辟了新的途径。
作为“美国二战后与政治结合最为紧密的作家之一”[5](P80),诺曼·梅勒创作了大量以权力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从《裸者与死者》(1948年)到《巴巴里海岸》(1951年)、《鹿苑》(1955年)、《一场美国梦》(1965年)、《我们为什么在越南》(1967年)再到为他赢得普利策文学奖的《夜幕下的大军》(1968年),“他(诺曼·梅勒)把目光定格在权力和竞争上,从来不能转移;后来经历过一切意识形态的曲折和心理学的变换,一次又一次返回原处,好比犁对于犁沟:犁掘深犁沟,完善犁沟,然后 再转回来。”[6](P313)通过 对作品的历 时梳理可以发现,作家所经历的“意识形态的曲折”和“心理学的变化”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它们很大地影响了诺曼·梅勒对极权主义的理解和认识。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当时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人不阅读《资本论》和《梦的解析》。梅勒二战前接触马克思主义,积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但在战后逐渐对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能否解决社会问题产生怀疑,转而在宗教和精神分析法中寻求出路。新精神分析派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性发展的影响,坚持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建议用弗洛伊德分析法修正马克思主义,对当时正在黑暗中摸索的梅勒很有启迪。在《裸者与死者》中,梅勒使用接近自然主义的写作手法挖掘人性和人的内心,描写了一大批被“权威主义性格”扭曲的美国官兵。美国通过战争会逐渐走向它曾以战斗姿态强烈反对的法西斯主义[7](P36),这不仅仅是梅勒的担心,也是那个时代的担心。
三 施虐与受虐:极权主义心理的运行机制
对希特勒的成长史研究发现,希特勒具有典型的“权威主义性格”:鼓吹种族主义,宣扬空洞的理想,用无理性和极端民族主义煽动大众情绪。希特勒认为,“反抗权威与接收和屈从权威并行不悖”[4](P32)。《裸者与死者》中的最高指挥官卡明斯将军就是美军中的“希特勒”。他喜欢说教,鄙视犹太人、黑人等弱势民族,常常高谈阔论,用极具主观性的、夸张的语言评论时事,鼓吹德国纳粹的领土扩张论。卡明斯热爱战争,战争对他来说,就是将国家的“势能”,即国家潜在的能力和资源,转变成“动能”,实现组织化、总体化,即“法西斯化”。他崇拜希特勒,想像希特勒一样做一个全能的上帝,并妄言打败法西斯德国以后,未来的天下就是反动派的天下。为了当上帝,他把军队组建成“恐怖梯子”式的权力阶梯。在这个阶梯上,一级压一级,每级都应该“对上级心存畏惧,对下级意有不屑”[8](P222)。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对有利自己发展的权贵人士和教会人员彬彬有礼,恭顺谦卑,内心里充满了怎样往上爬,如何获得更大权力、荣誉的欲望和野心;对待下属,他等级分明,军官和士兵待遇截然不同,战斗在一线士兵们的生命对他而言不过是战报上的一串数字。当明知派侦察排登陆人迹罕至的南岸岛屿并无胜算时,他本可以放弃这次意义不大的军事行动,“不过再一想,这样不需要花多少本钱。十几个人嘛,就是遭遇不利,也算不了什么损失。”[8](P513)生命无价值,死亡无意义,战争变成了个人玩弄权力的试验工厂。
慈爱、关心常常是权威主义者实施权力控制的另一张面孔。在大家面前,卡明斯是一位有亲和力、能力强的指挥官,他对副官侯恩更是表现得关爱有加。在侯恩与中层将领们发生争执时,卡明斯言行袒护侯恩。他经常把侯恩喊进帐篷,进行思想交流,对侯恩表现出的自由主义倾向,摆出一副全心为对方着想的样子,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劝说侯恩,甚至提及老婆出轨等家中私事,以示对侯恩的亲密程度。但卡明斯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侯恩不仅服从他的外在权力,还要对他的道德优越性顶膜礼拜。说服,作为权力的一种手段,是权威者所擅长,也是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人们只要一回想希特勒在台上或电台里充满激情的、狂热的、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如何激发民众狭隘的民族情绪,煽起他们的非理性战斗意志,就知道说服的力量在武力之前是不可低估的。这是一种外在权力向内心转化成为行为标准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洗脑”,生产出“权威主义良心”[9](P140),即外在权威 如父母、国家或者任何文化中的权威内化了的声音。这种方式的特点是说服的内容越理想化、抽象化,外在权威就越容易转化成为内心的指引。正如每一个希特勒的信徒会认为自己是遵循良心行事的,说服的对象也会在说服者面前失去原来的判断,在服从说服者的同时,还认为遵循自我。作为权力的使用者和掌控者,卡明斯深谙其道。他在侯恩面前大谈国家形势、军队里的潜规则、批判侯恩的自由主义理想,宣扬权力第一,“军队的现在就是世界的将来”[8](P413),用强势的主观性语言、潜在的权力威胁控制侯恩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这事实上是一种精神“施暴”,而不是真正的关心和爱护。最后,卡明斯听到侯恩死于非命,心头竟掠过丝丝快意,暴露了他的真实嘴脸。观察者制造痛苦,自己旁观他人体验这种痛苦时产生快乐,这就是典型的施虐狂[10](P112)。
有施虐方,就存在有受虐方。马克思说,人是社会的动物,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权威主义性格”不仅存在于个人性格特征中,而且还是美军命令-服从关系的深层驱动力,以施虐-受虐冲动的互动互构表现出来。在强势的权威者卡明斯面前,侯恩成为施虐的对象。二者的共生关系在卡明斯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下短暂维系了一段时间后,以侯恩的反抗而破灭。在收拾卡明斯帐篷时,侯恩明知卡明斯有洁癖而故意将烟头扔在地板上,这一行为宣告卡明斯施虐冲动以及说服手段的失败。权威要求绝对服从。虽然卡明斯内心里有些喜欢侯恩,因为侯恩在性格上“有些像他”,是个有思想、与众不同的人,但权威者绝对不会容许个人持有怀疑和批评的权力,卡明斯对侯恩的行为马上做出了回应。他没有立即处死侯恩。对共生关系破坏者最大的制裁不是惩罚或判死罪,而是抛弃、拒绝。惩罚还代表权威者仍在关心他,“受罪”就是赎罪,那么,抛弃则意味着无依无靠,以及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害怕。就像上帝通过遗弃罪者该隐宣判对他的惩戒一样,卡明斯选择了抛弃。他将侯恩从身边副官调至机关制图员,再到奔赴一线的侦察排,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侯恩远离,以示惩戒,然后上帝般等待侯恩如迷途知返的羊羔回到他身边,祈求宽恕和原谅。侯恩的死亡终结了这个游戏。失去权威者的统治和庇护,叛逆的侯恩遭遇了死亡,这仿佛预示了在战争非常态生存条件下的权力潜规则:不服从是主要罪行,而服从则是基本的美德[9](P32)。
与反抗者侯恩不同的是,大多数受虐方在权威面前选择了服从,或者在挣扎后选择了服从。在弗洛姆看来,受虐冲动是造成人们心甘情愿受制于权力的心理因素,只要有施虐冲动存在,就一定有相应的受虐冲动存在,它们共存于“权威主义性格”中。如果说施虐冲动的目的是在破坏欲中享受着对他者的无限权力,那么受虐冲动的目的则在于把自己消解,远离孤立和恐惧,分享权力的力量和荣耀。受虐者被反复灌输“个人微不足道,不足一提”[10](P165),并接受个人的“微不足道”,臣服强权,消灭自我。在《裸者与死者》中,上士克洛夫特和老兵雷德就是这样一对例子。比起卡明斯,侦察排的克洛夫特上士更具暴力倾向,他生性凶残,视生命如草芥,憎恨“身外的一切”[8](P205),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徒。置国际军事法律于不顾,支开同伴枪杀已降的日本俘虏;在士兵们面前捏死象征希望和生命的小鸟;谩骂、殴打弱小的犹太士兵罗思,任由他体力不支,坠崖身亡;故意知情不报,让日军打死威胁自己升职的侯恩;在战场上“杀个人真像拧死一只鸡那么容易”[8](P250),克洛夫特几乎就是恶魔的化身。在他变态的施虐心理下,整个侦察排变成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每个士兵“仿佛成了机器上的一只小小螺丝钉,机器转得飞快,要命的螺丝钉受不了,又挣不脱,只能吱吱直叫”[8](P895)。老兵雷德就是被这部机器压得“吱吱直叫”的“小小螺丝钉”中的一个。雷德兵龄较长,参加过几次重要战役,资历颇老,是侦察排里少数几个可以和克洛夫特分庭抗争的老兵。他和克洛夫特的明争暗斗常常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而一旦被注视,他便变成了孤立的。在执行最后一项军事任务侦察高不可攀的穴河山的过程中,雷德意识到是克洛夫特害死了侯恩,畏惧感油然而生。正如“亚当们对上帝的绝对服从,这种服从不是盲目,也不是所谓的异化,其深刻缘由在于对可作为生存本体结构的神秘领域的认可,神秘略带虚无,而对虚无人们产生恐惧”[11](P281)。和克洛夫特再次发生争执时,雷德在克洛夫特黑洞般的枪口下终于放下坚持,表示认输。让雷德屈服的是对死亡的恐惧,或是权力的武力威胁,但借此能从那个被注视的位置上撤下来,逃离孤立感,比起前者来说,这对雷德更具诱惑力。在宣布认输的一刹那,雷德心里一点挫败感也没有,相反他“居然会有庆幸之感:好了,事情总算了结了,他跟克洛夫特的长期争斗也终于结束了,今后他可以顺顺从从俯首听命了,不会再觉得非反抗不可了”[8](P886)。从被注视的高位转移到被统治、被控制队伍中的一员,这种“微不足道”感让雷德感觉到彻底的轻松,从而使他成为施虐-受虐关系中的被动接受者,解释了人与人关系中命令-服从机制形成的心理运行模式。
侯恩在反叛中丧失了生命,雷德在顺从中苟延残喘,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人们如同寻求动物界里的保护色一样,放弃自我,最后变成或服从外在权威,或受制于内化了的“权威主义良心”的集体公民。
四 “机器人”群体:极权主义心理的产物
对于制造了战争的美国国家机器而言,如何让美国民众如希特勒信徒般听话、驯服,是它实施强权外交和平息国内动乱所要面临的头等大事。改变美国民众的观念,对他们进行“洗脑”,让外在的权威内化为“权威主义良心”,或是“匿名”于建筑、媒体、科技等现代元素中,使人们对权力或极权的认识模糊化、边缘化,成为美国国家机器运作极权主义的重要手段。弗洛姆把后者称为“匿名的权威”,它比受命令-服从关系支配的外在的或“公开的权威”更可怕,因为“公开的权威”是看得见的,只要有“公开的权威”,就存在着冲突、反抗;而“匿名的权威”是看不见的,如同法令、规则一般看不见摸不着,从而也无法攻击。让权威内化,人们在 “权威主义良心”的支配下工作、生活、思考,其高明之处就是人们受制而不自知,从而变成了个性被消除、自主意识和经验被歪曲、主张集体信念的“社会的人”。
诺曼·梅勒在《总统文件》里深刻揭露了极权主义异化人性、摧残精神的真实目的,“它(极权主义)消解人的个性、多样性、异议、极端的可能性和浪漫的信念;它蒙蔽人的想象力,消磨人的直觉,抹杀人的过去。”[12](P184)《裸者与死者》中的“机器人”群体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毫无个性,主张集体信念,按照“权威主义良心”的引导习惯性地打仗杀人,诺曼·梅勒把他们称作“机器人”,借卡明斯之口描述了出来:
人一打仗,倒是都成了机器,不大再像人类了。这话是有些道理的,看来是不错的。打仗,就是组织成千上万成为机器的人,让他们在习惯的支配下杀上战场,烈日当头晒得他们汗气蒸腾,一遇下雨又冻得他们哆哆嗦嗦,僵得像块铁板。我从自己的思想中就觉察到,我们如今同机器也确实不是那么截然有别了。[8](P726)
战争作为国家机器驯化的重要手段,要求人们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习惯”和“思想”上都僵硬如“铁板”,更重要的是,其机器化、铁板化的过程就是权威“匿名”化、内化的过程。权威内化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普通人对权威的服从;另一种是担任权威的角色,以同样的严厉和残酷对待自己[9](P145)。卡明斯是典型的第二种。与第一种比起来,第二种人“觉察”到自己正在“机器”化,清醒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行为,却无能为力。一方面,在尼采看来,或多或少缺乏生产性的权威的性格,或者不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为,都会产生出一定程度的虐待狂和破坏性,然后在充当权威的角色和统治自己的过程中,宣泄出来;另一方面而言,作为国家机器权力的执行者,卡明斯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也是受害者。在现代权力的漩涡中,卡明斯最终没有做成上帝,他和他的士兵们一样,成为他所奴役和驯服的“机器人”中的一员。法西斯主义狂热煽动了一大批盲从的跟随者,美国极权主义也造就了一大批这样麻木的、丧失主体意识的“机器人”。军队是社会的缩影。梅勒称这样的美国社会患上了集体精神崩溃症,其中,人人都像卡明斯,生活在精神分裂中:一个“我”虚伪地和社会表面维系着一致性,另一个“我”清醒而痛苦地承受这一切。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影响。美国通过战争暴敛大量财富,不仅从战前的“经济大萧条”中迅速恢复,显示出超强的经济生命力,而且它的军事力量也增长到了历史巅峰期。经济、军事的蓬勃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必然导致盲目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的民众更愿意相信一个假象:美国的综合实力越强,离“自由”、“民主”的目标就越接近。在这样理念的引导下,社会舆论导向发生严重偏移。一些社会学家如罗伯特·达尔、大卫·理斯曼等纷纷提出“多元主义”权力观、“权力分散”论,认为美国的政治权力被分散的否定群体所分割,具有统治意义的权力群体不复存在。在《孤独的人群》(1950年)中,大卫·理斯曼举了美国二战期间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战略空军司令部是战时权力最大的部门,掌控海、陆、空三军的调配,但即使这样的权力机构也受到诸如国际科学委员会之类群体机构的制约,权力在平衡各种不同的集团和群体中被抵消,从而得出结论:独裁极权主义在美国不复存在。还有的学者将权力的表现形式分成“分散权力”和“完整权力”[13],或者是 “成员间权力”和“系统权力”[14],虽然称呼不一样,但二者都指权力是参与者之间权利平衡和划分领域,存在于一方权力与另一方权力相互抵消的关系中,其含义和本质与“多元主义”权力论和大卫·理斯曼的“权力分散”论非常接近。诺曼·梅勒对这些言论进行驳斥,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二战后的美国经济发迹于战争,迅猛发展是种假象,与之一起发展的还有美国在战争胜利中膨胀起来的政治野心和不断成熟的政治手段。“虽然对在美国谁拥有权力远要比问在苏联谁拥有权力难以回答,但是说在美国不存在权力,或者不存在权力的影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15](P197)。在现代的美国,相对二战时期简单的极权主义、纳粹主义,以及冷战期间的斯大林主义而言,现代极权主义不再以专制、非人道权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截然对立形式出现,而是运用各种方式将外在的、强制性的、会引起反抗或敏感的权威通过战争、舆论、媒体、法律、科技、教育等方式灌输给人们,这些“匿名的权威”一旦内化为“权威主义良心”,行为规范、思想顺从、如“铁板”僵硬的“机器人”是必然结果。现代元素的加入“匿名的权威”实质变得更隐蔽、更具欺骗性。梅勒犀利地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极权主义已经成为战后美国社会的时代精神,渗透到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这种极权主义并非政治性的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而更多的是一种道德、心理或精神层面的危机。“自由”不过是一种假象。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呼吁大家要逃离这种被权威内化的“自由”,与诺曼·梅勒对极权主义心理的深刻理解如出一辙。
诺曼·梅勒曾经在《裸者与死者》中借卡明斯之口预测“战争中还有一种渗透现象……就是胜利者往往会接过失败者的……衣冠来穿戴。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后,国家很可能会法西斯化”。而且“战后我们的外交政策必将变得百倍的露骨,决不会再有那么多伪善的姿态了。我们再也不会右手伸出帝国主义的利爪,左手掩住自己的双眼了”[8](P410)。担心在战后很快变成了现实。二战结束后没多久,美国便在极权主义心理的驱使下“伸出帝国主义的利爪”,开始了领土扩张和文化殖民运动,战争的炮声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背景音乐。
五 结 语
客观地看来,诺曼·梅勒受到新精神分析学派影响,夸大心理结构的社会功能,将弱势群体对强权的被动接受简单描写成主动受虐心态,把美国国家法西斯主义的野心、权力政治复杂的集体事业生物化地归因于原始状态的人性特征,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权威主义性格”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存在的心理基础,暗示了战争和杀戮的根源,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在世界矛盾和冲突日益升级的当下,产生“权威主义性格”的社会条件仍然存在,战争仍在世界各地陆陆续续地发生着,那么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有存在、酝酿和复苏的可能,诺曼·梅勒的预言将还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现代社会上演。这,就应该是诺曼·梅勒在《裸者与死者》里努力想要告诫我们的。
[1]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2] [美]丹尼斯·朗.权力论[M].陆震纶,郑明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 Hobbes,Thomas.Leviathan[M].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58.
[4] [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5] 谷红丽.理解诺曼·梅勒[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
[6] [美]丹尼尔·霍夫曼.美国当代文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
[7] Karl,Frederick R..American Fictions:1940-1980[M].New 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83.
[8] [美]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M].蔡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9] [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10][美]弗洛姆.逃避自由[M].孙名之主编,刘林海译.北京:北京国际文化公司,2000.
[11]季水河.文学名著精品赏析[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
[12]Mailer,Norman.The Presidential Papers[M].New York:G.P.Putnam’s Sons,1963.
[13]Doorn,J.A.A.Van.Soci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Power[J].Sociology Neerlandica,Winter 1962-63,(1):16-18.
[14]Lehman,Edward W..Towards a Macrosociology of Power[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9,(34):453-463.
[15]Mailer,Norman.David Riesman Reconsidered,Advertisement for Myself[M].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