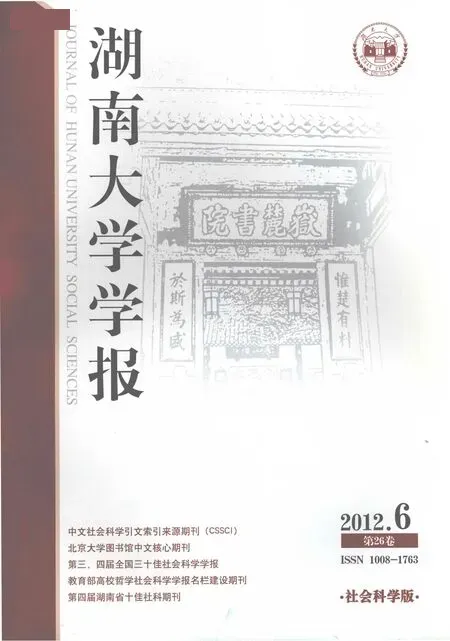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探险小说中的狩猎书写*
胡素情
(1.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2.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探险小说也称为“探险罗曼司”。因海外探索和殖民扩张,探险小说成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最受欢迎的文学类型之一。吉卜林(R.Kipling)、哈格德(R.Haggard)、亨蒂(G.A.Henty)等探险小说家的作品盛行一时,英帝国的进程与探险文学的繁荣齐头并进[1]。而丰沛的狩猎内容是探险小说最瞩目的特征之一,海外狩猎是大多探险小说的必备情节。如亨蒂这一在儿童文学中独占鳌头的探险小说家,其作品充满了对猎物、兽皮、猎枪的书写;里德(Mayne Reid)的系列探险作品仅从书名便可知内容:如《少年猎手》、《长颈鹿猎手》、《野马猎手》、《年轻的狙击手》等;金斯顿(W.H.Kingston)的作品《捕鲸者彼得》、《猎人亨德里克斯》、《在非洲野外》等都有大量狩猎内容。
因涉及帝国意识和性别歧视,探险小说及其理论研究在英语国家被长期忽略,被认为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类型而归于社会学领域。事实上,探险故事通过想象和叙述参与社群或国家的心理建构,亦有其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小说修辞。在率先进入工业革命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狩猎这一古老的象征性、仪式性活动为何在探险文本中如此盛行?大量的狩猎书写是否有特定的目的和现实意义?它又采取了怎样的方式与历史和文化互动发挥其影响?
一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海外狩猎风尚
狩猎在英国有悠久的历史,但多流行于王公贵族。它最初源自皇室的射鹿运动,可追溯到1066年诺曼底公爵占领英国前后的9到11世纪。在数世纪的英国狩猎变迁史中,狩猎及其相关法规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它与地位、身份、土地和经济状况的密切相关性,狩猎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2]。随着麋鹿及其他大型动物数量减少,狐狸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猎取对象。即便在18、19世纪的圈地运动和工业发展中,猎狐这一活动仍然得以保持,并且因圈地能提供大面积围场,拆除不利骑射的村舍,为城市新富提供了更好的围猎场所。也正是在维多利亚时期及其前后(1800-1914),猎狐作为大众娱乐在英国盛行一时[3],它从贵族项目转变为新兴中产阶级的日常娱乐,成为新富、新贵阶层彰显自身实力的最佳活动。英国现实主义大师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就是一名狂热的猎狐爱好者,在他的小说中,猎狐隐喻及场景总是不经意间被作家顺手拈来,其频率之高常导致读者抗议。
国内的猎狐活动以精确瞄准和策马追赶的姿态构建了富于野心的征服者形象,并将这种雄性气概带到海外殖民地的最深腹地。这在哈格德和吉卜林等人的海外探险小说中进一步深化。对海外动物的征服和猎杀情节反复出现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探险小说和游记中。如坎贝尔(Water Campbell)的《我的印度游记》中这样描述英国人与殖民地动物之间的对抗关系:“永远不要攻击一只在行进中的老虎。要是万一遇上这样的情形,那么,像大英帝国一样去面对它,杀死它!因为如果你不能杀死它,它肯定会杀了你!”[4]
老虎是东方丛林中的“百兽之王”,是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文化象征。在这段话中,猎杀一头印度老虎上升到国家意义上殊死搏斗的高度,可见海外狩猎在维多利亚时代有着重要的政治蕴涵和殖民意义。如威廉森(Thomas Williamson)认为,猎虎是男人的消遣,它需要冷静和眼力,它有利于培养典型的维多利亚性格[5]。此处的“维多利亚性格”自然与帝国扩张和海外殖民高度相关。泰勒(Philip Taylor)在《一个恶棍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Thug,1837)中回忆他在1820-1830年间的海外狩猎造就了一个更“男性”、更“强硬”的心智[6]。可见,成为一名英勇的狩猎英雄有着非同寻常的帝国政治意义,它象征的开拓和逐猎精神成为英帝国建构国家身份的重要表征。麦肯齐(John MacKenzie)指出,大型海外动物狩猎是19世纪英帝国在亚、非最主要的殖民活动。非洲的象牙是诱使欧洲殖民者深入非洲腹地的最主要原因,为更大规模的殖民扩张铺路[7]。英国国内的猎狐精神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海外动物猎杀中达到了一个顶峰,并演变出新的殖民意义。
二 维多利亚时期探险小说中的“伟大的白人猎人”形象
维多利亚时期的探险小说造就了一个所谓的“伟大的白人猎人”①“伟大的白人猎人”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探险小说对殖民地白人猎人的自诩性称谓。哈格德系列小说的主人公夸特曼最先得此“殊荣”。参见Sampson,Robert.Yesterday's Faces:Dangerous Horizons[M].Volume 5.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形象。该形象最初源自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探险小说家哈格德的作品。下文将主要以他为代表探讨探险小说中的狩猎书写。哈格德的探险小说如《所罗门的宝藏》、《她》、《阿兰·夸特曼》(Allan Quatermain)等至今仍被广泛阅读,他的小说充斥着对海外大型动物的猎杀场景。其探险系列的主人公夸特曼就是一个主要以获取象牙谋生的猎人,而且几乎在他的每一部系列小说中出于利润或娱乐动机杀戮无数动物。有学者这样评论哈格德的狩猎书写:“哈格德的非洲小说倾向于把非洲当成一个英国贵族家的林园,到处是各种等着被射击的大小猎物……他的创作想象离不开野外猎物。”[8]
为建构“伟大的白人猎人”形象,探险小说的狩猎书写遵循一些既定的叙述内容和形式。首先,狩猎情节强调对现代身体的展示与书写。在探险活动中,猎人们在陌生环境中经历疾病、瘟疫、危险,都是身体的戏剧化运动,尤其在遭遇野生动物时举枪猎杀的场景是不同程度上身体的展示。这对应着格林的观点,“探险小说与当代英语语言理论最合拍的是身体的重要性。”[9]探险小说很注重身体并强调其高贵性,而这种高贵性往往与猎人们的武器是分不开的。如怀特(Andrea White)评论《鲁滨逊漂流记》中的英国文明,他认为鲁滨逊的枪才是最关键的工具,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存活并显示出对野人的优越性[1]。类似地,在面对原始生态中的非洲人和动物时,枪弹是哈格德笔下白人猎人们须臾不可离的工具,是殖民者在他者境内生存的最大支撑和身体延伸。综观19世纪的探险游记或小说,几乎所有的白人猎手都带枪行动,即便是梦中也是枪杀动物的镜头:“我迷迷糊糊地记得利奥曾睡眼惺忪地说过如果能一把抓住水牛的两只角,再朝它脑袋上开一枪,准能把它打死,要不然就把子弹送进它的喉咙里去也行这类胡话。”[10]故探险小说或游记常花大量笔墨对枪弹和装备进行详尽的描写。装备叙述一方面是展示科技和现代理性的强大,另一方面也是间接的身体书写。人枪合一的状态使枪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对枪的重视就是对身体的重视。在这些探险小说中,在枪弹和探险精神武装下白人的体魄总是强健的,历经九死一生后还能完好无损,尤其在动物和土著的正面或反面衬托下,白人的身体显示出不失天然的强健。对强壮身体的展示与资产阶级的自我肯定密切相关,它是“力量、精力、健康和生命的一种无止境扩张。强调身体必须与建立和增强资产阶级的霸权联系起来”[9]。
其次,白人猎人形象的建构明显借助探险小说的“叙述英勇”。“叙述英勇”指一种凸显雄性特质和权威感的叙述方式。海外行猎是典型的身体、力量与霸权的完美结合,它预设着读者与主人公一起去体会暴力和杀戮,并带来征服的权力和兴奋感[9]。这些征服感不仅通过情节和内容,也通过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语言得以表现。尤其在对大型动物的猎杀叙述中,猎杀过程总是轻松、从容而有惊无险,而随从的土著或向导则被描述为无能、懦弱、女性化的形象。不仅如此,探险小说中的大型动物也常被“女性化”,猎杀过程常被隐喻为彰显男性征服的性行为。狩猎者的身体运动、追逐的刺激以及射击成功后的狂喜都是典型的性隐喻。这一隐喻进而意味着文明对原始和野蛮的征服,并从中获得文明人久违的生命和力量源泉。
第三,狩猎书写有意营造浪漫主义氛围。哈格德笔下的非洲总是风景优美,宛如仙境,那儿有着“极度荒凉而迷人的景色”以及“英俊的大羚羊”等着白人去享用和开拓。哈格德的主人公夸特曼总是无法忍受伦敦的“喧嚣”和“噪音”数次重返非洲,赋予非洲野性自然以乌托邦似的吸引力。若比较哈格德与康拉德笔下的非洲,便可发现前者浪漫的世外桃源在后者的小说,如《黑暗之心》中已成为一片被掠夺殆尽的狼藉之地。
三 兴奋与喜悦:维多利亚时期探险小说中的狩猎情绪及其重复模式
19世纪的探险小说在阅读心理上有两个功能,一是给没有政治地位和权力的人们以幻想空间,二是加强人们对已有之物的安全和快乐感。[9]探险小说对心理的补偿和娱乐功能在狩猎情节中尤其突出,它让普通读者在阅读和想象中间接参与帝国的海外殖民事业,激发浪漫的征服和扩张感。哈格德的小说对大型动物狩猎带来的兴奋感情有独钟[11]。在哈格德的小说中,打猎是刺激主人公去海外探险的借口和推动,能在海外带回大型猎物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上都是可称道之事。在《她》中,剑桥大学的学者霍利及其养子对是否去非洲寻找白人远祖游移不定时,正是狩猎的想法促成了这一冒险:“我想那一定是个幅员广阔的国家,一个遍地野兽出没的场所!……我不相信有险可探,但相信有大猎物好打。”[10]狩猎的娱乐精神掩盖了探险背后的真正目的,正是这看似不经意的猎奇之路铺就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恰如福柯的观点,当一种掠夺以娱乐的形式出现时,它带来的破坏是致命的,娱乐的主动性和渴望重复的特征使其成为无止境的饕餮。
在漫长的人类-动物关系史中,捕获动物带来食物和皮毛的饱暖无疑是快乐的。这种快乐满足的记忆长久形成于人类文化的心灵“脚本”中。在海外探险中,大型猎物的出现也无一例外地会激起小说中猎手的兴奋和射击的本能。因为有大威力猎枪,狩猎过程一般而言有惊无险,但野生动物的活力和自卫本能仍使得这种不平等的猎杀饶有兴味。以哈格德的小说为例,成功的猎杀总会带来快乐、兴奋之情,出现“狂喜”、“兴高采烈”等词汇。如在《阿兰·夸特曼》中作者写道:“有时我们带着专业训练的狗出去猎鹿,那可真是激动人心的运动。”而放鹰狩猎,也是“最受欢迎的”。[12]《所罗门宝藏》中,白人的寻宝探险队会停下来两天专门猎象。只要一谈起大型猎物,几个探险者无不“兴致勃勃”,“兴趣盎然”,谁也不能否认,来自“迷人的赤道地区”的美景和野生资源是探险者受用一生的快乐“美好记忆”的重要来源。而现实中来自英国的印、非探险者们与探险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也体验着海外探险的兴奋和跃跃欲试的雄心。谢尔(Heather Schell)在《维多利亚动物梦想》中描述一位现实中的探险者初到印度时的心情也无一例外是兴奋而快活的期待:“当桑德森在1864年到达印度的马德拉斯时,他想象着那愉快,充满着‘野象、老虎和野牛’的‘丛林生活’,而且也果然在日记中描述了猎得第一头老虎的骄傲满意之情。”[13]正如职业猎象者萨瑟兰(James Sutherland)说:“很难找到比这(指猎象,本文注)更狂野,更令人狂喜而兴奋事情了。”[13]
兴奋和快乐是正面、积极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塑造白人殖民者光辉显赫的自我形象中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因情绪背后常有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近年来人们对情绪的文化研究日益兴盛。快乐具有社会性,社会主流价值判断会使快乐表现出特定的倾向性,具有其时代特征。下文将引用情绪理论家艾哈迈德(Sara Ahmed)的正面情绪理论来考察狩猎中的快乐文化心理。艾哈迈德认为,愉悦或高兴等正面情绪并非主体无缘由的体验,它往往由某“对象”引起[14]。她重点考察了与快乐相关的重要英语词汇“happiness”,发现其词根“hap”有“碰巧”或“幸运”之意。因而,一个人之所以快乐,往往是遇上了令人快乐之“事”或“物”,它引起我们愉悦、兴奋等积极的情绪体验。海外探险的兴奋和快乐之情尤其可说明这一点。哈格德的主人公们在非洲的草原上常常与某只美丽或英俊的麋鹿或羚羊遭遇,这是不期而然的快乐体验,狩猎顺利的话,收获带来的快乐之情便是唾手可得的了。《所罗门的宝藏》中有这样一幕:探险者们在山下偶遇一群已超出射击范围的长颈鹿,“走在前面的古德手里正好端着一支快枪,他忍不住开了一枪,竟打中了跑在最后面的一只年轻的长颈鹿。”而“能打中这只长颈鹿绝对是个意外和巧合”[15]。这个情节暗示着一种既偶然又惊喜的帝国心态。19世纪因工业革命和海外扩张的英国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了世界头牌工业国家,拥有世上最广大的领土,对英国人自己而言都是一个“惊喜”。因经济和资源之“物”带来的民族自豪和自得之情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十分普遍。
从现象学角度看,快乐具有意向性。在意向性的指引下,快乐原则成为某些“物”的原则。此处的“物”指一切物质和资源之总称,如动物、矿产、果蔬等。快乐常常寄寓于“物”中,“物”带来的共同感受将人连结在一起,进一步形成胡塞尔所言身体的“近端范围”和“核心范围”,形成某种统一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探险小说中,海外动物作为快乐和兴奋的象征之物凝结了英帝国的殖民欲望和征服心理,它们意味着新奇、利润和异国征服,是具有政治和经济回报的愉快之物,是人人都该去猎取的对象。因而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想象中,去海外的“蛮荒之地”捕获大型动物是收获快乐和冒险的最好途径。对于不能去海外狩猎的国内人而言,观看异国动物带来的兴奋、快乐之情一度成为这个国家鼎盛时期的主要心态。来自非洲的大象、犀牛、狮子,来自印度的老虎、猴子在英国巡回展览,无论大人孩子无不前往观看。观看这些动物不仅能满足好奇心,更多的是为帝国征服之地的广袤,物资之丰富而欢欣鼓舞,汇成帝国膨胀的殖民民族情绪。
当然,当快乐之物在传播时,不见得它能引起每一个人的快乐之情,要分享此物,意味着认可此物是“好”的或“善”的。艾哈默德认为,对某物是否引起快乐的价值判断往往是预先设定好的[14]。猎取动物的快乐价值预设在西方有着漫长的思想传统。基督教的《圣经》在人类-动物关系上虽然有很多抵牾之处,但上帝将动物托管于人类是人尽皆知的故事。哈格德晚年创作过一部名为《马哈默与兔子》(The Mahatma and the Hare)的寓言,故事情节是一只被捕获的兔子与猎人之间的对话。猎人以圣经为权威替自己辩护:“你是一只动物,我是能统治你的人,你可以去读《创世纪》。”他又说:
“有些东西让我不得不告诉你等级秩序,让我在射杀动物时享受我的技艺,或者从狩猎和杀死动物中获得乐趣……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宗教恰恰允许我做这些事,从这个角度看我没有任何过错。”[16]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动物作为财产在资本主义拜物原则下有了新的诠释。洛克在以《圣经》为立论点的《政府论》中将猎取得来的动物归于神圣的劳动成果:“野兽仍被看作是共有的,不属任何人私有。只要有人对这类动物花费了这样多的劳动去发现并追逐它,他就使她脱离原来共有的自然状态,而开始成为一种财产。”[17]故基思(Thomas Keith)认为,基督教虽然在促成西方对自然的掠夺开发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17世纪开始的商业和贸易需求是更重要的原因。他引用1680年托马斯·特莱恩对印第安人和欧洲入侵者对自然的态度比较,发现前者是有节制的需求,后者出于新的商业动机的无情屠杀[18],其结果是非洲皮毛、象牙交易下巨大的利润和原始积累。异国动物是英帝国殖民经济链条中的重要而且首要的一环。《全球通史》以英国在非洲的开普殖民地为例,19世纪上半叶,掠杀非洲野生动物取得的财富在开普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到1835年,它占殖民地出口额的一半[19]。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广阔的草原上,成群结队的野牛是出口获利的源泉。非洲的象牙,非洲和美洲的鳄鱼皮,都是西方奢侈品的原材料。西方社会无论在衣食住行的哪方面都极其明显地高度依赖动物资源[18]。
维多利亚时期探险小说的狩猎书写不仅凸显了兴奋、快乐之情,也采取了相关叙事手段加强这些情绪体验。最典型的有重复叙事、清单式描写和平实风格。在探险小说中,有一脉互文性的对“物”的重复叙事。18世纪的英国文学已出现对“物”的书写,如艾迪森(Joseph Addison)的《一个先令的历险》和斯摩莱特(T.G.Smollet)的《一颗原子的历史和冒险》。对“物”的书写背后是18、19世纪资本主义消费经济的兴起。这些“物”在维多利亚的探险小说中进一步演变为异国猎物、昆虫、钻石、象牙……有着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自然探索的博物学背景。康拉德《吉姆爷》中的蝴蝶收集、《黑暗之心》中的象牙掠夺、哈格德《所罗门的宝藏》中的钻石探寻、吉卜林短篇小说《国王的象叉》中的象牙标枪等都算作是“物”的隐性叙述。它们遵循几乎雷同的“被追逐、被占有模式”。而狩猎情节更是遵循高度统一的重复叙述。狩猎书写能给读者带来对异域之物的“拥有”和“享用”愉悦,激起再次体验的需求。为让这种快乐多次重现得以持续,重复的狩猎叙述便成为小说情节的必要策略了。[20]麦肯齐指出,英国的国内猎狐或海外猎象逐渐形成了一种显示地位、实力和优越感的活动后,男性猎人(man the hunter)形象便成为一个不断被重复的神话[7]。
清单式描写是探险小说的另一个叙述特征。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中对清单式叙述有过专门论述。对物品清单式的清点和叙述并非文字累赘,而是一种有意义的重复模式。英国18世纪就已流行的狩猎笔记是猎人们对大型猎物的平实记录,这些记录包括围猎者人数、枪支数量、射击数目和所打野兽数量或失误的情形,还有一种是对猎物的非常详尽的清单式描写,包括解剖学式的数据记录。如所打老虎的身长、鹿角的大小、象牙的长度等。探险小说也继承了这种翔实风格。如《所罗门的宝藏》中对武器的清单式叙述:
三杆重型的后膛装弹的双八猎象枪,每支大概重15磅,能装8打兰的黑火药。其中两支是伦敦一家著名公司生产的……
三杆双精度的500快枪,可装六打兰重的火药……
一支双精度的12号中火步枪,有火药桶和阻气门。这支枪后来在我们打猎时非常管用。
三支温彻斯特循环步枪,备用。
三支单动作柯尔特式自动手枪……(省略号为本文注)[15]
从情绪的角度看,对描绘对象的清单式描写表现出对“物”的欣赏,对帝国财富、武器和科技文明的自我陶醉,明显有帝国意识形态的支撑。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对自然及其探索有高度兴趣的时代。每发现一个海外新物种,一处新地貌,都会被详尽地记录下来成为博物学的新进展,表达了英帝国欲囊括天下的野心。英国博物馆、动物园或动物学家的收集品种的重要来源就是海外猎人的动物猎杀。
为了使探险内容更可信,也基于内容的部分真实来源,维多利亚时期的探险小说也染上了自然质朴的风格,文字多趋于平白晓畅。英国探险小说的前身——探险游记就以真实为最高宗旨,并采用不损害真实感的平实叙述风格。哈格德的《阿兰·夸特曼》的主人公在故事中夸耀他是一个没文化、说粗话的猎象者。亨蒂(G.A.Henty)的主人公也同样宣称他们以亲身经历为基础朴实写作,而不是学究知识。不掉书袋的实用写作体在探险故事中十分常见。因平实创造的真实感及其煽情特征,探险小说吸引了一大批去海外为帝国效忠的年轻人。哈格德的小说叙述就很有效果,很多人正是读了他的小说后,毫不犹豫地奔赴非洲去寻求哈格德小说中那样的探险和狩猎之乐。哈格德的影响在下文可见一斑:“毫无疑问,哈格德的南非罗曼司使很多年轻人心中充满了渴望,希望亲自在那片广阔的空间和土地上见证自己的奇迹,因此,哈格德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新移民和影响力是我们难以估计的。”[21]这从探险小说的畅销程度也可得到印证:里德(Mayne Reid)的《头皮猎人》(1851)(The Scalp Hunters)在1890前销售了一百万本,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去西部吧!》(1855)(Westward Ho!)到1889年时卖了五十万册,哈格德的《阿兰·夸特曼》在出版第二年就卖了一万本。
结 语
维多利亚时期的探险小说对海外动物猎杀的大肆书写是探险小说的常见情节和看点,这与现实中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盛行的猎狐活动和海外大型动物狩猎互为印证。而探险小说激起的兴奋、快乐之情既以重复的形式塑造了西方白人猎人的身体和欲望,建构了扩张性的殖民形象,也以大众文学的形式增强了帝国的殖民意识形态,勾勒了这一时代独特的殖民扩张情绪图景。
[1]White,Andrea.Joseph Conrad and the Adventure Tradition:Constructing and Deconstructing the Imperial Subject[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2]Griffin,Emma.Blood Sport:Hunting in Britain Since 1066[M].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3]Howe,James.Fox Hunting as Ritual[M].American Ethnologisit,1981.
[4]Campbell,Water.My Indian Journal[M].Edmonston &Douglas,1864.
[5]Srameck,Joseph.Face Him Like a Britain:Tiger Hunting,Imperialism,and British Masculinity in Colonial India,1800-1875[J].Victorian Studies 48,4(2006):659-680
[6]Taylor,Philip.Confessions of a Thug[M].A.Blond,1867.
[7]MacKenzie,John M.The Empire of Nature[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
[8]Stiebel,Lindy.Imagining Africa:Landscape in H.Rider Haggard's African Romances[M].Westport:Greenwood Press,2001.
[9]Green,Martin Burgess.Seven Types of Adventure Tale[M].Pennsylvani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
[10][英]赖德·哈格德.她[M].胡心吾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1]Senior,John.The Continuity of the Spirit Among All Living Things in the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of Henry Rider Haggard[J].Current Writing,18(1)2006.
[12]Haggard,Rider.Allan Quatermain[M].1st World Library,2006.www.1stworldlibrary.com.
[13]Morse,Deborah Denenholz(ed.).Victorian Animal Dreams[C].Burlington:Ashgate.2007.
[14]Ahmed,Sara.Happy Objects[A].Melissa Gregg,Gregory J.Seigworth,ed.The affect Theory Reader[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
[15]Haggard,Rider.King Solomon’s Mines[M].New York:Tom Doherty Associates,Inc.1998.
[16]Haggard,Rider.The Mahatma and the Hare[M].New York:The Quinn &Boden Co.Press,1911.
[17][英]洛克.政府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8][英]基思·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M].宋丽丽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9.
[19]王志军等译.全球通史(第九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20]Haggard,Rider.The Days of My Life[M].ed.C.J.Longman.2vols.London:Longmans,2008.
[21]郭茂全.狩猎文化的式微与狩猎文学的勃兴[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9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