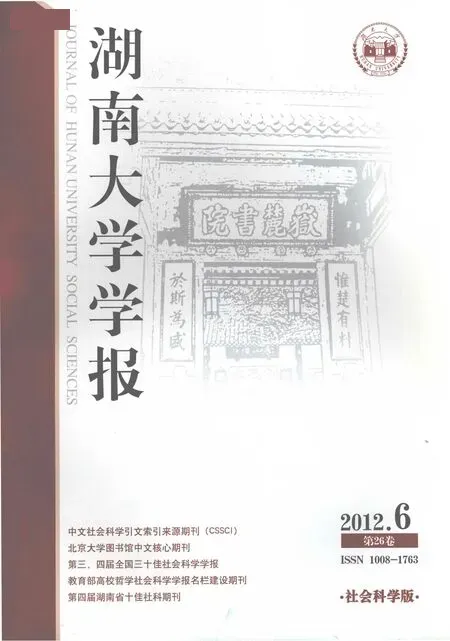从失语到“喧哗”:论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女性历史与文学史的追寻*
潘 建
(湖南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205)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①“Virginia Woolf”有几种汉译形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芙、弗吉尼亚·吴尔夫等,本文从第一种译法。但如果引文采用的是其他译法,为了尊重被引用者,则沿用其译法(包括书名和文本内容)。在剑桥大学的演讲《妇女与小说》(“Woman And Fiction”,1929)中说:“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1](P1627)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中,我们都寻不到女性的名字,她们生死都只是女儿、妻子和母亲。伍尔夫后来将该散文扩展并以《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出版,称:“如果是女性,我们就只能通过女性先辈思考过去。”[2](P557)这一观点旨在说明,现存历史没有女性的身影和声音,但那并不等于说,女性没有历史。那么女性历史何在?女性文学史何在?在伍尔夫看来,女性不仅被父权制赶下了可能创造历史的舞台,而且,即使女性曾经创造过历史,它也被男性历史撰写者或男性历史学家故意“遗漏”、“挤压”或“埋没”了。关于伍尔夫对英国女性历史的看法,散见于国外许多伍尔夫学者的论述中,但至今未曾见到专论;至于国内伍尔夫研究方面,学者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作品的叙事艺术、意识流写作、雌雄同体观,等等,鲜有学者注意到伍尔夫对于女性历史的叙述及其重建的努力。因此,本文将从伍尔夫抗议女性历史的缺失、追寻女性历史的努力等方面论述她对构建英国女性历史的贡献,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 集体失语
伍尔夫认为,女性一直游离于父权文化的边缘,被隐形、被排除在史书之外。《一间自己的房间》认为,英国的史书有一个共同点,即伟大政治领袖的名字充斥其中,但是,找不到女性的名字。即使偶尔有一两个,不是女王就是贵妇。如果人们去阅读英国历史,关于维多利亚人的父辈,人们总能知道一些情况。他们曾经是士兵或者水手,曾经使用过这间或那间办公室,曾经制定过这条或那条法律,等等。记载在史书中的不是战争就是政治,不是财产就是学校,不是军队就是教堂,而女性与上述这一切都没有多大关系。伍尔夫发现,对于18世纪之前的英国女性,历史就意味着空白。那么,关于维多利亚人的“母亲”、“祖母”、“曾祖母”……,历史记录中到底留下了什么呢?除了某种传统以及她们的姓名、结婚日期和子女数目之外,其他一无所有。也就是说,女性只被列入出生名单中,死时名字被刻在墓碑上,此外,再无其他信息。因此,当女作家想要追寻关于自己先辈的历史和文学史时,根本是在寻找不存在于任何谱系中的血统。如果沿根而上,直到古代的“母亲”,人们就会发现,她们的根源就是大地本身,但她们的痕迹却像灰尘。至于她们是否创造过丰功伟绩,是否受过教育,是否有自己的起居室,有多少女性在21岁前就有了孩子,为何伊丽莎白时代女性不写诗歌,等等,这些情况都无从得知。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还以特里维廉教授(G.M.Trevelyan)的《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1926)为例,说该书第一次提到女性是在15世纪的历史中。关于女性地位,有几种情况,一是打老婆被认为是男人的公认权利,不论高低贵贱,男人打老婆而不会觉得羞耻。二是女儿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父母所选择的夫婿,否则就有可能被关起来或挨打,而不会引起公众舆论的震惊。三是男女结婚早,往往一方或者双方还在摇篮里就已经订婚,未完全脱离保姆的照顾就已经成婚[2](P526)。《英格兰史》第二次提到妇女是在17世纪的历史中,说的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和一些回忆录中的女性,例如,弗尼夫妇的回忆录和哈钦森夫妇的回忆录中曾提到的女性。这些作品中的女性“似乎都并不缺乏个性和特色”[2](P526-527),但是没有详细描述,以至于弗尼夫妇和哈钦森夫妇回忆录中的女性到底有什么个性和特色,做过什么事情,有过什么丰功伟绩等情况,都不得而知。事实上,女性只活在文学作品中:在所有诗人的作品中,女性都像烽火般燃烧着,成为想象中最为重要的人。即使到了19世纪前半叶,女性依然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她们默默无闻地生活、结婚、生儿育女,直至终老。一如伍尔夫在小说《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中描绘的女主人公拉姆齐夫人(Mrs Ramsay),除了“拉姆齐夫人”这一身份,读者自始至终都无从知道她姓甚名谁。虽然她在小说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不可或缺的母亲、妻子和完美的女主人。她的职责包括照顾8个孩子、安慰需要同情的丈夫、操持做不完的家务、“总为50英镑修缮费发愁”等等。
由于女性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私人空间,无法去参加任何伟大的运动或行动,因此,她们不仅缺席于史书,也缺席于名人轶事录。她们因此而成了奇怪的“复合人”(“composite being”)[2](P528):想象中,她们最为重要,而实际上,她们则完全无足轻重,几乎不识字,只是丈夫的财产。她们最大的功能就是充当一面可以把男性“以其自然大小两倍的方式”[2](P520)放大的魔镜。如果没有这面魔镜,地球至今仍然还处在蛮荒时代。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不断强调这一事实,即女性的背后没有传统,或者说传统是如此短暂而又不完整,结果无甚助益。因此,女作家如果要追寻自己同类的传统,她(们)所面临的将是重重困难。
笔者认为,造成女性在历史和文学史中沉默与缺席的原因很多,至少有以下几种:一是菲勒斯中心社会的霸权与父权体制的压迫所致。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说:“纵观历史,显而易见的是妇女在各个领域里的成就——政治、艺术、哲学等等——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讲,都不及男性的成就大。这是为什么呢?……社会把妇女限制在一个低人一等的位置上,而这一点又影响了她们能力的发挥。”[3](P143)父权社会中的社会性别分工不仅限制了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女儿”、“妻子”和“母亲”,还将其活动空间严格控制在狭小的家庭之内。她们生来就被安排承担家务劳动,没有机会受教育,或者即使受了些许教育,也没有机会施展才华。她们既受到家长制的限制,又受到开放世界和职业制度的压迫。“未婚女士似乎无法自食其力,除非当家庭女教师,而由于她的天性和所受的教育,或者根本就缺乏教育,使她难以胜任这一职位。”[4](P1100)实际上,女性脖子上套着的是双重枷锁。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是有某位女性还能有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反而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像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不是在劳作者、文盲、仆人中诞生出来的。即使某些女性有天才,那她的才华也没机会诉诸笔墨。因此,每当读到一名女巫被人们所回避,或者某女被魔鬼所附身,或者一个聪明的女人在买药草,或者甚至某个杰出的男人有位母亲时,我就会想到,我们是碰到了一位迷途的小说家的踪迹,一位被压抑的诗人的踪迹,某个沉默而又淹没无闻的简·奥斯丁或者艾米莉·勃朗特的踪迹,她在荒野把自己的头撞破,或者在大路旁做鬼脸怪相,因为她的天赋折磨她,使她发狂。[2](P532-533)
伍尔夫断定,“在16世纪出生的任何一位具有了不起天赋的妇女都必然会发狂、杀死自己,或者在村外的某个孤独茅舍里了结一生,半是女巫,半是术士,为人们所惧怕又为人们所嘲笑。”[2](P533)因为她们无法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任何历史的丰功伟绩。稍微普通一些的女性,基本上无法自食其力,更谈不上参与和创造“伟大事业”的活动。除了女佣和家庭女教师外,当时没有职业女性的生平可写,而女佣和家庭女教师的生平,被记录下来的,根本就屈指可数。
二是男性历史和文学史编纂者或撰写者的刻意“遗漏”和严重挤压导致了女性和女作家的沉默与缺席。女作家被“挤压”到了一个极不正常的范围,以至只有极少数“伟大的”女作家被保留在文学史中,约翰·戈罗丝(John Gross)称其为“伟大传统的残余”(“the residual Great Traditionalism”)。至于那些“不够伟大”的女作家,人们根本就视而不见,并将其踢出文学史、文学选集、文学理论或教科书之外。其遭遇“就像有棵巨大的黄瓜将其枝蔓覆盖在花园里所有的玫瑰和康乃馨之上,使它们窒闷而死”[2](P544)一样悲惨。例如,英国历史上“为妇女地位而义愤填膺”的诗人安·温奇尔西夫人(Lady Winchilsea)和纽卡斯尔的马格里特公爵夫人(Lady Margaret Cavendish)、以书信写作著称的多萝西·奥斯本(Dorothy Osborne)、第一位女小说家范尼·伯尼(Fanny Burney)和第一位以写作为生的女作家阿弗拉·贝恩(Aphra Behn),等等,她们虽然有作品流传于世,但在文学史中却找不到对她们的记录和评价,而构成文学传统中必不可少环节的恰恰是这些不那么重要的作家,就是她们连接了文学传统链条中的一代又一代。没有了她们,我们就没有办法清楚地了解女性历史和文学史的连续性,也无法得到关于她们生活及其在法律、经济以及社会上的地位的可靠动态资料,女性文学史最终也就只能是空白。
三是女性本身的原因。由于长期的压迫和奴化教育,男性价值体系已经内化成为多数女性自身的观念,她们接受了处于边缘地位的命运,已养成了在男性面前怀着谦卑心态的习惯,即使有过什么“丰功伟绩”,也会闭口不谈,正如伍尔夫的散文《帕斯顿家族和乔叟》(“The Pastons And Chaucer”,1925)中的帕斯顿太太、《斯特拉齐夫人》(“Lady Strachey”,1928)中的斯特拉齐夫人、小说《雅各之室》(Jacob’s Room,1922)中弗兰德斯太太等女性的作风。留在家中照顾全家生活的帕斯顿太太写给丈夫的信中谈的不是她年轻时怎样独自面对冲进屋子里的“1000个挥舞着弓箭和火盘的男性”的英勇行为,也不是她所做的最值得人们记住的事情,例如,孩子们的呀呀学语、婴儿室和教室里讲述的故事等,而是家里牲畜的喂养、围栏的修补、抢劫和杀人案件等,就像一个忠心耿耿的管家对主人作的报告、说明、请示等。也就是说,帕斯顿太太只把自己定位在“管家”的位置上,虽然其职责和行为早已超出它,成为家庭的支撑和管理者。无论是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所表现出的巨大勇气方面,还是在只手撑起那个大家庭的正常生活本领方面,帕斯顿太太不比任何男性做得逊色。如果她更自我一些,如果她的女性意识更突出一些,她会将自己的“丰功伟绩”记录下来,供后世歌颂。至于那位“天生有处理大事能力”的斯特拉齐夫人,则把才华浪费在了按照丈夫的口授写公文急函、养育10个孩子和管理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大家庭等家庭事务上。
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她是个男人,她会统治一省或在政府管理部门中任要职。她天生有处理大事的能力以及从大处着眼对政治的把握,这些都是造就19世纪杰出的政府官员的关键要素。[1](P2052)
小说《雅各之室》中,独自抚养三个儿子的寡妇弗兰德斯太太在给儿子雅各写信的时候,说的不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殷殷思念和谆谆教导,诸如一定要做个好孩子啦,衣服要多穿点啦,不要跟坏女人鬼混啦,等等,而是俨然将儿子当成一家之主,细细报告着家里的大小事务,至于对自己是怎样独自凑足雅各的学费以及怎样维持家庭用度等艰辛只字未提。难怪夏洛特·杨(Charlotte Young)这样写道,“我毫不迟疑地宣称:我充分相信女性在各方面要劣于男性。同时,我还要毫不迟疑地说,这是她自己造成的。”[2](P773)女性早已经接受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而不自知。
有些女性既有才华,也并未养成在男性面前怀着谦卑心态的习惯,但是,摆在她们面前的困难仍然巨大,因为她们找不到施展才华的舞台,就像伍尔夫在散文《海斯特·斯坦诺普小姐》(“Lady Hester Stanhope”)中叙述的海斯特·斯坦诺普小姐一样。能干的斯坦诺普小姐给皮特先生当管家,没受过多少教育,却生来有一种魄力,有带兵的将才,可是,她的性别阻碍了她往最合适的方向发展。“假如你是个男人,海斯特”,皮特先生经常说,“我会给你一张空白地图,让你带上六万人进军大陆,我相信你不会让我的计划落空。我相信你绝不会让我的士兵闲着。”但事实上,她的力量只能在体内咆哮汹涌。她憎恨她的性别,仿佛以此来报复女性的局限。要不是因为普通女性的局限,她这样杰出的人物又怎么会被扼杀窒息呢。她只好把无边的雄心壮志全部投入她的想象中,为此她几乎把自己推到了发疯的边缘。[1](P2039)
斯坦诺普小姐最终去了威尔士的布威斯(Builth)过隐居生活,一边给穷人看病,一边写日记。“她随后出现在叙利亚,跨着一匹马,身着土耳其男人的裤装。此后直到去世,她只做过一件事,那就是对着英国咬牙切齿,抨击英国人忘记了他们中最伟大的人物。”[1](P2039)由此可见,即使有天赋的女性,其才华也是无用武之地的。
四是男女价值观差异使男作家和批评家很难公正客观地评价女作家的作品,更难使其从理论的高度去考察她们,从而导致其边缘化。18世纪出现了许多女作家以后,不少男作家/批评家都曾对她们作出过评价。但是,由于他们想要表现和加强的仍然是自己头脑中关于女性的固定文化形象,把女性写作看成是生物和美学创造力的永久对立面[5](P7),尤其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他们希望女性小说反映的是男性看重的价值观,而不是女性自己的价值观,虽然女作家早已超越了强制性的女性角色。男作家/批评家对待女作家及其作品的态度是挑剔的、批判的和居高临下的。他们利用自己的男性霸权话语来贬低女作家及其作品,例如,乔治·路易斯(George Lewis)、约翰·卢德楼(John Ludlow)、里查德·休顿(Richard Hutton)等都曾撰文对女作家作品进行过分析和评判①G..H.路易斯和里查德·休顿在《北英评论》(North British Review)上分别发表《女小说家》(“The Lady Novelists”,1852)和《约翰·哈利法克斯女作者的小说》(“Novels by the Authoress of‘John Halifax’”,1858);J.M.卢德娄在《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发表《悲哀》(“Ruth”,1853)。。休顿认为,女作家因为文化环境狭窄、经历经验有限以及受教育太少等原因,其最大的缺陷莫过于缺乏想象力[5](P90)。伍尔夫在书评《哈里特·威尔逊》(“Harriette Wilson”)中提到,《国家传记辞典》的编撰者托马斯·塞孔仅仅因为哈里特·威尔逊当过情妇,在评价其回忆录时就质问:“一个荡妇能爱一个姐妹吗?一个十足的娼妓能为一位母亲的死真正悲痛吗?”[2](P756)否定曾为情妇的哈里特·威尔逊没有亲情显然有失公正和客观。对待像简·奥斯丁那种被称为“伟大作家”的女性,也有许多敌意包围着她:说她不喜欢狗,不喜欢孩子,不关心英国,对公共事物漠不关心;还说她没有学问,没有宗教信仰,对人要么冷冰冰的,要么态度粗暴[1](P1965)。即使早期那些按照男性价值标准尽力模仿男作家写作的女作家也得不到肯定,其作品仍然不会被纳入“伟大著作”之列。19世纪70年代大多数男作家/批评家对女作家的看法是,女作家缺乏独创性、智力训练、抽象能力、幽默、自制力以及对男角色的了解。此外,由于男女作家的价值观不同,女作家认为重要的作品,男作家则持不同观点,例如女性的书信写作。虽然这些信件可能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写出来的,像弗兰德斯太太那样就着火炉边用浅淡饱满的墨水写出来的,身为女作家的伍尔夫视其为“女人们未曾出版的著作”,“你可以年年阅读,百看不厌”[6](P87),但是没有哪位男批评家认为这些普通女性就着壁炉边写出的书信是伟大著作。
既然能“名垂青史”的只是极少数女作家,很自然地,女性文学的所有理论也都来自这少数几个人。人们对女作家的批评也只针对她们,对其理论的研究也不停地围绕着“不可或缺的简和乔治”之洞见做文章。玛丽·艾尔曼(Mary Ellman)称这样的文学批评为“菲勒斯批评”(“phallic criticism”)。至于伍尔夫本人,虽然她也承认,简·奥斯丁(Jane Austen)、勃朗特姐妹(the Bronte sisters)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都是具有独创性的女作家,但她否认她们作为女性文学创始人的地位,因为女性文学传统应该远远早于简·奥斯丁,也应该有更多的女性为此传统做出过贡献。
二 “众声喧哗”
伍尔夫认为,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普通女性的生活一定散见于某些地方,人们经常会在伟人的传记中“瞥见”她们匆匆而过,消失在背景中。“她们隐藏了一个眼色,一阵笑声,也许还有一滴泪水。”[2](P529)倘若能把这些普通女性的生活收集起来,就能写成一本书。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建议,那些名牌大学的学生给历史加上一个“补遗”,并给那“补遗”一个“不惹人注目的名字,让女性可以不违礼法地出现在其中。”[2](P529)是否有名牌大学的学生这样做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伍尔夫本人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一重担。
根据伍尔夫的上述观点,女作家要重建女性历史与传统,就必须到“那些地位低微的无名之辈的生活中去寻找,要到那些几乎没有灯光的历史长廊中去寻找,在那儿,幽暗朦胧地、忽隐忽现地,可以看见世世代代妇女的形象”[7](P335)。身为女作家,伍尔夫不仅自己关注女性先辈的历史,尤其对改朝换代时期的历史以及女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感兴趣,就像其第一部小说《远航》(The Voyage Out,1915)中的男主人公特伦斯·赫维特一样,她关注普通女性“从未被人记录下来的那部分经历”。虽然她明白,很难真正了解自己那个阶级以外的女性,但是只要是有助于了解她们的书籍与资料,她都想知道。于是,伍尔夫广泛阅读能够找到的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并将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写进作品中。她“侵入”现有历史,挖掘那些“小人儿”和无名人氏的普通生活,把夹在国王与武士们英勇行为之间的卑下无名者的行为视为真正的历史,把大多数普通人在普通日子里的种种不为人所注意的行为以及他们的所闻、所思、所感都视为历史。伍尔夫搜集到了大量有关女性的生活资料,除了极少数资料是关于女王和贵妇的以外,绝大多数资料都是关于普通女性和文学女性的,并写下了许多关于女性的传记或评论作品。叙述女王和贵妇生平的文章有:散文《伊丽莎白女王的少女时代》(“The Girlhood of Queen Elizabeth”)、《阿 德 莱 王 后 》(“Queen Adelaide”)、《斯特拉齐夫人》、《荷兰勋爵夫人伊丽莎白》(“Elizabeth Lady Holland”)、《一位宫廷侍女的日记》(“The Diary of a Lady in Waiting”)等;记述普通女性生活经历的文章有:散文《美国妇女》(“The American Woman”)、《两位女性》(“Two Women :Emily Davies And Lady Augusta Stanley”)《范尼·伯尼的隔山姐姐》(“Fanny Burney’s Half-sister”)、《埃伦·泰利》(“Ellen Terry”)、《塞拉那·特林玛》(“Sarana Trinma”)、《海斯特·斯坦诺普小姐》、《萨拉·伯恩哈特》(“The Memoirs of Sarah Barnhart”)、《斯瑞尔夫人》(“Mrs.Thrale”)、《格雷老太太》(“Old Mrs.Grey”)等;更多的是记录和评价文学女性的生活及作品的文章,如散文《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纽卡索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Newcastle”)、《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简·奥斯丁》(“Jane Austen”)与《简·奥斯丁和愚蠢的鹅》(“Jane Austen and the Geese”)、《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我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I am Christina Rossetti”)、《萨拉·柯勒律 治》(“Sara Coleridge”)、《塞 维 涅 夫 人》(“Madame de Sévigné”)、《哈 里 特 · 威 尔 逊》、《威 尔 考 克 斯 夫 人 记 事》(“Wilcoxiana”)、《写个不停的妇人》(“A Scribbling Dame”)、《玛利亚·艾奇渥斯和她的朋友们》(“Maria Edegeworth And Her Circle”)、《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坡的海伦》(“Poe’s Helen”)、《多萝西·奥斯本的〈信札〉》(“Dorothy Osborne’s‘Letters’”)、《四位人物》(“Four Figurs”)、《奥罗拉·李》(“Auroa Leigh”)等。
还有许多文学女性的生活,虽然伍尔夫没有写成专章,但将其放在其他随笔和散文当中进行引介和评述。例如玛丽·卡迈克尔(Mary Carmichael)、伊丽莎白·布朗宁(Elizabeth Browning)、多萝西·奥斯本、乔治·艾略特、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玛利亚·艾奇渥斯、多萝西·理查逊(Dorothy Richardson)、温奇尔西夫人、玛格丽特公爵夫人等。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用了很长篇幅来论述使用了“女性句式”(“the woman’s sentence”)的女作家玛丽·卡迈克尔,说她“先是破坏了句子的格局,现在又破坏了顺序的格局”[2](P562),而且她那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创造”[2](P562)。于是,“句子与句子之间流畅的滑动被打断了。有的东西在撕裂,有的东西发着刮擦声,这儿一个字、那儿一个字像火把一样在我眼前闪现”[2](P561)。伍尔夫赞扬多萝西·奥斯本“像一个女人那样写作,但又像一个忘记了自己是女人的女人那样写作”[2](P564)。伍尔夫还对第一个女性小说家范尼·伯尼和第一个靠写作为生的女作家阿弗拉·贝恩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18世纪末,伯尼小姐创作起步非常艰难,她的第一部手稿被继母下令拿走烧掉,之后又被惩罚去做绣花缝纫等女工以赎“罪”。但是“伯尼小姐已经在文章中证明‘对一个女性而言是可能的而且理应得到的尊敬’”[4](P1391)。第一个职业女作家贝恩带动了一批中产阶级妇女克服重重困难,投身于写作事业,这标志着英国女性文学的转折,伍尔夫说,它比十字军东征或者玫瑰战争更为重要,更有意义。因此,“所有的妇女都应当一起把花撒在阿弗拉·贝恩的墓上,因为是她替她们赢得了写出她们思想的权力。”[2](P548)伍尔夫认为,没有这些先驱者,后来那四位成为“伟大女性”的简·奥斯丁和勃朗特姐妹以及乔治·艾略特就不可能写作,因为“杰作不是单一和孤立的产物”,而是“多年来的共同思考、集体思考的结果,因此这单一声音的背后有着大家经验的支撑”[8](P80),就像她对书籍的评价一样:
书籍与书籍之间有传承关系,如同家族世代相传。有些书继承了简·奥斯丁的传统;另一些则与狄更斯的作品一脉相承。这些书籍与其‘父母’辈相似,就跟人类的孩子与父母长得相像一样;然而又像孩子们跟父母有所区别一样,它们也跟它们的‘父母’有所区别,也像人类的孩子那样对抗自己的父母。[2](P709)
伍尔夫发现,还有一些女作家在世时,享受到了眩目的文学声望,可是在后人的记载中却声誉式微,甚至无迹可寻。例如诗人伊丽莎白·勃朗宁,“虽然她在生前得到了更为响亮的赞誉,现在却越落越远了。”[9](P414)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怪圈,每一代女作家都不得不重新发掘自己的传统,一次再次地打造自己的性别意识。伍尔夫通过论述那些女性小说家、诗人、日记作者和信件作者,建立了自己与女性文学前辈的真正关系,并界定了自己的文学身份。
伍尔夫曾在父亲96岁诞辰纪念日的日记中说,如果父亲还活着,她就不可能成为作家,因为她将父亲看成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权家长,除了性格暴躁以外,他会阻挡女儿通过创作的源泉即女性先辈思考过去,而伍尔夫的创作就是沿着女性先辈开拓出的道路进行的:
因为这条道路在很多年以前就开辟出来了,开辟者有范尼·伯尼、阿弗拉·贝恩、哈里特·马蒂诺、简·奥斯汀、乔治·爱略特等许多著名的女人,更有许多不知名的和被忘却的女人,曾在我之前把这条路修得平平顺顺,并且调整着我的步伐。因此,在我着手写作的时候,便只有极少的物质障碍来阻挡我的道路。[4](P1366)
不仅先辈女作家不断出现在伍尔夫的散文/随笔中,而且妇女教育的开拓者,“怪异妇女”(“queer women”)、妇女参政权论者等都曾成为她阅读和评论其传记、通信集和回忆录的对象。
伍尔夫的这些经历告诉我们,女性是怎样相互影响的,远不是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提出的“影响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概念所指的那样,而是相反,女性前辈将写作中的女性从“焦虑”中解放出来,充当历史的避难所,以便她们在父权制攻击的间隙里躲到那里去舔自己的伤口。如果说伍尔夫有“焦虑”的话,那也不是出于要怎样超越她的“母亲们”,虽然她的确希望超过她的当代女性同行,还嘲讽过凯萨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说她是简·奥斯丁再世。
伍尔夫不仅自己致力于重建女性历史与传统的工程,而且鼓励其他女作家一起关注女性自我意识、女性经历与经验、女性焦虑与痛苦,并重写历史:“我们,创造历史的人,追溯历史的人,必须树立新的墓碑,以刻下这些遗失的名字。”[10](P2)因为“在妇女身上,个人的历史既与民族和世界的历史融合,又与所有妇女的历史融合。作为一名斗士,她是一切解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1](P197)
伍尔夫意识到,在父权社会中,仅仅只有女作家参与到书写女性历史的行动中来是远远不够的,最要紧的是占这个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必须改变观念,心甘情愿地把女性写进历史中,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远航》中的特伦·赫维特就是这样一位男性同盟军。他喜欢听未婚妻蕾切尔·温雷克描述家乡里奇蒙的日常生活,并由她的生活而联想到广大无名女性的生活:那种单调、乏味、无聊的生活,就像街道两旁一模一样的房子,无任何变化。
其实,许多男性都有姊妹,与其有天生的“手足之情”,私下里与她们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有共同的目标。例如,大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那优雅迷人的田园诗歌灵感和素材大多来自妹妹多萝西(Dorothy)的日记;建立了纽汉姆学院(Newnham College)并成为其第一任院长的安妮·克拉夫(Anne Clough)视兄长亚瑟·克拉夫(Arthur Clough)为最好的朋友和导师:“亚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导师,……是我生命的慰藉与欢乐;正是为了他,因为他,我才开始追求所有可爱的、值得记录的东西。”[4](P1135)怎样才能把这种“私下的”手足之情延伸至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中是重要的课题,因为许多世纪以来,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如此不同:“‘社会’一词开始在人们的记忆中敲响了刺耳的、使人忧郁的钟声:不能,不能,不能。你不能学习,不能挣钱,不能拥有,你不能……”[4](P1136)
伍尔夫的自传《往事杂记》(“A Sketch of the Past”,1941)曾说,女性缺少的不是事实,而是阐释历史的新方法,即新的写作风格。新历史的写作即使用不同的手段,即使模仿男性对女性得体举止的描写方法,也会在模仿过程中将该标准贬低。阐释历史的新方法包括女性那“没有完全消失的眼色、笑声和眼泪”、对男性标准的嘲讽、对父权秩序的扰乱或将历史书写拉离其表面上崇高的学术中立立场等。书写历史的标准也会发生变化,原来被认为只是相关的,现在将变成标准;原来被认为是完整和真实的,现在将变成片面。战争和运动将不再被放在显著位置,其他事件如崇拜时尚和购买衣服等将取而代之,正如简·奥斯丁所做的那样:她选定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诸如社交宴集、郊游野餐、乡村舞会之类作为她的写作内容,摄政王或者克拉克先生请她改变自己的写作路子,她根本就不予考虑。浪漫传奇、冒险故事、政界动态、男女偷情等等,根本不能和她亲眼所见的乡间别墅里楼梯间的生活相比。那就是为什么伍尔夫把18世纪末期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这一变化看成比任何战争都还重要的大事件的原因。不仅女性开始写小说被认为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她们重写历史似乎也不是要用新的证据来纠偏,只是叙述不同的故事。
女性书写历史的新方法也包括打破传统上按时间顺序叙事的写作模式撰写自传。伍尔夫的自传《往事杂记》没有按时间顺序去交代她一生中的“大事”,而是从留在她记忆中早年生活的两个“瞬间”开始叙述。第一个“瞬间”就是母亲的印花衣服。除了黑底衬着红色和紫色小花的衣服及其式样以外,伍尔夫还通过其他与母亲有关的“瞬间”重建母女间的紧密关系。伍尔夫不仅将母亲留在了自传里,还把她移植到了小说中,这是另一种回忆的方式。伍尔夫的意识流代表作《到灯塔去》的中心人物拉姆齐夫人就是以伍尔夫的母亲为原型创造的。拉姆齐夫人常常去看望病人、为疗养所里的牛奶供应犯愁、热衷于通过盛宴把人们聚集到一起等特点,都是伍尔夫母亲的特点。伍尔夫试图通过女性先辈直接或间接扮演的角色模式传递人类价值观:这些母女在彼此的生活中是完整的,她们相互尊重相互爱戴,她们会亲密地沟通,即使意见相左也是如此。伍尔夫不仅与母亲的关系不同凡响,她和姑母、姨母的关系也很不一般。英国女性主义者劳拉·马柯斯(Laura Marcus)认为,伍尔夫的和平主义主张来自伦敦西南部克拉彭地区(Clapham Sect)的祖先以及那位贵格会(Quaker)教徒姑妈卡罗琳·斯特芬(Caroline Stephen)的遗产。卡罗琳姑妈那神秘的写作是影响伍尔夫的关键因素[12](P235)。伍尔夫的外甥昆丁·贝尔(Quentin Bell)认为,伍尔夫女性写作风格受到了姨母安妮·萨克雷(Anne Thackeray)的影响①伍尔夫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是大作家萨克雷的女儿,安妮·萨克雷(Anne Thackeray,1837-1919)是萨克雷的另一个女儿,即后来的安妮·里奇女士(Lady Anne Ritchie),出版过多部小说和回忆录。昆丁·贝尔在《隐秘的火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季进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中说,安妮的写作“是一种非常女性化的写作”,代表了“社会中的女性因素,而布鲁姆斯伯里正是从这个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贝尔,29)。神秘主义和女性化写作使伍尔夫的女性主义部分地从姑妈和姨妈传至侄女,从而避开了父亲。将母亲写进自传、小说、日记和信件中,实际上就是将母亲以及千万个像母亲那样默默无闻的女性写进历史的一个方式,同时,这也说明伍尔夫的确有“通过女性先辈思考过去”的习惯。
女性书写历史的新方法还包括打破传统模式的传记写作。伍尔夫发表于1928年的传记体小说《奥兰多》(Orlando,1928),虽然按照了时间顺序来叙事,但是又与传统传记写作有着天壤之别。该书的主人公是生活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年轻贵族,因为是女王的宠侍,得到大笔财产。他一路走来,历经数个朝代,一直到伍尔夫写作的1928年,变为一个36岁的魅力少妇。许多评论家都把该小说的出版看成是传记文学的一场革命。其他新的写作模式还包括:《达罗卫夫人》(Mrs Dalloway,1925)和《到灯塔去》使用的是意识流写作、《帕吉特家族》(The Pargiters)是散文小说(essaynovel),《海浪》(The waves,1931)是剧诗(play-poem)等。实际上,这些形式都不足以表达伍尔夫心中的所思所想,她最想做的是抛弃所有这些范畴,创造一个全新的类型:“我有个想法,即我要为我的书创造出一个名字来补充‘小说’这一名称。”[13](P31)她希望自己的文学“女儿们”能够写下她当年只能逃避的东西:“她们的脚上不再有蹩脚的束缚”,不再对描写女性的性而小心翼翼。
通过还原女性的真实生活,沉默、失语和“失落的”(lost)女作家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形成了几近“众声喧哗”的局面。伍尔夫发现,如果把文学女性作为整体来考察,把每个人的价值观、行事准则、经历和行为都结合起来,人们就会看到一个想象的连续体,某些模式、主题、问题、意象等都一代一代地重复出现。女性在父权中心社会的大框架中已经建构了自己的“亚文化”,女性,尤其是女作家,也是有历史和传统可循的。
当代女性主义者沿着伍尔夫开辟的道路,增强了对文学史中性别歧视及其表现形式的研究,努力发掘广大女性的真实生活,寻回“失落的”女作家作品及其生活与生涯的文献资料。她们发现,女性不仅有自己的历史与传统,而且不同阶级的妇女,其经历和话语也有所不同。同时,每个时期的文学中都有一种特殊的女性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女性文学在影响、借用以及亲和关系等方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传统可循。但由于“女性文学声誉的短暂现象”,该传统也充满了漏洞和裂缝[5](P11)。文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史家和艺术史家们都对此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要为女作家建立一种更可靠的批评话语以及更准确、更系统化的女性文学史,以便再现其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经历与经验。[14]有了新的视野之后,过去被认为是不存在的文献资料突然之间都跃入女性史撰写者的视线,就像亚特兰蒂斯从大海中冒出来一样,被淹没的女性传统大陆从文学海洋中升了起来。
[1]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IV[M].王义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II[M].张学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西蒙娜·德·波伏娃.妇女与创造力[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III[M].王斌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Elaine Showalter.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6]弗吉尼亚·吴尔夫.雅各的房间;闹鬼的屋子及其他[M].蒲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7]伍厚恺.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8]Jane Marcus,Art And Anger:Reading Like A Woman[M].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8.
[9]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I[M].石云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0]C.N.Davidson and E.M.Broner.The Lost Tradition: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Literature[M].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80.
[11]埃莱娜·西苏,美杜萨的笑声[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2]Laura Marcus,“Woolf’s Feminism And Feminism’s Woolf”,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M].S.Roe and S.Sellers.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3]Rachel Bowlby.Feminist Destinations And Further Essays on Virginia Woolf[M]Eding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7.
[14]张连义.身体写作与女性话语的建构策略[J].齐鲁学刊,2011,(6):158-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