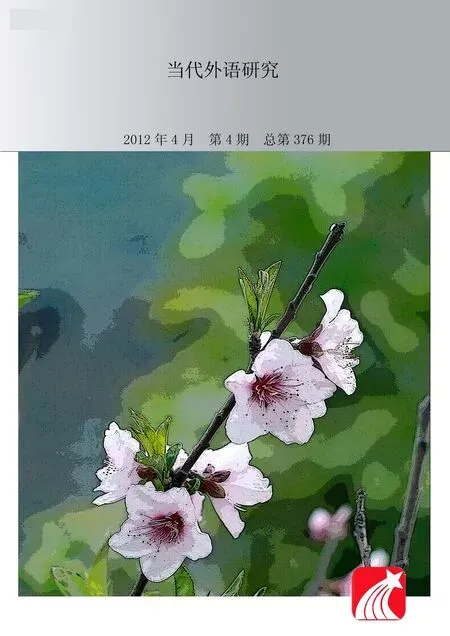一切照原作译
——翻译《老人与海》有感
孙致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洛阳,471003)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写出《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长篇杰作的海明威,在经历了十多年的低潮期之后,于1952年发表了富有寓意和诗化之美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该作发表后为海明威赢来了巨大的荣誉。1953年,小说获得普利策奖。1954年,瑞典皇家文学院以“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中,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为由,授予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
《老人与海》的基本素材来自作者1936年4月在《乡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蓝海上:海湾来信”的通讯,其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古巴老渔夫出海捕到一条马林鱼,那条鱼极大,“把小船拖到很远的海上”。两天两夜后,老人才把它钩住。后来遭到鲨鱼的袭击,老人与之展开搏斗,最后“累得他筋疲力尽”,鲨鱼却把能吃到的鱼肉全吃掉了。当渔民们找到老人时,他都“快气疯了”,“正在船上哭”。
经过十多年的酝酿,海明威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加工和提炼,写成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圣地亚哥的古巴渔夫,接连出海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终于在第八十五天钓到一条他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大的马林鱼。他竭尽全力,经过两天两夜的奋战,终于将大鱼捕获,绑在船边。但在归途中,遭到鲨鱼的疯狂袭击。老人在疲惫不堪中,与鲨鱼展开了殊死搏斗。虽然杀死了好多鲨鱼,但却失去了鱼叉、船桨和舵柄,自己也受了伤。最后,虽然击退了鲨鱼群,可是回到海港时,绑在船边的马林鱼只剩下一副空骨架。老人回到棚屋倒头便睡,梦中见到了狮子。
故事中的圣地亚哥是一个在重压下仍能保持优雅风度的老人,一个在精神上不可战胜的硬汉。他具有一般硬汉所共有的勇敢、顽强、百折不挠的特点。在长期令人难以忍受的失败中,他表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刚强与坚毅;在与大马林鱼和鲨鱼的殊死搏斗中,他显示了超凡的体力、技艺和斗志。他是明知要失败而不怕失败的英雄。他说:“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人尽可被毁灭,但是不会被打败。”他的不被失败压倒的顽强拼搏,昭示了人类那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虽然海明威并不承认自己的作品含有什么寓意,但是文学界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老人与海》显示了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达到了寓言和象征的高度(肖涤1992:655)。正是这一特色使《老人与海》成为海明威不朽的传世之作。
海明威是个文体家,一个独一无二的文体家,而《老人与海》又是最能集中体现海明威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因此,是否能忠实地展示原作的艺术风格,也就成为能否译好这部中篇小说的关键。有关译作的艺术风格问题,笔者在多年前曾表示赞同这样一个说法:译作的风格应是“作者的风格加上若隐若现的译者的风格”。但是,在翻译《老人与海》时,笔者似乎完全“归顺”了海明威,一心考虑的是如何再现海明威的风格,几乎完全意识不到自己风格的存在。也就是说,笔者最大限度地尊重海明威,尽量把自己埋没起来,一切照原作来译。
海明威的艺术风格可以概括成两大特征:一是“冰山”原则,二是“电报式”文体。
海明威曾把文学创作比作飘浮在大海上的“冰山”,认为用文字直接写出来的仅仅是“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隐藏在水下的占冰山的“八分之七”。一个优秀的作家,就是要以简洁凝重的笔法,客观精确地描绘出意蕴深厚的生活画面,唤起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想象力,去开掘隐藏在水下的“八分之七”,对现实生活作出自己的判断。海明威说,他本来可以将《老人与海》写成一部一千多页的巨著,把渔村的每一个人物,以及他们怎样谋生,怎样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过程都写进去,但实际上他献给读者的却是不到六十页的一个中篇,有关人物的背景、身世及其相互关系,仅作极其简约的交代,而集中描写老人在海上那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尽量突出主人公的行动和心理,借以彰显他那种历尽千难万险却能屹立不倒的英雄气概(吴元迈等2001:630-33)。
对于海明威的行文风格,英国作家赫·欧·贝茨有一个精辟之见:自十九世纪亨利·詹姆斯以来,一派冗繁芜杂的文风,像是附在“文学身上的乱毛”,被海明威“剪得一干二净”。他说“海明威是一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通过疏疏落落、经受过锤炼的文字,眼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海明威的“电报式”文体,采用结构简单的句子,常是短句或并列句,用最常见的连接词联结起来(董衡巽2003:381-82)。他讨厌大字眼,总是摒弃空洞、浮泛的夸饰性文字,习惯于选用具体的感性的表达方式。他总是保持冷静而克制的笔调,尽量用动作词汇来写,删去不必要的形容词,能用一字则不用两字(任子峰、王立新1999:1183)。
在简要阐述了海明威的艺术风格之后,笔者想结合实例,来谈谈自己是如何力求忠实再现海明威的艺术风格的。
1. 尽量展示作者用词凝炼、干脆、生动的特色
《老人与海》以老人(对大马林鱼)的“追逐、捕获、失去”为主线,展开了跌宕起伏的描写。作者的描写常常从视觉、感觉、听觉和触觉入手,使人物的语言、行动和心理的描写以及场景的刻画,都达到了惊人的凝炼和生动。例如:
(1) Then the fish came alive, with his death in him, and rose high out of the water showing all his great length and width and all his power and his beauty. He seemed to hang in the air above the old man in the skiff. Then he fell into the water with a crash that sent spray over the old man and over all of the skiff.
这是老人给了大马林鱼致命一击后,作者对大鱼所作垂死挣扎的生动描写。作者使用的都是最常见的、具有感性意义的“小词”,如came(alive),rose(high),hang(in the air),fell(into the water),sent(spray)等表示视觉、感觉意义的行为动词结构,以及crash这样的拟声词,读来既清晰又生动。笔者尽量模仿作者的用词特征,以小词对小词、以具体传具体,简洁干脆,避免拖泥带水:
这时那鱼死到临头,倒变得活跃起来,从水里高高跃起,把它那超乎寻常的长度和宽度,它的威力和美,全都显现出来。它仿佛悬在空中,就在船中老人的头顶上。接着,它轰的一声掉进水里,浪花溅了老人一身,溅了一船。
笔者体会,要模拟海明威用词凝炼、干脆、生动的特色,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原词的确切意义,并在译语中找到真正的对应词来传译。实践证明,抓不住原词的确实意义,就肯定找不到确切的对应词,所找到的只是假对应的“假朋友”,甚至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传译。
(2) “One,” the old man said. His hope and his confidence had never gone. But now they were freshening as when the breeze rises.
这里,作者用freshening来形容老人的希望和信心。有的译者将之译作“鲜活”,意义含混,令人费解。显然,无论“风”还是“希望和信心”,都不能用“鲜活”来修饰,海明威决不会写出如此别扭的话来。其实,《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的释义讲得很清楚,freshening用以形容风时,意思是becoming stronger(变得更强烈)。本着“语贵适境”的原则,笔者将这段话译作: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没消失过,这时就像微风乍起时那样给鼓得更足了。
翻译海明威,译者尤其要记住“朴则近本”的道理,尽量摒弃不恰当的大字,选择准确达意的通俗词语来翻译。
(3) “What’s that?” she asked a waiter...
“Tiburon,” the waiter said. “Eshark.” He was meaning to explain what had happened.
在故事的末尾,一位女游客见到大鱼的空骨架,就问一位侍者:“那是什么?”侍者先用西班牙语说了“鲨鱼”,接着就想解释what had happened。我国已出的译本基本都译作“事情的经过”,有的甚至译作“事情的来龙去脉”。设想一下:一位侍者会这么冒失,在客人没有向他询问详情的情况下,主动陈述事情的“经过”甚至“来龙去脉”吗?其实,what had happened问的是“出了什么事”,也就是简单的“怎么回事”,因此笔者译作:
“那是什么?”她问一位侍者……
“Tiburon,”侍者说。“Eshark.”他正想解释是怎么回事。
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界流传着“发挥译语优势”的说法,主张译文要尽量使用地道的、实际上是现成的汉语词语,特别是汉语的四字成语。请看下例:
(4) “...How much did you suffer?”
“Plenty,” the old man said.
我国大陆最早出版的《老人与海》的汉译本将Plenty译作“一言难尽”。有的译评者大加赞扬,说充分发挥了译语优势,因而是译文超越原文的范例。果真如此吗?笔者很难苟同,因为“一言难尽”属于答非所问,把话译歪了。在原文中,孩子问老人:“你吃了多少苦啊?”老人应该直截了当地回答多还是少,而不是发表什么感慨。所以,笔者将之译作:
“……你吃过多少苦呀?”
“可不少,”老人说。
要准确地传达原文的用词特色,最关键的是要透彻理解原文的意思,然后在译语中寻找真正对应的词语来传译。因此,译者在翻译中着力考虑的,不应是“发挥译语优势”,让原作适从译语,而是应“发挥译语的韧性和潜力”,让译语适从原作。
2. 尽量采取原文的表意方式
文学翻译,特别是经典文学翻译,不仅要译意(说了什么),而且要重视对表意方式(怎么说)的传译。准确而恰当地传译原文的表意方式,不仅可以更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义,而且可以展示原文的艺术美。例如:
(5) “I wish I had the boy,” the old man said aloud.
“I wish the boy was here,” he said aloud...
老人在大海上独自捕鱼时,总会不时地想起小男孩马诺林,因为他是老人的希望,老人看到小男孩,就能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能应付一切艰难的挑战。老人想念小男孩的话,基本有两个说法,一是“I wish I had the boy”,二是“I wish the boy was here”。我国出版的五个中译本都把原文的两个不同说法译成了一个说法:“要是那孩子在这儿就好了”。笔者觉得有些不妥,因为“I wish I had the boy”不仅表示希望那孩子“在这儿”,而且还有希望他是他的孩子的意思。不信请看他在此前的表白:“你要是我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出去闯一闯……可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孩子,你又跟了一条交好运的船。”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将这两句话分别译作:
“我要是有那孩子就好了,”老人大声说道。
“要是那孩子在这儿就好了,”他大声说道。
对于原文特有的说法,如果直译过来能通顺达意,能为汉语所接受的话,笔者还是尽量采取直译的,以便给汉语引进一些新鲜的说法。如:
(6) “Yes,” the boy said. “Can I offer you a beer on the Terrace and then we’ll take the stuff home.”
“Why not?” the old man said. “Between fishermen.”
“Why not?”已成为英语的固定用语,表示赞同之意。我国已有译本有的译作“好呀”,有的译作“那当然好”,笔者模拟原文的说法,译作:
“是的,”孩子说。“我请你到露台酒店喝杯啤酒吧,然后把东西拿回家。”
“干吗不?”老人说。“都是打鱼人嘛。”
做英汉翻译的人都有一个深切的体会,汉语在谈到某人某物时往往直呼其名(或名称),而英语则在第二次以后重复说起时,习惯于用人称代词或非人称代词来替代。所以,翻译中有一个技巧,叫改变人称(非人称)代词的译法。如下面两段话:
(7) “I’ll try to get him to work far out,” the boy said. “Then if you hook something truly big we can come to your aid.”
“He does not like to work too far out.”
有的译者将之译作:
“我要设法让船主在很远的地方作业,”孩子说,“那样,要是你捕到一个很大的家伙,我们可以来帮忙。”
“他可不喜欢在太远的地方捕鱼。”
这位译者将him翻作“船主”,理解自然是正确的,但是笔者认为该词以不点明为好,因为him在前面并没有先导词,海明威的人物就是这么说话的。一个人说him,另一个人立刻知道是指谁。我们的读者看后略加思索,甚至不假思索,也会知道是指谁。因此,译者最好不要剥夺读者这一点点思索的权利。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对上文做了如下的传译:
“我要设法让他也去得远远的,”孩子说。“这样,你要是钓到一条真够大的鱼,我们就可以来帮你的忙。”
“他不喜欢去太远的地方捕鱼。”
显然,将get him照实译成“让他”,更能显示这一老一少之间的心心相通,亲密无间。
3. 尽量追循原文的句法结构
笔者早就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译者不应随意对待原文的句法结构,而应彻底化解各成分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做出合情合理的传译。分析句法结构有时是个很细致的活,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误解。例如:
(8) He liked to think of the fish and what he could do to a shark if he were swimming free. I should have chopped the bill off to fight them with, he thought. But there was no hatchet and then there was no knife.
But ifIhad, and could have lashed it to an oar butt, what a weapon.
If I had是个省略分句,省略了什么呢?有人译作“如果我有”,显然指的是“我有斧子和小刀”。但是下面紧接着说and could have lashed it to an oar butt,就有点说不通了:lashed后面跟的是it,而斧子和小刀却是两样东西,因此这个理解肯定不对。再细读读上一段,我们发现if I had后面省略的是chopped the bill off to fight them with,后面lashed it中的it就指the bill。理顺了关系后,可做出这样的传译:
他喜欢想这条鱼,想它要是能自由自在地游,它会怎样对付一条鲨鱼。我该砍掉它那只长嘴,拿着去跟鲨鱼斗,他想。可是没有斧头,刀子也没了。
但是,我要是真把那长嘴砍下来了,我就把它绑在桨柄上,那该是多好的武器啊。
在《老人与海》中,作者运用大量的自言自语和心理活动来刻画圣地亚哥。为了标示这些自言自语和心理活动,作者使用了许多“他(老人)说”、“他(老人)想”之类的字眼。而跟汉语不同的是,这些字眼基本不放在句首,而是大量置于句尾,也有少量插在句中。对于这种句法结构,我国译者的译法很不一致,也有失规范:有人根据汉语习惯,较多地将“他说”、“他想”置于句首;另一些人则根据自己的意愿,随便调整“他说”、“他想”的位置。这两种做法都不能使我国读者真实了解英语的叙事笔法。在这一点上,笔者基本采取了跟着原文“亦步亦趋”的做法,完全遵照海明威的句法结构,就连标点符号也一概照搬。例8可以算是一例,再看下例:
(9) After it is light, he thought, I will work back to the forty-fathom bait and cut it away too and link up the reserve coils.
等天亮了,他想,我要回过头来解决四十英寻深处的鱼饵,把它也割断,把备用的钓绳连起来。
追循原文的句法结构来译,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能忠实地再现原文所蕴涵的思维轨迹和内在节奏。
4. 尽量体现原文的陌生化手法
海明威的中篇小说是用英语写就的,读者自然首先是英语读者。但是,故事描写的老人是古巴人,他讲的是西班牙语。于是,自然而然地,作者在书中使用了西班牙文词语,共十六个。我们体会,作者揉进一些西班牙文,首先是借以烘托老人的身份和背景,从而为故事增加了几分真实感。另外,对于广大英语读者来说,西班牙语很可能是陌生的,陌生产生距离,同时也能激起兴趣和美感。笔者翻阅了五个汉语译本,发现对于书中的西班牙文,中国译者大致采取了这样几种处理法:一是将西文直接译成汉语,也不加任何注释;二是将西文译成汉语,加注说明“原文是西班牙文”;三是保留西班牙文,加注解释其义。第一种做法完全辜负了作者的用心,可以说是最不足取的;第二种做法可以提醒读者不要忘记故事和人物的背景,但却消除了原文所具有的陌生感;相比之下,第三种做法更有表现力,因而应该提倡。但是采取这种译法的译者,基本都是有选择地处理其中的若干处,多数西文词语还是采取一、二种处理法。笔者对西文字眼的处理,则做得比较彻底——全都采取第三种译法。如故事开头:
(10) In the first forty days a boy had been with him. But after forty days without a fish the boy’s parents had told him that the old man was now definitely and finally salao, which is the worst form of unlucky, and the boy had gone at their orders in another boat which caught three good fish the first week.
笔者的译文是:
头四十天,有个男孩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钓到一条鱼,孩子的父母便对他说,老人如今准是极端salao,就是说倒霉透顶,那孩子便照他们的吩咐,上了另一条船,头一个星期就捕到三条好鱼。
并给salao加脚注:西班牙语中有salado一词,意为“倒霉的”。古巴当地老百姓使用该词时,吃掉了浊辅音d。
有人说,译文要有“洋味”,也就是说,要尽量保持“原汁原味”。笔者在本文中所说的尽量展示作者的用词特色、尽量采取原文的表意方式、尽量追循原文的句法结构以及尽量体现原文的陌生化手法,等等,就是为了帮助中国读者尽量真切地领略海明威的叙事艺术。
但是,翻译是一桩极其复杂的事情,充满了各种矛盾,需要讲究对立统一,不容顾此失彼,也不宜彻底地亦步亦趋。所以,笔者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加了“尽量”二字,不可绝对化。一方面,可能时要尽量坚持原则;另一方面,在不可能时则做灵活处理。比如old man这个字眼,在作品中出现频率极高:故事叙述人称老人old man,小男孩称老人old man,老人自言自语时称自己old man,译者能不能全部照译成“老人”或“老头”呢?显然不合适。笔者在处理这个字眼时,既适当地考虑到文化差异,又不做过分的汉化,将故事叙述者称呼的old man一律译成“老人”,把小男孩尊称的old man一律译成“老人家”(不是汉味较浓的“老大爷”、“老爷子”),把老人自称的old man译成“老头”或“老家伙”——这样的区别对待,在汉语里显得比较合乎情理。
总而言之,笔者在翻译《老人与海》时,既尽可能地讲究原则,又做了一定的灵活处理。原则上,笔者要尽量忠实地再现海明威的艺术特色。但在需要考虑文化差异和译语读者的接受力时,笔者又会做出适度的变通。
董衡巽.2003.美国文学简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任子峰、王立新.1999.欧美文学史传(下)[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吴元迈等.2001.外国文学史话·西方20世纪前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肖涤.1992.诺贝尔文学奖要介[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